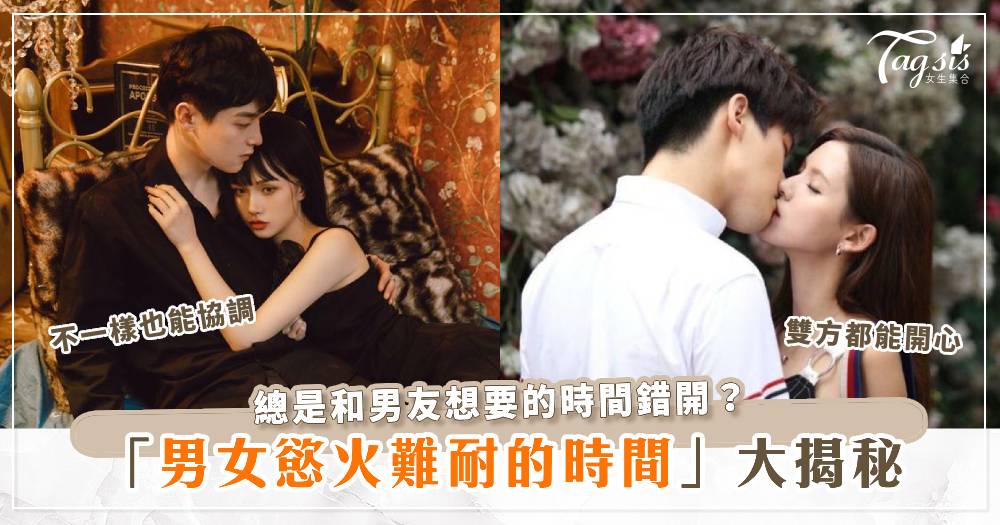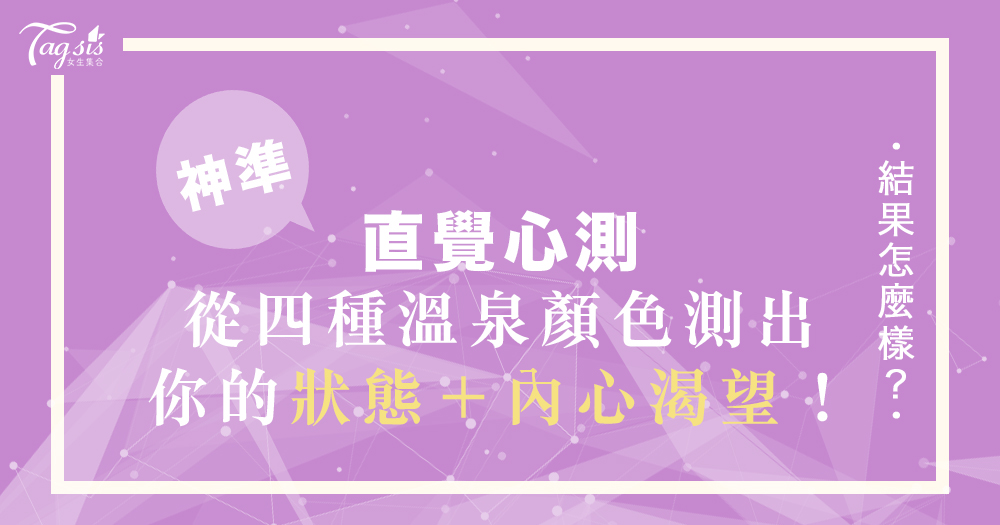潛伏交友軟件三年,一位學者觀察到的婚外“情”與“性”
2012年,程萍在一所傳媒類院校當老師。那時,她注意到有的學生上課時,會時不時用 “搖一搖”交友,他們還時常在社交平台上點讚、評論、更新動態,好像沉浸在一種興奮、新奇的狀態中。
那一年,交友軟件井噴式湧現——後來有人認為,交友軟件成了許多離婚案例背後的“隱形殺手”。在2015年首屆中國婚姻家庭諮詢服務行業高峰論壇上,執行主席舒心說,2014年以來,通過微信、陌陌平台“交友”,或者找了“小三”發生婚外情的案例激增20%。
“交友軟件是現代婚姻的‘隱形殺手’嗎?”2015年,正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程萍,將這個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起點。她進入交友軟件“刷來”(註:某知名交友軟件,出於研究倫理的考慮,論文進行了化名處理)“潛伏”了三年,平均每天會收到10名異性的搭訕,最後她篩選出28名具有明顯婚外性目的的已婚男性進行個案訪談,完成了博士論文《社交媒體中的婚姻與個體》。
 程萍的博士論文出版成了書。
程萍的博士論文出版成了書。程萍說,這28名訪談對像不像我們想像的夫妻關係都不好,有的回到妻子、孩子身邊,會全心全意陪伴家人,承擔家務,但時間空間相對自由的時候,他們在交友軟件上“交友”。
據她觀察,在這些訪談對象的婚姻關係中,有的“性和感情都不同步”,有的“感情同步性不同步”,還有的“感情和性都同步,在外面找點新鮮感對抗家庭生活的枯燥”。
她能感受到他們的內心有很多矛盾,考慮到孩子、財產分割、道德壓力等現實因素,婚姻解體的成本太高,但性的需求,情緒需求,情感需求如果在家庭內部得不到滿足,他們又需要有一個釋放的出口。
【以下是澎湃新聞與程萍的對話】
“夫妻關係是很複雜的”
澎湃新聞:據你的觀察,這些已婚男性網上“交友”,發展婚外情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
程萍:我在書裡面給他們做了一個歸類和分析。第一種是圈子文化,比如說個案M26,他的網名叫“品味男人”,他是做生意的,在他的圈子裡,帶一個所謂的女朋友出席朋友聚會場合,會被認為是成功的,婚外交友是社會地位和個人能力的象徵。
第二種是單純為了性享受,在一些受訪者的觀念里,婚外性行為只是為了身體享受,純粹的性是令人愉悅的,跟他是否已婚、是否彼此有感情無關。
第三種是為了彰顯男性氣概,比如M21是大型國企的中層管理人員,他本身工作能力很強,人也很強勢,在性方面充滿了探索欲。
第四種是婚姻平衡,M25、M28和妻子對於性的認知、觀念存在差異,他們沒辦法和妻子談論性的話題,比如M25的妻子總是催他快點睡覺,對性愛方面態度冷淡,他就會通過婚外“交友”獲取在婚姻中得不到的東西。
澎湃新聞:28名訪談對象的婚姻關係通常是怎麼建立起來的,有瞭解他們的家庭分工模式嗎?
程萍:我在訪談裡面沒有特別涉及到這類問題。但從他們描述中能看出,自由戀愛和相親認識的都有。比如M01和前妻是自由戀愛認識,他的後一段婚姻則是兩個人相親認識,交往過程中發現彼此不合適分手了,但父母給了很大的壓力,兩人又復合結婚了。M28結婚前條件不是很好,他的妻子是當時他能找到的最合適結婚的對象。
此外,這部分已婚男性比較認可男人賺錢養家,承擔家庭責任,這也是他們努力維持婚姻穩定性的主要原因。他們的妻子當中,只有一名是全職太太,其他的都有工作。
澎湃新聞:在他們的婚姻家庭中,夫妻關係是怎樣的?
程萍:不是我們想像的夫妻關係都不好,有的夫妻關係還挺好的。比如個案M01、M21、M26,夫妻雙方看起來相安無事,給各自的自由度都比較高,從來不看對方的手機,干涉對方去哪了,和誰在一起,但這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說明夫妻雙方內心有點疏遠?再比如個案M02、M22,夫妻異地的機會比較多,他們經常趁著夫妻異地的時候,釋放一下自己。但回到妻子、孩子身邊,他們又會全心全意陪家人,愛也是真實的。而M11的妻子對他非常信任,因為他每天上下班時間很規律,回到家也經常承擔家務。
夫妻關係是很複雜的,有的夫妻性和感情都不同步,有的感情同步性不同步。還有的感情和性都同步,家庭生活讓他感覺很安心,但是時間久了覺得枯燥,需要在外面再找點新鮮感來對抗這種枯燥。
澎湃新聞:在書中,你以小說《雙面膠》中的婆媳關係為例,提到婆媳矛盾給家庭帶來的一些困擾?
程萍:在現代都市生活中,雙職工獨立承擔照顧、養育孩子的責任是非常難的,時常需要婆婆或丈母娘的參與,婆媳關係容易成為家庭矛盾的導火索。比方說個案M05,他是一名大學老師,註冊交友軟件的時間不長,他說“交友”行為是“給生活一個出口”。接受訪談時,他的孩子11個月大,他母親到家裡照顧,婆媳矛盾他兩邊都搞不定,所以他就不想回家,在單位里加班,實際上是在用交友軟件,給自己找一個釋放的出口。個案M01也因為婆媳矛盾,在小區單獨租了一套房子給父母住,所謂“遠香近臭”。M10則說,如果只給老婆打分,我打90分,如果考慮她的家庭,我給她打70分。
他們謹守“交友”與“婚姻”的距離
澎湃新聞:婚姻對於參與訪談的已婚男性的意義是什麼?在他們人生不同的階段,婚姻的意義有發生過變化嗎?
程萍:我覺得在不同的階段意義是有變化的。有兩個非常典型的人物,剛才我們也有提到。個案M01有過兩次婚姻,他是一個把瓊瑤小說全部看完的人,第一次婚姻時,他堅信世界上是有愛情的,他大學畢業原本在省城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但是為了初戀回到縣里做公務員,所以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奔著愛情去的,對待感情很忠誠,後來因為前妻的原因離婚。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到了一定的年紀,自己又是家裡的獨子,有延續香火的壓力。儘管夫妻感情淡薄,但因為孩子,財產分配,以及嶽父母對他非常好,資助過他買房。所以對於他來說,這個時候婚姻的意義是責任。
M28現在是國企管理層,當時結婚的時候,他的條件不好,選擇的餘地不多,他為了“完成任務”找了現在的妻子。用他的話來講,他的妻子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很賢惠,把他和孩子都照顧得挺好。但是她不是他理想中的女性,不夠漂亮,不夠有品位,兩個人的共同語言不多。但是妻子對他有恩,對家庭有恩,所以他不能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一旦離婚,來自親戚、朋友、同事的輿論壓力將沒法承受。
澎湃新聞:書中有提到:“婚外性方面,24人婚後有過‘交友’經曆;2人婚前有過‘交友’經曆;1人婚後有過婚外性(情)。”之所以大部分人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婚外性行為,有哪些內在和外在的屏障嗎?
程萍:這個問題我正好澄清一下。28名訪談對象中有24人有過“交友”經曆,這裏的“交友”經曆就是網絡話語中的“約炮”經曆,雖然“約炮”在學界已有相關研究,但考慮公序良俗和出版審核,我們用“交友”替代它。而且在訪談的時候,我發現很多已婚男性不喜歡被用“約炮”來形容,他們喜歡叫找知己、紅顏、朋友,用弱一點的字眼,美化自己的行為。之所以單獨提到1人婚後有過婚外性行為,是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是在約炮,他覺得自己是帶有感情的,和一個異地女性保持挺長時間這種關係。
澎湃新聞:這些已婚男性身上是否存在共性特徵?
程萍:這些人的時空自由度相對比較高,比如經常出差、異地工作,從事大家預設經常需要加班的工作,他們的妻子能監控到的時間空間比較少,所以相對有條件發生婚外“交友”行為。其次,他們的隱秘性比較高,比如回家卸載交友軟件,或者把它隱藏到文件夾里,手機設置密碼。

澎湃新聞:有少數沒有發生過“交友”行為的訪談對像是什麼情況呢?
程萍:M24當時剛剛用交友平台,使用時間不長。他是一個國企的高管,異地輪崗。他跟妻子之間的感情很枯竭,但為了面子和孩子,拖了十幾年沒有離婚,在他的觀念裡面離婚是一種失敗。所以他在平台上聊天,有兩重渴求,既有性的,也有情感的。他想找到一個價值觀趨同的女性,聊一聊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
M8是因為年紀比較大,50歲,做後勤管理,他對自己的事業不是很自信,收入不高,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他對平台當中的一些規則、話術也不會用,他可能覺得有的女性看不上他。但他們大多數選擇交友平台是對性方面有期待和需求的,只是因為各種原因還沒有實踐。
澎湃新聞:這些已婚男性中有因為婚外交友行為給家庭帶來實質性的影響嗎?
程萍:大多數是沒有的,因為他們在交友平台上,一般不會使用真名,風險控製做得非常好。但也有少數“出過事”,M16開始時和交友對象提出三個原則——AA製、互不影響家庭、互不約束彼此,但告訴了對方自己的姓名和單位,結果後來女方愛上了他,希望和他各自離婚後重組家庭,他花了不少錢才擺平這件事。
M16的妻子是全職太太,從道德上,他的太太全心全意投入家庭,一旦要離婚,他背負的道德壓力,財產分割的壓力是很大的,他還有兩個孩子,不可能為了女方放棄這些東西。此外,男性交友的時候基本上非常理性,不然也不會選擇“交友”平台。
“中國的傳統男性很壓抑,在家庭中是硬邦邦的存在”
澎湃新聞:這些已婚男性在交友軟件上怎麼呈現自己?
程萍:他們的個人資料並不是很豐富,因為他們本身不是真正地想交友,而是想尋求婚外性,所以不會在平台上展示太多信息,如果有熟人看到不安全,被“交友”對象瞭解太多,也不容易脫身。有的人會在網名和簽名中表達自己的“交友”訴求,比如M11的網名是“猥瑣的胖子”,M09的簽名是“再不瘋狂就老了”,M26的網名是“品味男人”。
澎湃新聞:他們“真實的自我”和熟人眼中“現實的自我”形象存在一些偏差嗎?
程萍:會有偏差,比如說M28,他的熟人圈對他的定位是顧家、傳統、老實,但他在訪談中說現在婚外性現象很普遍,“我這樣的人都有了(婚外性),誰還會沒有。”有的人為了吸引異性也會包裝自己,例如M09對自己的定位很高,他是做醫藥銷售的,對女性的生理結構比較瞭解,他覺得自己特別懂女性,他炫耀說自己很乾淨,每天都會換內褲,清洗身體,這點很多男性做不到。
能感受到他們在交友軟件上更能放得開,有些跟熟人、妻子溝通不了的事情,可能更願意跟陌生人聊,這也屬於一種自我療愈,只不過是選擇了一種粗獷的,原始的療愈方法。他們也會面對很多矛盾,比如傳統的家庭主義和個人的理想主義之間的矛盾,性、情感、道德之間的張力。他們需要解決矛盾,但有的人可能沒辦法離婚,情緒、訴求需要有一個釋放的出口,所以在網上找到一個思想比較成熟,能夠解答他的一些困惑的所謂的紅顏,一定程度上抵消他在現實中的壓抑感。
澎湃新聞:訪談對象普遍傾向於選擇30歲到40歲,“安全、魅力”的女性交友,看重女性的內在氣質,這些要求和現實中他們的擇偶標準是否存在差異? 這是受到客觀條件限制還是自主選擇的結果?
程萍:他們在平台當中的擇偶標準和他們現實當中擇偶的標準差距不大,只不過在現實中種種原因,他們的擇偶標準沒有實現或者是打了折實現,但在交友軟件上選擇面廣,他們堅持同樣的標準,實現的可能性更大。
這種選擇受主客觀因素雙重影響。一般來說,年輕、漂亮、未婚的女性有戀愛市場,不太能接受“玩一玩”這種方式。30歲到40歲的女性,要麼大齡單身,在戀愛市場受歡迎程度不高,要麼婚姻不幸福,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此外,也和他們需求“樹洞”,有點感情閱曆的女性更容易理解他們有關。

澎湃新聞:他們在現實當中實現不了的擇偶標準,在交友軟件上實現的可能性更大。那這部分女性和這些已婚男性交往的動因是什麼?
程萍:其實我也很睏惑。我本來是想做一個雙性的研究。但是我在平台上主動聯繫一些女性,她們都不搭理我。我聯繫的女性都是發動態、照片挺多,一看就是希望被搭訕的。所以能看得出來,她們在平台上想吸引異性,並不想跟同性做很深層次的交流,或者說女性的警惕性可能更高一些。
澎湃新聞:這些已婚男性既害怕孤獨走進婚姻,又時常想要逃避婚姻,出來一個人靜一靜,這怎麼理解?
程萍:這是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之間的矛盾。從現實層面上來講,婚姻對於男性有很多紅利。比如說我們的研究表明婚姻對於男性的收益比較大,組建家庭有老婆,有孩子,好像是男性人生成功的一個標準形象和標準定義。他的香火得到延續,也有人照顧衣食住行。
但是婚姻里不只有面子,也有很多責任和壓力,他要履行好丈夫的責任、父親的責任。比如掙錢夠不夠花、工作有沒有晉陞、有沒有盡到家庭責任,壓力是比較大的,所以在各種壓力下他必須把他的自我壓縮,一旦生活有了一定的縫隙,他願意讓自己緩一緩,出來釋放一下。
澎湃新聞:像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已婚男性中有的人跟妻子的關係是和諧的。那他們有情感訴求的時候,為什麼不去找自己的妻子交流?
程萍:有的和妻子的認知不同,無法同頻共振。也有的是性方面不和諧,他的妻子不能理解他,他也不可能跟身邊人說。所以他們找“交友”對象傾向於年齡在30歲到40歲,因為這個年紀的女性有比較豐富的情感閱曆,可能更能理解男性說的一些話。
我的感覺是他們找的不是知己,而是“樹洞”,找一個吐槽的對象,抱頭痛哭一下,互相安慰一下,宣泄過後,各過各的生活。其實“樹洞”這個角色也可以由心理諮詢師,婚姻家庭諮詢師也來替代,但現實中有多少人會去找諮詢師?而且報班學心理諮詢、個人成長類課程的,咱們可以看到,大多數都是女學員,男性真的很少。所以說中國的傳統男性是很壓抑的,好像他們在家庭裡面是硬邦邦的一種存在。
澎湃新聞:他們會怎麼去把握一些邊界?
程萍:首先在目標篩選上,就要做好風險控製,比如選擇年紀稍微大一點、獨居、有過婚姻的女性,雙方都認可互不幹涉對方家庭的價值觀。此外,要主動情感剝離,比如說M11有過一段越線的關係,他現在還很想念那個女性,但是他們都各自有家庭,知道自己的底線,不可能結合的,如果再交往下去,比較危險,出於婚姻穩定性的考慮,兩人都各退了一步。
“我看到了更豐富的男性,這些問題也不是男性獨有的”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處理作為女性用戶和女性研究者的雙重身份?
程萍:雙重身份其實不太好處理。比如有的人會忽略我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份,問“約不約?”,如果約的話,他就接受訪談。還有人要求我給他介紹女學生,或者用照片、語言來挑逗我,所以我才從80名有過雙向交流的男性用戶中篩選出28人接受訪談。因為這28人能夠理解我作為女性研究者身份,他們不會用“被搭訕者”的身份來定義我,他們的態度是中肯、真誠的。
至於作為女性用戶,只要在交友軟件保持一定的活躍度,就會有更多的人來搭訕我,從而有更多選擇訪談對象的餘地。系統會自動根據我的地理位置的變化,給“附近的人”推薦我這個“新面孔”,從而收到更多打招呼的信息。我為了提高活躍度,經常發一些動態,比如最近看的書的摘錄和名人名言。一方面,這樣的動態比較符合我的真實身份,另一方面,可能會讓男性用戶覺得這個女性有點思想,有點文化層次。
澎湃新聞:相較於傳統的婚外性行為,借助交友工具後,婚外性行為呈現出哪些新的特點?
程萍:首先,通過交友軟件,選擇面更廣一些,在面向陌生人的交友軟件上有很多女性的資料。而傳統的婚外性途徑無非兩種,一種是去專門的場所找專業的,另一種是通過生活圈、工作圈、求學圈認識。
第二,更加速食、快餐化,在陌生人交友軟件上,你只要發一段語音、一張圖片或者發點文字“勾搭”對方,如果對方有意願,可以很快速地推進,見面吃飯、看電影、發生性關係,不需要前期投入很多時間、情感、物質等。
第三,具備工具理性。在使用“交友”軟件的時候,他們的目的非常明確,並且控製風險的能力強,很容易隱藏自己。但如果嫖娼,顯然會面臨法律責任、生理健康、社會名譽等多重風險。
此外,通過研究觀察到已婚男性在“交友”平台上不只是具有單一的性需求,也會享受搭訕,雙方調情的過程,而且他們不介意告訴別人已婚的身份,因為“已婚”相當於一個免責公告,告訴女方“我不可能對你負責,你不要想太多”“大家就是相互娛樂下而已”。
澎湃新聞:“穩定性大於一切”是“中國式婚姻”所特有的嗎?
程萍:無論中外,責任是婚姻最核心的東西,但是“穩定性大於一切”我覺得是比較中國化的。因為在傳統觀念里,婚姻解體是一種失敗,而且現代婚姻解體的現實成本太高了,往往要圍繞判定誰是婚姻解體的過錯方、共同財產分割、孩子撫養責任分配等經曆長期、反複的博弈和糾葛。所以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性,中國式婚姻比較多見的情況是高穩定、低質量。

書店裡的《婚姻法》區域。
澎湃新聞:交友軟件的使用對婚姻穩定性有怎樣的影響呢?
程萍:研究發現,這些已婚男性使用交友軟件恰恰是為了維持婚姻的穩定性,給自己找一個釋放的出口。軟件只是一個工具,人有充分的自主選擇性和主體性,他隨時可以安裝、卸載,他也可以選擇上線、下線的時間。
借助交友軟件的婚外性跟傳統的婚外性比起來,成本、風險更可控,對於婚姻穩定性的影響相對較小。如果這些已婚男性沒有了網上 “交友”這種渠道,他也可能會選擇其他的宣泄出口,比如QQ漂流瓶、微信搖一搖、到酒吧認識,或者和周圍同事、朋友“交友”。
澎湃新聞:親密關係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是否有所謂的方法幫助人們更好地處理親密關係?
程萍:親密關係不是兩個人的事,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理想的、現實的、傳統的、現代的、家族的、個體的,環境的等因素,永遠充滿了不確定性和流動性。需要有足夠的智慧、知識、技術,在變動中維繫親密關係。
因為建立親密關係這麼費勁,要花很多精力、時間,消耗熱情和耐心,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不願意建立這樣的關係,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孩子。但其實每個人都有建立親密關係的需求,只是要看他願意為了這個需求付出多少。比如夫妻關係里,他真的盡力跟自己的妻子溝通了嗎?還是他只是有需求,但是沒有努力去表達需求,或者努力讓自己的需求找到一個健康的,正確的釋放端口。
澎湃新聞:做完這個研究之後,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程萍:我們現在有一種社交障礙叫“恐男症”,可能有“男性是下半身動物”之類的刻板印象,但做完這個研究,我一定程度上能夠看到他們身上的多重張力,看到了更加豐富的男性。實際上,男性能夠建立這種婚外性關係,必定有女性的參與,說明這種問題不是男性獨有的,是把男性“他者化”了。
在這個時代,我們發展到了追求個體自由,追求個人空間,釋放和滿足個人慾望的階段,和婚姻制度發生矛盾是必然的。這28個個案願意接受訪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內心裡面沒有那麼安寧,他們也是非常的痛苦的,希望通過跟我的交流,瞭解女性的想法,瞭解社會其他人的看法。作為訪談者,我要保持價值中立,有一定的同理心,才能夠真正地理解他們。
此外,現代教育里缺乏對戀愛、情感、婚姻的專業化教育,這些男性採用婚外性行為的方式自我療愈,是很原始粗獷的,一旦被配偶發現,有很大殺傷力。我希望心理教育、情感教育能進一步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