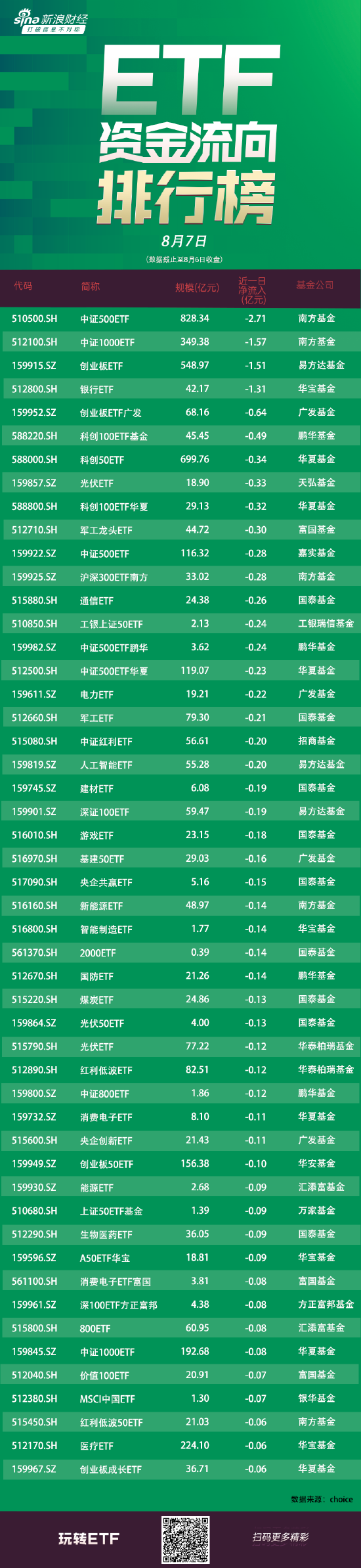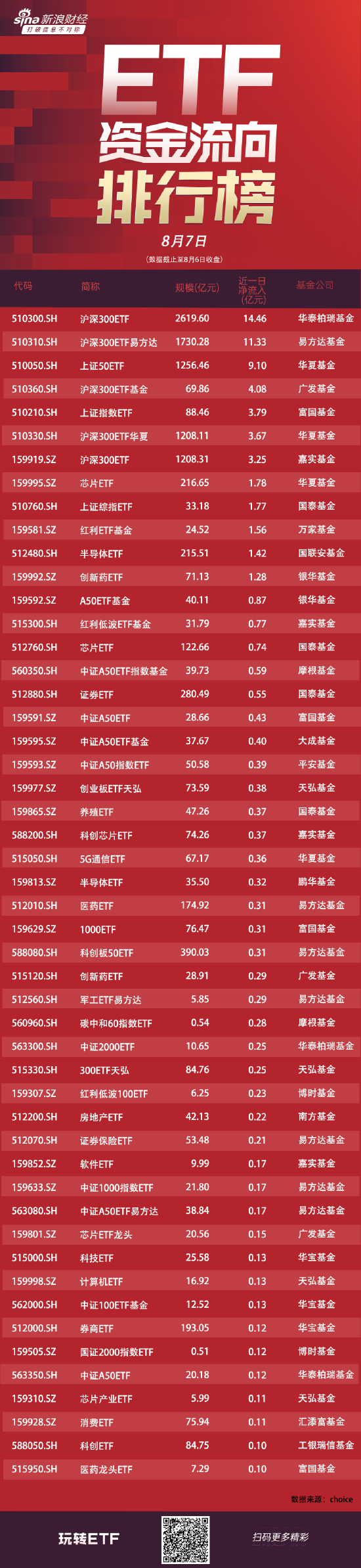為何我們無法擺脫社交媒體?
這半年來,馬斯克收購推特一事餘波不斷。從最初高達440億美元的收購價格,到特赦推特封禁賬號,再到裁員風波,12月19日,這位推特的新任首席執行官在個人賬號上發佈民意調查,就他是否該卸任問題進行投票。超過半數網友希望他“下台”。12月21日,埃隆·馬斯克在推特發文宣佈,在找到接替人選之後,將辭去推特首席執行官職務,但仍會負責管理推特軟件和服務器團隊。
作為社交媒體巨頭之一,推特曾被視為社交媒體革命的代表,象徵一種對於即時交流和更廣泛的民主參與的願景,然而,就近幾年的現實而言,這一曾經的烏托邦景象正在逐漸被技術統治取而代之。

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劇照。
《推特機器》講述的正是這一畸變過程。從無盡慾望的書寫者,到無所不在的假新聞,從鬼魅的網絡詐騙到橫行的網絡霸淩……作者理查德·西摩以精神分析的方法剖析社交工業帶來的深刻影響,為我們展示了數字世界究竟如何改變了我們說話、寫作和思考的方式。如果社交媒體曾經允諾我們可以從當代絕望而孤立的現實生活中逃脫,那麼,在今天,它多大程度成為了我們的噩夢?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如果網絡烏托邦主義土崩瓦解,真正的書寫烏托邦又會是什麼模樣?
下文摘編自《推特機器》第三章“我們都是網紅”。作者在本章中指出:社交平台清楚地示範了,只要我們允許他們的聚光燈照向我們最黑暗的角落,我們的日常生活就能被轉化為商品。這種入侵抹殺了我們在生活中“保持沉默的可能性”,實際上是“能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最嚴重的侵犯”。篇幅所限,較原文有刪減,小標題為摘編者所擬。

《推特機器:為何我們無法擺脫社交媒體?》,[英]理查德·西摩著,王伯迪譯,拜德雅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11月。
在注意力經濟中
我們都在求關注
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中有一代人是在無處不在的圍觀中長大的。人人皆可成名,哪怕只有那麼一點點名氣。媒體批評家傑伊·羅森(Jay Rosen)說,我們這群競逐成名的人其實就是“曾經的觀眾”。在注意力經濟中,我們都在求關注。
注意力經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在社交工業出現前,喬納森·克萊利(Jonathan Crary)就寫到,自19世紀以來,人們就盡力在注意力方面塑造自己的個人能力。而視聽文化上的變化,讓生活成為被碎片、時有時無的注意力和一連串讓人目瞪口呆的刺激所拚湊出來的結果。廣告、電影、新的循環——所有這些都依賴於它們與日俱增、強迫人們關注的能力。

電影《玩樂時間》劇照。
如今,社交平台採取了一系列強製技術,這些技術就好比號稱有心靈感應能力的人和魔術師使用的技巧一樣,能製造出一種自由公平選擇的印象。這些技術不限於各種各樣的獎勵和“點讚”這樣的手段。“已讀回執”讓我們焦急得渴望要回覆信息,並讓這樣的一來一回連續不斷。預設設置本身的偏好不僅比其他設置方式更具視覺吸引力,而且它獎勵順從,讓改變的道路障礙重重。預設值經常與打對勾這樣的確認提示聯繫在一起,進一步鼓勵服從。而無限下滑頁面,讓你的社交媒體資訊供給有點兒像強迫喂食,你永遠滑不到頁面最底端。自動播放則意味著,通過讓你的資訊供給中的視聽部分變得更加博眼球,來鼓勵你駐足觀看。
我們與機器互動中的意識形態影響力,源於選項雖已被設定,但仍被視為自由選擇的愉悅體驗,不管是令人抑製不住的自拍潮,還是淩晨3點讓人發狂的爭吵。從遊戲到資訊,我們做白日夢的能力被鑲進了一個完全設計好的夢幻空間里,我們隨意飄浮的注意力,被牽著鼻子走上了一條已佈滿強化措施的軌道,而我們往往對這些並沒有察覺。

紀錄片《隱私大盜》劇照。
注意的能力受稀缺性影響。神經科學家告訴我們,從生理角度看,大腦無法同時關注兩個“對注意力要求高的對象”。當人們沒完沒了地收到有關新消息的“提醒”時——例如新郵件、更新、軟件提醒、應用程序提醒、新警告——走神的狀態所體現的並不是能同時兼顧多項任務的遊刃有餘,而是一個人不斷地將注意力從一個對象轉移到另一個對象上,費時費力的情形。一經分散,重新恢復注意力可能需要半小時以上。我們將走神美化為“多任務同時處理”,但走神實則就是在浪費注意力。關注本身就是在消耗一個人擁有的注意力,而用這種走神的方式關注事物就是浪費它。
這樣的解讀聽起來可能會讓人認為,成問題的是注意力產出。浪費注意力的機會,或者說處置多餘注意力的機會,大概是我們在尋找的。精神分析學家亞當·菲利普(Adam Phillips)提出了“注意力空缺”(vacancies of attention)這一說法。如果將注意力經濟化,注意力的條件就是不注意。因為要關注一個對象,我們必須忽略其他對象,而被我們忽略的“那個”對象可能是我們故意迴避的。我們必須填補的注意力空缺,會在我們乘公交、吃午飯、上廁所、飯局聊天陷入僵局的時候出現,也可能在慣常的工作間歇出現,上班族其實無事可做但必須看起來很忙。如果我們無處安放多餘的注意力,誰知道我們又會做什麼夢?

美劇《人生切割術》劇照。
對多餘的注意力來說,明星就像磁鐵一般:注意力都被吸走了。而明星並非天生的,而是後天被塑造出來的。根據曆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的說法,這一點在19世紀時就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發現“名人其實是被製造出來的”。到了世俗、民主的時代,名人更是被剝去了神秘的外衣,其機制構造暴露無遺。明星現在成了“偽事件”(pseudo-events),用來遷就市場對無人相信的大新聞的需求。名氣脫離了自身之外的所有語境,變成了里奧·布勞迪(Leo Braudy)口中的“幾乎無可比擬的無城之名”。
建立在這種理解上的現代明星經濟,已經演變成了一種越來越複雜的生產。除了現有的一二三線明星、新聞目擊者、街頭受訪者、見義勇為的英雄、選美皇后以及那些定期“跟編輯通信”的人外,互聯網還帶來了女主播、微網紅與“Instagram上的富二代”,其中有些人後來比他們出現在傳統媒體上的同行們更富有、更出名。社交平台製造的明星包括Justin·比伯(Justin Bieber)、饒舌歌手錢森(Chance the Rapper)和網紅模特夏洛特·達利西奧(Charlotte D’ Alessio)。每個人都能分一杯羹。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想成名,但每位用戶都牽涉其中。只需開一個賬戶,就能擁有自己的公眾形象;只需發一條狀態,或者回覆一條評論,就算擁有了自己的公關戰略。

英劇《黑鏡》(第二季)劇照。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善於利用這個系統,但沒人確切知道明星是怎麼產生的。太多事都取決於運氣。一些在線平台的模式是將日常生活的點滴包裝成商品,在這樣的平台上,任何事都可能“爆紅”。就連差點遭遇不測都能讓你一夜成名。
對真實性的表演
逐漸成為營銷的必需品
如果說追求名利會給想當明星的人帶來危險,那麼對明星日益增多的公眾關注度對那些“粉絲”的身心健康也存在影響。越來越多的“明星崇拜綜合徵”表明,對他人生活的真實面貌的持續消費不僅對他人來說是一種侵犯,對崇拜明星的粉絲來說也令人感到擔憂。焦慮、壓力、生理疾病和越來越嚴重的身體畸形恐懼症,都與對明星的癡迷有關。這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何粉絲會在自己的偶像爆出醜聞時,突然轉而攻擊他們,並從他們的毀滅中獲得一種不合時宜的快感。這種以親密的自我暴露為基礎的明星-粉絲關係一旦被普遍化,就有可能迅速傳播其最有害的病症。換句話說,就名氣而言,推特機器提供給我們的,貌似是當明星和當粉絲這兩個世界中最棒的體驗,但除此之外,它也讓我們體驗了其中最糟的部分。

英劇《黑鏡》(第三季)劇照。
慰藉以“顛覆”的形式出現。Instagram上逐漸走紅的“無濾鏡”發文和標籤的傾向,顯然表明了用戶正以嘲諷的態度戲謔並挑戰媒體的審美常規,例如#自拍醜照,#接受肥胖,#身體正能量,#慘敗,以及#無妝。
報紙意識到其中的經濟利益,向讀者們推送“全盤接受自己的身體”的網絡趨勢,引導他們去“關注對身體展現出無比自愛的人群”。這挑戰了壓抑的文化準則,但這種挑戰算不上什麼顛覆性策略,雖然它乍看之下很像。網絡帶給人的體驗或許是流動的圖像,但這種視覺表現形式掩蓋了其真正的工作原理:在這些圖像背後是一套協議與控製的書寫系統。要想成為平台上的內容,就得首先成為此上癮機制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發佈的內容要能讓用戶與這台機器相連。如果這算顛覆,那麼我們也可以把更換手機背景圖解讀為顛覆智能手機。
拒絕美的常規標準與注意力經濟中越來越受歡迎的“真實性”結合在一起。自從19世紀明星民主化以來,“平易近人”“自然”和“真實”成為名人備受好評的特徵。今天,人們對目睹明星私人關係混亂、整容失敗、高溫天脫妝、發脾氣、爭吵和不良行為這些真實的“無濾鏡”瞬間所表現出來的癡迷,其根源就在於想要撕掉層層假象、暴露出被隱藏的恐懼的那種衝動。

美劇《美麗新世界》劇照。
而這種對真實性的渴望在社交媒體工業中則變得更加急迫。網絡語言是圍繞對虛假的恐懼建立起來的:用戶名、密碼和用戶反應測試,都是為了確保每一個用戶賬戶都應代表一個能夠履行合同義務的人。臉書的廣告宣傳稱:“虛假賬戶不是我們的朋友。”在一個人人時刻極度警惕以防被擺佈的環境,“造假”是一個人能做的最糟的事。一家網站甚至允許用戶檢測被標記為“#無濾鏡”的帖子是否偷偷使用了濾鏡,以便揭穿“造假者”。
此外,社交媒體非常適合用來遷就人們對真實性的渴望,比如讓粉絲們覺得他們能與明星直接接觸。直接的粉絲管理取代了由公關公司集中管控的接觸。最能適應媒體的傳統明星看似為粉絲們在“後台”提供了接觸機會,但這種精心設計的方式在滿足粉絲期望的同時保留了地位差異。明星一般不會關注粉絲,也不會與他們進行長時間的交流,他們期望粉絲能對他們抱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小明星也模仿這種精心設計的親密模式,例如Instagram和YouTube上的網紅們,他們將自己部分的私人生活、人際關係與情緒當作可供消費的表演公之於眾。

英劇《黑鏡》(第三季)劇照。
對真實性的表演也逐漸成為營銷的必需品。截至2015年,以與消費者“真實”的個人關係為基礎的社交網站廣告,占數字廣告開支的十分之一以上。我們可以改變我們在媒體上的策略,用它來推廣那些能與傳統媒體普遍認可的看法相抗衡的形象與觀點。但只要我們這麼做,我們就同時肯定、佐證和鞏固了這台機器擺佈我們的能力。
現代自戀的典型是自拍
但自拍是一個悖論
自拍本應呈現一個獨一無二的人:在最好的光線下、從最好的角度、過著自己最好的生活。但自拍所使用的技術,如亞當·格林菲爾德所說,卻在“全球節點與鏈接的網絡上”,散播著一個形像已經模糊的自我。從手機傳感器到通信基站、海底光纜、微波中繼設備和網絡用戶,這些硬件基礎設施以點對點的方式組織著一個人對世界的體驗,如是,也就組織著這個人的自我。除了將一個人的自我肢解成數字化零部件外,令人擔憂的是,自拍的技術還讓每個人看起來都長得一樣。
自拍的手法導致了自拍照的單調重複與平庸。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對點擊率的追求刺激著流行圖像重復出現。然而,像Snapchat和Instagram這樣的平台,以及像美圖這樣的軟件程序也讓模仿擁有了某種形式的吸引力。濾鏡,即一系列有限的現實調節器,對自拍照進行加工:Snapchat的濾鏡讓我們看上去像卡通人物,有著可愛的小狗耳朵和鼻子;Instagram最初的濾鏡讓人懷舊、思鄉,但給人很惡俗的感覺。濾鏡模糊了我們的臉部特徵與缺陷,讓我們看上去精緻、完美,甚至充滿神秘感。身為攝影師,布魯克·文德特(Brooke Wendt)認為,這些濾鏡鼓勵我們“為了上相,要表現得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

英劇《黑鏡》(第三季)劇照。
威廉姆斯·布羅夫斯(Williams Burroughs)認為,現代消費者對圖像上癮。而我們的自拍照急劇增多就是這種圖像癮的縮影。人類曆史上的大部分時候,自拍都是權勢階層的特權,這些圖像描繪的要麼是貴族,要麼是藝術天才。隨著18世紀與19世紀民主與工業革命的到來,新的呈現方式得以湧現 :窮人接觸到印刷技術,人們發明了攝影與電影技術,而且還出現了新形式的自畫像。從圖魯斯-勞特累克(Toulouse-Lautrec)的《鏡前自畫像》(Self-Portrait Before a Mirror),到杜尚(Duschamp)的《五棱鏡前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Before a Five-Way Mirror),被描摹的這些新的自我往往是殘疾、憂傷、焦慮、憔悴的。這些自畫像呈現的是全人類共有的缺陷與脆弱。
自拍似乎預示著我們回到了那個以貴族為理想的年代,只不過這次人人都能參與。自拍照傾向於避開任何明顯可見的傷疤、憂慮和虛弱。它們所呈現的是無瑕的欲求,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滿足的自我。這種畫像不僅是一個謊言,更是一個發自內心的謊言,而這個謊言恰恰說明了現代的自戀有多麼易碎。1970年代,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注意到一股正在興起的自戀文化後,就斷言這種自戀不堪一擊。這種自戀高估了個體的價值,以至於個體特徵開始逐漸消失。

《自戀主義文化:心理危機時代的美國生活》,[美]克里斯托弗·拉什著,陳紅雯、呂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8月。
市場中的“獨立個體”只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消費者,著了魔般被困在像賦格曲一樣,基調簡單但又能讓人暫時心滿意足的狀態中。這種滿意的模版就是商品形象,即那些出現在電視上、銀幕里或廣告牌上的形象。如今,自我就是商品。但禍不單行,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生產我們自己的商品形象,我們忙於生產有關我們自己的數據,好讓社交媒體平台能向我們賣廣告。我們才是產品。
產品不是活物。盯著一張自拍照就像重新盯著一件已被完成、死去的作品。文德特說,在自拍照里我們看上去就像已經死了一樣。與其說照片里的我們過著自己最好的生活,不如說那裡面的我們看著像死得其所:一具在看(looking)與被看(looked at)的雙重意義上都好看(good-looking)的屍體。自拍照表面上的主題就是其效果。照片是技術社交的沉澱物與石化物,作為其產品,自拍照的形象就是技術組織我們自我感知的方式。

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劇照。
充滿了對鏡自拍的上身裸照、健身房照片、新髮型等圖片的推送,或許能被看作一種形式獨特的偶像崇拜。但與其說這是向用戶致敬,不如說這是向機器對用戶的權力致敬。這種權力無須規定任何事,就能讓人們對何謂自我、何謂生活的理解變得十分狹隘又極其相似。在機器權力的精心策劃下,注意力被分散、被異化,而這一切本身卻充滿悖論。被分散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自己身上,但與此同時,自我卻是萬眾矚目的焦點。在這種意義上,問題不再是多大限度的自愛才能被公共接受,而在於我們是否能發現更令人滿意的東西。
社交媒體平台
更擔心數字化自殺
從生命之初開始,我們在鏡子裡看到的形象就不只是愛人,更是對手。嬰兒一旦被自己的鏡像吸引,就會像君王一樣對鏡子裡的自己指手畫腳,好像在說“嬰兒陛下”——正如弗洛伊德對這種初級自戀所進行的描述那樣。過於完美的形象與經驗形成鮮明對照。儘管嬰兒的感官運動系統還不能發揮作用,他也幾乎不會說話,但他已經為自己找到了一副既能被自己認同,也能從自己父母的目光中得到認可的完全統一的形象。認同這一形象也就是認同他人凝視這一形象的方式。不僅他在凝視,別人也在凝視他。這就是為什麼這一形象如此專斷的原因。在此意義上,被弗洛伊德同死亡驅力聯繫在一起的對身體進行切割、分解、去勢與屠殺的迷戀,可以被理解為自動破壞偶像主義(auto-iconoclasm)。死亡驅力也帶有一種弑君的故事情節。
推特機器內的生活並非與媽媽一起照鏡子的翻版。鏡子像核心家庭一樣,是一項陳舊、幾乎要被取代的技術。弗洛伊德的理論不僅鞏固了拉什對自戀的分析,還因強調極少數成人在兒童情感世界中起到的作用而帶有起源論的特徵。在古典弗洛伊德理論中,父母的認同讓嬰兒的身體充滿力比多(libido)。不過,核心家庭結構現已搖搖欲墜,原本封閉的家庭場所現在遍佈著各種新式的溝通科技。

電影《藍白紅三部曲之藍》劇照。
現如今,孩子們不再通過鏡子,而是通過屏幕找到自己的形象,隨之而來的還有那份凝視。精神分析學家亞曆山德拉·列瑪(Alessandra Lemma)認為,無論存在何種形式的自愛與自怨,它們現在都是因身體與技術之間的這種新聯繫而產生的。如果存在死亡驅力,或者真的存在任何形式的驅力,它現在都被暗含在這一虛擬世界中。但這意味著什麼?在某種意義上,驅力本身就是虛擬的。弗洛伊德用“虛擬”一詞來描述精神世界、幻想、夢境和慾望的空間。他所定義的驅力並非身體本能,而是精神對身體衝動的再現,也就是說,驅力將身體現實虛擬化。現實世界本身就已經是虛擬現實,我們最初通過發明書寫,繼而通過發明印刷,最後通過發明數字化書寫添加的所有一切,都是一層又一層新的虛擬化。
正因此,拉康將所有驅力都定義為潛在的死亡驅力。因為如果驅力是虛擬的,那麼與本能不同,它將無法被滿足,而是將長久、永遠地旋轉下去,體面、愉悅或是基本生存都無法對其產生影響。驅力對一切製約因素發動了一場並非勢均力敵的戰爭,其中也包括對認同的致命製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死亡驅力站在生命的一邊。只要有機會,它就會粉碎我們稱之為自我或自拍的偶像,它也可能選擇數字化自殺。的確,困擾網紅們的公關災難和網絡罵戰,也許與困擾傳統荷李活明星的毒品和酒精狂歡一樣,都是一場自動破壞偶像主義的失敗嚐試。

《視覺文化的奇觀:視覺文化總論》,[法]雅克·拉康著,吳瓊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社交媒體平台更擔心數字化自殺,也就是斷聯,而不是以所謂“顛覆性”的方式使用他們提供的手段。在被認為是社交媒體美好舊時光的日子裡,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機剛結束不久時,大規模虛擬自殺的想法差點兒席捲網絡,正如自殺的想法本身從不缺少受眾一樣。藝術家肖恩·多克雷(Sean Dockray)的“臉書自殺炸彈宣言”敦促用戶們實施在線“剖腹自殺”。一些網站為網絡用戶註銷賬戶提供了快捷新潮的方式:Seppukoo.com讓用戶們寫下自己的“遺言”,並將這段話自動發給其好友,在永久刪除賬戶前,該網站還以用戶的名字為其建立悼念網頁。Suicidemachine.org則刪除用戶的所有好友及信息,將用戶頭像換成一張繩索圖標,然後將用戶添加至名為“社交媒體自殺者”的群組中。
由於社交平台受益於“網絡效應”——平台連接的人越多,其價值越大——斷聯因此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倒退。這兩家網站都收到了臉書要求他們停止並終止向臉書用戶提供此項服務的律師函,他們也被迫照做。經過精心設計的社交媒體平台協議,就是為了阻撓斷聯,因為這將威脅平台本身的生存。臉書本身雖為其用戶提供了永久刪除賬戶的選項,卻別有用心地將該選項隱藏起來,讓人無法在任何菜單或設置選擇中找到它。用戶若想刪除賬戶,就必須填寫一張表格並通過臉書幫助中心上傳,然後等待“複議期”結束。在此期間,臉書會通過顯示“想念你”的朋友照片來讓你回心轉意——也就是利用它們能控製被你上傳的內容這一點,來達到商業目的。

電影《她》劇照。
有證據顯示,現有的社交平台已達到其用戶峰值。臉書、推特和Snapchat的用戶數量都在下降,其中 2018 年尤為嚴重。諷刺的是,Snapchat的衰落可能就是由該平台依賴明星導致的。當凱莉·珍娜(Kylie Jenner)告訴她的2500萬粉絲她“已經不用 Snapchat”時,僅因這一條推文,該公司的市值就瞬間蒸發掉了13億美元。但這一趨勢相當普遍。隨著青少年人數減少,臉書一年內就在歐洲損失了100萬用戶和相當於1200億美元的市值;受假新聞和網暴的影響,推特也失去了100萬用戶,其股價因此暴跌。
不過,至少40%的全球人口仍在使用社交媒體。當超過60億個眼球全神貫注地盯著屏幕時,這依然意味著一場大規模的注意力同步。社交平台或許會式微,也可能改變其形式,但他們不可能消失。他們已經成為擁有巨大政治與意識形態力量的壟斷機構和巨頭。他們的系統是一個永遠都不會被完成、總處於製作中的作品,通過對最新的流行趨勢做出回應來讓用戶們保持上癮的狀態。可能的是,在沒有替代品的情況下,社交平台將與現有的風險資本、娛樂產業和新聞媒體的結合體合作生產分散注意力的新技術。
但社交平台只加工社會熱點的原材料。這樣做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好勝的個人主義已經從政治和文化上得到了激勵,而大眾明星生態系統的崛起也已經是進行時。另外,這也部分因為社交媒體滿足的是合理要求:平台為認同、有創意的自我風格、打破單調乏味、白日夢或閑暇時間的思考提供了契機。可是,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這些活動具備經濟價值。社交平台非但沒有讓我們從勞累的工作中得到休息,反而讓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辛苦的工作。

短片《虛假的你》劇照。
社交平台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注意力的價值。但如果我們採納作家馬修·克勞福德(Matthew Crawford)的建議,將我們的注意力當作不應被浪費的寶貴之物呢?如果我們主張我們有權不被無休止地推送信息,不沒完沒了地為一個命運與其平台股價一樣不穩的形象提供服務呢?社交平台已經清楚地示範了,只要我們允許他們的聚光燈照向我們最黑暗的角落,我們的日常生活就能被轉化為商品。精神分析學家喬什·科恩(Josh Cohen)認為,這種入侵抹殺了我們在生活中“保持沉默的可能性”,但我們的生活本就是“由黑暗與沉默這樣的自然元素所構成的”,因此這種抹殺實際上是“能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最嚴重的侵犯”——如果我們真如他所提議的那樣想呢?如果說有令人滿意的工作、職業與曆險在等著我們,而我們只需想清楚我們的漫不經心是為了什麼,並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呢?
原文作者/[英]理查德·西摩
摘編/青青子
編輯/青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