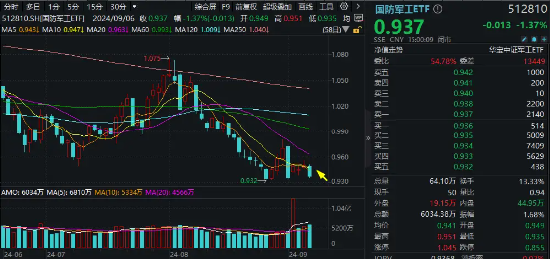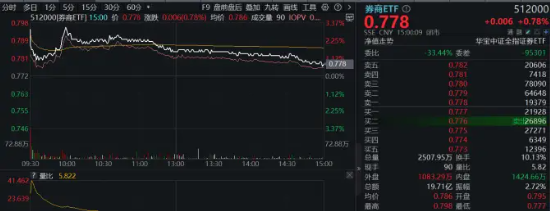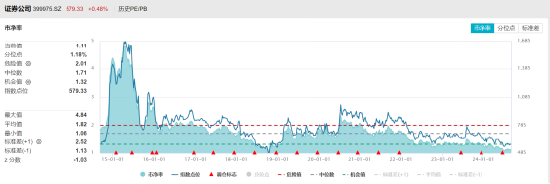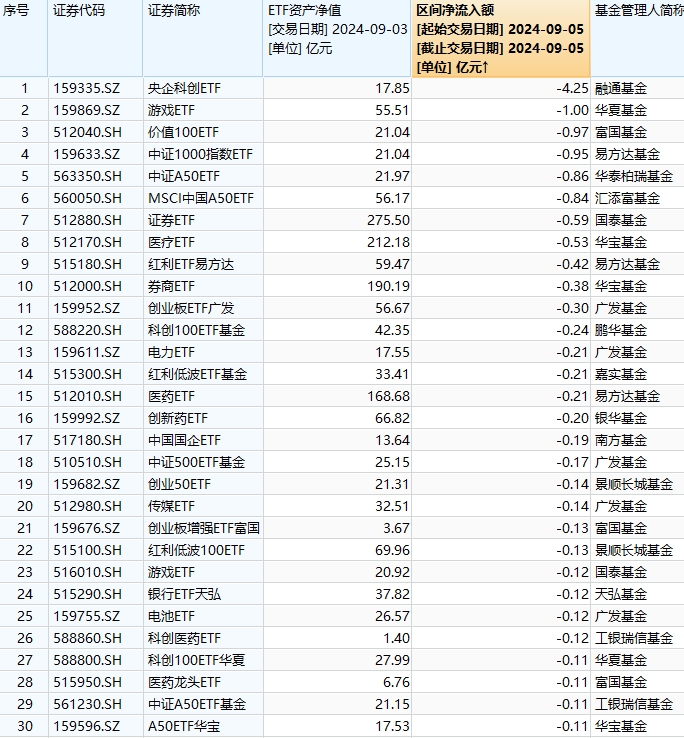李孝悌談新文化史、民國戲曲文化和作為價值的逸樂
 李孝悌(章靜 繪)
李孝悌(章靜 繪)李孝悌,美國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曾任台灣“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曆史學系主任,現為台灣“中央”大學曆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研究方向為明清以來的社會文化史、城市史。《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慾望與生活》(以下簡稱《戀戀紅塵》)是李孝悌教授的名作,已有中、英、日等多個語言版本,2022年10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戀戀紅塵》最新的簡體中文版。以此為契機,《上海書評》特邀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中心副教授胡簫白對李孝悌教授進行了專訪,從《戀戀紅塵》談到其英文新著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在這篇訪談中李孝悌教授表示,回看自己幾十年的學術體驗,“逸樂”最能代表他的學術誌向。
 《戀戀紅塵 : 明清江南的城市、慾望和生活》,李孝悌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戀戀紅塵 : 明清江南的城市、慾望和生活》,李孝悌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新文化史的邏輯與方法正在成為“常識”
《戀戀紅塵》近期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據我所知,近二十年來這本書以不同的面貌、文字與書名和讀者見面,凸顯了經久不衰的生命力。您覺得這本書為什麼如此受歡迎?
李孝悌:廣西師大的新版賣得很好,已經二刷了,這讓我非常訝異。可能是因為這本書迎合了大眾對新文化史的興趣,這讓我尤感慰藉。新文化史作為一個已經不算太新的史學思潮,在美國、法國、中國大陸的發展態勢非常不一樣。先講美國。2019年時我去哈佛開一個關於“五四運動”的會議,算是重遊故地,但發現哈佛的學術世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一方面,我讀書時常常流連的區域已經基本找不到書店了,倒是多了很多咖啡館,雖然方便了學生一邊用餐一邊溫習,但整體環境看起來有點頹靡,不太像讀書的環境。僅存的兩家書店裡也全是全球史和後殖民理論的作品。此行期間我還去參加了蔣經國基金會辦的一次評審會,發現百分之九十五的優秀論文也都是全球史。我已經過世的老師林毓生先生就曾經說過,“美國人的學術就像女生的裙子,每五年就換一個樣式”。這個評價還是很犀利的。美國的學術熱潮的確是一輪一輪地更替變幻,每一股風潮都像秋風掃落葉。當然,在這樣的情景下,也容易刺激學者在範式層面進行革新,激發創造力。
那麼法國和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呢?
李孝悌:新文化史在法國的樣態與美國不同。法國學界有很堅實的新文化史傳統,他們對愛國主義、民族認同的建構認知,對禮儀、情感、心態和集體記憶的考察,都豐富了我面對史料時的聯想空間。當然法國學界也並非不進行自我革命,我們能夠看到幾代年鑒學派間的範式轉換,從關注長時段的整體史向計量史學的過渡,從心態史、情感史的橫空出世,都能感受到這個偉大學派在不斷推陳出新。與此同時,法國學者的理論功底深厚,他們提出的很多理論都為新文化史開拓了研究領域,也多被應用於中國曆史的研究。比如布迪厄就是典型。他所提出的“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區隔”(distinction)等概念可以和中國史研究聯繫,比如區隔理論探討了品味的等級劃分與社會階層之間的對應關係,而明代晚期的中國社會也展現了相當程度的品味差異,不同社會階層的審美風尚是截然不同的。
美國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實能看到很多來自法國學界的影響。比如我的老師孔飛力可謂是一個堅定的社會史學家,但我一直認為他的那本《叫魂》,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地帶上了新文化史的色彩。這本書描繪的是乾隆年間民眾的集體恐慌心態,是新文化史很喜歡的議題。我一直認為《叫魂》和《屠貓記》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是對“符號”(symbol)的詮析手段。其實人類學對新文化史的影響非常大,孔飛力教授當時讓我們一定要讀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那時候他還沒開始寫《叫魂》,我們都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現在明白他其實就是在解析意義。文化是由人編織的意義之網,而人類學的任務就是要解釋貫穿於研究對象活動中的文化結構,深描行為發出者眼中的意義。這種破譯(decipher)當然可以溯源至詮釋學,但新文化史賦予了其新的內涵。
 《叫魂》
《叫魂》 《屠貓記》
《屠貓記》我其實對當下大陸學界的狀況不是非常熟悉,但我知道像葛兆光教授這樣的學者是很支持新文化史的。他同我關係很好,在我的《戀戀紅塵》剛出版之時,他給了很好的評價。在開辦兩岸曆史文化研習營前,我曾和王鴻泰教授等人合辦了“文獻與田野:閩南文化研習營”(金門營)。一共辦了四屆,其中最後一屆是在廣州舉辦的。我的好朋友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在研習營上說:“你們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想給你們一句忠告。你們做社會史做了這麼多年,應該有一個文化轉向。”宋怡明關於明清衛所的研究是十分紮實的,而他也強調曆史學的文化轉向。所以你看,文化史的影響還是無法完全抹除的,像現在很多學者都喜歡使用的建構理論,其實就是一個標準的新文化史概念。
的確,現在很多學者慣用的思維方式和研究邏輯,其實都受惠於新文化史帶來的啟發。比如您說的建構,要求我們對史料的“生產語境”多加探索,對“曆史書寫”的話語霸權生成過程保持警惕。換句話說,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已經成為一種“潛移默化”的常識,甚至不需要被專門強調。
李孝悌:對,“書寫”也是新文化史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法國學者最先提出了這個概念。雖然新文化史無法像全球史那樣被旗幟鮮明地承認,但其研究範式已經融入曆史研究的傳統之中,你不能完全把它忽略掉。我有很多同事雖然不標榜自己是新文化史家,但顯然他們都受到了很好的文本分析訓練,可以透過文本表面去挖掘其本質(reading through)。關注語言、文本以及敘述結構在曆史事實的描述中所發揮的作用,無疑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大貢獻。它提示我們在解析文本的時候要格外的小心,切忌不加甄別地使用史料,史料後面有各種各樣的可能。當然,我們在應用這些所謂的理論或者視角的時候,尚需注意形式。我記得餘英時先生以前說過,採用西方的理論做研究,要做到“鹽溶於水”。比如我們看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在比試的時候,肯定不會傻裡傻氣地將自己使用的招式直接喊出來。曆史寫作也是同樣的道理,你不能直接說“我用了某某研究方法”,而是要將這些理論方法融入行文當中。理論是你的論文的內在架構,不應該在表面體現。台灣地區學界會把在論文中生搬硬套理論的做法稱為“夾棍”(jargon,指一般只限於內行人之間進行交流的術語、措辭),說明寫作者並沒有真正進入研究對象的世界,而這樣的文章註定是枯燥無趣的。
和這個討論相關,我注意到您的研究運用了很多文學性的材料,比如將詩歌、小說作為史料,強調可以借由詩歌進入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豐富我們對其日常生活的認識。這確實是其他類型的史料所難以達成的。您認為學者在使用文學材料進行史學研究時,需要注意些什麼?
李孝悌:確實,傳統的社會史或政治史研究是極少使用文學或藝術作品的,社會史強調鋼鐵一般詳盡紮實的資料,政治史也強調“實”而非“虛”。但我認為文學材料中其實潛藏了非常重要的訊息。做社會經濟史的學者也應當閱讀《金瓶梅》,因為有很多社會經濟史的線索。所以小說這類的文學材料完全是可以使用的,就看你從什麼面向去解讀。我的研究中使用了很多文學作品,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己的偏好,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從中提取一些不一樣、在傳統研究範式下往往會被忽視的信息。例如詩文對我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一旦把各種看似佶屈聱牙的表達拆解開,你就會發現詩裡面蘊藏著大量的資料,不管對於物質生活還是日常生活的研究都是有很大裨益的。對於古代中國的文人而言,他們未必會把所有生活細節寫在文集裡面。但他的詩作,一定是和他的感情、內心世界聯結最緊密的。你要通過詩作里的那些細節,進入他的情感世界,瞭解他的所思所感。我很推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寫的《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我覺得他真是很了不起,能夠從汗牛充棟的古典文獻中揀選了十數篇杜甫的詩文,通過精彩的分析與考證捕捉中國文人對回憶的獨特體驗。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也寫得好極了。這本書在堅實的檔案基礎上,對康熙有很多細密的心理活動的描寫。而如果你不具備高超的文獻解讀能力,你是無法進入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遑論瞭解一位古代君主的內心世界。
 史景遷
史景遷戲劇文化所見民國上海的混雜現代性體驗
我們來聊聊您的英文新書吧。您2019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新出了一本英文專著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現代中國的戲劇、社會與政治》),由於這本書尚無中文譯本,可能大陸的讀者朋友們對此書的瞭解還不夠多,能否請您給大家做個簡要介紹?
 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李孝悌: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是我去杜克大學參加的一個學術研討會,後來我又和梅嘉樂(Barbara Mittler)教授一起去海德堡大學參加了關於中國“文革”時期的文化與音樂的專題會議,在會上我就產生了一些想法,認為“文革”時期的文化形態和清末民初的時事劇存在關聯性。隨後我在寫作過程中對這一想法進行了擴展,並將關注重點放在了二十世紀前四十年間,考察其時的中國戲曲在上海的新舞台和西安的易俗社的帶領下,實驗新型舞台形式及劇本,並尤其圍繞社會改革推出新戲劇的曆史進程。我認為,在二十世紀前中期,“政治化”的趨勢成為中國戲劇最鮮明的特色,並與當時的政治文化交織纏繞。
在寫這本書時,我受到了東京大學田仲一成(Issei Tanaka)教授關於中國戲劇史研究的很多啟發(《中國戲劇史》)。作為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田仲一成教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投身對中國戲劇的研究,以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戲劇,將實地調查所得的新材料與既有文獻相結合,極富開創性。田仲一成教授是最早關注到晚明時事劇的學者之一。他認為明末清初江南的戲劇表演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傾向,即取材時事、反映時政的時事劇逐漸取代了以古代傳說為主題的戲劇。時事劇在晚明盛極一時,可惜到了清代就被禁止了。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時事劇又在上海的改革派劇團“新舞台”的推動下複興了。而且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共產黨早期的兩位領導人——陳獨秀和瞿秋白都十分注重戲劇改革。陳獨秀是第一個提倡用戲劇啟蒙大眾的,他把戲劇給捧到極高的位置。在1904年發表的《論戲曲》一文的開篇,陳獨秀談到“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的大教師”;而瞿秋白則是在三十年代初開展了關於大眾文藝的論爭,倡導利用民間文化的形式和其他宣傳手法,將共產主義變為一般民眾生活中的常識。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傾向就是深入地方,充分發揮大眾文藝作品在動員民眾中所起到的作用。
您在書中討論“新舞台”的時候提到一個細節,即上海的新式表演空間乾淨、整潔,與舊式戲院的惡劣衛生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甚至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女性觀眾參與了文化場域的形塑。這一點很有意思,讓我對民國上海的認知又細化了一層。
李孝悌:我覺得衛生方面的進步看似微不足道,卻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衛生條件的革新恰恰證實了當時戲劇的現代化。而當時上海戲院文化展現出來的現代化特質,其實可以用光怪陸離來形容。我在書中提到,在明治維新前,日本的劇院也是相當落後的。演出通常是露天的,普通觀眾只能坐在地上看戲。後來有個叫市川左團次(Ichikawa Sadanji)的歌舞伎演員,他在遊曆歐洲和美國期間觀看了許多戲劇表演,被西方劇院所使用的華麗佈景大大震撼,後來將西方戲劇的模式引入到日本。而新舞台建成沒多久,創建者夏氏兄弟就前往日本東京取經,從市川那裡學到了改革劇院的經驗,並在回國後對新舞台的設施進行了升級。因此我認為,新舞台絕不是一個地方性質的小舞台,而是一個同世界接軌的現代化大舞台,在舞台設計和建造上都進行了極大的創新,使用了當時較為先進的技術,從而區別於同時期北京等地的傳統劇院。所以1913年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新舞台時,他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的。首先,北京當局禁止夜間表演,人們不能在晚上觀戲,而上海則不同。得益於現代照明技術的引用,夜間表演在上海的劇院非常普遍,且廣受歡迎。我在書中引用了晚清徽州士人詹鳴鐸的自傳《我之小史》。詹出身於商人世家,1909年曾在上海法政講習所學習。在《我之小史》中,他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滬上的休閑娛樂和都市風情。上海的煤氣燈和電燈,讓詹這樣一個從偏遠鄉村來到繁華上海灘遊曆、學習的“末代秀才”新奇不已,燈光創造了上海令人驚歎的夜景。與同時期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真可謂是一個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
其次,在劇院功能上,北京的舊式劇院是供人聽戲,而非看戲的。當時台下觀眾的主要目的是朋友聚會、喝茶、聊天,觀看表演只是附帶的活動。一些老戲迷聽到台上的演員唱戲走了調,甚至會直接喝倒彩。而上海新舞台的舞台設計跟北京截然不同。新舞台在當時中國的地位,可以類比美國現在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可以說,新舞台的建立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戲劇時代,新式劇院也從本地人的娛樂空間躍升為展示國際化與現代品味的場所。但與此同時,我們又能看到上海戲劇場域中很多奇妙的組合,以當時新舞台最成功的戲劇《濟公活佛》為例,濟公向劇中的女性指出了封建包辦婚姻可能帶來的災難,告訴她“你要走自己的路,不要回去做一品夫人,不要變成男人的玩偶傀儡”——後半句顯然是在向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致敬。編劇將胡適等五四代表人物的主張投射在了濟公這樣一個五四時期最反對的封建神怪的產物身上,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我們現在或許會對這種混雜的現代性感到不解,但其實你細想一下,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充斥著現代與傳統的碰撞,對一般人而言哪有什麼純粹的現代性,無非是把所有的信息都獲取進來。
據我所知,這本書是從您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請問從博論到成書,您做了哪些方面的調整?您又如何與包括田仲一成、梅嘉樂、郭安瑞(Andrea Goldman)等專研戲曲與戲劇史的學者對話?
李孝悌:最大的轉變應該是結構上和方法論上。本來,書籍的前半部分有大量關於思想史的內容,我都進行了刪減,只留下了核心和比較新穎的觀點。例如梁啟超的戲劇理論和創作,還有胡適、傅斯年等知識分子對傳統戲劇的批評,已經有太多人談過,所以我在書中只是一筆帶過,而重點刻畫了熊佛西、餘上沅、趙太侔這些在美國受訓、繼而對中國的戲劇改革起到了非常大影響卻不為世人所熟知的戲劇家的故事。此外,起初我並沒有打算寫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因為當時的上海實在是太吸引人了,所以講述上海新舞台的那一章也就成了我投入的情感最深、著墨最多的章節,之後又拿西安的易俗社與新舞台做了對比研究。但後來有一個審稿人跟我說這樣不行,研究的時段從1920年代一下跳到1949年,中間的二十年就斷裂了。為了他這一句話,我又用了一年的時間把三十一冊的《中國戲曲誌》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瞭解每個地區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戲劇發展情況,作為我這本書最後兩章的史料基礎。
 熊佛西
熊佛西在寫作過程中,我時刻都提醒自己,雖然我的研究是一個文化史的議題,但處理的其實是規模廣泛的社會運動,因此要把這些事情放在具體的時空環境中去理解。韓書瑞(Susan Naquin)教授參加過我們明清文化史團隊好幾次的會議,我和她很熟,有一次她就跟我說:“孝悌,你到上海可不能只顧著參觀遊覽,還得進行田野調查。”她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刺激,我後來真的在上海的城市里做田野調查。把與新舞台相關的南市十六鋪、九畝地區域都好好走了一遍。十六鋪東臨黃浦江,由於它地處外灘以南,也被稱為“南外灘”。明清時期,南市十六鋪一帶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後來逐漸被租界取代,商業重要性降低。因此夏氏兄弟決定在此建立新舞台,以振興經濟。後來劇院失火,新舞台遷往位於城區西北部的九畝地重新開張。我在實地造訪的過程中發現,九畝地其實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地方,它坐落於租界交界處,彙集鴉片館與賭場,從清代開始就是毒品走私盛行的區域。不過由於當地劇院稀缺,仍然可以挖掘出許多潛在的觀眾,因為票價不高,隨便一個百姓都可以花得起錢看戲。在上海的城市田野調查,對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經驗。後來我也發現,讀者對這一章的社會史描述頗為讚同。
至於我的研究和既有研究成果的差別,我認為我們處理的角度不一樣。郭安瑞教授關注的主要是性別問題(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她對清代戲曲的研究吸收了社會性別史的研究方法,認為戲園是時人進行對話的公共領域,體現了民族、階級和社會性別等多個層面的界限跨越。她的文筆也很好,讀她的書就像在讀故事一樣。梅嘉樂教授則是從音樂、舞台表演、文學等角度,在中國傳統戲曲的漫長流變中看樣板戲的誕生(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她的研究打破了我們對樣板戲的刻板印象,告訴我們“文革”時期的戲劇其實相當豐富,既體現了對中國戲劇傳統的延續普及,也汲取了外國的現代經驗。而我的研究更多是圍繞戲劇與時事的關係開展的,雖然也討論了音樂和舞台的創新,但主要關注的還是知識分子的話語與行動。在書中,我探討了從明清中國的時事劇,到二十世紀中期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治劇的流變過程。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和戲劇是如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政治事件又是如何迅速被轉換為戲劇情節,搬上舞台供人們欣賞的。
作為價值的“逸樂”
如果把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這本書和您早年的其他著作放在一起,我們好像能看到您的學術成長脈絡是由二十世紀早期開始,關注晚清到民初知識分子的下層啟蒙,隨後上溯到明清時代,關注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我們知道,很多學者或自發或被動地徘徊在一個時代、一個主題進行研究,而您則在幾個主題之間遊刃有餘,請問是什麼造成了您學術關注的改變?
李孝悌:我想一是和我的個性有關,我的性格呈現出矛盾的兩面。一方面,在飲食起居方面,我習慣採用一套固定的做法——吃同樣的食物、去同一家店喝咖啡、走同樣的路線散步……看到那些經過幾百年留存下來的古籍我也會感動不已;可在思想文化層面,我會求變求新。創新對我來說很重要,所以我會喜歡上海,因為上海總能給你呈現一些新奇的事物。也可能跟我是雙魚座有關吧。
第二其實是我對學術傳統的“反動”偏好。我最初做的是晚清思想史,後來又做了政治史。在日複一日地閱讀近代的史料後,我對這一段曆史產生了倦怠感。由於我接觸到的晚清民國的材料多是用白話文寫作的報紙文章,我擔心自己每天看白話報,會越看越白,就想做一些關於古典詩詞的研究。此外,近代史學界的標準敘事是將1840年以後的中國曆史與失敗、錯誤等負面詞彙掛鉤,許多著作中描繪的晚清中國都是一幅衰敗的景象,這使我感到很難過。所以我決定暫時從近代史的研究中抽身,回到明清,重新審視那個中國尚未走向衰頹的曆史時期。我想我們可能高估了中國古代思想、道德的壓製性,同時又低估了整個時代的複雜性和殊異性。在官方的政治社會秩序或儒家的價值規範之外,中國社會其實還存在著許多異質的元素,潛藏著一個不同於人們固有印象的文化世界,而這股文化的潛流在晚明的江南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戀戀紅塵》一書,就是我在主流之外,發掘非主流、暗流、潛流乃至重建更多的主流論述的嚐試。我覺得晚明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就像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在《維米爾的帽子》里描繪的那樣,當時的中國並非是與廣闊世界脫節的封閉空間,而是一個開放且多元的世界。特別重要的是,當時的西方商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物產豐饒的寶藏之所,有無限的商機,是一個廣大的磁吸機,能夠吸引幾十萬的西方人前仆後繼地遠渡重洋,跨海而至。
回頭看過去這幾十年您的學術體驗,您覺得哪個關鍵詞最能代表您的學術誌向?
李孝悌:我想應該是逸樂。就像我剛剛說的,主流史學界對中國曆史的寫法太過森嚴,從而導致了對中國傳統文化豐富性的忽視。單就上層社會而言,中國古代不同朝代的文化特徵也迥然不同。比如“竹林七賢”彰顯了超脫世俗、不拘禮法的魏晉風度,而胡旋舞則反映了唐代承平許久、開放昂揚的盛世景象。中國文化如此多元,而我們很多曆史學者卻將其越做越狹窄,我對此是很不滿意的。我在《戀戀紅塵》一書的導言部分寫到“逸樂作為一種價值”,這當中其實包含著兩重含義:一是用來呈現作為研究對象的明清文化的一種面貌——在明清士大夫和民眾的生活中,逸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甚至衍生成一種新的人生觀和價值體系;二是提醒我們這些研究者,要正視“逸樂”作為一種價值觀、一種分析工具、一種視野以及一個研究課題的重要性。倘若我們囿於傳統學術的成見或自身的信念,只願意關注內聖外王、經世濟民或感時憂國這類大的議題,那麼我們對整個明清曆史或傳統中國文化的理解勢必是殘缺不全的。考慮到曆史學的長遠發展,關注中國曆史的獨特性與豐富性也是很有必要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不少優秀的思想史家、政治史家了,相關研究也是汗牛充棟,不妨換一個面相,傾聽被主流聲音遮蓋了的複調。
當然,很多前輩學人也為我們給“逸樂”這個軟性、輕浮的、往往具有負面道德意涵的概念在學術史上爭取一席之地做出了很大貢獻。譬如彼得·蓋伊(Peter Gay)在《啟蒙時代》一書中提到的當時哲學家關於逸樂到底會不會有損人類理性的辯論、斯特亞特·休茲(H. Stuart Hughes)對實證主義外的無意識作用和“世紀末”思想風氣的論述,都啟發著我去彰顯逸樂的價值。
話說回來,我其實就是想要去除纏繞於中國史研究的刻板觀念,深入探索那些頗具魅力卻被學界有意無意忽視的文化要素。它們漂泊於廟堂之外,也鮮少為人所瞭解。因此《戀戀紅塵》能在大陸有這麼多的讀者,我是非常感動的。在台灣地區,很多人覺得風花雪月的東西怎麼能算是學問?我想應該是中國大陸足夠大,可以容得下各種各樣的事物。中國文化是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而在這種文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們也具備很強的包容力,能夠欣賞不同的文化。
您在此前的一個採訪中說過,南京是真正可以寄託您人生理想的城市,為什麼?接下來還打算進行南京相關的研究嗎?
李孝悌:首先南京有許多文學作品,從六朝延續下來的文化傳統很紮實,讓人覺得這個城市的文化脈絡是持續不斷的。其次,南京和北京、上海這些都市截然不同。我也很喜歡上海,但上海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現代性,而南京則具有一種獨特的“頹廢”氣質,這是傳統文化發展到極致所呈現出的面貌,與晚明時期江南地區在文化層面的解放有密切的關係。雖然蘇州、揚州也是繁華富庶的江南城市,但南京在政治上的輻射力是蘇州、揚州無法比擬的。我們可以說蘇州是人間天堂,但它絕不是人間的政治中心。南京素有“十朝都會”之稱,從六朝到民國時期,南京都是江南地區毋庸置疑的政治中心,城市的發展在不同曆史時期都受著政治因素的驅動,從而形成了南京獨特的城市性格。這種城市性格也很影響生活在其中的人,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行為模式。
不過我不打算再做南京的研究了,留給你們去深挖細化吧!這或許也跟我的學術“反動”個性有關。這些年,我希望逐漸把眼光從江南移走,去關注福建泉州地區的文人士大夫生活。福建這個地方很有意思。福建有儒學,而晚明江南地區的這些人卻都不是儒家。文震亨、張岱這些文人都出身科舉世家,而他們自己雖然也參與了科舉考試,卻只能止步秋闈。他們留下的多是文化生活層面的痕跡。在他們身上,你幾乎看不到科舉制度的影響,更不要說朱熹的影響。而福建則不同,福建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一方面,福建出商人、出海盜;但另一方面,福建也出了相當多的進士,福建籍貫的進士占比是非常高的。這與朱熹在當地的影響力脫不開關係。福建的儒家學者也非常關心商業的發展,對福建商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具體到泉州,它在古代被稱作“泉南佛國”,是佛教文化傳入較早較集中的地方,泉州的開元寺是福建省最大的佛教寺院。泉州的天后宮則是海內外現存年代最早、規格最高的媽祖廟。此外,泉州還有很多伊斯蘭教、摩尼教留下的痕跡,可以說全盛時代的泉州,對宗教的態度是相當開放包容的,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像泉州這樣宗教形態極度繁複的城市。文士們如何遊走於正統的孔孟之道與駁雜的民間文化傳統之間,讓我非常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