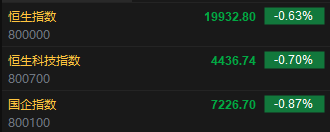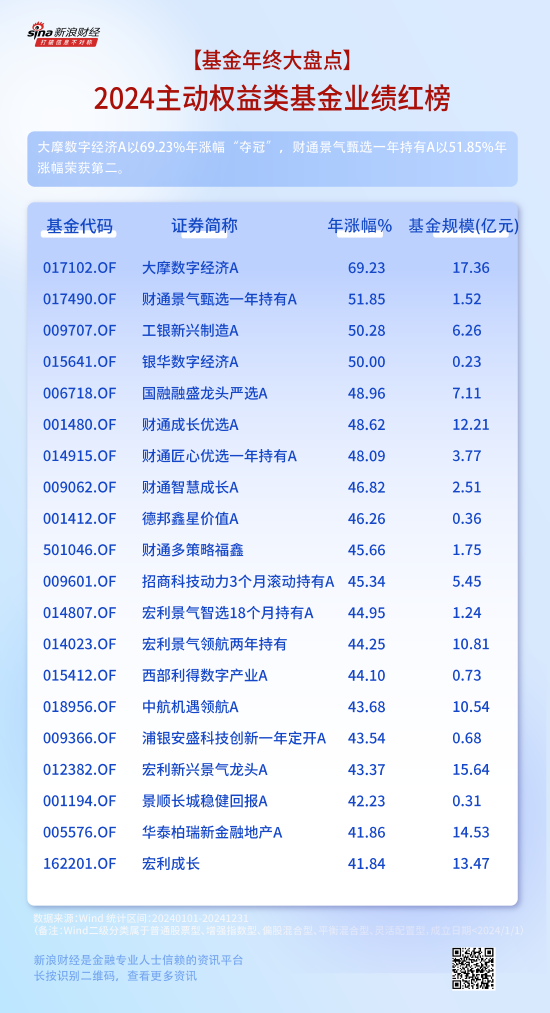專訪|導演田曉鵬:海的“深處”有什麼?
田曉鵬從小喜歡海洋和天文。雖然大學時候怕學天文不好找工作現實了一把,學了軟件工程。但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堅持著“追星星”的愛好,也始終為一片與眾不同的“深海”魂牽夢縈。
正月初一上映的動畫電影《深海》是導演田曉鵬繼《大聖歸來》七年後推出的新作。影片展現了一個小女孩潛入大海最深處,邂逅一段獨特生命旅程的奇幻故事。
從2020年《薑子牙》片尾彩蛋驚鴻一瞥的露出後,《深海》的質感就讓不少觀眾一見難忘。在田曉鵬營造的這個世界里,美輪美奐的國風3D效果堪稱極致——海洋呈現出前所未見的絢爛與斑斕,油彩質感和水墨氣質交融的幻想世界包容著歡脫的天真與沉浸的憂鬱。
而這部帶著強烈反差的故事,恰如銀幕背後那個創造這個世界的人。
 《深海》海報
《深海》海報A面
七年磨礪,不計勇往
因為喜歡《海底兩萬里》,一直以來,田曉鵬都特別喜想講一個關於大海的故事。但一個動畫導演腦海里的海,可以超越物理常識,承載新奇曼妙的無限存在。“海洋應該像天空一樣,魚在裡面暢遊的時候,多彩有很多變化的層次感。”
在技術層面上,《深海》的里程碑意義毋庸置疑。其中最顯而易見和值得說道的,是那個將東方海洋氣質的斑斕層次展現到極致的粒子水墨技術。
讓水墨畫變成三維動畫,導演的執念。田曉鵬曾說,“如果不能創新,我可能不會做這部動畫”。但將飄逸的水墨變成具象的三維,絕對寫實和靈動的抽像是兩者美學構成上的天然矛盾。為達成這份執念,團隊從0到1的研發曆程充滿波折,最終,在嚐試了一百餘次的“洗潔精、丙烯、食用色素、牛奶”混合實驗後,製作人員嚐試以無數粒子堆積成水墨的形態,以此打破三維物體的硬輪廓。而從2016年第一張概念圖的誕生,到讓水墨畫面動起來,整整兩年就在這樣的執念中“耗”過了。
據悉,影片中,許多單幀畫面的粒子數就高達1-2億,“深海之眼”鏡頭,粒子特效數量高達20億,色彩分層多達200層;而 “劈海”鏡頭,單鏡頭粒子特效多達一百餘層,粒子數量高達幾十億,負責該鏡頭的特效師更是將原計劃“3天”完成的鏡頭硬生生熬到“15個月”。
這樣的“打磨”發生在電影的方方面面。從“深海號”令人眼花繚亂的海洋生物細節,到海獺們下巴毛尖尖粘連的濕答答口水滴;從人物皮膚毛孔的質感,到表演上細緻入微的控製……《深海》被讚“美哭”“每一幀畫面都是壁紙”的國產動畫美學巔峰背後,是1478位中國動畫人的7年的創作心血。
有意思的是,在決定啟動這一趟冒險探索時,田曉鵬曾談到動畫審美被日本、美國定義的不甘心,也曾放下豪言“想把中國動畫帶到全世界”。而如今電影完成,即將上映之際,又恰逢今年柏林電影節公佈片單,《深海》入圍了新生代單元,如同一種“說到做到”的兌現。
電影節組委會評價:“《深海》是一部雄心勃勃的電影,它為觀眾展現了一個豐富精彩完整的世界:這是一次有深度、有複雜性的奇妙冒險,用令人著迷的色彩和奇觀來敘事,這是我們前所未見的”。
 《深海》劇照,深海之眼
《深海》劇照,深海之眼B面
心之所往,比海更深
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導演田曉鵬有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是——曾經不被信任、找不到投資做“大聖”的孤獨,和後來被無數人信任寄望,付出巨大努力埋頭奮力向前衝的壓力,哪個更大?
《深海》的A面是一個導演克服重重困難實現長久以來夢想,並推動動畫藝術邁上新台階的勵誌傳奇;B面則有另一片屬於創作者極為私密的心海,其中的心事幽暗綿長,比海更深。
看過電影的人,一定會為片中最後30分鍾顛覆性的情節反轉所驚歎。絢爛色彩之下,包裹著令人心疼與痛心的內核,既是對劇情主題的昇華,亦是對國產動畫敘事邊界的拓展。
電影里的船長南河,拍了一幕動畫在“深海號”上放映,讓參宿在其中看到自己,有驚奇,有刺傷,有治癒。
一個顯而易見的聯想是,那個有著動畫導演技能、會變魔法的小醜船長就是田曉鵬自己,而事實上,那個不快樂的小女孩,同樣也是創作者的投射。
堅持每年“追星星”的田曉鵬鍾愛“參宿四”。作為一顆紅巨星,它是冬季天空中最亮眼的存在之一——因為處於“晚期”,它處於爆發邊緣。影片中的紅衣小女孩參宿同樣是這樣極為不穩定的存在,隨時都可能吞噬自己。
紅外衣是參宿亮麗的盔甲,也是內心隱秘的恐懼和刺痛。比上一次讓孫大聖變成長臉頹廢大叔更大膽的是,《深海》一反國產動畫主角人物“偉光正”“真善美”的傳統設定,塑造了一個“喪眉搭眼”“討好”“晦氣”的女主角。她一面懂事,一面偏執,表面上看起來他經常用微笑來跟別人相處,卻並不是真正的快樂。田曉鵬說,“雖然她是一個小女孩,但是我覺得她的內核,很多性格,我自己特別能感同身受。我特別想講這一類人的遭遇。這也是我想做這個片子的原因。”
 《深海》劇照
《深海》劇照無論是當年“大聖”曆時八年的橫空出世,還是如今《深海》“七年磨一劍”終於夢圓,時光是事後說起顯得很厚重的榮耀加持,但只有真正身處其中的人,才知道那些磨礪真正作用在每一天有多痛苦和黑暗。
《大聖歸來》的成功,也帶來許多動畫之外的非議與挫敗,讓田曉鵬一度陷入抑鬱,加上原本就是個“社恐”的屬性,很長時間,他選擇躲進動畫的世界里閉門不出。而《深海》中那些讓人難忘的絢爛色彩,則來源於田曉鵬看到自閉症兒童的畫作。可以說,《深海》既是故事里無助小女孩不願醒來的一場美夢,也是田曉鵬給自己造的一座“安全屋”,而紮進《深海》的創作,重新找到“微亮瞬間”,也讓田曉鵬找到繼續前進的動力。
動畫是迷人卻艱苦的創造。從做《大聖歸來》開始,田曉鵬就自嘲自己“每天都想放棄,好在有拖延症一直沒實施”;多年之後的《深海》,同樣是一個“每天都在走彎路”“每天都在低穀和振奮間擺盪”的艱辛曆程。
在採訪中,田曉鵬談到,成年人總有正反兩面,“一方面是在逃避現實的參宿,一方面要是每天不得不面對的那些生活的南河。”
《大聖歸來》成功以前,動畫電影是個製作週期長,回報天花板難以突破的“坑”。“投資人連碰都不敢碰”是田曉鵬曾經舉步維艱的困境。而《大聖歸來》打破了國產動畫電影曾經低幼闔家歡受眾的限制,突破了市場票房的天花板,更重要的是,帶動了觀眾和從業者對於國產動畫品質和未來的信心。“國漫崛起”從那時起,真正成為一聲聽得到迴響的口號。
對田曉鵬來說,《大聖歸來》成功的意義,不僅僅是他可以更任性和專注地去實踐自己內心的夢,他更有一份“墊腳石”的使命感,1995年就進入動畫行業的田曉鵬算是這輩動畫人的“大師兄”,他想用自己的創作,為更年輕的動畫人們去蹚一蹚路,“我們來做拓展邊界的的測試,看看動畫能走多遠、走多廣。”
電影上映前,田曉鵬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談到七年來在那片“深海”徜徉曆險的艱辛與昂揚。
 《深海》劇照,深海大飯店
《深海》劇照,深海大飯店【對話】
不是對技術有執念,而是為瞭解決“相信”的問題
澎湃新聞:之前我們看到大多數動畫都是神話IP,一個原創動畫它要克服哪些困難?
田曉鵬:作為一個原創故事,它可能真的是從一開始的開發階段,就不光是故事本身的創造,很多美術的、技術的一些開發都是和故事並行發展的。而這確實會帶來很多的就新的挑戰。對比我自己當時在做“大聖”的時候,很多東西它都是有準備的,是現成的技術和方法,我只是用自己的能力去把它變成一個現實,讓大家能看得到而已。
但《深海》是有一點野心的,是希望做更多的探索和嚐試,不斷地探索出新的邊界。我自己給自己一個小小的使命,是我覺得在大聖之後,我們獲得了一些資本的幫助,也有很多資源的優勢。所以當時就想著我們不要固步自封,還是要拿這些可能比整個行業都要在稍微領先一點的資源,去做一些更探索性的工作。這種探索我相信本身它對於全行業都是有價值的,同時它是有巨大風險和代價的,我們不可能讓年輕人他們去承擔這樣的風險,所以更願意在這兒去多做一些這樣的嚐試。
澎湃新聞:這個野心是指讓大家很驚豔的粒子水墨技術嗎?
田曉鵬:粒子水墨只是其中一項,其實我們在其他的包括流程,包括表演,包括動畫的表現力上都是有所探索的。可能粒子水墨這一項是最明晰,最容易被大家記住的,因為它確實很漂亮,之前見得也不多,但是我們實際上在動畫的其他探索上,甚至是遠遠大於粒子水墨。
 粒子水墨技術
粒子水墨技術澎湃新聞:可以展開說一下其他方面的探索?
田曉鵬:這次其實有一個我自己覺得還比較值得探索的東西是動畫的表演。如果是一個真人電影的話,攝像機去拍的真人演員,機器幾乎可以不動,只要是這個演員他自己有一些很微妙的變化,眼神呼吸,就自然就會跟觀眾之間產生一種情感的張力,因為他是真實存在、有鮮活的生命力的人。但是動畫不是這樣,動畫里所有的人物的一切都是需要創作者去賦予的,所以這樣會先天造成一個問題——但凡是你經過精心設計的東西,就顯得那麼虛假、沒有生命力。
這次我想做的探索就是在表演上如何能夠讓觀眾真實的信服這個世界和人物的存在,甚至可能大家會一直不太理解說為什麼我要把一個人物的毛孔汗毛很多的細節都要做出來,是因為我真的是希望觀眾看到這個電影的時候,覺得這個角色是真實存在的,你會覺得那是一個鮮活的生命體,而不是說我對這項技術本身有多麼執念,說我多麼想把挑戰它的毛髮,挑戰它的皮膚質感,想要跟荷李活的工業水平去比肩。其實我並沒有這種執念,我只是希望從劇情故事或者叫表演的張力層面,讓它更值得信服。這是整個《深海》里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發,但這些看起來非常細微的。
《大聖歸來》的時候很多技術其實還是很表象,它可能什麼都具備了,但是什麼都很粗糙,我希望我現在的作品就是能夠真正的解決“相信”的問題,讓普通觀眾能真實地感受到那種存在。
澎湃新聞:工業流程上呢?經過這些年動畫發展的積累,會比當年“省心”一些嗎?
田曉鵬:如果跟《大聖歸來》比的話,肯定是有質的飛躍,但是我覺得依然是不夠的,遠遠不夠。因為你要做新的東西的時候,永遠會還是那樣的,你在探索邊界的時候,稍微跨出邊界一步,以前的東西就都不適用。不管它發展到了多麼成熟,總要不斷的要去在全新的領域去做探索。就像當時“大聖”的探索一樣,一個未知的領域,難度風險都是相通的。
澎湃新聞:最近《阿凡達2》的熱映也有各種技術科普,都在說做水的特效有多難,放到動畫片里,和這個粒子水墨技術結合,以及和動畫人物的表演,使你們面臨怎樣的挑戰?
田曉鵬:挑戰非常大。我作為導演的要求是我希望這個人物立在這,他的呼吸和週遭環境的互動,都是有生命的,當這個小女孩沉溺在這個海洋世界里的時候,或者說漂浮在海里的時候,你能感覺到海水跟她身體產生了一些碰撞,給她帶來的寒冷、刺痛,或者說她在溺亡的那一刻,她的窒息,這些也是需要觀眾能夠感受到的。如果觀眾不相信這個海水是真實存在的,就沒法去體會她的痛苦。但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訴求,結合流體的特效是非常難的,不光是對我們國內的現有的技術水平,放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巨大的挑戰。我們也為這個問題發愁了很久,也去諮詢了很多國外的一流的特效團隊。各方給出的辦法也都沒有特別的好的很優的解決方案,也無非都是在一遍一遍的去死磕。
表演上,我們是先拍了演員的預演,同時模擬了在水中的他們的表演效果。當然這個東西以我們現在的水平來講,我們不可能真的能做到像荷李活那種那麼真實的模擬,只能有一部分是靠無實物的表演,發揮自己的想像,另外還有很多的找大量的海洋環境的作品作為參考。所以有一種評判標準叫做“看起來真實”,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法做到真的確切的真實。
 《深海》劇照,海獺
《深海》劇照,海獺“美”是為故事服務的,參宿南河是成年人的兩面
澎湃新聞:談談這個故事的創作淵源吧?
田曉鵬:淵源就是來自於我自己喜歡的海洋題材的這類故事,從小因為特別喜歡《海底兩萬里》這本書,所以一直想做一個關於海洋的作品,老實說今天走到今天這一步,其實已經跟我當時的設想有了很大的偏差。
整個《深海》的故事是來自於叫參宿的小女孩。她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所有的東西都來自於她自己的經曆跟現實世界的映射,通過自己的一些幻想,重塑了深海的世界。
澎湃新聞:《深海》對色彩的運用非常突破大膽,令人印象深刻,怎麼會想到這樣的表現方式?
田曉鵬:前幾年買過一幅自閉症兒童的畫作,發現他們運用顏色色彩特別的鮮豔豐富。到我自己在做《深海》的時候,考慮到視覺的設計,從美術上就想做一個不一樣的海洋,它有別於物理世界,更像是可能我們在做夢的時候經常會夢到那些五彩斑斕的東西。我想把這片海做得非常誇張,用極致的色彩加以表現。這既是展現不一樣的美術風格的這層的執念,也是希望五彩斑斕的幻想世界是有別於現實間的灰,希望造成一個很強烈的反差。
澎湃新聞:從第一次《薑子牙》貼片預告亮相開始,大家對這部片子最直觀的反饋就是“美”。這次在“美”這件事上花大力氣追求,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田曉鵬:首先我覺得我們不能迴避“美”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一個動畫片,如果它只講劇情講邏輯,而不講外在的美術設計,那我為什麼要去做動畫,我只要去拍實拍就好了,動畫片的美學,有它自己的獨特性和使命。
另外就我們的故事和表達本身來說,對這種“美”的追求是不能脫離表達和故事,其實還是是為故事服務的。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很普通的小女孩,在現實的世界裡面沒有那麼被重視,她的心情是很灰色的,看待世界也變成灰色的。於是在塑造這個世界的時候,她就極力用自己的這種想像力,在塑造了一個極致的五彩斑斕或者極致美的世界。
整個片子的這種美,恰恰是為了讓觀眾相信這個世界是她塑造的,是她想要去沉溺的世界,她用這種美好的想像去逃避現實。當這個世界崩塌的時候,伸手去抓去挽留這些美的東西的時候,觀眾才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種痛,才能知道她為什麼長久以來不願意醒,一定要沉溺在這個世界里。我們希望觀眾能產生那種共情是,如果是我,也想在這個美麗的世界,也不想醒過來,不想去面對灰色世界里的現實。我覺得如果有這一刻的感受,這種美的設計它就是成立的和成功的。
澎湃新聞:確實也能在觀影中感受到這種共情,同時也很意外這個劇情的走向。所以《深海》裡面小女孩的內心世界,是否有一些您自己內心投射的部分?
田曉鵬:對,這點是非常強烈。而且我覺得可能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時刻。有時候我在形容我們片子裡的小女孩和男主角南河的時候,覺得他們更多的像我們成年人的正反兩面,一方面是在逃避現實的參宿,一方面要是每天都要去給自己打氣,又不得不面對的那些生活的南河。我相信大家能感同身受。
 《深海》劇照,海上日落
《深海》劇照,海上日落一群人的探索,為中國動畫的未來“探路”
澎湃新聞:整個過程曆時這麼久,中間有哪些“彎路”,回頭想最低穀和令人振奮的時刻分別是什麼?
田曉鵬:彎路基本上是天天都在走的。每天都在低穀和振奮中來回激盪。這個也是這個片子很有意思的一點,每天去的時候可能都是帶著解決問題,解決一些可能會相當絕望的問題。
你如果問我振奮的點,我覺得不是解決了某項具體的技術難題或者實現了某個具體的場景,而是我看到一群人的改變。
在《深海》頭幾年的時候,包括我們的製作人員在內,很多人經常會說一個問題,好像“不知道導演要什麼”,但這恰恰是我的一種創作方式。我是希望我們整個團隊能在《深海》里完成一種探索,不光是我一個人的探索,我在用一種方式在激發我團隊的這些動畫師的潛能,希望他們帶著自己的東西加入這個旅程。如果我只說我想要什麼,可能最後真正做出來的也未必是我想要的,而當大家都是激發自己的想像力、創造力,放開手腳去做一個東西的時候,結果往往水到渠成。所以《深海》帶給團隊的成長到後期不光是來自於技術的,有很多是在於對整個動畫藝術層面認知的提升。
澎湃新聞:《深海》耗時這麼久,有哪些曾經的限制是因為《大聖》的成功,得以帶來助力和突破的?
田曉鵬:我覺得可能是“相信”。這個答案說起來挺虛的,但是我認為對我很重要,就是團隊對我的信任,包括投資人對我的信任。因為有《大聖歸來》,他們相信我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可能並不是為了自己一廂情願的喜好,他們是相信我最終所表現出來的這個東西的,會是有力量有情感的一部作品,所以他們願意去陪伴我。但是在《大聖》的時候,這種相信是沒有的,無論是團隊之間的信任,或者對我個人的信任,都沒有像今天這樣,大家願意花這麼久,去做這些很任性的研發。在那些很漫長的或者自己很黑暗的時刻,大家依然會相信這是一個好東西,願意去陪伴我把它做出來。
澎湃新聞:狀態上來說,之前做《大聖》遇到撤資,投資方不信任你;和《大聖》成功後,很多人信任你,跟著你熬,哪種對你來說壓力更大?怎麼化解這種壓力?
田曉鵬:不知道哪個更大,但是體驗確實是不一樣。怎麼化解,這個我沒法回答,其實就是強撐,我到現在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我知道大家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因為這是我們喜歡的,是我們的動力來源,我們就去努力地做,但是我真的沒法去排解這個東西,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我也不知道我這樣做是不是對的。我確實有很大的壓力,覺得團隊跟了我這麼多年,他們走過很多的彎路,在這個過程中受了太多的委屈,吃太多的苦。我可能自己還好樂得其中,但是其他的人這些東西我是沒有辦法去幫他們去解決的,這個東西可能會背負很久。也許有朝一日有一個好的結果的時候,可能才能覺得對大家都有所回饋,但是今天此刻,真的不知道。
澎湃新聞:第一次在彩條屋“宣講”《深海》這個項目的時候,當時《大魚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還沒問世,你說你看到其他導演們都在“往前跑”,很振奮,這些年大家也合力把中國的動畫電影帶上一個新台階。想知道你作為“大師兄”,怎麼看你們這一代動畫人?
田曉鵬: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動畫人其實到目前今天來講還是“墊腳石”,可能我們“這一代”不太嚴謹。他們比我更年輕一點,但像當年我自己做的預判,我覺得應該今年是準的。那些年輕的導演,和更多更有才華的年輕人會不斷的湧現出來,未來也是這樣的,因為我又看到了大量的這樣的人才存在。我們這一波或者叫這一代,其實更多的是鋪墊的作用。
中國的動畫曾經輝煌過,特別輝煌過,然後又經曆了低穀,這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認為靠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我們的創造力、我們的美學審美,自己的處世哲學和思維方式,一定會創造輝煌。可能我們做的事情只能是鋪墊,因為動畫真的非常依賴於基礎才能打造。
 《深海》劇照,蝠鱝
《深海》劇照,蝠鱝澎湃新聞:我們之前採訪很多動畫導演,都提到《大聖歸來》當年的成功是他們面對國漫未來的一劑強心針。所以你自己怎麼看待曾經的“成功”對後來的動畫電影是什麼樣的意義的存在?
田曉鵬: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告訴年輕一代,動畫其實是有很多可能的,不要去懼怕動畫存在的這些所謂的技術壁壘或者其他的東西,他們只需要思考自己怎麼樣去探索,做好自己的表達就可以了。我們來做做拓展邊界的的測試,看看動畫能走多遠,能走多廣。
澎湃新聞:近年來其實大量的國產動畫都是有著東方文化背景的,也都會選擇以水墨意境來做美術上的表現,這次深海研發的粒子水墨技術未來會在其他作品里獲得進一步廣闊運用的空間嗎?還是它也會存在一些技術壁壘或者門檻?
田曉鵬:我覺得不會有技術壁壘,因為首先這個技術並沒有那麼難,它真正的難點不在於這個技術本身,而是在於你一開始選擇運用的時候。其實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很大的工作量,這會存在不確定和危險。而《深海》做的探索其實是告訴大家,這條路是可以走的。
當然未來如果有其他的作品,他們需要用這套技術的時候,我說需要並不是說從商業的考慮,而是說從自身的表達或者劇情上,覺得這項技術能夠帶來對錶達的支持,我覺得它是開放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而且我們自己的團隊其實曆來在做的事情,都沒有什麼是神秘的,它都是對外開放的,我們探索的價值就是可以給未來的人去利用。
澎湃新聞:前些年發佈的你擔任導演的作品還有《大聖鬧天宮》和《三體》,按照過去兩部電影的這種死磕節奏,其他的作品觀眾會不會還要等好久?
田曉鵬:得看,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特別想去“死磕”下一個作品。我需要找到下一個作品的興奮點,如果它真的是足夠讓我覺得去“死磕”很多年,我可能還會這麼做,不是的話,我可能會放過自己,讓自己輕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