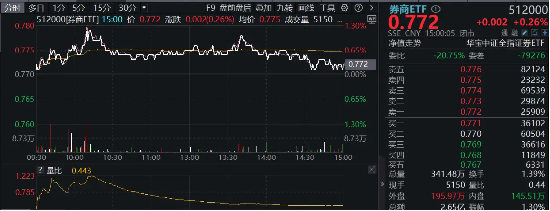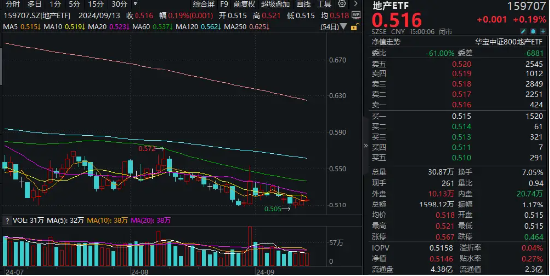新民藝評丨《無名》:他們曾來過
轉自:新民晚報
記得電影上映前,影片出品人及總製片人於東提到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紀念碑上,刻有這樣一段碑文:“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勳永垂不朽。”《無名》的片名由此而來。有趣的是相比電影里,唯一有完整名字的是一條叫“羅斯福”的狗——幾乎所有人,頂著姓氏、家庭關係、工作職位的名義,“無名”著——“無名”在這個層面上除了是片名,更像對影片最精闢的概述,展現了影片所折射曆史的某些特性:
拯救者是無名的——他們是隱姓埋名的英雄,
受害者是無名的——他們是暮鼓晨鍾的凡人,
施暴者是無名的——他們是雙手沾血的兇手,
騎牆者是無名的——他們是厚顏無恥的賭徒,
背叛者是無名的——他們是首鼠兩端的懦夫。
至於影片里,人物有“(姓)名”與否,並不會影響觀眾的觀看——這像極了一個精妙的中國文化觀念比喻:“名”終究是“虛”,“人”與“名”相比略微“實”一些——但終究是虛妄的。

影片里梁朝偉在漢奸汪精衛的畫像前,有一段關於什麼“痛快”的台詞。不免令人想到曆史上,這個漢奸曾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少年時光。當他丟失了捨生取義的信念,看似多享了幾年榮華,但本質與廣州轟炸時,那條被呼來喝去,跑進風雨討一口乾糧的喪家之犬別無二致。至於瓦礫上的死亡是它生命曆程的必然,也是錯誤選擇的終點——至於那條“有名”的“羅斯福”又怎樣?皇家空軍又怎樣?貴族苗裔又怎樣?
《好了歌》開頭四句寫:“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在曆史綿長悠遠的中國文化中,其實並不奉行如今網上盛行的“生死之外皆小事”論調,因為古人很早就明白:一個人哪怕位高如皇帝也是要死的。但我們的古人在先秦時,發現了人生的“無意義”後,找出了具有中華民族個性的“生命存在意義”:因此,魚與熊掌的故事里,孟子引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的道理。自此,每一代華夏義士為我們的文化留下了諸多捨生取義、慷慨豪邁之歌。

如果說《無名》的電影感,來自他精準地展示場面,手藝人似謹慎地用鏡頭遣詞造句;如果說《無名》的尖銳感,來自他克製地描寫殘酷,不給某些意圖展現人性光輝而胡編亂造的“懺悔者”形象留有空隙;那麼,《無名》的力量感,來自他耐心地刻畫時代,像綿綿的拳影在結尾彙成重重的一拳叩擊觀眾的心靈,讓人在走出影院回想的時候,也許會自發意識到一個問題:影片中地下工作者們和曆史上千千萬萬為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而獻身的仁人誌士們為什麼甘願“無名”?
如果從影片誕生的這片土壤來看,問題的答案本是天成:因為他們身上流淌著中華文化的血液,所以正面人物的行動動機,不是由西方編劇教材中常見的“個人性格”“原生家庭創傷”“家庭親情紐帶”等個人主義情結推動。相反,片中人物自覺而堅定的反抗,是作為一個覺醒的中國人,看到廣州遭受轟炸滿目瘡痍的痛心疾首,聽到日本人姦殺一家四口人的義憤填膺,認清蔣氏地方政權與汪氏賣國政權本質後自己扛起重整山河的使命擔當。

影片對於日寇暴行的揭露,殘酷且直接,讓人想到《黑太陽731》、《紫日》、《紅櫻桃》等諸多“童年陰影”——只是各地史書上的滄海一粟。於是在《無名》中,出現了程耳導演提及,純屬“計劃之外”的白色小羊。日寇在用水泥虐殺小鎮村民那場戲的最後,鏡頭裡,前一秒活人,後一秒水泥活埋;前一秒活羊,後一秒燉羊湯的對比,將戰爭時期,暴虐的日寇群體與孱弱的國民群體間的關係勾勒得通俗易懂——《伊索寓言》里,狼吃羊的理由有許多,最後也可以不需要理由。戰爭讓那群圍坐吃飯的無名兇手們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吃羊”,那種喜悅興奮的狀態也許比常見的“懺悔”者更能客觀上解釋為什麼能在1931年到1945年間,在我們這片大陸上出現源源不斷的人間慘劇,也解答了那群無名者,所求者何!
曆史上,他們來過,為了中華民族捨生取義。在21世紀20年代,能有這樣一部質感的電影,緬懷來過的他們,實乃開篇所謂觀眾之幸也。(孟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