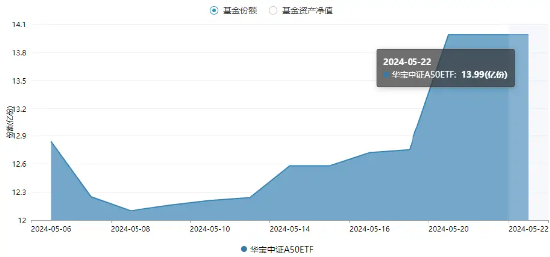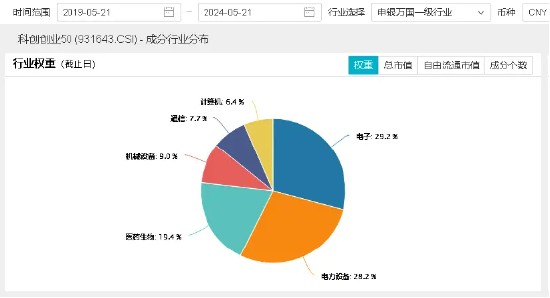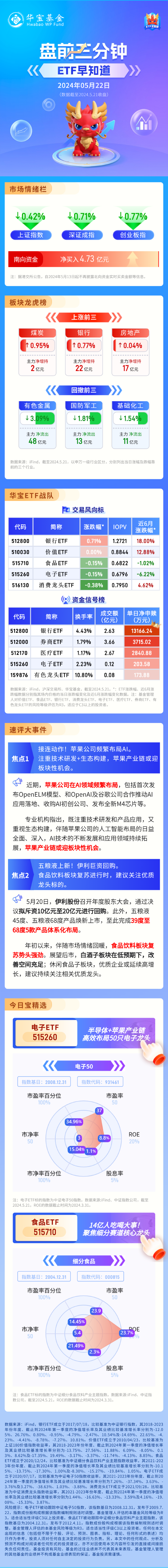專訪|導演翁子光:拍《風再起時》是義無反顧的冒險
2016年,一部《踏血尋梅》幾乎橫掃第五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和最佳攝影從故事和技術上充分肯定了電影的表達,最佳男女主、最佳男女配、最佳新演員等表演獎項大滿貫,更是金像獎史上罕見。這部當年被影評人譽為香港本土最佳犯罪題材的佳作,因為暴力的影像內容和深刻的人文關懷,成為很長一段時間港人熱議的對象,導演翁子光也因此驚豔影壇。電影所呈現的那種令人後脊發涼的銳利,和準確命中演員最佳打開方式的才華,都令人過目難忘。
於是,曾經遍尋不得投資一度抑鬱的年輕導演,再轉下一部電影時,擁有了操盤和建立一個更宏大世界的機會。

翁子光《踏血尋梅》獲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
2023年2月5日,翁子光的新片《風再起時》上映。影片創作曆時6年,促成了郭富城、梁朝偉兩大影帝的首次合作,許冠文、譚耀文、金燕玲、謝君豪等老牌港星的加盟,也為影片的“港味”加足了料。
《風再起時》是翁子光寫給香港的一封洋洋灑灑的情書。影片以英政府殖民下的香港為背景,講述了上世紀40-70年代,磊樂(郭富城 飾)與南江(梁朝偉 飾)加入警隊,聯手打拚上位,叱吒香港黑白兩道,最後在時代浪潮下,過往輝煌皆隨風飄散的香港往事。
 “四大探長”
“四大探長”曾被無數次講述的梟雄故事裹上曆史的塵埃,舊日時光殘忍激盪的風雨雲都終化作一場風流夢。
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香港華人地位低下,備受欺辱。到1941年日軍入侵,香港淪陷,這個城市又經過飽經摧殘蹂躪的三年。日本投降後至1960年代,在華探長與黑道、洋警司的相互勾結下,香港警隊貪腐風氣肆虐橫行。以呂樂為首的四位華人探長建立維繫香港警界的貪汙制度,權傾黑白兩道,逐步攀至警察系統的最高職務,成就“四大探長”的梟雄傳奇。直到1974年港督麥理浩設置廉政公署緝捕四大總華探長,那個黑白不分、腐敗叢生的時代才徹底畫上句號。
這是香港苦難的曆史,而宏大的時代沉浮下,是一個個鮮活的血肉之軀,和由此組成的一段段傳奇。
上世紀90年代起,香港誕生了一系列梟雄電影,包括《跛豪》《五億探長雷洛傳》《四大探長》以及近些年觀眾熟悉的《追龍》系列等。基於曆史原型人物和民間的市井傳聞,梟雄片中講述的小人物在亂世中改變命運的發跡故事,再現了五六十年代獨特的香港曆史記憶。
兒時的翁子光常聽奶奶和長輩們講曾經探長們的傳奇故事,被那個年代的老香港所深深吸引。他的迷影情懷發源於此,有朝一日能拍一個屬於他的“四大探長”的故事,也成為了翁子光小時候的夢。
 兒時的翁子光與奶奶
兒時的翁子光與奶奶但當這個夢真的付諸實踐,有太多難以割捨的情感和超過一部常規電影體量所能承載的野心,讓這場“夢”有些“力不從心”。橫跨30年的情節原本就將劇本撐得滿滿噹噹,加上好演員們融入戲中導演不自覺的“添磚加瓦”,不斷豐富和飽滿的細節,讓這個80天拍完的電影初剪版本達到6個小時之久,從五個小時、三小時四十五分鍾,再到最終上映的143分鍾,《風再起時》在過去幾年屢屢出現在許多媒體和影評人的年度期待片單上,又遲遲難見真容。
“千呼萬喚始出來”,曾經承載多少期待,如今也就承受著重大的非議。豆瓣評分6.4(截至上映第五天),討論區許多觀眾高呼“不建議觀看”,社交網絡上的負面評價甚至讓導演感到“去到了‘侮辱’的階段”。
2月6日,影片上映次日,翁子光在微博發佈動態“我和我的《風再起時》”回應觀眾評價,對各方的包容、支持與付出表示感謝,並遺憾奶奶曾經與兒時的自己分享這些“美好與辛酸”的故事,但當他終於把這些夢還原在電影里,現在卻來不及在她在世時,與她一同坐在影院里分享那段舊時光。
 翁子光與奶奶和弟弟
翁子光與奶奶和弟弟翁子光知道大家因為《踏血尋梅》而對《風再起時》充滿期待。面對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的觀眾對影片接受程度的分歧,他承認自己拍攝《風再起時》的“任性”,也在這個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生階段充分共情了電影里人物的“無力感”;他在微博中回應並“背鍋”觀眾的每一點質疑,也抱歉無法左右宣傳對於“動作猛片”招攬顧客的無奈……但“電影里經營的愉悅和痛,對香港情懷的真誠致意,都是存在的”。翁子光稱《風再起時》是“從拍攝到後期,都耗盡我身心之力”的電影,拍攝這部電影付出的心血,大概足以拍十部《踏血尋梅》。
截至記者發稿,《風再起時》的排片率已跌至3.4%,票房3800萬元。這部港片中的大製作,市場表現尚不如人意。梁朝偉安慰翁子光“所有的電影都是一場實驗”,翁子光也知道自己義無反顧的原因,“香港需要一部能溫故知新的電影”。事實上,無論是今年代表香港地區“出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或是目前拿到亞洲電影大獎的多項提名,都多少說明這部電影在藝術上擁有屬於自己的質感。
電影上映當天,翁子光接受了澎湃記者新聞專訪,談及他對香港的深情回望,埋藏在光影里的良苦用心,也回應了如今關於電影的爭議。那些要冒的風險,他早有準備。而電影里呈現的種種,就是他的初心和選擇。
 《風再起時》拍攝現場
《風再起時》拍攝現場【對話】
傳奇人物是代表香港精神的符號
澎湃新聞:“四大探長”的故事被多次拍成電影,為什麼一代又一代香港電影人對他們的故事情有獨鍾?《風再起時》是怎麼樣去找新意的?
翁子光:我覺得那個貪腐氾濫,黑白兩道互相打眼色的年代,的確是一種很有故事感的氛圍,就像說上海電影總是會講到杜月笙一樣,這是城市裡面的記號標籤。這幾個人是有代表性的,代表著香港那個年代的向上爬、利字當頭這些精神面貌,故事里的價值觀牽涉到香港的五六十年代迅速起飛的那種節奏。當然,這些人物和故事框架很容易在拍攝的時候融入動作場面、黑幫片元素,成為特定類型電影的舞台。對我來說,是在用它緬懷香港電影曾經帶給我們的回憶。
但《風再起時》想拍的主題一直是香港,而不是四大探長。這個主題是比一些同類型的電影更大的。梁朝偉、郭富城、許冠文等人,每一個角色都是代表香港的某一種精神。拍電影的時候,我會希望自己有一種使命感,真誠實意地希望觀眾看完電影,對香港有一種精神上比較深入一點的瞭解,認識一下香港是怎麼一步步走來的。
 郭富城、梁朝偉
郭富城、梁朝偉澎湃新聞:為什麼是這些人物代表香港?他們承載了什麼樣的香港精神?
翁子光:這些探長的故事是我小時候的夢。以前的《雷洛傳》《跛豪》等等,我對電影的感覺就來自童年的觀影回憶,我的迷影情懷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我想著長大之後我也要拍一部“雷洛傳”,拍一部“藍剛傳”,都是我為兒時的自己圓夢的電影。
但到後來要做這部電影,實現我的夢的時候,我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人,我會意識到“四大探長”是一個比較符號的東西,它沒有一個實際具體的曆史上對他們的記載。這些符號是讓觀眾比較容易進入那個時代的一個標識。
這裏是一種借代關係,包括人物命運和情感流動,包括他們對自己的往事和罪惡,曾經模糊的記憶,怎樣變成了現在的自己這些命題,來表達這個城市的一種精神屬性。比方說,六七十年代的很多人會說自己是白手起家、目不識丁的,他們會覺得自己創造了很多東西,把自己從一個小人物最後打造成了一個大英雄、大人物。
郭富城飾演的磊樂,身上有很多那種上輩人的影子,那個時代的人都是這麼一路過來的。他們有香港往上爬的精神、非常強的適應力、當機立斷、有手腕的,他們很有魅力、領袖風采,有他們的那股氣。我小時候一直在香港,看到很多這種人,特別是我進入到電影圈,很多大老闆,或者各種商業名人,我覺得他們都有這口氣,也是某一種江湖氣。
 郭富城 飾 磊樂
郭富城 飾 磊樂另一方面,因為香港那時候處在文化上的特殊節點。在全亞洲地區來說,香港早期就有相對比較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從外到內,默默地為香港做出很大的貢獻。開始的時候,是貢獻他們的專業,比方說香港很多建築師、醫生、律師等比較精英級別的紳士、公務員,這些人貢獻了他們的智慧、學養和能力。這就是梁朝偉飾演的南江,像一位紳士,但不是特別謙虛,而是冷板式的,又比較能站出來的。他們先從實際層面去建構香港,而後變成了從精神層面去支撐香港,他們會提出很多對香港有益的原則性的東西。香港就是由磊樂、南江這兩種具有典型人物品格的人建立起來的。
 梁朝偉 飾 南江
梁朝偉 飾 南江許冠文(飾演的李子超)則是站在更高的視點,他是一個用來製衡的正義力量。在出現問題的時候,一些真心實意愛香港的人,會在每一個年代的亂局中給出一個說法。在電影中,這是一個比較虛構的人物,我們需要這種能量去為時代的紛亂定一個性。
 許冠文 飾 李子超
許冠文 飾 李子超澎湃新聞:你之前的電影都是關注社會的現實主義題材,這次回過頭去拍一段曆史的時候,如何發掘其中的當代性?
翁子光:我希望電影是有一種“當代性”的,可以通過電影溫故知新,重新認識香港這個地方。我覺得《風再起時》是讓所有人看清楚香港這些地方的來由,它的精神面到底是有哪些?是比較具體的,會引發你去想的,哪怕我講得不完全,不那麼準確,因為香港數個時代的跨度太龐大了,但我會讓大家從我提出的幾個角度去看香港這座城市。
拍的時候很任性,剪的時候保演員
澎湃新聞:《風再起時》從體量上來說是部“史詩”了,橫跨三四十年的長度,聽說第一版剪輯出來有6個小時,到最終的140多分鍾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翁子光:劇本剛開始拍時已經是8萬字了,當時即便是按照本來的劇本來拍的話,也會是三個小時。演員來了之後,他們的表演狀態比我想像中有意思很多,所以我們的確在拍攝過程中不斷去調整劇本,給演員更多想像和表演空間讓他們發揮。很多戲都是在這個過程里加出來的,甚至是與演員共同創作的。
說實話,我們在剪輯的過程裡面是很痛苦的,我的壓力很大程度上面都是來源於時長的,我們當時想能不能做成上下兩部上映。最近,我跟剪輯師說,如果是三個小時的話,哪怕我們都是同樣的場景,最終效果都會更舒展,有一個更穩定的表現。
澎湃新聞:你覺得現在的敘事是過於倉促的嗎?
翁子光:現在整個節奏非常緊,甚至是擠的效果,但我覺得,也算一種沒有出現過的帶有實驗性的樣貌,也未嚐不可,因為我想讓觀眾感覺到,這就像是兩位探長的一場夢。也有觀眾和我講,經過前面的混亂和擁擠,但到後面靜下來時會回味前面的東西。我覺得人生真的有這樣的一種滋味,很多錯綜複雜的東西讓你應接不暇,讓你覺得突然發生了無數人來人往的場景,但到你老了,安靜下來的時候再回看,就會有那種很奇怪的滋味,會有點懷念當時那種喧鬧。
 《風再起時》劇照
《風再起時》劇照澎湃新聞:這個故事脈絡天然帶著警匪、犯罪、黑幫的背景,觀眾自然會抱著對類型的期待進入影院,從現在的結果來看,確實有一部分觀眾感受到了被“冒犯”,你覺得這是一部有欣賞“門檻”的影片嗎?
翁子光:其實是存在一個觀影習慣上的挑戰。因為還是有一些框架性的感情表達,有時我們故意不走向一個細節,或者是我們偶然給出一兩個細節,它已經很有代表性,我們就不會更多去講。電影在講人情世故,甚至是婚姻觀、愛情觀、親情、友情等,都會在裡面有觸碰到。兩個角色的決定與選擇,如何去表現自我的過程。我採用一種像寓言故事的方式,觀眾看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滋味和感受。
這與一般的戲劇會有不同,它雖然快,但反而更需要用心看。很多人看的時候就會覺得會脫線,因為沒有向觀眾明確要從哪個方向進入這部電影,從什麼軌道走完這部電影,這對觀眾的觀影習慣來說是一項挑戰。我也用了很多好的音樂和光影,以一種“純電影”的方式吸引包圍觀眾,“哄”著他們把電影看完。我也希望它能留給後人一些回憶,是帶回家可以收藏的。節奏也好,技巧也罷,實際上都包含了一些實驗特質,是我真心實意地在過程里不斷嚐試和體驗中呈現出來的。但這還是一個實驗,有得就有失,有些觀眾可能在觀影時難以投入。但一旦投入,便會呈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觀影體驗。
澎湃新聞:拍的時候就知道這是“冒險”的吧?
翁子光:大家知道我做這個電影做了幾年,花了很多的精力,真的是全力一搏,也知道《踏血尋梅》之後,大家對我有很大的期望。如果我再拍一個犯罪片,或者拍一個比較簡單的家長裡短的當代故事,可能會輕鬆很多,但是我還是願意走出這麼一步,因為我覺得,香港電影需要這麼一部溫故知新的電影。香港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的講述自己城市曆史的電影了。從整個拍攝到後期的壓力,對我來說像拍了十部《踏血尋梅》,儘管很有挑戰性、爭議性,但我還是把它做出來了。
澎湃新聞:因為電影里都是非常好的演員,所以也好奇那些在拍攝過程中中途不斷加出來的部分,具體是一些怎樣的火花?
翁子光:比如南江的往事,講南江和父親跟日本人的特殊關係,以及後來他在回憶片段裡面講了很多他的感受。這個部分是梁朝偉有一天跟我講他家裡面的一些事情,他自己對人生的一些感覺的時候,創作出來的。後來他形容我寫出了一種創傷後遺症的感覺,南江和磊樂都有,他是這麼總結我的創作脈絡。我覺得情感的東西或許不只是在電影中,也有可能是梁朝偉本人他對家裡人的那種比較複雜的羈絆。我最近也幫他拍了一部紀錄片,有講到這些故事。
另一個是許冠文,在跟外國人在開會的戲里講我們應該怎麼對待香港。劇本本來是很完整很長的對白,但是當我們換成英語之後,他改了對白,用他認為更順暢的口語的表達和講話習慣去說。後來他就跟我講,他講這些話不是這個角色要講,而是他本人要講,變得好像這並不是一個表演,而是他的演講。到底什麼人關心這座城市?很多香港本土的人都是一種很漂泊的感覺,大家要怎麼去面對這座城市的命運?很多東西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還有一個是杜鵑的上海話。在劇本創作時並沒有想到這個角色的身份,而見到杜鵑之後,我們就決定這個角色要是上海人。其中有一段關於高跟鞋的對白,也是在跟她聊天的時候產生的靈感,她那麼高的一個人都還要穿高跟鞋的情感,也是她給了我很多的靈感用這個方法來展現這個人物的背景和情緒。
 杜鵑 飾 蔡真
杜鵑 飾 蔡真澎湃新聞:上一次《踏血尋梅》拿了好幾個表演獎,這次包括郭富城在內的二次合作的演員,帶來哪些特別的感受?
翁子光:我合作過的演員,他們會讓我很放鬆。比方說郭富城、金燕玲、太保、白只等,我們合作過都很熟悉,他們來了就好像是家裡人來了,大家都知道要做什麼,有一個默契在,對我都非常的信任。我只是給他們一個很小的點或者感覺,哪怕是有點功能性的,但他們一出來就可以感覺得到這些角色性格是怎麼樣的,是什麼類型的人,又有怎樣的角色魅力?他都是自帶的。因為我對他們很熟,他們怎麼去把握鏡頭,表現他們的特質,我是手到擒來的。
也有一些不熟的演員,我們是第一次合作,我也很感謝他們的信任,我跟演員的溝通還是比較舒服,比較有把握的,我覺得這算是我的強項。比如謝君豪、張繼聰、周文健、張可頤等等。這些新合作的演員來了,對我還是很信任的,說實話他們戲份也不是特別多,但他們會很放心地交給我。我把他們的某種特質放進電影裡面,就好像用電影介紹了這些演員。雖然電影里是介紹在那個年代有這麼一個人,但在銀幕之外,我在向大家介紹我們香港有這麼一位演員。我覺得這種東西是鮮活的。大家在看到這部電影之後,很多人再看到哪一個配角會讓大家想起來,一方面是想起了香港電影有這些美好的回憶,另外一方面就會覺得這些人,這些面相還是挺帶感的,是有他們的味道在的,將來有可能在其他的電影里他們也會有更多更好的發揮。
澎湃新聞:當不斷加入新的東西進來,原來的體量又已經“超綱”,取捨的時候怎麼衡量?
翁子光:很多人對《風再起時》會有不同的評價,但是對演員還是非常肯定的,是因為他們發現我一直都是給演員的空間,無論我怎麼拍怎麼剪,怎麼呈現一個世界觀,一個故事走向,我都是“保演員”的。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得出來,我始終堅持,演員才是在我們這部電影里站在最前方,讓觀眾第一個看到的,因為他們是觀眾情感流動的代言。
把“導演”的位置放得很低,拍電影共情人物的“無力感”
澎湃新聞:電影里的大事件都被剪得很碎或隱晦,但感情線卻保留得很完整,甚至直白,於是很多人覺得這是個三角戀的故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取捨?
翁子光:我是個很想去做些不一樣的東西的人,但是同時我也是一個很傳統的人。我放鏡頭的機位,很多都是很典型很經典的方法。我有迷影情懷,一些對老電影的記憶,我真的會“毫無節操”地把這些東西都放進去。三角戀就是一個典型的經典人物關係的模型,我也需要有這種情感關係支撐起電影。
杜可風拍《踏血尋梅》時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這地球上所有電影都是愛情電影。我覺得這話很扯,但後來我又發現他說得非常對。其實不是愛情電影,是用愛情的思維,用一些包含的荷爾蒙、有生命力的東西,吸引觀眾理解和感受。這就是他所謂的“愛情電影”,你看王家衛所有電影都是愛情電影,包括《一代宗師》最後也變成愛情。
我受這些電影影響挺深的。但我比較笨,並不如很多導演有才華,我還是回到最為原始的愛情,甚至它和香港的關係是一種寓言性的——兩個男人對一個女人不同的愛情姿態,或是曖昧或是直接,各種微妙的態度,也是一個寓意,香港人是怎樣看香港的,怎樣去看自己喜愛的東西。包括磊樂和小愉、蔡真和小燕的感情里,有愛與恨的糾葛,是在愛里包含著愧疚、或是責任感,也可能包含了一個謊言。它不只是在講愛情,更深層次上也是跟城市跟時代裡面人的處境的關係,我們能看到很多人在面對自己的命運時會有不同態度,希望有人閱讀出不同的味道。
澎湃新聞:前面也講到你的迷影情懷,很多影迷也能在《風再起時》裡面看到很多致敬經典的戲仿段落,在創作這樣一部“香港往事”時,受到哪些經典的影響?
翁子光:《美國往事》是絕對有的。比如片中抽大煙形象的那種感覺,還有磊樂在雨中跳舞時,他把傘給了一位小孩,小男孩的服裝和羅伯特·德尼羅在《美國往事》里童年的形像是一模一樣的。還有一些鏡頭的處理和細節的設計,包括槍戰的音樂,我都在向我從小到大看過的喜歡的電影致敬。很多人都覺得導演這真的是太放肆了,任性地放了很多這類東西進去。但也有一些很影迷的朋友,他們的興奮點正在於此,會覺得我給他們分享我喜歡的電影,可能看到會很有共鳴,這是一種情懷的東西。我覺得這種放任我是義無反顧且沒有罪惡感的,因為我投入了很大的心力。
澎湃新聞:之前你做過和電影相關的各種工作,在做《風再起時》的導演時會有一些特別的工作習慣和方式嗎?
翁子光:會有,對我來說這個挑戰是很大的。我之前是以編劇為主的導演,但拍《風再起時》的時候,重心還是放在導演的工作上。我還是注意協調好每個部門,將每一個部門的能量提升到一個比較高的點,比如美術、服裝、攝影、音樂等。我把能表現我電影能量的部門都提升到一個最大、最高亢的表達空間,他們也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還是對這些部門有很大的一個敬意的。特別是丁可的音樂,我相信這應該是過去兩三年最好的音樂原聲。他的音樂本來是比較慢的,但是他去法國找了一個團隊研究歌舞片的音樂風格。另外在一些美術方面也有突破。
我一貫把導演的位置放得很低,雖然這次我做了很多導演的工作,但是我依舊是一樣的態度。就好像《踏血尋梅》,大家會加很多標籤給它,比方說是表演的勝利、劇本的勝利,但說實話,它不是一個導演的勝利,到現在我沒有贏過任何一些較大的導演獎項。我自己也會扛機器去拍一些鏡頭,因為我怕攝影有時候會沒有辦法抓得住演員的表演,我就立刻去追。有時候我也會去看這些美術的東西,有些細節的東西說了半天,我還不如自己就把它給管了。這可能是因為我很早的時候就從副導演開始過來的,所以在工作上比較有親力親為的習慣。
澎湃新聞:電影里很多人物在時代的浪潮裡面浮沉,在現實中你對“不可抗力”和“無力感”的體會是怎樣的?
翁子光: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在拍攝過程中,我就強烈地感受到角色這種無力感,因為我之前拍的比如《踏血尋梅》,或者是我前年監製的《正義迴廊》,包括我自己更早的兩部電影,都是在講人在小場景中,小命運的波瀾下是如何去闖過去的。但《風再起時》這個感覺就更大了,當你面對的是一個時代的時候,如何去擺自己的位置,到最後還是一種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是非常文學的。
但也可能我是一個剛剛成熟的人,對這些東西的感觸會特別深,也許比我年長的人會覺得這沒什麼,比我年輕的人也不會懂。原來很多人告訴我,每個時代都是這樣,很多東西都在隨浪潮變化,但是我覺得我到了感受最深的人生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