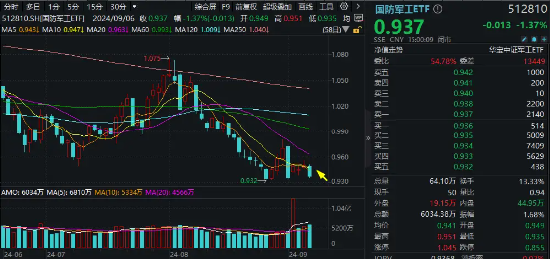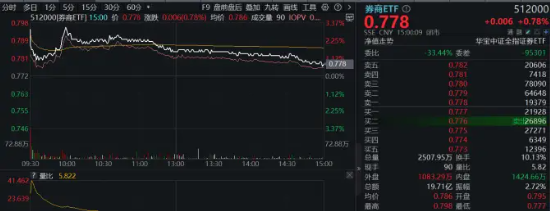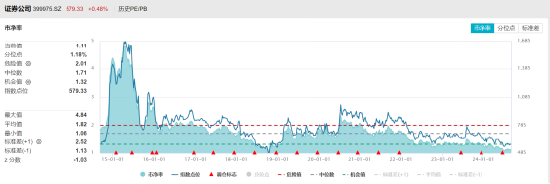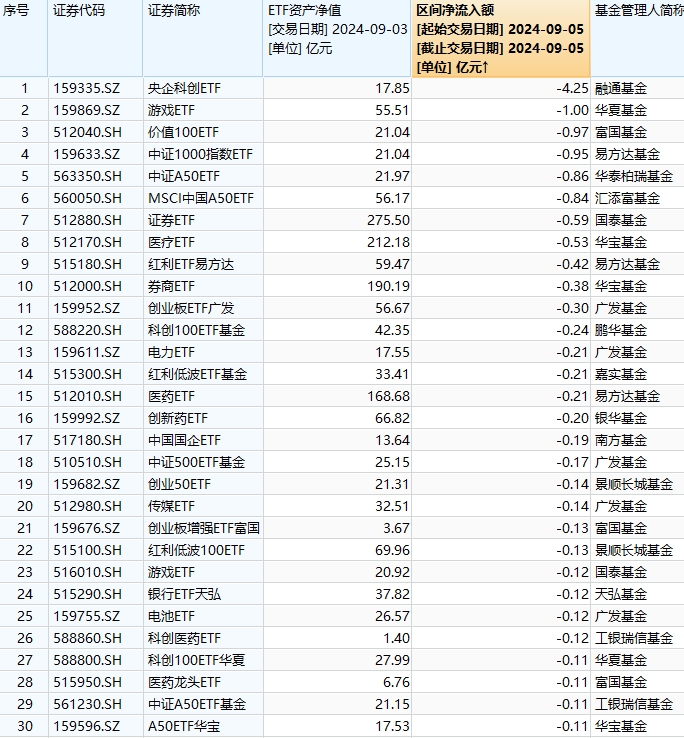上野千鶴子:“活下去”,不只是生存|書評
《為了活下去的思想》是日本知名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學術論文集。
在書中,上野千鶴子圍繞國家、暴力、性別等議題進行思考。從本世紀初的9·11事件開始,追溯到上世紀的沖繩島戰役以及之後爆發的海灣戰爭……統攝這一系列問題的關鍵線索,便是這位女性主義者一貫的主張:“女性主義是讓弱者以弱者的姿態受到尊重的思想。”選擇成為“弱者”,也意味著主動選擇不去濫用權力,並將“活下去”確立為一種雖沉默卻有綿綿力量的價值。

電影《小早川家之秋》劇照。

《為了活下去的思想》,(日)上野千鶴子著,鄒韻 薛梅譯,明室Lucida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年12月。
貫穿全書的問題線索
一直知道上野千鶴子這位學者,也聽過她在東京大學著名的開學演講,但這是第一次打開她的著作。在書店看到這本新書,隨即就被標題深深吸引:“活下去”,這與當下的處境似乎格外相關。
翻開這本書,才發現它更像是一本被“包裝”成通俗讀物的學術論文集。日文原書屬於“上野千鶴子的研究”叢書。因為學術論文和為別人寫的書跋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讀者在其中經常會看到一些與其他學者展開專業對話的段落,如果不是對這個領域的專門研究很熟悉的話,會有點摸不著頭腦。此外,像“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一章中出現的對“民族”概念的不同含義的細緻辨析,對於第一次接觸的人來說可能很有幫助,但對於已經熟悉這個話語場的人來說又顯得有些繁冗而不必要了。總之,閱讀本書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不能指望快餐式地獲得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對於有此類訴求的讀者,我推薦只讀前言和第四部第一章的訪談);更重要的是與作者一同思考求索。
本書看似涉及了非常多的話題,包括女性主義、民族主義、“平等參戰權”、“後方史”、戰爭與核記憶、家庭暴力、護理看護等,有的時候甚至是在非常“潮”的學術新領域之間遊走,但統攝全書的問題線索是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想像一種超越了“男女共同參畫”式平權運動的女性主義、如何通過它來反對暴力、如何將“活下去”本身確立為一種雖沉默卻有綿綿力量的價值。以下僅僅評論、重構乃至發揮這條問題線索,不求全面。

電影《敦刻爾克》劇照。
平權運動的局限
上野千鶴子在本書中切入第一波女性主義所推進的平權運動的方式很特別:她直接考察了這種運動最極端的後果。在日本的語境中,由於“男女平等”說法的敏感性,平權運動更多地採取了“男女共同參畫”這樣的話語,與中國早年“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有著類似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平權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而目的本身則是依照民族主義、國家發展這樣的模式來刻畫的。
上野千鶴子考察了全美最大的女性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簡稱NOW,全國婦女組織)要求女人有權“像男人一樣”從軍參戰的呼籲背後隱含的邏輯。由於現代民族國家在成立之初便以戰爭的可能性為永恒的預設,服兵役的義務與完整的公民權是互為條件的。NOW認為,如果女性被排除在國家的軍事力量之外,她們就也將被排除在圍繞著退伍老兵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國家福利制度之外,從而事實上成為“二等公民”。因此,爭取女性的參軍權,就是在為女性爭取“一等公民”的地位。

紀錄片《她在憤怒時最美》劇照。
儘管這種邏輯看似無懈可擊,上野千鶴子卻指出:“一等公民”的權利本身就是一種特權,它總是以將另一些人排除為二等、三等公民乃至非公民來實現和維繫的。在曆史上,這種權利是以成年、男性、同族裔的有產者為標杆來設立的。由於這個有限的群體往往是通過結構性地歧視其他群體來確立自身的邊界與特權,要求女性加入這個被認作“一等公民”的群體就意味著要求女性也成為歧視者的一員。但是,並不存在只有歧視者而沒有被歧視者的社會。例如,在發達國家的移民社會,白人女性的“共同參畫”是以將她們原先被迫承擔的無報酬勞動轉嫁給少數族裔來實現的。
這當然並不是說女性應當安於“二等公民”的地位,而是說,假如只追求同樣的權利,而不問支撐著這樣的權利的社會政治結構本身是否正當,結果就只能是在“向上爬”的同時將不正義的“梯子”踩得更結實。上野千鶴子一以貫之地用最極端的例子——參戰的權利——來說明問題。她提出,軍事的本質是通過將暴力變成國家的行為,而使得這種暴力免於公民社會對暴力的責難與懲罰。戰爭成了“正義”的、因而免責的暴力。為女性爭取參戰權,卻不去過問參戰行為本身所意味著的暴力,這並不會導致“軍事的女性化”,反而導致了“女性的軍事化”。

紀錄片《轉折點:911與反恐戰爭》劇照。
上野千鶴子進一步將戰爭暴力與家庭暴力進行對比:兩者都是在公民社會中被免責的暴力,因為國家和家庭恰處於公民社會之外的兩端。換言之,公民社會本身就是其成員通過對外部(敵國)和內部(家庭中的附庸性成員)的雙向暴力來建立的,它實現的僅僅是這種暴力施加者之間以力量均勢為前提的平等(非暴力)。無論這樣的公民社會如何容納更多的成員,它的基本結構都是排他性乃至攻擊性的。因此,假如女性主義的訴求僅僅在於平權,那麼它就會止於在暴力的再生產結構中分一杯羹,而無力改變這個結構本身。
女性主義的內在價值
因此,女性主義當然不是要停止平權的訴求,但同時也不必停留於平權的訴求——它本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女性主義除了“平等”,還可以訴求“差異”。但是,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很容易讓我們覺得,這個“差異”指的是女性的“特質”乃至“本質”,從而女性主義的希望就在於和平主義、關懷倫理等等。儘管後者確實有其價值,將其建立在男女的“自然”差異上卻不啻一種思想“陷阱”,因為這會導致像關懷這樣的價值重新成為獨屬於女性群體的義務,從而進一步加深不平等。
上野千鶴子對這種思想陷阱非常警覺。她論證說,參軍女性(如在伊拉克虐囚的美國女兵)的例子已經反駁了上述本質主義,因而更有意義的問題是人在什麼樣的情境中會展現出對和平的愛好和對彼此的關懷,儘管在現實的曆史上女性更多地處於這種情境中。一旦如此發問,我們就會傾向於努力將無論什麼性別的人都置於同樣的情境中,而不是延續本質主義的“性別分工”。

延伸閱讀:《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美)辛西婭·恩洛著,楊美姣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但是,為什麼要將更多的人置於女性曾處於的情境中?這種情境及其所培育的價值,為什麼是更好的價值?上野千鶴子在本書中提出了兩個回答,儘管它們都還是嚐試性的。
第一個回答:女性主義意味著對差異的包容與認可,而這是因為,只有像女性(但不限於女性)那樣曾被結構性地置於弱勢地位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意識到結構之惡而試圖去改變結構本身。因此,上野千鶴子聲稱,女性權利是“即便不同也不會招致歧視的權利”。嚴格說來,每個人身上都有與眾不同之處,而在歧視性的結構之下,任何一種不同之處都可能會在某一天成為歧視者手中的“把柄”。從而,伸張女性權利,實則是伸張每個人無所羞赧地做自己的權利,同時是在對抗那種只有踩別人一腳才能站得穩的處世方式,從而使得人們不再為自己的獨特而恐懼,不再只是心存僥倖地希望歧視不要落到自己頭上。
第二個回答:女性主義意味著承認人們對彼此的虧欠。它揭示出,現代主體貌似的自主乃至主權,是通過遺忘它對一系列服務性的前提的依賴才成立的。如今,我們不是要在對這種自主的無限擴大中造就更深的遺忘和壓迫,而是要承認對彼此的依賴和虧欠。上野千鶴子在護理看護(care-giving)的語境中,甚至使用了“希望他們(男性)可以放棄成為強者,選擇成為一個弱者”這樣的說法。一個人“選擇”成為弱者,並非出於愚蠢,而是因為意識到所謂的“強者”是那種一旦在權力的遊戲中取得優勢地位、掌握了對別人的生殺大權,就立即追求充分使用、乃至濫用這種權力的人。
上野千鶴子舉例說,“像性騷擾、家庭暴力、職場騷擾、精神暴力、霸淩、虐待……這些都發生在對方無力回擊、無法說‘不’、也無法逃離的時候。”面對這樣的“對方”,主動選擇不去濫用權力,這才是她說的“選擇成為弱者”的真正含義。這裏的“弱者”,指的已經不是力量的多寡,而是能夠對他人的脆弱感同身受的能力,是“共同脆弱”的能力——它甚至可以看作對尼采的“同情”(Mit-leid,字面意思就是“共同脆弱”)主題的一種反轉式的新解。

紀錄片《情熱大陸 上野千鶴子篇》劇照。
活下去,並非是懼怕死亡
無論是包容和認可差異,還是承認對彼此的虧欠,都構成了對生命自身的認可。但是在這裏,我們立即遇上了一系列的挑戰,它們往往聲稱:活著總是為了什麼超越生命自身的事情;而如果活著只是為了活著,就會通往平庸的苟活,會使人與禽獸無異。
上野千鶴子對這樣的挑戰是有所預料的。事實上,她寫作本書正是要挑戰“活著是為了別的什麼”這樣的想法。書名《為了活下去的思想》(生き延びるための思想)是正面回應池田晶子《埴穀雄高論》中“我們不需要為了活著的思想,我們需要的是為了死亡的思想”的說法。
如果僅僅是為了生物學層面的“活著”(survival),似乎的確不需要思想。因此,思想往往以超越“活著”為己任,因而往往通過觀照作為“活著”之對立面的死亡來確認自身的力量。這樣的做法,在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說出“哲學就是練習死亡”(《斐多》)時就已很明顯了。在此之後,哲學不斷地為人們提供“可以為之赴死”的價值,彷彿生命本身是一種祭品,總要獻祭給某種高於生命的東西。上野千鶴子承認這種思想模式的巨大誘惑力;相形之下,“為了活下去的思想”卻“老土、丟人、猶疑不決、毫不得體”。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戰爭與和平的對立中:戰爭是崇高、壯麗、振奮人心、給人自豪的,而和平則“鬆散緩慢,空虛,漫無目的……無聊枯燥”。在以前現代的榮譽觀、“偉大”觀來映照和批判現代性“怕死的平庸”的思想路線中,我們也能辨認出柏拉圖主義、乃至整個哲學傳統的持續影響。

延伸閱讀:《斐多》,(古希臘)柏拉圖著,楊絳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3月。
然而,一方面,在戰爭所代表的榮耀之下,巧妙地隱藏著“惡毒的壓榨、侵占、殘暴、迫害”。英雄主義所追求的偉大,是對人的卑微的刻意隱藏和遺忘。醉心於生活中各個領域的“戰爭”及其所代表的“偉大”的人,首先需要扭頭不看自己對世界和對他人的深刻的依賴,需要將由自己所推動、參與或縱容的惡偽裝成曆史的必然,需要通過“拉遠鏡頭”來屏蔽同類的呻吟、呼救和歎息。換言之,通過抬升死亡(及其背後的崇高價值)來貶抑生命的思想,同時也是“冷血”的思想,是一個尚在思考的生命矯揉造作的主動“失溫”;而它在吹噓與世界和他人的切割的同時,又不得不繼續寄生於後者,甚至因為濫用暴力而更“腐蝕性”地寄生著。這樣的人和這樣的思想,本身就是暴力的附庸,是暴力的第一個犧牲者。
另一方面,“活下去”也不僅僅意味著“活著”。我們在to live(vivre)與to survive(survivre)之間的日常區分,本身預設了“活著”是“為了”某種超出了活著的事情。但是,這種超出未必是以崇高價值的方式懸在死亡的大門之後的東西;它也可以意味著生命本身的差異化和深化——事實上,我們通常正是以後一種方式來理解life超出survival之處的。因此,上野千鶴子所說的“活下去”,不能歸結為to live或to survive的任何一方,而更接近to live on:這個on蘊含了對未來可能性的無限期待。

電影《小早川家之秋》劇照。
“為了死亡的思想”當然可以將生命的一切可能性貶抑為一個無聊的平面的自我擴張。但當這樣做時,它就既不能被平面所承托,也不能被平面之外的某個“高處”所接納,而是墜入虛無,墜入死亡。而死亡才是最無聊的,因為它是一切可能性的不可能性——它甚至不是平面,而是一個無處可尋的、封閉的點。這種思想,看似是主動地“為了”死亡,實則是不由自主地被獻祭給死亡。
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而活下去,並非只是意味著作為一隻動物而存活。那種認為“明天也會像今天一樣”的希望,動物是不會有的;在其中蘊含著守護我們曾有幸敞開的意義空間的艱辛努力。在上野千鶴子看來,超老齡社會的到來,有望教給我們一件事:即使生命中的大部分是在走“下坡路”,即使為了走完這段旅程,我們將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賴,生命仍然是值得過的。因為生命並非只是在通往更高、更強的路上才有意義;在日複一日的衰老乃至“腐朽”中,生命亦有其自在的節律和尊嚴,它能夠通過衰敗(而非在衰敗的彼岸)展開無限的“褶子”。假如思想不夠堅韌,不能陪伴和見證這種衰敗,不能給它足夠的耐心,它就學不會尊重真正的生命,而會急匆匆地要趕往生命的盡頭。

延伸閱讀:《一個人最後的旅程》,(日)上野千鶴子著,任佳韞 魏金美 陸薇薇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0月。
而要使得生命在衰敗中亦有尊嚴、亦有無限的希望,人就不能只是獨自前行。事實上,也沒有人可以獨自前行。承認這一點,承認相互扶持的意義,就意味著不僅學會積極地幫助,也要學會積極地被幫助——而非一面寄生於幫助,一面否認幫助的必要性。“為了活下去的思想”,終究只有在“人與人之間”才是可能的。從這個“之間”的滋養中,將不斷湧現或重新湧現出行動的勇氣與存在的正直。在此意義上,人類文明之所以不同於自然,恰在於這個容許了生命與生命相互信賴、託付和承擔的“之間”。
書的盡頭,同時也是思索的起點。上野千鶴子的女性主義思考、她關於“為了活下去的思想”充滿希望卻仍有待發揮的論述,將我們帶到了阿倫特所說的“人的複數性境況(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of plurality)面前。思想唯有正面回應這種境況,才能走出所謂“怕死思維”的迷局。
作者/劉任翔(清華大學哲學系)
編輯/青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