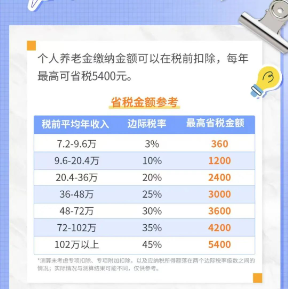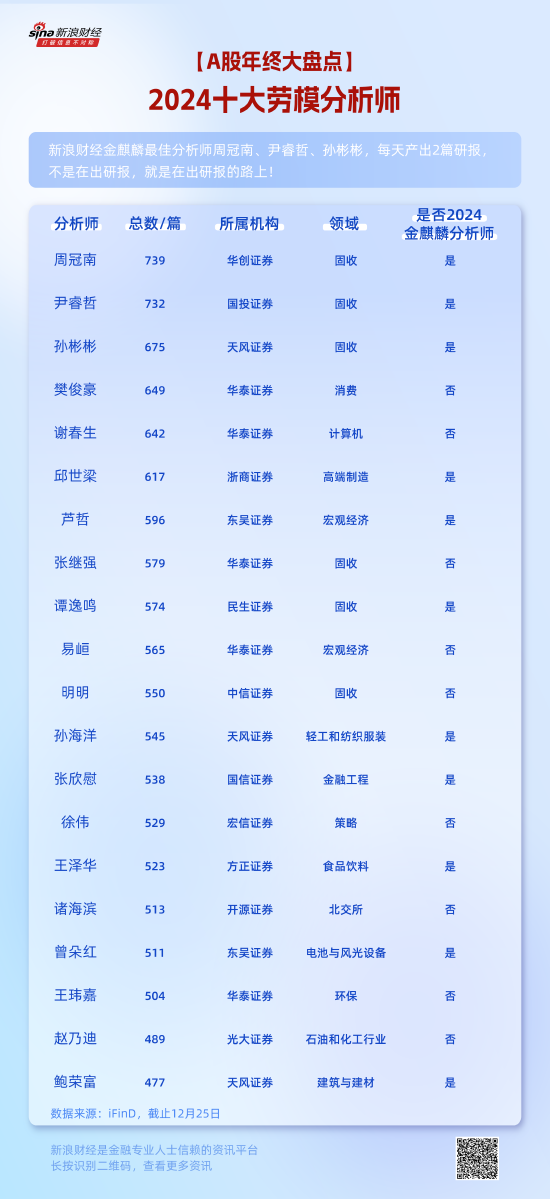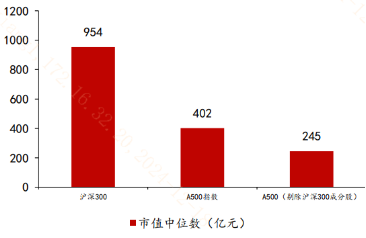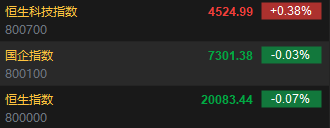瓦格納逝世140週年|《尼伯龍根的指環》的寓意
【編者按】
2023年2月13日,是德國音樂家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逝世140週年紀念日。瓦格納創作的《尼伯龍根的指環》(簡稱《指環》),由四部歌劇組成,是其代表作品,也是音樂史上偉大的作品之一。本文摘自英國作家、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探索《指環》情節、音樂、象徵意義和哲學思想的《真理之戒 : 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智慧》一書,為其第五章《劇情理解》,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理查德·瓦格納
理查德·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內涵隱晦,涵蓋大量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是《指環》的核心,或者說整個故事就是圍繞他或她展開的,人物間的對手戲也沒有前後一致的衡量標準。本章我會儘可能地闡述這部劇的寓意,也為之後要討論的哲學及道德思想提供大體框架。
故事圍繞沃坦、阿爾貝里希、齊格弗里德、布倫希爾德及其他一些主要人物展開,反映人類的生活世界——由人類構建並參與其中感受的世界。我們無法用科學的方法分析其前因後果,以解析這些感知,只有親身經曆,才能獲得一些概念,而這些概念可能根本就不符合科學。
以人的概念為例,人是自由而又有理性的個體,既能觀察他人,又能審視自己。這一哲學思想繼康德之後風靡德國,德國唯心主義思想家也曾發表言論詳細闡釋這一概念。這一概念在人體生物學上的解釋是:人由大腦和有機體構成,是無差別的個體。但從人的自我意識這一角度來說,人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意識區分個體與事物、主觀與客觀、動作和運動、理智與動機、理解與解釋,人也因此對同一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為了探究人類世界,人類的祖先通過他們對於日常活動敏銳的觀察,創造了神話故事。故事圍繞眾神和英雄展開,描述他們英勇崇高的行為,以及阻礙他們前行的重重困難。他們的經曆讓我們區分善良與邪惡、自由與束縛、責任與權利、神聖與褻瀆、可做之事與不可做之事。他們的各種情感豐富了世界的色彩,將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公之於眾。
瓦格納創作的《指環》故事與之十分相似。這個故事就是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它表現了人類內心世界的許多方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瓦格納意圖以此修復人們心中的道德信仰,揭示人類真實的本質,而這一本質卻被生物科學淺顯地解釋,就像一部毫無內容的電影。
我們可以想像最早的人類靠著自然生存,日複一日地重複勞作,外出打獵和尋覓獵食的人也只是模糊地知道生存的準則。那時生存條件雖艱苦但世界卻是簡單的,人類的需求也與現在完全不同,他們同野獸一同競爭有限的自然資源。自然及其資源,包括水和空氣,都是世界的餽贈,而火的出現卻帶來了一系列的改變:由寒冷到炎熱,由生到熟,還可以鍛造金屬,並以此製造武器,同其他種族和部落爭鬥,掌握統治權。我們仍可以想像出人類最原始的需求,以及生存給他們帶來的恐懼與希望,這些都可在瓦格納戲劇中半人半神的人物身上找到。瓦格納的戲劇大篇幅地表現“起源”世界,那時還沒出現獨立的自由人格,也沒有意誌和律法。自由和獨立人格是新世界的誕生物,世界已經從動物“起源”世界演變為了意識世界。
 拜羅伊特劇院里的《指環》紀念牆
拜羅伊特劇院里的《指環》紀念牆《指環》講述了新世界的故事及原罪的由來。人類漸漸瞭解自己的處境,試圖掌控自然秩序,如今他們必須建立律法和條約,律法依靠權力生效,而如何獲得權力呢?如何讓人類願為遵守律法而自願犧牲個人利益,抑或人們自願放棄收穫的可能而履行契約呢?一開始,人們想像出這樣一種權力來實施律法——自願遵從律法的人會獲得獎勵。因此至少在一開始,律法和眾神的作用有些相似,而那些崇拜眾神的人會自願順從眾神的旨意。眾神是永恒的,會帶給人類渴求的幸福與和平,也會為其追隨者帶來意想不到的禮物。人類由此產生永恒的信念,想像出天堂的樣子,相信天堂里沒有凋亡。
但如何維持這種信念?如何在現實世界讓人們相信超自然的事情及永恒的幸福呢?人類原始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需要新的文化及獎賞鼓勵人類繼續勞作。我們必須為將來積累財富,修建教堂和城堡,用尊貴的處所和高尚的血統維繫我們脆弱的地位。我們必須大方而又自願地維繫律法效力。男人們必須接受努力勞作的目的就是獲得“愛情和女人的價值”這一傳統思想,絕不是圖一時新鮮。唯有將肉體之愛變成眾神給予人類的禮物,即永恒的天界對凡人的恩賜——換一種說法就是“聖禮”——我們才能勸說人們進入教堂成就一段完滿的愛情,當然這其中也包括肉體之愛,儘管人類不像鳥兒或是禽獸僅僅追求肉體之愛。但人類的愛情也需要增添一些額外的歡樂來填補。誰能創造這些歡樂呢?這些歡樂會花費人類多大代價?
隨著人類的進化,能否擁有一段完滿的愛情取決於能否有節製地享用它,慾望成了摧毀愛情的因素(激起慾望的誘餌變化多端,比如戲劇一開始的萊茵少女)。道德和律法以婚姻的形式約束愛情,弗麗卡目光機敏,掌握著婚姻律法。最高級的肉體之愛不是感官愉悅,也不是家庭內部和諧,它包含二者,是凡人的愛情、齊格蒙德與齊格琳德的愛情,這種愛情遠比眾神的愛情高尚、尊貴。它包含兩性之愛,同時愛情的雙方都願為對方犧牲自我。它是對人類最大的餽贈,若失去它,人類通往自由的旅程也會不完整。
另一方面,愛情並不是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人,那些長相醜陋或是不討喜的人總是遭受愛情的挫折,阿爾貝里希就是一個例子。出於憤恨,這些人可能會將內心對愛情的渴望轉換為對權力的追求,視他人為可利用的客體,則非應該被珍視的主體。我們延遲滿足的慾望形成的世界現在正是由這深埋心中的憤恨支撐著。這種不留情面的拒絕帶來的受挫感包含了一種新的破壞性動機,即競爭的衝動,將他人當作可利用的工具,並將一切,包括愛和人格,都當作統治的手段。通過這樣利用世界,受到羞辱的阿爾貝里希強迫他人順從自己,這就是他在尼伯爾海姆言辭激憤地指責眾神的意義所在。他還創造了眾神需要卻從來未能創造的東西——這些多餘的東西可以用來支付建造瓦爾哈拉城堡的費用。
人類世界變得不太平,憤恨忌妒在作祟。人世間存在各式各樣的矛盾:英雄受到特殊獎勵;人們為爭奪領土和配偶而衝突不斷。人們崇拜眾神,祈求他們的庇護,但有一點要知道,眾神不再是世間萬物的統治者,他們的統治依賴於人類是否願意順從,他們是否能滿足人類的願望。
因此,理想回到了它所屬的人類世界,在萬物中處於休眠狀態,只有將殘留原始信仰付諸禁忌之火,才能保護理想免受褻瀆。一開始人類建立森嚴的律法、職責及權力體系,後來這個體系逐漸被宗教教規取代,教規鼓勵人們獨立,實現人生價值,而不依賴於眾神。但這樣也會出現不公平的事,人們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獎賞,這也是引發憤恨的緣由。人們能否獲得生存的價值和尊重,取決於人們能否克製內心的憤恨。可是最終還是憤恨佔據上風,因為宗教無法證明其教義是有道理的,也無法遮掩其騙人的把戲,最後不得不退出人類舞台。
《齊格弗里德》描繪了我們當代人所處的危險境地。人類實現了一直以來追求的理想,但卻無法維繫它。人類屢試屢敗,但人類的腦海里一直渴求神聖、仰望理想,相信會有一個獨立的自由人完成使命,實現這一理想。齊格弗里德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喚醒了世界,也喚醒了自己。他告知眾神結局,沃坦最終接受結局,把世界餽贈給齊格弗里德,而齊格弗里德也由此認識到了“愛情和女人的價值”。

瓦格納的學生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為1876年在拜羅伊特的《指環》首演設計的《齊格弗里德》舞台場景
齊格弗里德作為一個自我創造的存在可以自由自主。他以自己的方式掙脫律法和傳統的思想觀念束縛,內心的聲音讓他對完美的女性充滿嚮往。充分擁有神聖的愛情後,齊格弗里德會繼承沃坦的遺贈。但他也會摧毀沃坦的權威和他借助律法——刻在靈魂中的律法——維持的統治。當他從充滿崇高愛情的山巔降入世界,因為他對神的違逆,一切誓言和契約都變得可以討價還價,甚至對他而言最珍貴的東西也被遺忘,被推翻,被用來做交易換取更好的東西。生活在超越時間和交換的世界中的眾神避開了轉變的力量,然而我們作為凡人必須服從時間的規則。人類世界的一切都是暫時的,甚至最絕對的價值觀也有可能因為我們一時的衝動而被棄置一旁。
替換的世界,被斯賓塞(Spencer)稱為“萬變的世界”,指的就是由指環帶來的世界——不再被天地律法所不容的世界。齊格弗里德墮落了,失去正直的品行,他的正直被那些心中無愛、只有等級與地位的人陰謀破壞了。《諸神的黃昏》最後一幕中,齊格弗里德望著萊茵少女,湧現出與全劇一開始阿爾貝里希面對三少女一樣的情感。他對一位並不喜歡的女人許下了諾言,這個承諾阻止他去追求自己的真愛,但這個女人終有一日也會被取代。
唯有一事可以糾正這種精神世界的混亂,那就是女性可以蕩滌混亂不堪的精神世界,清洗汙濁的愛情。在這一幕我們能完全理解布倫希爾德為何會與萊茵少女們產生關聯,能夠深刻明白事情的本質,相信齊格弗里德在向她求愛的那一刻顯露出他最真實的一面,即使是追求自己的自由導致他毀掉了置身事外的能力,他也只是受到外在汙濁世界的影響,但他的內心並不汙濁。布倫希爾德完全明白這一點,因此最後選擇原諒齊格弗里德,兩人的命運也由此緊緊地拴在了一起。在布倫希爾德的死亡中——在睡夢中被獻祭,之後死亡——獻祭的不只是她的生命,還有整個人類世界的意義,將自然規則植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生根發芽,最終成長成龐然大物。然而從音樂中我們能夠感知到,這個龐然大物非常重要,布倫希爾德放棄與寬恕的姿態,無論是對她身為眾神之一的父親還是對她身為凡人的丈夫,都一樣重要。
眾神消失時受到了齊格琳德的祝福,這祝福曾是送給布倫希爾德的。給出祝福的是一位凡人女子,她為了拯救愛情被剝奪了一切。瓦格納這裏向觀眾拋出一個問題:為何這祝福拯救了世界?
《指環》的初稿向觀眾們解答了這一問題:人類可以從眾神手中接管世界,並能更好地經營它,但與眾神不同的是,人類不是靠一人統治,而靠眾人一起經營。同費爾巴哈一樣,瓦格納在1849年革命中預言人類未來將會擺脫奴、役獲得自由。費爾巴哈主義認為,人類是鮮活的有機體,最初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從自然平衡規律。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人類有了自己的語言和獨立意識,但這獨立意識就是人類的原罪,因為它不再受自然秩序的束縛,人類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這種獨立意識衍生出自由、人格及對權力的渴望。科技使得自然秩序按照人類的意願運行,幫助人類製造產品滿足需求。人類對權力的渴求催生出貨幣經濟和勞動力貿易,競爭打破原有的平衡,世界秩序不再依靠自然規律維持,忌妒引發各種衝突。律法是維持人類和諧的唯一手段,它需要最高統治權維繫。最高統治權可以保證履行各種契約,但它同時也帶來支配力。這種支配力必須存在其合法性,有宗教的支持,通過這種方式,遵守律法的人會獲得獎勵,而這種獎勵卻虛假而不可靠。
瓦格納這一時期的文章及對舊式形而上學的深刻研究給費爾巴哈學說擴展了新思路。瓦格納認為宗教並不虛假,儘管宗教不如真理強大而有力,但它揭示出人類的深刻真理。宗教真理會不知不覺地潛入人類意識,但是意識往往與宗教教義背道而馳,人類會懷疑並摧毀宗教這股力量。藝術以其象徵形式揭示人類的深刻真理,建立新的精神秩序,真實可靠地反映人類的狀態。
 齊格弗里德
齊格弗里德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瓦格納最初就是這樣構思齊格弗里德的故事。正如保羅·海澤所表明的那樣,從費爾巴哈式的前提出發,最終完成品有可能讓整個組歌發展出影響深遠的表現形式。在一個被人格和自我意識所背離的世界里,經受財產和交換的暴政,在宗教所維護的法律的約束下,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憤恨在萬物的心坎里滋長:財富至上,導致愛已無藏身之地,我們所信仰的極樂淨土被科學這個蛀蟲完全吞噬了。與此同時,我們真正的自由——意識里的原罪所許諾的自由——卻被維繫事物存在的力量從我們這裏偷走了。只有創造自己未來的自由英雄,才能擺脫束縛人類的枷鎖——宗教幻覺的枷鎖、財產和貨幣經濟的枷鎖。
這位英雄必定是個藝術家,一開始一無所有。他就是詩歌自身精神的象徵,引領一種新的意識潮流:自由勝過律法,真理勝過幻想。然而,正如詩人不能擔負起新藝術作品(講述這位英雄的故事)的全部重擔一樣,這位藝術家兼英雄也無法靠自己的努力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只有通過男女之間、男女主人公之間的自由結合,在以自我犧牲為主導原則的愛情中,新世界才能誕生。正如詩歌需要用音樂來創造未來的藝術作品,英雄也需要所愛的新娘從宗教幻象的世界中來到凡間,與他結合去解放世界。
然而,整個故事並不完全吻合費爾巴哈學說。費爾巴哈認為人類自由屬於政治領域,而社會和經濟秩序已經完全轉變,只有完全打破宗教幻想,人類才能獲得自由。瓦格納已經意識到獨立的靈魂會幫助人類獲得解放,他必須找到自己心愛的人,與他一起追求自由與獨立,因為單獨的一個人根本不可能實現。愛情讓人類獲得解放,但愛情也可能會有負面作用,這便導致了齊格弗里德的悲劇。他從高山之巔喚醒布倫希爾德,享受片刻歡愉,之後則來到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各種陰謀和交易的誘惑下,他飲下了失憶藥水。
這解放將原本分離的男女、詩歌與音樂結合起來,解放舊式的奴役,但並沒有打破傳統的秩序。瓦格納逐漸意識到這裏的解放是一個精神曆程,與政治無關。觀眾對於布倫希爾德的自願犧牲產生疑問。救贖並不意味著開始更美好的新生活,而是對現有生活的重新安排。二人一開始都並不理解這一點。布倫希爾德開心地向齊格弗里德揮手告別,支持他完成新的偉績,相信他會回來,從未對山下的世界有所懷疑。而齊格弗里德與妻子再次團聚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前是為了追求愛情,而這一次則是為了獲得權力。你可能會說,在創作《指環》組歌時,瓦格納用青年黑格爾派的樂觀主義哲學來檢驗這部歌劇,而歌劇本身對其做出了駁斥。
瓦格納的最初構想在故事表面掩蓋下不斷浮現。保羅·海澤也精心闡述過,他認為個體人物、事物和行為代表著人類狀況的其他更普遍的特徵,即具有廣泛的宇宙或政治意義的動機、利益和過程。有時候富有寓意的解釋似乎有道理,有時候則沒那麼有道理。但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是寓言,什麼時候它才是藝術作品的意義的一部分。通過將人物和事件一一關聯起來,將一個寓言意義賦予任何故事,都可以賦予它更具普適性的意義。但是,如果說第二個故事賦予了第一個故事寓意,那就說明寓意與故事並不具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在真正的寓言藝術作品中,寓言的意義體現在主體情節和人物身上。也就是說,當你沉浸於故事情節的時候,寓意成為你感受的一部分。因此,海澤和納蒂埃都告訴我們,在齊格弗里德和布倫希爾德的結合中,前者代表詩歌,後者代表音樂。但我們自己聽到的是這樣嗎?從齊格弗里德劃開沉睡的布倫希爾德的盔甲開始,我們對他的感受是詩歌嗎?我們是否認為布倫希爾德對愛的宣言是音樂的聲音,一個被情人喚醒的女人的聲音?在我看來,這個特殊的“寓言”對我們的觀看體驗沒有任何幫助,這更像是一種學術上的探索。當然,這是瓦格納為使自己未來的藝術作品理論能夠具有啟發性所做的探索,但對所有這一切來說,它只不過是一個隱藏在藝術作品之外的理論,而不會成為藝術作品的一部分。只有當一個角色的意義增強了他在戲劇中的存在感,並賦予了他更豐富的動機時,他的角色才會具有超越角色本身的意義。這種增強應該是彼此促進、相互作用的。戲劇應該闡明寓言的意義,而寓言的意義又應該放大戲劇的內涵。
一個寓意往往表現兩個故事,其中一個直白地講述故事中的人物、動作、時間和地點,而另一個則隱晦地表現抽像的思想、世間的各種力量及道德教義。有時兩個故事中的各種元素能一一對應起來,比如斯賓塞的《仙后》;有時寓意直白地表現出來,比如《天路曆程》,故事涉及基督教、不輕易屈服、希望、絕望及失望,還有惡魔亞玻倫。結合上述幾點,我認為《指環》不是寓言故事,而是一部充滿象徵意義的作品。
象徵主義與寓言的區別在於象徵既表達一種意義,又增強了它的意義,所以意義和象徵是分不開的。儘管貨幣經濟在一種似是而非的意義上解釋了阿爾貝里希的指環的含義,指環也是貨幣經濟的含義:故事告訴我們一些關於貨幣經濟的事情,否則我們可能不瞭解甚至對此一無所知。如果一個符號是有實際意義的。那麼它也是許多思維方式的凝結,這就是這個詞的詞源含義,希臘語中的symballein意為“把它們放在一起”。因此,指環也是人類傾向於將所有事物視為手段而非目的的象徵;它是權力和慾望的象徵、剝削的象徵、占有的慾望的象徵、意識的象徵。這是一種原罪,將人類與自然分離開來,賦予我們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生活”,在其中我們獲得承認,取得地位。指環意味著所有這一切,而所有這一切又代表著指環,指環向我們展示了它們的真實面目。通過將許多意義濃縮成一個單一的象徵符號,藝術使每一種意義都能讓人進一步瞭解所有其他的意義。如此一來,這個象徵符號向我們展示了將它們聯繫在一起的道德現實。
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寓意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寓意可能會脫離整部戲劇,不符合全劇的美學效果,無法引起觀眾的共鳴;另一方面,若是寓意過於淺顯易懂,讓全劇染上說教色彩,那就成了宗教寓言故事或是給兒童準備的警世寓言。我認為,這對我們是個警告,即不能對《指環》做直白的寓言解讀。但還是有些人覺得這樣的解讀應該得到維護,其中就包括喬治·蕭伯納及費爾巴哈學派的保羅·海澤。
蕭伯納的闡述得益於作者豐富的寫作風格,其中包括他對魔盔的著名描述。魔盔就像是資產階級標誌性的大禮帽,代表了資本的多種偽裝,能夠隱藏在股票、分紅和利率中,逃避一切負債,為那些不知道其下落的人秘密工作。
頭盔十分常見,常常是一頂高高的帽子。戴它的人可化身多種身份——股票持有者、虔誠的基督徒、住院者、捐助窮人者、模範丈夫兼父親、精明獨立的英國人等。他就像團體里的寄生蟲一樣,只知道謀取好處,貢獻不出一點兒力量。什麼感覺也沒有,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相信,什麼也不做,除非團體里其他的人都做了,他才會跟著幹,因為他害怕不做會受到懲罰,但也只是假惺惺地裝模作樣。
這是很聰明的指代,它影響了組歌的一個主題動機,很明顯是瓦格納對整個組歌最初的創作想法,我們大體上同意,這也反映了人類生存環境的真實情況。然而,隨著組歌的行進,劇情越來越不符合蕭伯納的寓言,有人認為齊格弗里德開始顯得越來越脫離瓦格納的初始意圖。
蕭伯納也認識到這一點,提出《諸神的黃昏》是部“大歌劇”,這一詞源於《總體藝術作品》一文(由瓦格納提出,他提倡在歌劇中將故事情節、音樂及舞台場景融合在一起)。蕭伯納在評論齊格弗里德擊斷沃坦之矛這戲劇性的一幕時再次提出這一術語。布倫希爾德是沃坦意識的化身,她追求更高尚的生活,並最終脫離眾神。她值得被齊格弗里德追求,但齊格弗里德應該換一種方式追求,絕不是通過熾熱愛戀的方式。
 約瑟夫·霍夫曼設計的《諸神的黃昏》舞台場景
約瑟夫·霍夫曼設計的《諸神的黃昏》舞台場景蕭伯納認為“愛情靈藥”給瓦格納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同時又把《指環》引向“大歌劇”的方向。齊格弗里德不應該就此沾沾自喜,而應建立起新的秩序。蕭伯納認為相比於在肮髒的資本世界做出新事業,齊格弗里德更應該努力地培養新的人才,帶領眾人擺脫寡頭政治的束縛。值得慶幸的是,瓦格納並沒有這樣設計劇本。
儘管全劇一開始,沃坦是“眾神之王”,與眾神共同維護瓦爾哈拉城堡,但作品忽略了人們的宗教信仰。阿爾貝里希被迫回到地下工廠,作品里完全忽視了阿爾貝里希本身的罪過,反而引得人們更加同情他。庫克認為阿爾貝里希不是偽善者,他在人群中不常見。除了代表資本經濟的貨幣以外,魔盔還有更深層的含義,它是“變化”的象徵:一種事物可以神奇地變成另一種事物,人物性格和思想里有真亦有假。這種變化真實地存在於人類世界中,是人類墮落的起因。
海澤的費爾巴哈式寓言更具說服力。這部劇涉及向全世界展示人類的自我意識,以及由此產生的與自然規則的背離。它也涉及因恐懼和侵略而誕生的眾神,並將我們賴以建立法治和政治秩序的宗教幻象戲劇化。它涉及思想對這些幻象的侵蝕,以及我們在科學知識所提供的黯淡前景面前對其他希望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齊格弗里德體現了這一希望,但同時也將圖謀阻撓這希望的所有事物聚集起來。所有這些想法都是從海澤的敘述中發展出來的,值得仔細研究。
另一方面,儘管海澤的敘述很有啟發性,但是他對人物的觀點經常通過寓言式的講述表達,這樣就會使人物特點不那麼鮮明。以下面一段為例,這一段描述了齊格弗里德面對巨龍的場景。
布倫希爾德,代表著潛意識。它的特殊語言是音樂(其中齊格弗里德這類音樂戲劇家——比如瓦格納——會本能地試圖壓製我們的內在意識,特別是內在意識里的危險的東西),世俗藝術家會在失去宗教信仰後將音樂作為替代品。正因為如此,它將成為藝術家對知識恐懼的替代品、信仰的基礎,保護信徒們不去探究費爾巴哈所表達的宗教奧秘,而這些奧秘正是費爾巴哈最開始無意識地、不自覺地創造出來的。由於齊格弗里德將無意間給宗教信仰帶來致命的打擊(法夫納),承擔起守衛指環、魔盔和他即將繼承的責任,他還必須為保守沃坦的秘密而承擔起責任。
這個故事是有道理的,它解碼了一些隱藏在戲劇中的信息。但這也激發了人們的不同想法,齊格弗里德不是一個音樂劇作家,而是一個孤膽英雄;法夫納不僅僅是一個宗教信仰的象徵,還是一個變味了的古老承諾的遺留物,一個存在於任何英雄道路上的所有障礙的最終代表,一個對人類核心事務漠不關心的象徵。這也提醒我們,布倫希爾德對瓦格納來說是音樂精神的縮影,她曾經是一位女武神,出於對凡人的憐憫而放棄她的神性,在沉睡前用過人的智慧安排了自己的未來。在某種程度上,海澤的對組歌的解讀雖然充滿見解,但是都是對神秘主義的解讀,缺少尖銳的評判。
 約瑟夫·霍夫曼設計的《女武神》舞台場景
約瑟夫·霍夫曼設計的《女武神》舞台場景馬克·貝瑞(Mark Berry)對組歌寓言式的看法的核心也是費爾巴哈哲學。在貝瑞的著作中,《指環》包含了對財產、政治秩序和民法的譴責,這與青年黑格爾派最激烈的謾罵是類似的。根據貝瑞的說法,在深刻解構代表法律的沃坦和代表資本主義的阿爾貝里希的過程中,他發現瓦格納的激進政治觀點依然存在。費爾巴哈戳破了宗教的幻象,使戲劇充滿了活力,它把神描繪成人類的夢想,把人的激情幻化成虛無飄渺的影子。青年黑格爾派,而不是尼采,首先宣佈了神的死亡。在貝瑞的著作中,對於我們這些活了下來的人來說——無論在個人層面還是政治層面——《指環》是對這個最終死亡的意義的探索。
毫無疑問,貝瑞提醒讀者,這部劇無論是音樂還是劇情都帶有黑格爾學派的色彩。他指出,黑格爾學派反對統治和奴役,而這也在劇中的主要人物身上有所體現。他還強調只有認識到死亡也是愛情的一部分,才會擺脫愛情與權力這對互相對立的事物的束縛。隨著劇情推移,基督教教義逐漸取代單純的情愛,到了《諸神的黃昏》的結尾處,全劇一開始體現的青年黑格爾學派思想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貝利的寓言就像蕭伯納和海澤一樣凝視著神秘的虛空。
觀眾必須從沃坦的自述中瞭解到音樂有意表現沃坦的同情心,有意展現律法規則——一開始的“篡奪”為之後永恒的愛做鋪墊。瓦格納初創《指環》時,將齊格弗里德設定為擺脫陳舊統治的自由英雄,但之後卻變成背叛者,背棄誓言、諾言、契約和律法,把自己和他人引向毀滅。掌管律法的神能夠滿足人類訴求,神也存在人性的缺點,和人類一樣終將死亡。但重要的一點是,毀滅眾神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就是毀滅人類自己,人類從一種宗教信仰解脫出來,必將會經受另一種精神混亂。
《指環》提醒人們自由也存在不足。它雖不受權力政治的束縛,但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人類要克服自私及生理需求,才會實現最終的自由。《指環》不僅涉及權力、金錢或愛情,還與原罪有關聯,叔本華稱之為“存在的罪過”,海澤把這一觀點融入複雜的寓意理論。但還是要透過象徵主義理解《指環》的人類特徵,而不是通過人物及其行為背後複雜抽像的寓意。
這裏有一點要提醒大家,瓦格納改編的神話未受當代科學的洗禮,拒絕將人類真理用日常的散文故事表達。神話往往借由象徵表達,也就是瓦格納在藝術作品中運用的手法,這種表達方式一直延續到20世紀,與弗洛伊德理論不謀而合。神話的深層含義下意識地反映人類無意識的想法,榮格認為神話是“無意識的集合體”,反映了人類共通的情感,只能透過象徵將其表現出來。榮格認為,這些象徵,也被稱作“原型”,以神的形象出現在神話中,下意識地反映人類發展的曆程。一些具體的事物,比如巨龍、指環、烈火,反映了人類的心理世界。故事中的人物克服困難,其中的女性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她們的經曆可被編成寓言故事。故事中,男子和女子相互尋覓對方,而這一切並不是刻意為之。羅伯特·多寧頓採用這種方式解讀瓦格納四聯劇,重寫《指環》故事。在多寧頓的故事中,普遍存在的自我意識(齊格弗里德)去尋找能讓其變得完整的阿尼瑪(布倫希爾德),一路上與潛意識中的惡魔做鬥爭,並受到利比多(指環)的控治。指環的力量並非來自對愛的棄絕,而來自對“純真、孩童式幻想”的放棄,這就是《萊茵的黃金》開場明確傳遞的信息。
 約瑟夫·霍夫曼設計的《萊茵的黃金》舞台場景
約瑟夫·霍夫曼設計的《萊茵的黃金》舞台場景所有這些解釋的問題在於,如果它們是正確的,它們就會把戲劇中的個別人物放到適用於我們所有人的類別中。榮格學派相信,每個男性自我都在追求能使自我完整的阿尼瑪,相信它與可怕的母親競爭,相信它在生命中伴隨著黑暗的陰影,等等。因此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齊格弗里德的旅程毫無新奇和吸引人之處,其中巨龍法夫納是“真正的”萬惡之源。它喬裝打扮隱藏在叢林中,布倫希爾德則是齊格弗里德的阿尼瑪(《女武神》中她曾是沃坦的阿尼瑪),哈根則是齊格弗里德陰暗的影子。《諸神的黃昏》結尾處,我們還可知道古特魯妮也是齊格弗里德的阿尼瑪,古特爾和哈根同是齊格弗里德陰暗的影子。在全劇的結尾處,“一場大火終結整個世界”,齊格弗里德浴火重生——全劇被拙劣地理論化了。我們也會反思這些分析是否有意義,當然,如果僅僅得出以下結論,那就毫無意義。
《指環》的內涵是,所有無意識的原始渴望所引發的過度沉溺,以及所有阻礙我們達成潛在目標的障礙,都會受到災難性懲罰,除非我們動搖或改變原始渴望,擺脫原始狀態。
我不是全面否定多寧頓的見解,我也引用過他的一些觀點,但我想說的是,榮格學說對於象徵的理解過於片面,而忽視了真正的象徵主義藝術手法。德里克·庫克對此解釋得很好。
榮格學說最大的不足便是對於人物的分類過於簡單,因為它提供的類型也就這麼幾種。齊格琳德和布倫希爾德代表男性追求的對象,洪丁和哈根代表障礙,而巨龍則代表萬惡之源。又比如,《哈姆雷特》中奧菲利亞是哈姆雷特的阿尼瑪,克勞迪亞斯是他的影子,格特魯特則是“可怕的母親”,整部作品可看作一個人心理療愈的曆。同樣,最後的階段應該是沒有人真正死去,所有人都獲得重生,除了陰影,它將會消失,心理經曆了轉變後最終達到了健康的狀態。那麼,《哈姆雷特》這部傑作的含義觀眾也就一目瞭然了。
庫克把多寧頓的解釋拆分開來,正確地得出結論:“關於它最公平的說法是,它是一個‘對《指環》的榮格式的解釋’。”就像任何其他戲劇作品都可能有榮格式的解釋一樣,它並不能解釋指環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這讓我對所有精神分析的解讀有了一個普適的觀點,那就是,它們有可能用一般理論取代特定的東西,用關於我們人類是什麼的一般理論來取代特定的東西,這種深層意義存在於一些特定的戲劇中。如果《指環》不能作為一部戲劇來分析,那麼任何解釋都是無效的,也不能真正引起觀眾的注意。如果一部戲劇作品並不是按照戲劇格式創作,那麼戲劇藝術就不可能成為具有普適意義的有效象徵。通過將《指環》理解為戲劇,我們就可以接近瓦格納所說的“隱藏的深層真理”。因此,如果我們使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就應該像讓·信田·博倫(Jean Shinoda Bolen)在研究人物時所使用的那樣,而不是像多寧頓使用時那樣只是為了改寫情節。
博倫認為《指環》描寫了各種破碎的家庭,沃坦與弗麗卡、齊格琳德與洪丁、沃坦與布倫希爾德、米梅與齊格弗里德、吉比雄家族、阿爾貝里希與哈根,戲劇性地表現彼此的關聯,對女性的虐待和對父權製的否定。在她的詮釋中存在一個事實,在瓦格納的角色中,博倫發現了在她的心理治療實踐中所熟悉的衝突和考驗。然而,作為象徵,瓦格納筆下的人物所包含的意義遠遠超過博倫所看到的。如果我們看不到他們每一個行為和感受所代表的個性,那我們就錯過了整個組歌的本質含義。
 《真理之戒 : 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智慧》,【英】羅傑·斯克魯頓/著 殷萌燦/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年9月版
《真理之戒 : 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智慧》,【英】羅傑·斯克魯頓/著 殷萌燦/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