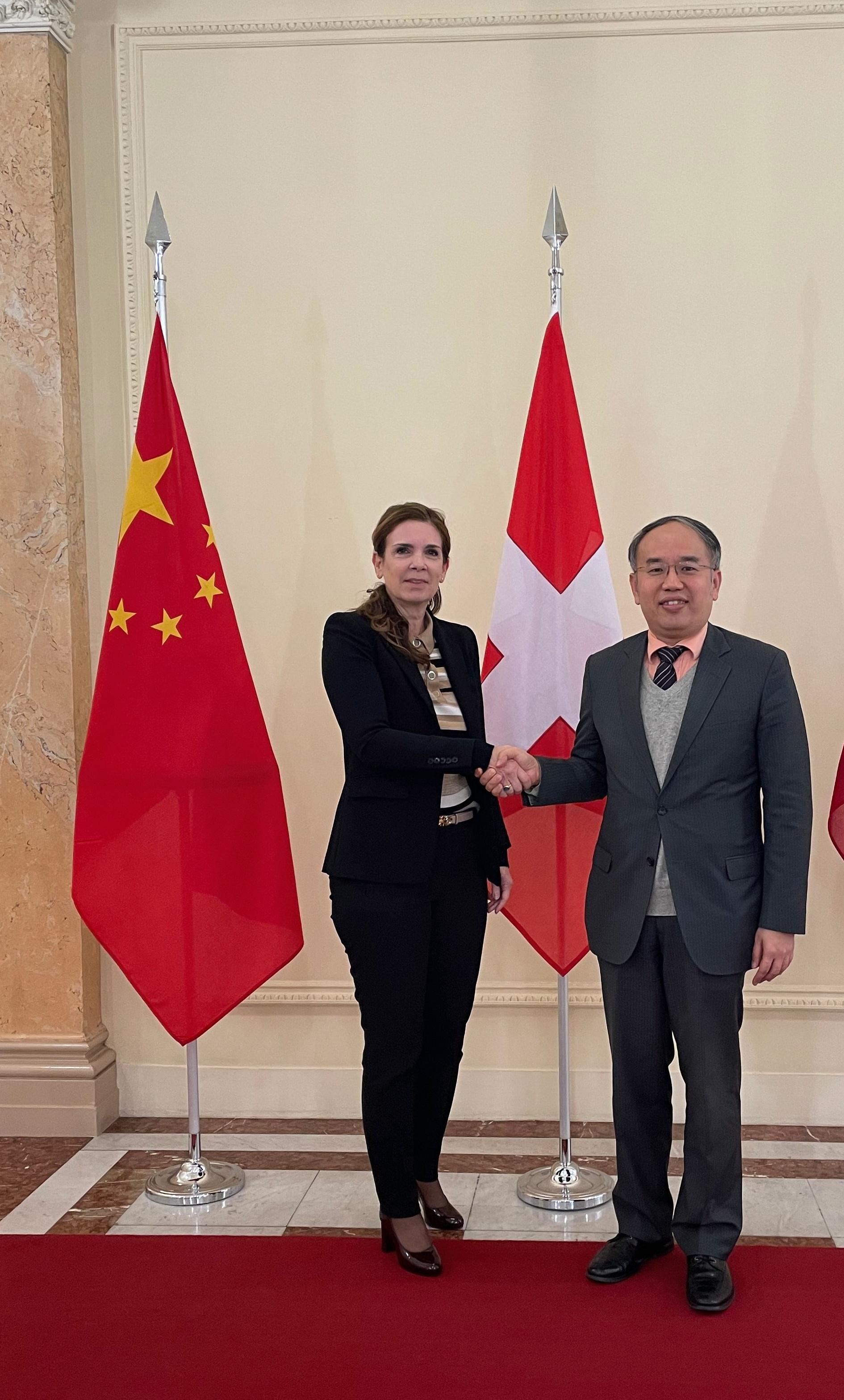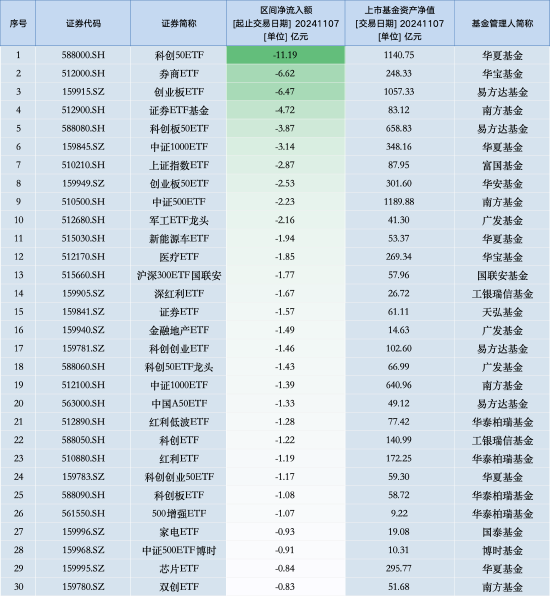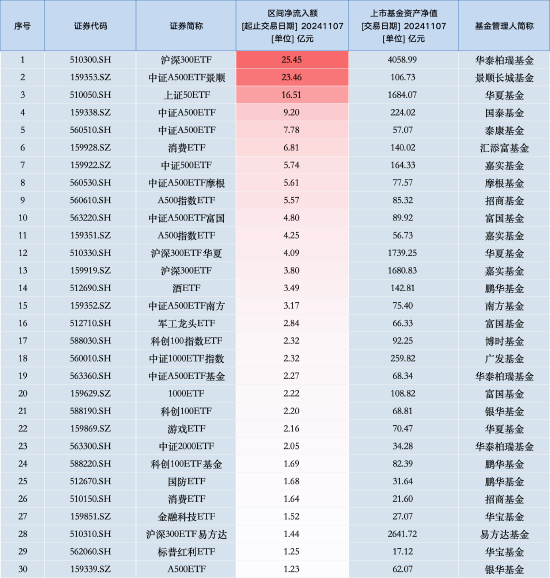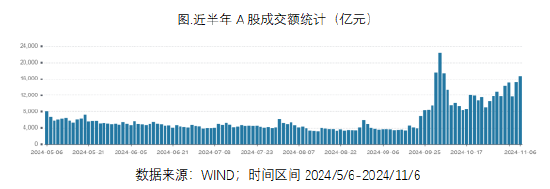“礙事的鱷魚教授”:安德森的暹羅研究之旅
|
||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大名早已因為其享譽世界的民族主義研究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而為國人所熟知。他於2014年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的盛況即為明證,不僅現場人潮湧動,媒體也趨之若鶩,讓他不由地追問,“啥事情啊,中國讀者為啥這麼愛我?”(出自戴錦華)事實上,作為東南亞區域研究專家,除了印尼之外,安德森同樣對暹羅(泰國)和菲律賓投入了大量的學術精力。1966年他和同事合作完成了針對印尼1965年未遂政變後的大屠殺事件的初步分析,後因報告流出,使得蘇哈托暴怒,從1972年禁止他入境印尼,直至1998年蘇哈托政權下台。因此他不得不調整研究對象,最終他的目光落到了暹羅。他利用1974-1975年的學術休假前往曼穀,年近40開始學起了泰語,開啟了對暹羅長達40餘年的智識探索。這一“被迫轉向”於安德森而言可謂因禍得福,因為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比較框架,把暹羅和印尼這兩個具有不同曆史傳統的國家納入其中,為他後續寫出《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奠定了基礎。毫無疑問,安德森在泰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並沒有以著作的形式呈現於眾,我以為這就是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項目要編選出版《探索與反諷:暹羅研究四十年》(以下簡稱《探索與反諷》,2014年)文集的初衷。
超越地域的想像
事實上很少有人能像安德森那樣僅靠幾篇文章就贏得了泰學研究專家的名聲,但只需從這些文章冗長的註釋就可以窺見他的用功之勤。此後至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安德森逐漸減少學術工作,他沒有再專門關注暹羅,但依然在他弟弟——同樣知名的曆史學家佩里·安德森——擔任主編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發表了《暹羅現代謀殺及其演變》(1990年)、《共產主義之後的激進主義:泰國與印尼》(1993年)。前文相當於是針對80年代在泰國上映的一部成功的商業片“槍手”的另類影評,他勾勒了政治謀殺在泰國的演進過程,並不無新奇地指出80年代來以來針對國會議員的暗殺可以看做是政治進步的結果。後篇文章不忘貫徹其比較視野,對比了泰國和印尼兩國左派勢力的不同曆史境遇和後共產主義時代的境況。泰國左翼的命運相較於印尼同伴實在是過於幸福了,安德森不失狡黠地發問,激進主義對泰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在書中安德森曾多次提及泰國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集·普米薩,他的《當今泰國薩迪納製的真面目》一書猶如一顆炸彈,扔進泰國保守主義曆史敘事建構的“平靜的池塘”中,激起了社會思潮的持續交鋒,至今仍有迴響。澳州著名曆史學家克雷格·雷諾爾斯(Craig J. Reynolds)對該書評價極高,認為集在運用馬克思社會形態學說研究泰國古代社會性質方面無出其右。他不僅完全翻譯了集的大作,還對該書及其社會影響做了深入的考察和重構,讓我們得以透過這段泰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片段來體察曆史的多樣含義(讀者可參閱克雷格專著的中譯本《泰國的激進話語:泰國薩迪納製的真面目》,2022年)。
2001年安德森正式退休,卸下學術事務的束縛,可以更加自由地追尋過去未盡的項目。新世紀他在泰國有了新的朋友圈,結識了泰國女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活動家四人組,他/她們是《閱讀》雜誌的創辦人艾達·阿倫翁、電影製作人阿彼察蓬、諷刺作家穆虹·翁帖,英國威斯敏斯特學院教師、電影評論家梅·英加瓦尼(May Ingawanij)。受這些朋友的影響,他的興趣轉移到文化、藝術上來。文集最後四篇文章就是他為泰語讀者寫作的成果,它們發表在《閱讀》《文化藝術》雜誌上。即便是看似更輕鬆的文化評論,依然能夠看出其一貫的揶揄與反諷。不論是在《兩封無法寄出的信》里對泰國政府對待曆史文化遺產的自欺欺人和嫉妒心理的點破,還是在《輪番上演的反諷》里,以廣告牌、雕像和T恤衫為抓手,比較泰國、日本和菲律賓的異同,透視背後的權力與資本邏輯。最後還有他為阿彼察蓬的《熱帶疾病》以及阿諾查的《俗物人間》撰寫的兩篇影評。阿彼察蓬是那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泰國導演,因電影審查制度,他的很多電影無法或放棄在國內上映,所以他在國際影壇上聲譽頗高,但在泰國卻曾不太為人所知,曼穀中產階級對他的接受度還不如外府普通民眾。安德森的影評里就直指這種中產階級與外府鄉村的文化斷裂,諷刺了中產階級不接地氣的品位以及追逐名人光環(包括學術明星)的浮誇。阿諾查的《俗物人間》是一部構思精巧、內涵豐富的影片,安德森也對片中的隱喻做了深度的解讀。對泰國/東南亞藝術電影感興趣的讀者,這兩篇評論不容錯過。實際上2012年安德森還出版了他所謂的業餘人類學調查的小書《農村地獄的命運:佛教泰國的禁慾主義和慾望》(青年學人王立秋已翻譯為中文並在“人類學之滇”公眾號上分六期連載)。總之,不論是專業學者,還是對泰國/東南亞政治、文化感興趣的讀者,都能夠從本書中獲益。
“擋住河道的鱷魚”
該書原版封面插圖化用了泰國俗語“擋住河道的鱷魚”,用一隻戴著墨鏡、夾著一本書的鱷魚圖像隱喻安德森在探索暹羅四十年的曆程中勇於挑戰成見,大膽分析論證又善於反諷的智性品格,圖與人高度契合,熟悉該俗語的讀者應該會會心一笑,對其他讀者而言也會被勾起好奇心吧。至於該書副標題為什麼叫做“暹羅研究四十年”?安德森一直堅持使用“暹羅”而非泰國跟他一貫的立場有關,他認為“泰國”這一國名暗示了以泰族為中心的國族意識,是對其他少數族群的不公正,因此傾向使用更具包容性的“暹羅”一詞來指代他的第二故鄉。至於“四十年”,指的是從1974年安德森開始進入泰學研究領域到2014該文集出版之前他針對泰國政治發表過公開演講。該文集一共選取了安德森在不同學術階段探索暹羅社會文化的9篇智識成果,他的同事——康奈爾大學曆史系塔瑪拉·路斯(Tamara Loos)教授為該文集撰寫了一篇精彩的導言。路斯教授不僅精當地總結了安德森各篇文章的核心內容和貢獻,而且分析了其研究興趣的轉移。鑒於此我無意再重複路斯教授的工作,而是結合自己的閱讀體會對這些文章稍作梳理,並加以自己的評述。
前三篇文章可以說是奠定了安德森泰學研究的專家地位,這段時間也是他研究泰國用力最深的時期。安德森在其回憶錄《椰殼碗外的人生》中坦承在曼穀的一年因為薄弱的泰語基礎,他無法展開任何嚴肅的研究,只能讀遍當時幾乎所有關於泰國的英文文獻。當1976年10月6日政變發生後,安德森旋即致信《紐約時報》對軍政府和美國國務院予以譴責,而當時美國的泰國研究專家們竟無一人願意聯署簽名,也許作為反擊,安德森於1977年發表了《撤軍症候:1976年10月6日政變的社會和文化面向》,從階級形成和文化-意識形態劇變兩條線索勾勒出“美國時代”背景下泰國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發展變遷的矛盾性。緊接著,1978年在一個滿是泰學研究權威的研討會上,作為學術青年的安德森宣讀了《對泰國國家的研究:泰學研究現狀》的論文,在文中,他向前輩們的智識成就發起了猛烈的抨擊,不僅提出自己新的見解,而且揭示出前輩們在知識上的政治保守立場。針對學界形成的真理性前提,安德森提出了四條“誹謗性假說”,概述如下:(1)暹羅在某些方面被間接殖民;(2)幾乎是東南亞最後一個取得獨立的民族國家;(3)卻克里王朝的貢獻是殖民地總督式政體意義上的現代化;(4)泰國領導者們一直不太靈活,國內政治屬於不穩定的典型。這些假說現在看來似乎已經被視作新的公理,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卻是大膽而尖銳的。安德森的學生、泰國法政大學政治學者卡賢·特加皮讓(Kasian Tejapira)(即本篇文獻的泰語譯者)認為其老師的綱領性文獻持續引領了後續的泰學研究發展。這依然是新一代泰國/東南亞區域研究學人無法繞開的重要參考文獻。文集把它安排在首篇的位置是再恰當不過了。
第三篇《<鏡中>導言》摘選自由他主編翻譯的泰國短篇小說譯本《鏡中:美國時代的暹羅文學與政治》(1985年)。安德森的同事都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在1983年出版了《想像的共同體》後竟然會費工夫去出版一本泰國短篇小說集。在這篇導言節選里,安德森勾勒了泰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史以及泰國左翼青年的社會文化史,從另一個面向豐富了大眾對真實的泰國社會的認知。如果不是出於真心的熱愛,我們可能無法想像安德森從零開始學習泰語到翻譯出版一本泰語小說集付出了多少心力,文學是安德森終身保持的嗜好,也是他的底色,也許通過文學他反而看到了他人未曾留意的政治線索,從而成為其學術研究的養料。反觀我們,國內也一直有對東南亞文學的譯介,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對亞非拉國家的瞭解和政治團結,曾有組織地翻譯出版過一些東南亞文學,到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新的發展,80-90年代的“東方文學叢書”出版過多部東南亞小說譯本。進入新世紀,隨著雙邊經貿關係密切、人員流動增強,流行文化的相互傳播等,國人對東南亞的興趣與日俱增,但我們依然缺乏豐富的認知途徑,而文學在促進民間人文交流上有著巨大的優勢。可喜的是,近些年馬華文學在圖書市場掀起了一股小熱潮。新近成立的“玻璃屋”團隊有誌於出版東南亞優秀的小說和非虛構作品,例如備受安德森喜愛的印尼國寶級作家普拉姆迪亞“布魯島四部曲”的第一部——《人間世》——已經修訂再版,此外還有越南小說家武重奉的《紅運》等。像安德森一樣,通過文學的橋樑,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到東南亞民眾的精神世界。
撰文/金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