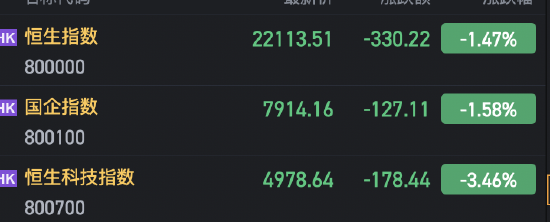數學史上的女性在哪裡?——被隱藏的“她們”
導語:在日常生活中,也許我們不難聽到這樣的說辭“女孩子不適合學數學”“男生對數字比女生更敏感”。然而我們訴諸數學史,女性的成就和光輝絲毫不遜於男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她們的天賦和勤奮啟迪並引導了男性。然而在今天的數學界,女性的所面對的障礙與打擊與以往有增無減。或許當我們不再稱呼她們是“女數學家”,數學史的寫作中不再有特殊的章節針對她們,學術界的不平等才會真正消失。

《數學那些事》作者:(美) 威廉·鄧納姆 譯者:馮速 版本:圖靈新知| 人民郵電出版社 2022年11月
如果讀者一直在做統計, 那麼很顯然, 在本書中男性出現的次數多 於女性。這種不平衡反映了數學科學中男性的曆史優勢。但是, 這是否 就意味著女性過去對這門學科沒有貢獻, 現今沒有貢獻, 將來也不會有 所貢獻呢? 以上問題的答案是“不”“當然不”“請嚴肅點”。數學史中女性的 身影可以追溯到古典時代, 而今天女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活躍。女性想在數學界生存, 就要面對男數學家幾乎無法想像的障礙, 不僅因為她們缺少鼓勵, 還因為對女性加入數學界的強烈抵製。
首先, 我們承認, 在曆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學家的短短清單中, 阿基米德、牛頓、歐拉、高斯等人清一色都是男性。在 1900 年之前, 數學界的女性人數非常少。其中經常提到的是亞曆山大的希帕蒂婭(Hypatia), 她大約生活在公元 400 年。夏特萊侯爵夫人(Emilie du Chatelet, 1706— 1749)和瑪麗亞·阿涅西(Maria Agnesi, 1718—1799)活躍在 18 世 紀, 索菲·熱爾曼、瑪麗·薩默維爾(Mary Somerville, 1780—1872)以及愛達·洛夫萊斯(Ada Lovelace, 1815—1852)活躍在 19 世紀初。19 世紀中後葉, 索菲亞·柯瓦列夫斯卡婭(Sofia Kovalevskaia, 在文學作品中也被稱為索尼婭·柯瓦列夫斯基)也躋身這一名單。

索菲婭·瓦西里耶夫娜·柯瓦列夫斯卡婭(1850年1月15日-1891年2月10日),俄國女數學家。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在偏微分方程和剛體旋轉理論等方面有重要貢獻。1888年因解決剛體繞定點旋轉問題而獲得法國科學院鮑廷獎。
在這些女性當中, 希帕蒂婭是一位頗有影響力的幾何學家、教師和 作家, 夏特萊侯爵夫人因為把牛頓的著作翻譯給法國人而知名, 薩默維 爾因為把拉普拉斯的著作翻譯給英國人而知名。1748 年, 阿涅西出版 了數學教科書, 為此得到了應有的認可。洛夫萊斯在查爾斯·巴貝奇 (Charles Babbage)製造他的第一台“分析機”時與他一起工作。熱爾曼和柯瓦列夫斯卡婭是這個清單中最多才多藝的數學家。前 者對純數學和應用數學都有研究。我們在第 F 章提到過她對費馬大定 理的研究。1816 年,熱爾曼憑藉對彈力的數學分析工作而獲得法國 科學院的大獎。而柯瓦列夫斯卡婭取得了博士學位, 並在大學擔任職務, 取得了她那個時代女性的開創性成就。在這一過程中, 她在各方面贏得了曾經對她持懷疑態度的男性同事的尊重。
所以, 在20 世紀之前, 女數學家肯定是存在的。令我們驚訝的不是她們人數很少, 而是真的存在。因為女性不僅要克服對數學充滿渴望 的人要面對的通常意義下的種種障礙, 即高級數學真實的困難, 而且還 必須克服各種各樣的文化層面所帶來的障礙。我們討論一下擋住她們 道路的三個最大的障礙。 第一個障礙是這一學科人群中對女性的普遍的負面看法, 這一看 法在不少男性和女性心中都已根深蒂固。其核心就是相信女性不具備做純數學的能力。這樣的觀念已經深深印入很多人的大腦之中, 其中不乏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據說伊曼紐爾·康德就曾說, 女性“動用她們漂亮的腦袋思考幾何問題時”會長出鬍鬚。這種評論出自一位如此重要的哲學家之口, 實在令人氣餒。
女性的稟賦不適於數學?
遺憾的是, 這樣的看法在 過去絕不是個案。在那個時代, 很多希望學習三角學或者微積分的高中女生都被指導老師、家長或朋友勸說去從事家政學或者英語這些所 謂更適合女性思維方式的學科。不管你相信與否, 這樣的狀況一直在 持續。 證明女性不能從事數學研究的諸多證據之一是從事這一研究的女性很少。換句話說, 數學界女性的缺乏被用來證明她們沒有從事這門學科的能力。當然, 這些說辭的理由是荒謬的。這與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中缺少非洲裔美國人歸結為他們沒有玩這種遊戲的素質的觀點是一樣的。正如傑基·羅賓森、亨利·阿倫和其他很多 人已經充分證明的那樣, 職業棒球大聯盟缺少黑人球員不能證明他們 缺乏能力, 而只能說是缺少機會。
上面提到的具體人物充分說明了女性也能研究數學。我們可以用近來非常活躍的女性數學家來證明這一點。格雷絲·揚(Grace Young) 在 20 世紀初高等積分理論的改進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祖莉婭·羅賓森(Julia Robinson)是希爾伯特第十問題的解決者, 還有埃 米·諾特(Emmy Noether)是 20 世紀最有成就的代數學家之一。女性不能研究數學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 但是, 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觀點就是女性就不應該研究數學。

格蕾絲·奇斯霍爾姆·揚(Grace Chisholm Young)是英國數學家。她在英國劍橋的吉頓學院接受教育,並在德國的哥廷根大學繼續深造,並於1895年獲得博士學位。她的早期著作以丈夫威廉·亨利·楊(William Henry Young)的名義出版,他們一生都在數學方面進行合作。
往好處說, 那是在浪費時間;往壞處說, 那是有害的。正如小孩子不應該走 近高速公路一樣, 女性不應該走近數學。我們以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為例, 她後來在醫學藝術領域贏得了聲 望。年輕的時候, 她對數學表現出極大的熱情, 她母親對此感到奇怪, 於是問道:“數學對結了婚的女人有什麼用?”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提到 的那樣, 人類事業中沒有什麼比數學更有用的了。但是南丁格爾卻被告 知它是無用的。鑒於強加給 19 世紀女性的各種傳統角色, 數學無論如 何都會被看成對她們毫無用處的了。
而且, 女性還被告知研究數學將有損她的社交魅力。更有甚者, 據說有什麼醫學證據顯示, 思慮過多的女性其血液將從生殖器官轉移到大腦, 並造成非常可怕的後果。令我們好奇的是男性似乎不用擔心類似 的血液流動。 這類觀點很快變成了行動, 或者更準確地說, 變成了阻礙行動的絆 腳石。熱爾曼不得不用一個男性化的筆名發表她的數學論文;柯瓦列夫斯卡婭儘管擁有不可置疑的能力, 但最初還是得不到學術地位。甚至是偉大的埃米·諾特, 她在德國哥廷根大學謀求低等職位時也遭到了冷遇。她的誹謗者堅決反動, 也有人擔心一旦女人走入這一大門, 將帶來 無法阻止的倒退。
為此, 戴維·希爾伯特用下面一段巧妙的諷刺做了回應:“我不明白這位候選人的性別為什麼成了反對她就職的依據。畢竟, 我們這裏是大學, 而不是洗浴場所。”最終諾特得到了工作, 而且這個數學團體(哥廷根大學)還活得相當好。 第二個障礙是缺乏正規教育。數學這門學科需要訓練, 高強度的訓 練。為了到達前沿, 你必須從基礎開始進發, 對於數學這樣既古老又複 雜的學科, 這需要花費幾年的努力。在過去, 很少有女性開始過這樣艱 辛的路程。因此, 她們想在高級數學中取得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
男性又是如何學習這門學科的呢?他們通常接受家庭教師的輔導, 或者一對一的授課。我們已經看到萊布尼茨去請教克里斯蒂安·惠更斯, 而歐拉與約翰·伯努利一起研究學習。這是培養把火炬傳向未來的 大師的過程。幾乎沒有女性有這樣的機會。 而男性經過適當的訓練之後進入大學, 在那裡他們的才幹和能力 將會得到進一步的培養。高斯就讀於赫爾姆施塔特大學, 旺策爾就讀於 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 羅素就讀於劍橋大學。
相比之下, 熱爾曼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人, 卻因為性別關係甚至被 拒絕進入大學講演禮堂。她只能在教室門口聽課, 或者向有同情心的男 同學借筆記來抄, 就這樣, 她秘密地跟上進度。用高斯的話說, 她所取得的成功證明了她是一位“最具勇氣”的女性。 因此, 太多的女性根本沒有實際接觸過高級數學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上面提到的很多女性家庭都比較富裕, 而且擁有相應階層的優 勢。熱爾曼可以隨意使用她父親的圖書館。薩默維爾偷聽她哥哥的家 教課程。這些富裕家庭的女兒們顯然有權選擇不去順應那些更合時宜 的傳統。正如邁克爾·迪肯對貧窮女性的數學研究前途的評論:“貧窮 和女性身份這一對絆腳石太沉重了。”把這種情況與大致同一時期的女性作家的境遇比較一下會很有趣。
讀和寫是貴婦人訓練的一部分, 儘管這隻被看成必要的社交技巧, 而不 是通向藝術生涯的手段。但是, 很多女性還是具備寫作條件。如果有充 足的時間, 充足的訓練和能力, 她們也許會利用這些條件去進行詩或文 學的創作。其中簡·奧斯丁就是一個例子, 她的作品是她對周圍人的生 活的仔細觀察, 並通過她非凡的才能加以提煉而成的。奧斯丁會讀、會、寫, 她是一位藝術家。她創作的著作使她躋身英國文學偉人之列。
很多女孩還是學習了一些初級的計算, 這倒是事實。但是與文學訓練不同, 數學學習就到此為止了。高級數學的進步需要對幾何、積分和微分方程等學科的瞭解, 每一門學問都是以前者為基礎的。如果沒有 相應的訓練, 幾乎沒人能夠掌握它們。當女性的這種訓練需求遭到拒絕 時, 她們也就無法擁有數學工具了。她們通向科學未來的大門被砰的一聲關上了。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誰是數學界的簡·奧斯丁, 因為她缺少必要的正規教育而被數學拋棄了。 這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
現在情況如何呢?表面上的障礙已經消失, 各大學也不再強製執行熱爾曼所遭遇的針對女性的禁令。正相反, 從美國各大學數學學科登記入學的數據來看, 我們有理由樂觀。在 1990 年到 1991 年的這一學年, 美國研究機構授予了 14 661 個數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證書, 其中女生有 6917 人, 約占 47%。這幾乎接近一半的比例在一個世紀前男性占主導的數學領域是不可想像的。但當我們再看一看高級學位時, 數據就令人很失望了。
就在同一學年, 女性只占獲得數學碩士學位的人數的 2/5, 而且只占獲得數學博士 學位的人數的 1/10。這種狀況表明, 儘管從數據上看接受本科教育的女性人數增長迅猛, 但是她們很少能繼續訓練, 進入研究生階段, 而從這裏開始將產生明天的研究型數學家和大學教授, 所以形勢仍然是男女不平衡。為什么女性很少能繼續進入研究生院呢?從曆史上看, 很多女性立誌當一名大學預科層次的老師, 因此沒有獲得研究型學位的需要。
嶄露頭角的繆斯
在某種情況下, 因為女性身處上述的各種觀念之下, 較低的自我評價的確對 追求更高層次的成功產生了負面影響。勇氣, 以及找到能鼓舞自己並幫 助自己掃除學習高級數學之路上的各種障礙的良師益友, 是成功的關鍵。男性有太多同行和榜樣, 而女性在競爭激烈的學術領域中總是感覺 很孤單。她們的正規教育之路在很多方面不同於她們的男性同伴。 甚至當女性戰勝了各種負面的看法, 獲得了堅實的教育時, 她們仍然面臨很多障礙:女性要滿足日常生活需求, 卻缺少全力從事她們工作的支持。
數學研究需要不受各方面干擾的大塊時間。研究型數學家要花很長時間坐在那裡思考。在過去如此, 今天也是如此, 但這樣大塊的時間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樣,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非常富有。據傳說, 阿基米德有部分錫拉庫紮王族的血統。洛必達侯爵 (Marquis de l’H[gf]f4[/gf]pital, 1661—1704)非常富有, 能僱用約翰·伯努利在新興微積分領域指導他, 繼而聞名歐洲。而我們上面所說的各位女性中, 夏特萊侯爵夫人是一位女侯爵, 洛夫萊斯則是一位女伯爵, 阿涅西 也是富人家的孩子。這些人當中沒有人靠洗衣度日。
另一方面的支持來自歐洲的各家學會, 這是那個時代的智庫。來自柏林、巴黎、聖彼得堡的各家學會的讚助養活了無數學者。在柏林和聖彼得堡取得職位的歐拉就是一位利用這樣的機會取得成功的數學家。 或者你有一份要求不高的工作, 允許你在閑暇時間進行研究和沉思。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萊布尼茨就是在巴黎的外交工作期間, 尋找時間學習了數學並最終創造了微積分。地方法官費馬似乎從來沒有盡力做法院的工作, 而是一心做數學研究。
總之, 對於有潛力的數學家, 有錢是無害的, 成為學術團體的成員, 或者只有部分時間用來工作, 都是無害的。當然, 今天對數學家的主要讚助來自研究型大學, 這些機構提供辦公室、圖書室、旅行費用、想法相似的同事以及適度的教學任務。作為回報, 學校希望數學家對這門學 科的前沿進行深層次的思考。 對照一下女性的曆史角色:在丈夫或兄弟在外面工作的時候待在 家裡, 撫養孩子、做飯、縫縫補補和照料家務雜事。即使她們有數學方面的訓練, 又如何有時間去思考微分方程或者是射影幾何呢?環境對她們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的。 事實上, 女性甚至很少有自己的空間。
正如維珍尼亞·伍爾夫在談及這類話題的短文中提醒我們的那樣, 女性很少有獨處、思考、寫作 (或進行數學研究)的空間。伍爾夫講述了莎士比亞富有想像力的妹妹朱迪思的一個故事, 她有與她哥哥一樣的才能。在她的哥哥威廉全身心投入其作家生涯的時候, 她的生活就是負責家庭的日常需要。據伍爾夫說, 莎士比亞的妹妹 和他一樣敢作敢為, 富有想像力, 熱切希望瞭解這個世界。但是她沒有被送去學校。她沒有機會學習語法和邏輯, 只能讀一點賀拉斯和維吉爾的東西。她偶爾拿起書……看幾頁。然後, 她的父母就會走進來提 醒她去補補長襪或者別忘了做飯, 而不要沉迷書本和紙墨。兄妹倆, 一個是支持的提供者, 而另一個卻是接受者。這種差別也太大了。
再說一下萊昂哈德·歐拉, 13 個孩子的父親。必須有人來撫養孩子們, 替他們換尿布, 清洗他們的衣服。但是這個人不是萊昂哈德。再看一下斯里尼瓦瑟·拉瑪努金(1887—1920), 他是 20 世紀初一位非常有才華的數學家。但在日常生活中, 他卻像一個孩子那樣無助, 他的 妻子照顧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再看保羅·埃爾德什, 這個人我們在前面遇到過, 他在 21 歲時才學習如何往麵包上塗黃油。顯然, 他在進行數學發現的初期, 得到了來自母親的不同尋常的支持。

斯里尼瓦瑟·拉馬努金,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英屬印度人,是英屬印度史上最著名的數學家之一。沉迷數論,尤愛牽涉π、質數等數學常數的求和公式,以及整數分拆。慣以直覺導出公式,不喜歡做證明,而他的理論在事後往往被證明是對的。他所留下的尚未被證明的公式,啟發了幾位菲爾茲獎獲得者的工作。
如果交換一下, 情況又如何呢?歐拉夫人、拉瑪努金夫人和埃爾德什夫人如果在數學上取得了成功, 她們的另一半會滿足她們的日常生 活需要嗎?如果這些女性已經成名, 那麼她們可以投入大塊的時間去研究數學嗎?沒有人知道答案。但是, 如果女性能夠得到與這些男人相 同的支持, 那麼她們之中會有更多人出現在數學編年史中。這是毫無疑 問的。
在索菲亞·柯瓦列夫斯卡婭這位“20 世紀前最偉大的女數學家” 的生活中, 上面提到的所有障礙, 如數學教育方面的負面觀念和困難以及缺少系統的支持, 都出現過。
被邊緣化的天才
1850 年初, 柯瓦列夫斯卡婭出生在莫斯科, 並在一個比較富裕的書香之家長大, 她有一名英語家庭教師, 並有機會學習數學。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說, 她臥室的牆上貼滿了她父親的微積分課程的舊講義筆記。 這位年輕的女生被這些奇怪的公式深深吸引了, 它們就像朋友一樣靜靜地圍繞在她的身邊。她發誓有一天一定要知道其中的秘密。
當然, 這需要訓練。一開始, 她學習了算術。她被允許參加她堂兄 的家教課程, 家人這麼做基本上是為了勸誘她堂兄更加努力地學習。就 這樣, 她獲得了代數知識, 而她堂兄還是學不會。接下來, 柯瓦列夫斯卡婭從住在附近的物理學家那裡借來一本他寫的書看。在讀這本書時,她遇到了三角學的困難, 這是一門她幾乎一無所知的學科。不願意放棄 但又得不到適當的指導, 柯瓦列夫斯卡婭就從零開始做起了研究。當她 的物理學家鄰居意識到她在做什麼的時候, 他驚奇地發現, “她已經第 二次創造了整個三角學這門學科”。
這樣的成就顯示了超凡的數學創造力。在她 17 歲的時候, 她和她的家庭來到聖彼得堡。在那裡, 柯瓦列夫斯卡婭說服了反對她學數學的父親, 接受了微積分的家教課程。儘管她是一位女性, 但是憑藉如此的才能, 她本應該立即進入大學。遺憾的是, 對於一位 19世紀的俄羅斯女性來說, 她沒有這樣的選擇權。
以現代的觀點看, 她對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的反應有些極端。在 18 歲的時候, 她自己決定與一位準備前往德國的年輕學者“假”結婚, 她希望通過這樣的婚姻得到進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個男人是 弗拉基米爾·柯瓦列夫斯基, 一位自願參與這次“虛假婚姻”的古生物 學者, 他認為這對女性解放有利。他們兩個人動身去了海德堡大學, 表 面上維繫著婚姻關係, 事實上各自從事著自己感興趣的研究。
柯瓦列夫斯卡婭在海德堡一如既往表現得非常出色, 所以在 1871 年她瞄準了更高的目標:柏林大學, 以及它令人尊敬的高級數學教授卡爾·維爾斯特拉斯(1815—1897)。下定了決心的柯瓦列夫斯卡婭安排了一次與這位世界著名學者的見面, 懇求他的指導。維爾斯特拉斯在提 出一些非常有挑戰性的問題之後就把她打發走了, 他不希望再見到她。
但是, 他還是再一次見到了她。一週後, 柯瓦列夫斯卡婭手裡拿著 答案回來了。用維爾斯特拉斯的評價說, 她的工作展示了“對維度的天才直覺……這甚至在過去的學生或者層次更高的學生當中都是很少見 的”。她讓這位當時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從她的懷疑者變 為她的仰慕者。
由此, 年邁的維爾斯特拉斯和年輕的柯瓦列夫斯卡婭開始了長期的合作。她的精力和洞察力贏得了他的尊敬, 而且他還安排她與歐洲很多數學團體接觸。在維爾斯特拉斯的指導下, 柯瓦列夫斯卡婭開始研 究偏微分方程、阿貝爾積分以及土星環的動力學。由於這些成果, 1874 年, 她獲得了哥廷根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她是第一位獲得現代大學博士學位的女性。
一生中, 柯瓦列夫斯卡婭不僅對數學感興趣, 而且對社會和政治公平等議題也感興趣。作為一名自由主義活動的支持者, 她支持女權運動和波蘭人的獨立。當時她給一家激進派報社寫文章。在她丈夫的幫助 下, 她在1871 年公社期間秘密進入巴黎, 當時這座城市被俾斯麥的軍 隊包圍了。在這次冒險中, 她被德國士兵的子彈擊中了。到了巴黎, 她病倒了, 受了傷, 還與這座被包圍的城市的激進派領導人取得了聯繫。這就是一個渴望實現自己的社會信念的人物。
除了是科學家和革命者之外, 她還是一位作家。柯瓦列夫斯卡婭寫小說、詩歌、戲劇以及《童年的回憶》, 後者是一本自傳式的童年記錄。 她在俄羅斯度過了青春, 因此她見到過杜斯妥也夫斯基, 在後來的生活 中又認識了屠格涅夫、契科夫和喬治·艾略特。這位有社會責任感的 數學家進入了著名的藝術圈子。
總之, 索菲亞·柯瓦列夫斯卡婭擁有各種驚人的才能。聰明、果斷、 伶牙俐齒, 因此她被同時代人描繪成“簡直是光彩奪目”。 下一頁的 畫像展示了這位有著超凡脫俗的人格魅力的女性, 人們創作了很多關 於她的暢銷書和電視連續劇。
如同所有連續劇一樣, 她的故事以喜劇開場卻以悲劇收場。儘管她的婚姻背景很特殊, 但是她與丈夫產生了真正的愛情, 這對夫婦於 1878 年生了一個女兒。但是五年後, 一次生意上的失敗使他損失了大量財產, 之後, 沮喪的弗拉基米爾·柯瓦列夫斯基吸食三氯甲烷自殺了。索 菲亞成了寡婦和單身母親。
幸運的是, 她還是世界一流的數學家。在維爾斯特拉斯的另一名弟 子米特格–雷弗勒的熱情幫助下, 她被指定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任教。1889 年, 她成為該校的終身教授, 這在數學界對女性來說也是第 一次。
在斯德哥爾摩的那段日子也並非沒有困難。對女性固有的偏見又 阻礙著她對進步事業公開而堅定的支持。那些保守的學者們因為對她的數學無可挑剔, 轉而指責她與一位著名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接觸。而維爾斯特拉斯和米特格–雷弗勒也委婉建議柯瓦列夫斯卡婭採取更謹慎 的政治態度。但是她沒有這樣做。
在數學這一邊, 她被指名擔任《數學學報》雜誌的編輯, 她是擔任這一職位的第一位女性。她與埃爾米特和切比雪夫(我們在前面遇到過他)等數學家聯繫, 併成為俄羅斯數學團體和西歐數學團體的重 要紐帶。1888 年, 柯瓦列夫斯卡婭獲得法國科學院的鮑廷獎, 獲獎理 由是她的論文《剛體繞固定點的旋轉問題》, 由此國際盛譽、媒體報導以及賀信迎面撲來。這樣的喝彩聲足以使她獲得俄羅斯皇家科學院的會員資格(作為一名女性, 在她的祖國, 這樣一個學術職位還不足以養活她)。
1891 年, 充滿希望的未來似乎就擺在這位著名人物的面前,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災難突然降臨。在去法國的途中, 柯瓦列夫斯卡婭開始咳嗽, 好像患了普通的感冒。但是, 當她返回斯德哥爾摩時, 在陰雨和寒冷的氣候條件下, 她的身體狀況變得更糟。回到家裡, 她變得太虛弱以至於無法工作。一次昏迷過後, 1891 年 2 月 10 日, 柯瓦列夫斯卡婭去 世, 年僅 41 歲。
一如既往, 當這樣一位天才永遠地離去的時候, 她給世人留下了驚歎、無盡的懷疑和沒有實現的夢想。整個歐洲傳來了人們的讚美之聲, 隨之而來的悲傷也是真誠的。我們無法估計柯瓦列夫斯卡婭原本還能為數學做出什麼樣的貢獻, 我們也無法知道這樣的貢獻會使這門學科中的女性地位提高多少。
柯瓦列夫斯卡婭這樣的天才是罕見的, 但是自她去世後, 在20 世 紀, 女性進入數學領域已經越來越普遍。但隨之出現了一個麻煩的問題。我們把本章獻給女性數學家, 是否反而令她們更顯邊緣化, 反而被當作異類?我們是否應該有罪惡感呢?隨著眾多女性進入醫學和法律 等專業領域, 很少有人談及“女醫生”或“女律師”。在本章, 我們並不是說數學職業應該分成兩組:數學家和女數學家。這當然不是我們的意圖, 而且它也不是真實的現狀。但是, 有這樣的危險。
這是祖莉婭·羅賓森的觀點。隨著她聲望的增大, 當她進入美國科學院並獲得麥克阿瑟獎的時候, 她被視為在男性領地上獲勝的女性。在一篇非常重要的短文中, 她寫道:“所有這些關心都令人愉快, 但也令人感到困惑。我就是一名數學家。我更希望僅僅因為我證明了一些定理或者解決了一些問題而被記住, 而不是因為我是第一位這樣、那樣的女性。”
儘管需要進一步根除女性所面對的不平等, 但我們有理由對實現羅賓森的願望充滿信心。很多偏見和障礙正在消失, 投身數學的女性已經開始增多。即使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完全解決, 但是不可否認, 進步已成事實。我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 提出“女性在哪裡?”這樣的章節會 被認為完全沒有必要。
作者/(美)威廉·鄧納姆
譯者/馮速
編輯/袁春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