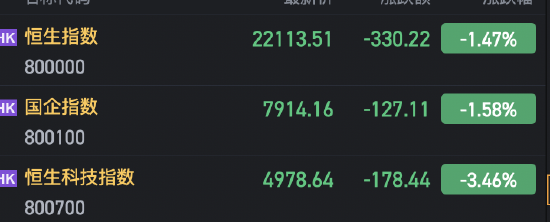科幻與社會學|《基地》與社會變遷(下)
科幻與社會學|《基地》與社會變遷(上)
科幻與社會學|《基地》與社會變遷(中)
六、預測社會變遷的趨勢
預測社會變遷的具體因素
討論了社會變遷的宏大理論之後,更為具體的問題應該是將這些理論應用於實踐。到底有哪些具體的因素影響社會變遷的過程?社會變遷的趨勢又是如何可以從當前的社會狀況推演出來的呢?
總的來講,推動社會變遷的具體因素大體上包括自然環境、人口資源、經濟水平、科技發展、政治情勢、價值觀念、文化倫理、社會心態等。需要說明的是,社會變遷是一個連綿不絕的過程:在特定的時點,社會變遷的結果會表現為上述這些因素的特定狀態;同時,這些狀態又是接下來社會變遷進程的起點與決定因素。在《基地》中的心理史學中,這些因素已經納入在預測模型里,只是沒有標明利用這些資料的具體數學算法。
 《基地》第一季劇照
《基地》第一季劇照數學計量模型
說起算法,毫無疑問,心理史學的預測過程應該是,一整套包含了初始參數、輸入數據與資料、特定算法模型的運算結果。這些術語與社會學的一個細小分支領域,數學社會學,更為相關。一般的結論認為,數學社會學的概念在1940年代早期,由理論物理學家拉舍夫斯基(Nicholas Rashevsky)與數學家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最早提出來(對,這兩位科學家和阿西莫夫一樣,都是從前蘇聯移民到美國;拉波波特就是那位在1984年參加阿克賽爾羅德的“囚徒困境”競賽,寫了4行Fortran語言的程序,並且一字不改提交2次,然後簡單直接地贏了2次的數學家兼心理學家),他們將數學程序和數學模型用於社會學的純粹理論研究之中。這兩位科學家堅信,數學不僅是一種思考的語言,同時是威力強大的工具,當數學與社會學思想緊密結合時,能夠以數學模型的形式,在解釋社會生活的過程中給出更為一般的、更具解釋力的理論結果。
顯然,這些數學家認為,數學是宇宙中最為精妙、最為準確的語言,人類社會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數學的語言表達出來。並非完全巧合的是,阿西莫夫構想心理史學的1940年代早期,跟拉舍夫斯基與拉波波特提出數學社會學的構想,基本同步,顯示這一社會思潮在當時的影響力極為廣泛。需要指出的是,哈里·謝頓在《基地》的身份也是一位數學家。
個體層次到宏觀層次的“湧現”機制
詹姆斯·科爾曼1964年的《數學社會學導論》更進一步奠定了數學社會學的基本原則與實踐方法技術,數學社會學更廣泛地使用線性代數、圖論、博弈論和概率分析等數學方法,來解釋人們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的策略選擇、流動軌跡、因果關係、關係網絡等行為與結構。這些用於搜尋因果機制的數學社會學模型,更是有著與心理史學相似的理論目標——也可以用來預測未來與製定應對措施。使用微觀數據,得出宏觀社會變遷趨勢的過程,需要社會科學中特定的從微觀(個人層次)“湧現”到宏觀(社會整體層次)的機制轉換。所謂“湧現機制”,是指僅僅由於單純數量上的聚合,使得群體在整體層次上顯示一種新的特徵屬性與行為模式;同時,其產生影響與效果的過程,與個體層次的行為與動機沒有直接關聯。比如,在美國亞裔學生(特別是東亞與南亞裔學生)學習內卷,學業成績鶴立雞群;這使得他們在大學申請的競爭中占有學業優勢;其他族群因此針對此一問題發難,要求限制亞裔學生學業優勢在申請過程中的錄取比例;這反而使得整個亞裔群體受到“反向”的學業歧視。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個體層次的努力的結果——因為群體間的競爭過程——反而帶來整體群體競爭的劣勢的湧現機制。如今,計算社會學更進一步使用計算機模擬、人工智能以及複雜統計等方法與工具,來演算模擬社會行為與社會進程,達到解釋與預測的目標。
 詹姆斯·科爾曼出版於1964年的《數學社會學導論》
詹姆斯·科爾曼出版於1964年的《數學社會學導論》曆史動力學:宏大尺度上的趨勢分析
無獨有偶,近兩年美國學者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退休前擔任康尼狄格大學生態與進化生物系、人類學系、數學系三系合聘教授,現擔任牛津大學人類學院與維也納複雜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對,他也是在1970年代末從前蘇聯移民美國的),因為在2010年做出了預測,美國和歐洲在未來10年陷入不穩定狀況(包括社會政治暴力浪潮的出現),而聲譽鵲起。事實上,圖爾欽更重要的學術貢獻在於,他建構了曆史研究方法“曆史動力學”(clíodynamics;Clío是古希臘神話中掌管曆史的繆斯女神,這一術語是圖爾欽在阿西莫夫1992年去世後的次年生造出來的),運用數學模型分析曆史大數據,預測了人類曆史上社會經濟發展,顯示出了鮮明的週期性勞動生產率下降、工資下降、出生率降低,這些特徵一致性地反復出現在世界各國的曆史上。圖爾欽的抱負十分雄偉,希冀著能夠使用數學模型,尋找到遙遠曆史上的社會變遷規模,然後用來預測未來。
前面提及的心理史學與數學社會學、曆史動力學、計算社會學、大數據行為分析等學科領域,相互之間有著重要的差異:有的是虛構的,有的是真實的學術研究;它們研究的對象涵蓋曆史、當前、未來,以及模擬情形。但是,這些學科領域有著相同的關於如何理解社會的基本哲學觀念,那就是人類自身的過去,留下了不可磨滅與有意義的痕跡;人類自身的未來,也必然是從現在出發。因此,作為世間最偉大的刻畫者,數學可以找到人類社會的過去,也能夠發現人類社會的未來。
七、《基地》與社會學的學科學術糾纏
虛構心理史學的目的在於推動小說情節的展開。但以此來蓋棺定論阿西莫夫的《基地》與社會學之間的學科學術糾纏,那就實在是低估了他作為一個天賦超人的科幻以及科普作家的洞察力了。事實上,阿西莫夫在22歲就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機器人三法則,即:第一法則,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者在人類受到傷害時熟視無睹袖手旁觀;第二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發出的指令,除非該指令與第一法則相衝突;第三法則,機器人必須維護自己的生存,除非與第一、第二法則相衝突。如今,人工智能飛速發展,但阿西莫夫的“三法則”仍然是學術界與科技界預設的思考機器人的基本出發點。
阿西莫夫的思考與社會學的緊密關聯
現在來看,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用來討論阿西莫夫與社會學學科的直接關聯。但是,從思想體系中可以輕鬆看出,阿西莫夫的未來世界的構想與社會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梳理《基地》的各種關於社會設定的思路中,可以得出,阿西莫夫借鑒了當時社會學重大的學科學術進展,也構想一系列未來的學科知識體系。這兩者的相互糾纏顯得如此明顯,成就了《基地》可能就是社會學意味最濃的科幻小說。
阿西莫夫是在1941年打定主意開始構想《基地》,並於1942年5月發表了第一篇短篇故事,隨後幾年中連發8篇。這一時期,阿西莫夫在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完成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學習(其間,他短暫應徵入伍)。可以說,《基地》就是阿西莫夫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研究生時期的作品。
哥倫比亞社會學
我們再來看看同一時期,社會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情形。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是1894年成立,是芝加哥大學之後在美國設立的第二個社會學系。在芝加哥社會學系一統江湖40多年後,發生了一件爭奪學術影響力的標誌性事件。那就是,1936年美國社會學學會設立新刊《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替換掉芝加哥社會學系創辦的系刊《美國社會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成為新的學會會刊。從此以後,其他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科影響力開始上升,哥倫比亞社會學系與哈佛社會學系名列其中。當時已經聲譽卓著的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與保羅·拉紮斯菲爾德(Paul F. Lazarsfeld)於1940年與1941年,先後來到哥倫比亞社會學系,扛起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方法研究的大旗,推動哥倫比亞社會學系,成為芝加哥社會學系影響力下降之後,能夠與之抗衡的社會學重鎮。另一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帕森斯在這之前的1937年出版了《社會行動的結構》,標誌著結構功能主義成為壓倒性的美國大一統社會學理論,主宰了二戰以後整個社會學學科,引領了社會思潮,在整個社會科學界也影響巨大。帕森斯本人也因為這本書的出版聲譽鵲起,後來他擔任過眾多顯赫學術機構的領導職務,也培養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學生(默頓就是其中後來名氣最大的學生),奠定了自己作為美國當代社會學與社會科學大師的地位。
 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
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現在無從查考阿西莫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哥倫比亞社會學的影響。但給定當時社會學學科推動社會思潮狂飆式的發展——特別是在二戰結束前後社會議題成為整個美國社會關注的重心,給定哥倫比亞社會學繫在社會學學科內的重大影響力,很難想像身處哥倫比亞大學校園里,涉獵廣泛、酷愛閱讀與思考的阿西莫夫沒有關注到這些學科學術的動態。因而,從成書於這一時期的《基地》中,能夠讀出濃烈的社會學味道,也就不足為奇了。
社會學的宏大理論與《基地》的設定
讀到《基地》中銀河帝國的設定,以及心理史學所展示的社會變遷過程時,一個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可以輕易地聯想到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雖然說帕森斯的另一本著作《社會系統》出版於1951年,但整個1940年代,帕森斯理論的基本思想在《社會行動的結構》基礎上已經成熟並廣為傳播,成為最為主要的社會思潮。在帕森斯的理論中,行動系統與社會系統的結構,對應著適應、目標達成、整合與模式維護等四種功能(AGIL),使得整個社會體系能夠均衡運轉。在這個體系中,社會變遷通過分化、提升適應力、容納與價值整合等過程自我調節實現進化。心理史學所預測的銀河帝國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基本都是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完成,政治、軍事、文化、社會以及文化等各個因素都有著分化變動的趨勢,推動著帝國的曆史進程。
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明確點出了北方蠻族的入侵以及東方阿拉伯人的進攻,是羅馬帝國衰亡的重要外來影響力。而《基地》的銀河帝國的社會系統設定,是與此論斷相反的帕森斯主義的封閉系統。這一功能系統的設定,在後期的《基地》系列寫作中,才開始有所鬆動(而此時帕森斯的理論在學術界飽受攻擊,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輝煌),阿西莫夫暗示銀河帝國中有另外的智慧生命。當然,這種設定下的心理史學,其預測人類社會未來的過程與模型,也應該有相應的巨大改變,整個《基地》三部曲的情節與寫作也許又應該是另外一番場景。
“社會事實”與定量社會學研究
阿西莫夫在《基地》的底層社會設定中,將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理解為“社會事實”,因而是可以測量並轉化成數字的,進而可以運用數學工具分析加工,達到預測社會演化過程的終極目的。這樣理解社會的哲學觀念,一方面與阿西莫夫理科知識背景相一致;另一方面也與當時的哥倫比亞社會學系的學術傳統相一致。作為帕森斯最有成就的學生,默頓並不完全沿著其導師的學術思想前行,他斷言宏大社會理論的時代尚未到來,社會學研究應該更多地專注於“中層理論”。而拉紮斯菲爾德正好是一位擅長使用社會調查收集數據,使用數學、統計學分析數據得出中層結論的專家。這兩位社會學大師,奠定了當代社會學定量分析方法與過程的基本原則,開創了到現在為止依然最為重要的社會研究範式。從某種意義上講,阿西莫夫在80多年之前的1940年代初,設想極為類似的理解社會與預測社會的方法,顯示了他非凡的想像力。阿西莫夫不僅僅成功預測了一系列“硬科學”技術在未來的誕生,也預見了“軟科學”技術在未來的應用。
心理史學與大數據分析
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學的內核思想觀念,在當前運用大數據的計算社會科學中有著同樣的體現。進入數字時代,生活在數字社會中的人們,一舉一動都留下了數字痕跡,這些數字痕跡構成了數字社會中的大數據。計算社會科學家堅信,通過分析無所不包的大數據,可以展示人們相互之間通過數字網絡連接的複雜性,最終揭示人類活動的規律,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輔以人工智能的計算過程,根據這些“即時”痕跡數據的分析結果,可以輕易轉換成“實時”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直接進入到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參與人們的決策過程。
 交通數據
交通數據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對實時交通數據的收集(包括出行時段、行車路線、花費時間、駕車習慣、速度控製等等),可以生成交通大數據,被用來挖掘分析交通出行狀況。當數據足夠時,可以進一步細分在特定場景下的交通情形,給出導航指導路線。例如,冬天大風降溫的週一,在早晨7:30上班高峰時間,在途中某地點內車道出現了車禍,清華大學到動物園的各條路線中,導航數據能夠找出一條最便捷的路線。這是因為,收集的大數據已經重複覆蓋過多次不同以及相似的交通情形,通過智能計算挖掘整理,可以直接用以往的大數據模擬現實的情形,給出實時導航。記得數年前,最早期導航數據給出的結果並不準確,甚至不如一些老司機的經驗有效。隨著收集的交通大數據越來越多,實時導航越來越精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當成“就是”未來的即時情形),作為用戶完全可以信任大數據導航。顯然,心理史學預測未來社會的基礎邏輯,與大數據分析結果應用於實際生活完全一致。“謝頓計劃”也正是根據當前的社會狀況數據,來預測並改變未來社會變遷的進程。
心理史學的根源與基礎社會學思想
可以想像,當年孔德創立社會學時的心態、塗爾干思考實證主義社會研究範式時的心態、構想心理史學時的阿西莫夫的心態,以及當前大數據分析熱情投入者們的心態,應該是高度相似的。他們都認定,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是可測量、可轉化成數字的“事實”,現在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是可以解釋為因果機制,而未來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則完全是可以預測的。只不過,孔德命名他的學問為“社會動力學”;而阿西莫夫則使用了“心理史學”。我們發現,當今的大數據社會計算的代表人物之一、MIT人類動力實驗室的阿萊克斯·彭特蘭,在他2014年出版專著中討論了大數據社會計算如何帶來創新思維傳播(很遺憾,2015年出版的中文版將書名更改為《智慧社會》,譯者顯然誤讀,或因為商業原因故意忽略了彭特蘭的哲學思想的淵源),並命名他的 “新學問”為“社會物理學”(英文書名直接就是Social Physics)——他明確追溯自己的思想來自孔德。
心理史學有兩個前提假設。一是,心理史學只能作用於大規模人口,不能預測特定的個人與小群體,這與社會學的學科前提一致。二是,心理史學的應用過程中,人類對於觀測過程並不自知。這第二個前提假設在社會學的研究中,鮮為人所認可,反而常為人所詬病。這是因為,社會學家的隊伍中,另有一部分並不確定,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是獨立於人們思想的“事實”。在韋伯的研究方法思想中,社會學的確應當研究社會行為(與孔德、塗爾幹一致);但他卻認為,因為人的行為隨時隨地為自己的思考所決定,所以社會行為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社會事實”,而是蘊含著豐富的社會動機與社會意義的過程。在韋伯看來,社會研究的方法並不應該是嚴苛的實證主義,理解與詮釋人們社會行為動機與意圖的人文主義方法,可能更適合用來研究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也只有在理解了社會行為動機的基礎之上,才能夠尋找到其背後的因果機制。這兩種不同的理解社會的哲學觀念,導致了基礎社會研究方法的差異。
另一種社會研究的範式
可以想像,從韋伯的思想出發的社會研究,一定將在基礎方法論上,與大數據計算社會科學的方法產生根本性的衝突。因為,在韋伯的門徒們看來,大數據無法完全捕捉行為背後的動機與價值體系。當然,大數據計算社會科學者們可以進一步爭辯,人們的行為呈現了動機與意義,只要數據足夠巨大,終究可以涵蓋變化多端的動機與意義。這樣的爭論可以繼續下去,而對於動機與意義的假設變得至關重要。如果認為人的智能基礎是自由意誌,而自由意誌高於一切,趨於無限;那麼大數據的測量與預測不可能完全準確,而是永遠處於隨時出錯的可能;同時,基於學習的人工智能,即使可能發展自己的智能並超越人類,也永遠無法完全學習與複刻人的智慧。也正是這樣的爭論涉及到了更為根本的哲學原則,也許應該把它留給科學討論之外的領域。
八、餘音:社會變遷中的人能做些什麼?
預測未來的願望
人們在追逐富足的同時,也總是希望富足的生活能夠確定到來。暗含在這樣的美好願望背後的就是,一直希望擁有預測未來的能力。對於阿西莫夫這樣的天才來講,成年之後他就用不著擔憂眼前是否有富足的生活,從他19歲用稿費支撐生活開始,富足的生活唾手可得。他的思緒更多地放在思考人類社會的未來,他給出了眾多關於未來人類社會的預言。毫無疑問,阿西莫夫也期盼人類社會,能夠有著確定的美好未來。這應該也是《基地》中的謝頓創立心理史學的初衷所在。
沿著這樣的思路往下,可以想像得到,應該有著更多的學者致力於預測未來。在研究社會變遷演進理論與機制的同時,也將各種社會生活與生產的過程數字化,進入更為簡潔清晰的數學統計模型中,推演出確定的未來。接受以上這些學說,意味著堅信社會進程是有著明確規律的,並且這些規律是能夠為人類理性所無限接近的。
預測未來的困境
這樣的結果就是,即使我們普通人無從知道,有時也無從理解,但是社會的進程是確定的,我們只不過生活在有著自身運行軌跡的曆史過程之中。深入一層思考,這帶來一個“預測未來的悖論”:社會有著自身的演進過程與運行邏輯,人類的理性能力才能夠認知這一規律並提前預測未來;但是反過來,也正是社會有著自身的規律,人類的理性能力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聽起來似曾相識,跟康德的第三組“二律背反”有些類似)。在這一點上,謝頓顯然有些自相矛盾:如果未來真的可以被修改,那人類的理性怎樣去理解社會之中恒定的規律呢?更加令人難過的是,任何折中的想法,都只能是指向一個讓人不願深思的、更為黑暗的結論:未來只能夠被部分人所修改。
在積極預測未來的同時,也必然需要承受未來所帶來的一切。
這可能帶來一種無奈的感受。在茫茫的曆史長河之中,在可預知的未來社會之中,人是不是終將歸於一粒無足輕重的塵埃?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生活在社會之中的人們,將只能夠隨波逐流,順勢而為了。或許,可以稍微積極一點,在社會變遷的大趨勢之下順其自然;也要在眼前的具體生活中,尋找人世間煙火的五彩斑斕。
正如康德所言,既要仰望“頭頂的星空”,也要堅信“心中的道德”。
那接下來的問題,立即轉換成了,從何處才能夠更好地尋找社會變遷演進的“趨勢”呢?沿著阿西莫夫的思想軌跡,應該瞭解得到,未來趨勢藏在人類過去的曆史之中,在對於社會的深刻理解之中,在對於社會變遷機制的深入探索之中。更為簡潔的,阿西莫夫可能還會說,在數學這一描述宇宙最美的語言之中。所以,阿西莫夫也許會說,從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當然還有數學中,能夠找到社會變遷演進的規律。
能夠確定的就是未來的不確定
反過來思考,未來可能又將展示另一幅圖景。
不用說心理史學能夠預測,3萬年間的銀河帝國的變遷軌跡與曆程;如果任何一位學者能夠預測自己一生所涵蓋的曆史進程,必然成為所有學者景仰的聖賢。事實上,所有事關人類社會未來的預測,都有或多或少的謬誤。不僅僅阿西莫夫本人的預測中,有的失之偏頗;在《基地》的“謝頓計劃”中,也沒有預測到騾(Mule)的出現。作為一個突變個體,騾橫掃大半銀河帝國的疆域,險些徹底破壞了“謝頓計劃”。
在預測人類社會變遷演進的工作中,必然面臨測量與計算的誤差,這樣也將帶來預測結果的不準確。在現實生活中顯示出來的則是,人們的社會生活必然面臨著不確定性。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人與科技之間的社會連接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使得人們的社會生活瀰漫著各種不確定性,極大地增加了社會的焦慮。過去三年的新冠病毒對於全球的衝擊,正好就是一個例證。
事實上,前面提及的“預測未來的悖論”下謝頓的矛盾,絕不僅僅顯示預測中一定會有偏誤。更重要的是,它顯示了人類理性的力量一直在探知自身的邊界,而這一邊界往往處於人類能夠掌控與無法掌控的模糊地帶。
因此,有人堅信,人類社會最大的不確定性必然是人類自身。因為人太複雜,經常還會胡思亂想。正如韋伯所言,人們一定會思考意義與價值,因此人們的社會行為一定蘊含動機與意義。自由意誌是人類最為本質的屬性,人生而為思。
青春期的叛逆
讓我們簡單討論一下青春期的叛逆。很多時候,青春的選擇是這樣的,“我將要這麼做,你知道我會這麼做,於是我知道你知道我會這麼做,然而我偏偏就不這麼做”。青春期的叛逆是人類青少年的基本屬性,跨越所有地域與文化(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討論了在特定社會中,青春期叛逆並不存在,成為了人類學經典著作,可能也成為了人類學學科曆史上最大的論爭;後來有學者重訪米德的田野,否定了她的研究結論;論爭逐漸收斂於,青春期的生理學基礎比文化的影響力來得更為根本更為重要)。為人父母的有時會慨歎,給人類社會帶來這麼多資源浪費的青春期叛逆,為什麼沒有在進化曆史長河中被淘汰掉。事實上,可能與之完全相反,青春期的叛逆完全有可能就是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進化優勢。因為,通過漫長的社會化過程,進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承接上一代的各種社會規範;而此時的青春期叛逆凸顯了代際之間的差異,確保新的一代在傳遞社會規範的過程中,能夠形成社會變異,這無疑給演化中的人類社會帶來了進化優勢。
 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
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因此才會有,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叛逆傾向顯著的青少年都是才能出眾之輩;但是,一代人中未來最有成就的那一批往往是在青春期最叛逆的那一部分。所以,有極大的可能,在人類已經沒有什麼生態壓力的條件下,青春期的叛逆維繫著人類的進化優勢,並加速了人類進化的步伐(每一代都有變異),成為人類保持長久創造力的根源。
自由意誌與理性牢籠
人類的自由意誌是人類社會不確定性的根源。一方面,因為人類能夠思考,才會在理性的道路上狂奔,甚至無限接近預測未來。但是,這樣追逐理性,也必將陷入韋伯所擔憂的理性的“鐵籠”。另一方面,也正是人類的自由意誌,能夠保持進化優勢,保證代際的差異,保有逃離“鐵籠”的可能。
在這兩派的討論之中,韋伯的理性“鐵籠”又注入了新的數字時代的內涵。人類理性已經找到了更為強大的代理,人工智能的運算能力看起來正在不斷突破人類自身認知的邊界,它成為前面提及的聖賢也許只是時間問題。天才的索菲·科瓦列夫斯卡婭(對,又是一位俄羅斯的數學家)已經證明了不可能存在揭示全部宇宙命運的公式,“拉普拉斯妖”也僅僅是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臆想出來的“全知全能者”。但是依然令人擔憂的則是,即使人工智能無法成為“萬能者”,沿著當前的道路它也能進化成一個全新的統治性的新物種。到那時,如果人類成為了新物種攫取生存資料的來源,那麼人類可能就真正進入韋伯所言的自身理性所編織的“鐵籠”。
心中的善良與自己的未來
至於人類社會是否真的能夠被預測,有的人堅信如此,有的人不以為然。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應該堅信,自由意誌是最為珍貴的人性特質。它在人世間無處不在,體現為人們的創造力,支撐著人類社會的演化進程,推動著人類文明向前。它曾經帶領人類邁向理性之光,也必然能夠指引人類掙脫理性鐵籠,向善而行。
人類社會走到今天,我們應當與阿西莫夫一樣,期盼人類未來的美好。我們所能夠確定的是,我們自己的生活,還有我們自己的未來,只能是我們自己去創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