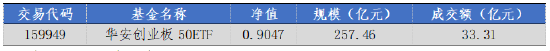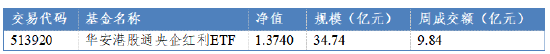上野千鶴子結婚背後:非性緣的婚姻關係與日本照護保障的缺失
3月15日,一條名為#上野千鶴子承認秘密結婚#的詞條出現在了微博熱搜榜的第一位,一時間輿論嘩然,針對上野千鶴子本人的爭論四起。而這些爭論則大多聚焦在上野千鶴子與色川大吉的婚戀關繫上。
當天與熱搜相關的熱門微博里,有一條微博傳播得尤其廣泛,博主將上野千鶴子此次的輿論風波籠統概括為四點,其中的第一點,也是最具爭議的一點是:“她承認,的確與已故的曆史學家色川大吉‘註冊登記了婚姻關係’”。
其實,上野千鶴子在那篇由她撰寫,如今被稱為“承認自己與色川大吉的確註冊登記了婚姻關係”的文章《15時間の花嫁》的開頭處明確表示了她並不喜歡這種行為,甚至認為這是一種冒犯。她在文中寫道:“在這世界上不乏存在著四處打探他人隱私,並將之當作八卦的卑鄙之人,而所謂‘文春炮’便是其中之一。”
被稱作文春炮的雜誌,是日本著名文娛雜誌《週刊文春》,該雜誌曾經寫文“揭露”過上野與色川的婚姻關係。在色川大吉去世後,有不少媒體試圖打探上野千鶴子和色川大吉的相關事宜,但都被上野拒絕了,她在文章里稱:“尚未整理好自己悲傷的心情,也不想販賣自己的隱私。”
與其說這是一篇被概括為“承認秘密結婚”的澄清文,我更願意將其視為上野千鶴子陪伴在“最好的朋友”身邊度過最後一段時間的記錄,文章中關於兩個老人在年老後該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是複雜且具體的。
在引發人們關注的婚戀關係與女性主義者標籤之外,上野千鶴子和色川大吉是兩個超高齡老人,他們都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即如何作為一個年邁的老人,獨自面對衰老與死亡。該起事件揭露出的問題——上野與色川在拒絕進入以家庭為單位的關係後就無法在強硬、暴力的系統下維持日常的正常運轉,也許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社會切面。
 上野千鶴子
上野千鶴子一,婚姻關係並不等同於性緣關係
上野千鶴子秘密結婚這一事件在中文互聯網上引起的軒然風波,從側面說明了一個問題:大部分人預設一個人在社會之中集結的方式只有兩種:一是公司,二是家庭。一旦人與人之間的性別相異,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只可能是由性緣關係構成的情侶或夫妻。
上野千鶴子曾經在她和鈴木涼美的書信集《始於極限》里說道:團塊世代也許是被“浪漫愛”意識形態洗腦最嚴重的一代人。而洗腦裝置就是少女漫畫與電視劇。年輕時狂熱追捧《凡爾賽玫瑰》,上了年紀之後又為《冬日戀歌》心潮澎湃的正是團塊世代的女性。她們大概也是渴望真命天子、相信紅線傳說的最後一代人。
其實追溯起來,無論是“戀愛腦”,還是“戀愛”,都是獨屬於近現代的詞彙。近現代以前的日本,有權力的貴族們懼怕且堅決反對“門不當戶不對”的“自由戀愛”。因為在過去,貴族們懼怕其他階層的外來者通過婚姻提升自我階層,所以“自由戀愛”一度是一種罪名。為此,日本舊社會所準備的戰略,是將羅曼蒂克式的愛情意識形態與婚姻緊密結合。滿足社會規訓下的“愛情”的隱藏前提,是“門當戶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與“合適的對象”戀愛,才能稱之為“戀愛”。不僅如此,任何“下嫁”與“高攀”的戀愛,都會因為階級的分化影響了社會的秩序與安定,而被列入不正當的“戀愛”中去,被世人所譴責。
在上個世紀以前,戀愛的“正當性”始終與“合適的”婚姻互相捆綁。任何與“不合適”的結婚對象產生戀愛感情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有可能擾亂階級秩序與家族秩序。如果將人與人之間自然而然產生的情愫稱之為戀愛,那麼無論是自由戀愛關係,還是過去在父母之命下,嚴格依託宗族關係而產生的戀愛關係,都是一種由社會與文明構建而成的記述概念。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戀愛關係有不同的規範概念。而由戀愛關係所延伸的家庭關係,與所謂的近代式家庭關係,同樣是社會規訓下的規範概念。這些概念在不同的時代形成,每個階段的關係與範式,都具有其當下時代特定的曆史特徵。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在《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中,上野曾經提及過:“1994年,聯合國家庭年的標語是“從家庭開始的小小民主主義”,但實際上家庭里沒有民主主義。家庭是性和世代不同的異質度很高的小集團。在家庭中,權力和資源被不均等地分配著。年長的男性統治支配著年少男性和女性的父權製概念,也適用於近代家庭。隨著社會與文明的發展,國家進入新的階段後,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家庭的關係都在悄然發生改變。所謂近現代家庭的崩潰,由此而來。”
與過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關係一樣,強調女性無私奉獻、蝸居於家庭之中做家庭主婦的家庭分工範式,開始成為舊理念。202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日本30歲年輕人的不婚率高達55%。日本進入少子化、老齡化社會以後,選擇進入家庭的人們和不組建家庭的人們,開始出現分化。不組建家庭的人們與選擇組建家庭的人們,都需要面臨新的挑戰。
過去,日本社會曾經興起過一陣購買照護保險的興潮,該保險剛推出的時候,有不少人稱其為“子女不孝險”。然而,據調查報告顯示,當時照護保險的主要推行對象,並非是獨居無子的老人,而是需要護理老人的年輕一代。照護保險的出現,能夠大幅減少家庭護理的負擔。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照護保險受到推崇也與日本部分年輕人存在“棄老”的動機有關。關於這一點,上野曾在《一個人最後的旅程》中這樣寫道:回顧社會保障先進國家的老人福利曆史,就會發現,老人福利的推廣往往是響應護理一代的要求,而非被護理一代的願望。“棄老”很容易獲得護理一代的支持,他們是社會中擁有話語權的多數派。
在逐漸變老的過程里,許多老人都會面臨被社會、家庭、周邊的人所忽略、甚至拋棄的境遇。在現代社會,衰老在很多時候被隱喻為一種慢性疾病。對於有孩子的老人而言,家庭或許能夠為老人提供更多的幫助,但老人也可能面臨“養兒不防老”的問題,美國作家路易斯·阿倫森(Louise Aronson)也曾在其著作《銀髮世代》中講述過,有病人經常表示:“我選擇生孩子,但他們沒有選擇照顧我。”阿倫森認為,對家庭最好的定義是家庭成員能在一生中互相照顧。另一方面,不為老人提供必要的照顧則是針對老年人的一種暴力。我們會看到赤裸裸的虐待:包括身體上的、經濟上的、性上的和情感上的虐待。這對於任何年齡群體都是非常惡劣的行為。但是,當老年人不得不在生活上依賴施暴者時,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尊嚴會變得非常困難。
當有孩子的老人無法依賴自己的後代時,他就需要和無子的老人一起,轉向社會醫療體系的照護之中。但在美國,政府為阻止虐待老人所提供的資源甚至要少於為阻止虐待動物而投入的資源。對於如何“一個人居家臨終”的問題,無論是美國社會,還是日本社會,至今似乎尚未交付一份有著良好計劃的答卷。
二,超高齡社會下的弱者
在新書《快樂上等》里,上野千鶴子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超高齡社會是一種福音,因為無論是誰都會早晚站到弱者的立場上。”90多歲的色川大吉在各種意義上,似乎都已經成為了弱者,尤其是色川大吉在93歲那年摔斷了大腿骨以後,已經無法下地行走,不得不依靠輪椅生活了三年。在這期間,因為“新冠”的原因,上野千鶴子由東京遷往山中的家避難,工作也基本轉為線上。她工作的地方和色川大吉的家屬在同一地界;因此契機,她成為了可以在第一現場照顧色川大吉的人。色川大吉的原配妻子已經去世,和兒子也鮮少見面。因為距離和疫情的關係,上野開始著手處理色川大吉的照顧事宜。
 《快樂上等》
《快樂上等》關於上野千鶴子與色川大吉的關係,上野千鶴子她在文章中是這樣闡述的:有色川大吉故鄉的親友前來看望他,他在介紹我的時候這樣稱呼:“這個人是介護的專家”,要這麼說也沒有錯,不過不知道內情的人可能會以為我是專業的介護士。色川大吉不僅頭腦清晰,也相當的有幽默感,“上野啊,現在是你實踐理論的最中心處啊。”色川大吉向其他人介紹我時,最讓我開心的一種是:這是我最好的朋友。(この人はボクの親友)
上野千鶴子在過去寫過許多一個人老去後應當如何生活的文章,這也正是色川大吉表示“上野啊,現在是你實踐理論的最中心處啊”的原因,她和色川大吉都是高齡的獨居者,也都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在照顧逐漸老去、疾病纏身、一個人住在療養院時的色川大吉的過程中,上野千鶴子也深感無力。在色川大吉臨終前的某個深夜,上野因為色川大吉痛苦的呻吟而醒來,她因為自己無法為色川大吉做任何事情而感到無力,捂著臉一直痛哭。
上野在過去曾表露過她對於一個人步入老年生活狀態的擔憂:“要說為什麼未生育過的女人會被視為弱者,變老就是起因。沒有什麼比沒孩子的老年生活更讓人覺得淒涼了。生不生孩子這件事是有選項的,但變老這件事對誰來說都別無選擇。”
這大概也是上野面對色川大吉的衰老與死亡時感到無力的原因,上野在照護色川的過程里,逐步預見了自己衰老與死亡的過程。“就這樣下去的話感到自己無力支撐,有誰能來幫幫我?”這樣想著,上野千鶴子撥通了朋友N的電話。N是這樣安慰上野千鶴子的:“上野,你依照自己書里寫過的那樣照顧色川大吉了呢。”也正是這句話讓上野千鶴子如釋重負。
“就像120%地知道自己會無法控製自己的肉體一樣,我漸漸深刻地認識到精神也會變得無法控製。這是我在看護研究中的學習成果。”他們開始頻繁地談及自身的後事。上野作為色川法律關係以外的人,連“死亡證明申請書”都無法替色川大吉辦理,到了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甚至連入院和手術的同意書也無法替他簽署,她徹底感受到了各種手續都以家庭優先的現實。當上野試圖將色川大吉的銀行賬戶歸攏到她名下的賬戶時,銀行工作人員問她,“你們是什麼關係?”,上野回答是“朋友”以後,對方便表示無法辦理。
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成為收養關係,第二種就是結婚。如果建立收養關係,上野千鶴子便只能改姓色川,因為日本的收養制度是為了家族的存續而存在的,年長的一方自動歸為父母的一方,因此年紀較小的那一方必須隨父母改姓。而婚姻關係的姓氏則必須統一,在上野千鶴子還在艱難選擇的時候,色川大吉已經先行簽署了兩封文件,決定改姓為上野。
如上野千鶴子在文章里所說的那樣,“如果日本擁有‘夫妻別性制度’,事情也不至於發展成這樣吧。我因為沒有改姓而避免了一切不利。我也從這件事意識到:原來沒有改姓的那一方,會難以理解另一方的不便和痛苦。如果日本法律不是以家族主義至上的話,也不止於此。”
作為讀者,我反倒覺得“澄清自己和色川大吉有過15個小時的婚姻”是這篇文章里最無足輕重的一點,因為婚姻關係並非是上野千鶴子自願選擇的關係,而是一種對不合理制度無奈的妥協。上野千鶴子曾在她的書里不止一次提到,她渴望建立的世界,是一個讓弱者有所依靠的世界。讀文章的時候每每想到這句話,都會令我感到異常難過。
上野千鶴子已經足夠強大,但在最好的朋友面臨死亡的關頭,她卻仍舊不得不對這樣龐大而荒謬的制度做出妥協。想到上野千鶴子在《一個人最後的旅程》里寫到的:追求精英的時代,原本就是一個不正常的時代。社會有缺陷、有紛爭的時候,才會期望超級英雄的出現。尤其是,政治精英出現的時代往往不是什麼和平的年代,這恰恰證明了一個無須由精英來運轉的社會才更為健康。
 《一個人最後的旅程》
《一個人最後的旅程》從這一次上野照護色川、陪伴其走完最後旅程的風波中,我們可以窺見的遠不止“一個女性主義者選擇照顧一個九十歲的老人”這件事,除了上野選擇承擔起照顧色川的責任之外,我們能夠看見日本社會之於年老群體關懷的缺失,一個90歲的、有孩子的老人的介護義務,為什麼需要轉移到一個75歲的高齡女性上?療養院可以為色川大吉看病、配藥,解決老人所需要的身體健康關懷,但當一個老人獨自面對衰老的恐懼與孤獨,醫療看護人員又該解決他的情感需求?在維護身體健康之外,如何直面老年群體存在的精神需求,仍舊是日本社會存在的一大問題。
生與死,已然是超越了個人意誌,且無法以人力掌控的事。在當下,日本社會無疑已經進入了人口不斷減少、孩子的數量也毫無増加跡象的時代。不論個人的意願如何,今後的日本,獨居的人口都會不斷增加——這也意味著,“無處臨終的難民”也會愈來愈多。2022年的年末統計數據顯示,日本每年有超過三萬人的獨居老人在家中死去。老齡少子化的趨勢下,一個人如何度過最後的旅程,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與思考的命題。如上野千鶴子所說的那樣,我們所需要的,應該是一個無需恐弱的,能讓人安心、自然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的社會。
參考文獻:
1.《始於極限》鈴木涼美,上野千鶴子
2.《ロマンティック・ラブ・イデオロギー再考》,佚名
3.《專訪|路易斯·阿倫森:人都會老去,善待老年人就是善待未來的我們》,澎湃新聞記者:龔思量
4.《一個人最後的旅程》,上野千鶴子
5.《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上野千鶴子
6.《快樂上等》,上野千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