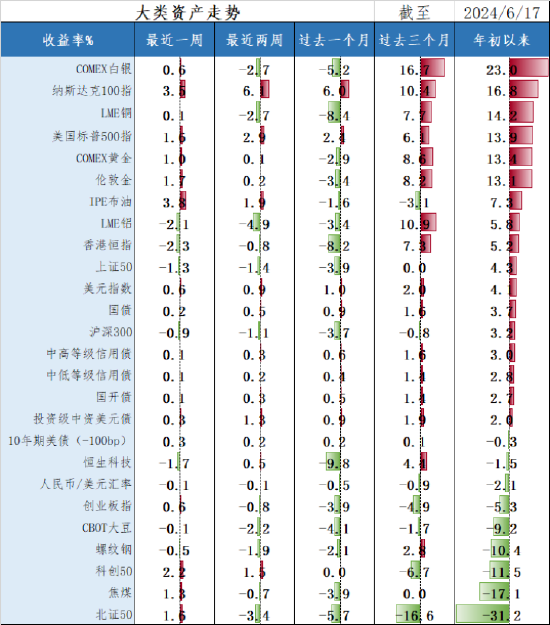破產法的溫度|一個韓國失信債務人眼中的張國榮之死
“聽說張國榮自殺了?”
當“我”忍受著刺鼻的煙味,在網吧的電腦上,收到離異的女網友發來的這條消息,第一反應是不願意相信。可能是謠言。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說不定張國榮第二天就會召開新聞發佈會闢謠。
這是一種奇怪的感覺:“與我連接在一起的世界風平浪靜,靜悄悄的。然而,在這個世界之外,卻有一位外國演員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是韓國小說家金勁旭的短篇小說《張國榮死啦?》的主人公,一個無名無姓的失信債務人(這篇小說被收入金勁旭所著《您可疑的近況》一書)。

《您可疑的近況》,(韓)金勁旭 著,安鬆元 譯,新經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22版
2002年4月2日,“我”和妻子的婚姻走到盡頭。“我”為父親在銀行的借款做了保證人。而且,“我”是在簽字畫押後,才告訴了妻子這一事實,事前沒跟她商量。
“我”的父親是一個小型建築商。他動用銀行貸款和退休金,建了一幢樓,想著依靠商舖租金收入安度晚年。不過這幢樓還沒來得及完工,父親就破產了。周邊的居民,不斷抗議,導致設計圖也再三修改。為了補償周邊居民,父親不得不收購了周邊的老舊房屋。居民還抗議工程質量有隱患,可能導致房子塌陷……對此,父親束手無策。
妻子火冒三丈的原因,不在於“我”做了父親的保證人,而在於事先沒跟她商量。妻子強調的不是錢或者債務,而是信任。“我”的辯解蒼白無力。
工程一再延期,材料價格飛漲,最終給父親致命一擊。原來的工程計劃一再擴張,最終吞噬掉了父親,父親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貪慾和不幸劃上了句號。
父債子還,天經地義。父親身上的巨債,並未因為其死亡而消失,而是分毫不差地被“我”繼承下來。“資本連坐製法網嚴密,窮追不捨。我束手就擒,成為信用不良者。”
對於“我”來說,父親死後“我”就成了催收對象。不但月薪被扣,銀行和信用卡公司的催收人員都追到了“我”上班的公司。“他們好像是在嚴守一項工作守則,總是一身黑色西裝,說是黑白無常也不為過。坐電梯時,見到穿黑西裝的人,我就慌不擇路,掉頭奔向緊急出口。”無奈之下,“我”向公司遞交了辭職信,公司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
背負巨額債務後,妻離家破,走投無路。一個慘不忍睹的事實,就是認識“我”的人仍然信任“我”,但銀行卡和信用卡公司卻失去了對“我”的信任,“如同張國榮的死,那不是任何人的錯。”
“我”向妻子提出了離婚的請求。只有這樣,才能保住我們按揭抵押買的房子。“我”不能連她的人生也一起毀掉。“我”把房子變更到妻子名下。妻子開始不願意離婚,但當“黑西服”找到她的公司,她不得不接受了現實。“黑西服”一度懷疑我們是假離婚,在我們離婚後有段時間還經常出現在她的周圍。
原來妻子提出,還清銀行貸款前,我們先不要孩子。我們為了買房沒要孩子,但最終為了保住房子,卻離了婚。現在看來,不要孩子是對的。離婚那天,“我”把衣服和隨身物品裝進箱子,走出門外。妻子故作鎮靜,說那裡還是“我”的家,隨時可以回去。“我”很感激,但沒有說謝謝。
我的網聊對象,一位離異的女網友,對於張國榮的電影如數家珍。巧合的是,13年前《阿飛正傳》上映那天,“我”、妻子、離異女網友居然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看過這部電影。更為巧合的是,“我”和妻子結婚的日子、蜜月旅行地、蜜月酒店,跟離異女網友都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舉辦婚禮的酒店不是同一家。
我們結婚那天,是4月1日。看來,至少有兩對新人在愚人節辦的婚禮,最終都沒有好的結果。
離婚後,“我”居無定所。為了購買勉強餬口的食物,“我”幹過形形色色的工作。“我”沒有耐心跟人說話,“我”打工的工作,比如在“廣開土網吧”里收銀,大部分都不需要跟人說話。
只有,偶爾在禪雲寺漫步時,“我”才會留意到大自然一如既往,山茶花兀自開落,完全不顧“我”的自暴自棄。“我那不能歸責於任何人的不幸,以及由此而來的憤怒,在四季常開的山茶花面前,竟然如此微不足道,我難以承認這一點。然而真正使我恐懼的,不是我的憤怒過於渺小,也不是我的不幸毫無意義,而是我害怕山茶花林,我怕不能像山茶花林一樣不改其色。”
就這樣,“我”和離異女網友在虛擬空間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張國榮的電影,聊著張國榮的死亡,聊著中國的SARS,聊著我們虛無縹緲的人生。
當“我”不想聊天了,退出聊天室,“我”回到單身公寓。警察正等著“我”。“我”的屋裡,除了一小塊躺人的地方,堆滿了雜七雜八的物件:搪瓷鍋套件、高壓鍋、電飯鍋、旱冰鞋、榨汁機、電吉他、嬰兒車……都是全新的,甚至包裝都沒拆。
警察說,有人舉報你窩藏贓物。警察問“我”:這些破玩意都是從哪兒來的?
“我”指著晶體管收音機。這些電台節目,都需要故事。“我”就把從各處聽來的故事,整理出來寄給電台,得到了這些小獎品。為了獲得這些獎品,“我”投稿的對象,既有《主婦時代》,也有《正午希望歌謠》。警察理解不了“我”為什麼為了一些用不上的東西,費這麼大勁。
其實,“我”也會為一些需要的東西寫故事。比如,有一期《直播希望列車》的獎品,是野外充氣簡易床;他們需要經曆失業和挫折的故事。
為了得到這張床,“我”把自己的故事和盤托出:一個男人,因為父親破產,不得不從公司辭職,成為信用不良者,最後向妻子提出離婚;還有,在禪雲寺茶花林中體會到的微不足道的恐懼感。
這不是聽來的故事,這是“我”的親身經曆。然而,我沒有得到那張床,我再也沒寄送過故事。“那是我不能再放棄的最低限度的自尊心,跟世上的任何一張床都無法交換。”
張國榮的葬禮在一週後舉行,“我”在網吧櫃檯上看了直播視頻。因為SARS,參加葬禮的人們都戴著口罩。這個時候,“我”收到了離異女網友的郵件,以《阿飛正傳》里的“無腳鳥”落款,約“我”見面。為此,“我”以父親死亡為由向網吧老闆請假,老闆不僅準假,給“我”手裡塞了10000韓元……
張國榮死了。很遺憾。這不是個玩笑。
如今,張國榮逝世已經20年了。“我”,一個無名無姓的韓國失信債務人,到底怎麼樣了呢?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