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出版八十週年|李雨軒:《小王子》與一個倫理學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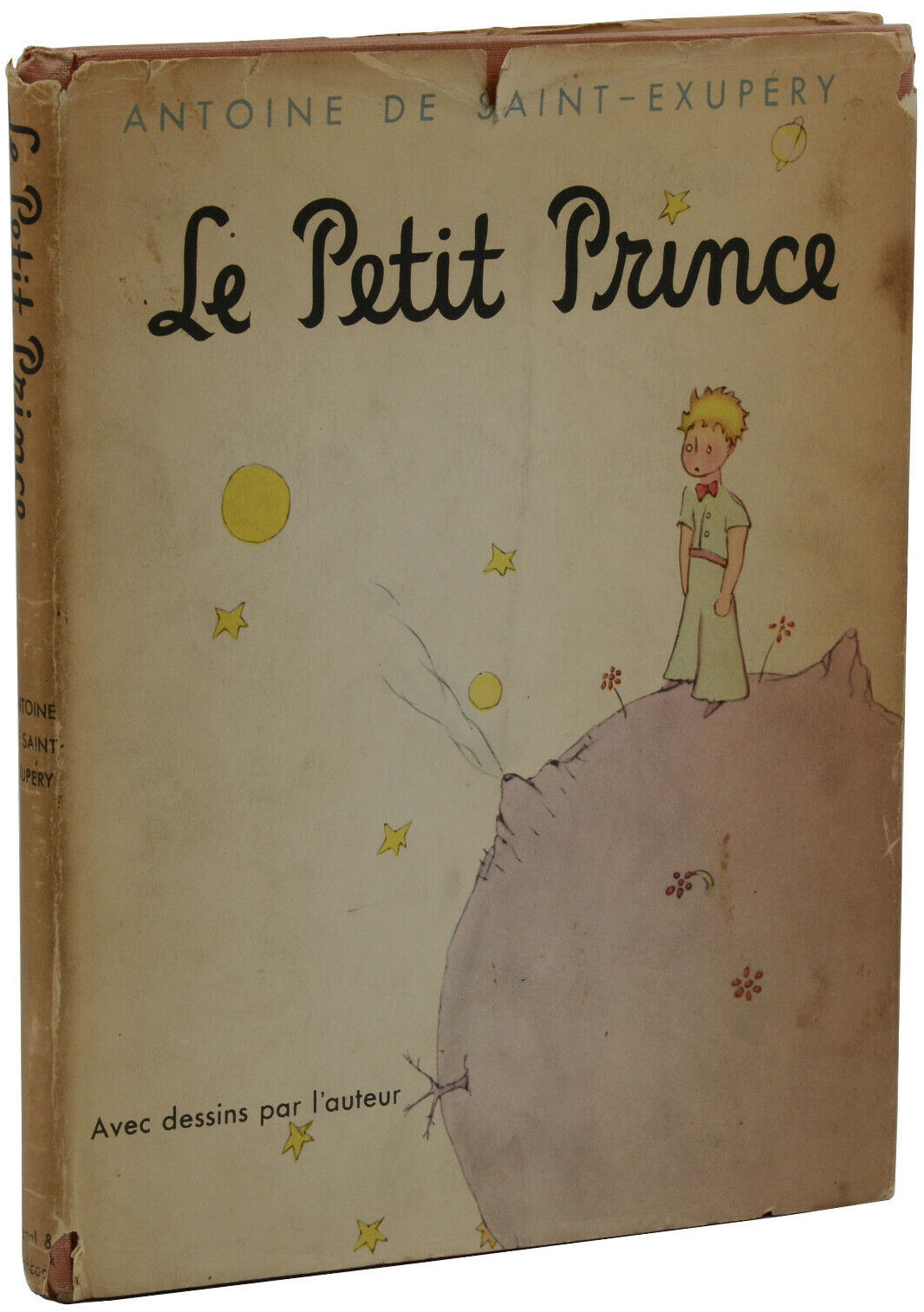 《小王子》初版本
《小王子》初版本聖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創作於1942年,並於1943年4月在美國首次出版,2023年是它出版的八十週年。這部在世界範圍內經久不衰的作品以童話為外衣,卻向“大人們”揭示了很多至深的道理,甚至能夠以某種預見性與其後五十年的哲學問題產生跨時空對話。這個問題具體是指德里達在《贈予死亡》(1992)中以獨異性哲學為背景提出的一個倫理學難題。這個難題是什麼?《小王子》又能為其解決提供何種啟示?
一
“獨異性”(singularity)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其間形成了多條理論支脈,如獨異性事件理論、獨異性文學理論等。其中一個支脈是本體論問題,這一支脈在法國理論中存在較多“家族相似”的生發,比如布朗肖、德里達、讓-呂克·南希等,他們既確證了個體的獨一無二性,又使個體與他者保持著關聯。
我們討論的這個難題正是以德里達的獨異性哲學為背景產生的。德里達從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故事談起,這個故事記載於《創世紀》第二十二章:上帝讓亞伯拉罕將其子以撒獻為燔祭,亞伯拉罕準備照做,但在最後一刻被上帝中止,上帝知曉了他的敬畏和誠意,最終賜予他大福。在基督教的意義上,或許正如克爾凱郭爾的解讀,這個故事是要將面向上帝的絕對責任淩駕於世俗倫理之上([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栗》,趙翔譯,華夏出版社,2017年,70頁)。德里達引述這個故事,卻不是想在宗教的原始意義上討論它。他削弱了其宗教內涵,最終將上帝闡釋為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他者”。這樣一來,亞伯拉罕與上帝、與以撒之間的關係就被平等化了:對於亞伯拉罕而言,上帝和以撒是彼此平等的他者。但德里達的闡發也繼承了這個故事的核心宗教成分,即每一他者都分享著上帝的至高無上性,每一他者的呼召都是絕對緊迫的。
隨之而來的便是有關獨異性的“絕境”(aporia)。德里達指出,為了回應一個他者,自我只能將另一個他者犧牲給他。每一個他者都是全然他異的(Tout autre est tout autre),每一個他者都是一個獨異性存在(可將其稱為“獨異體”)。自我與獨異體建立的關係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秘密性,正如亞伯拉罕始終對眾人隱瞞真相,因為他處在一種與上帝的無法言說的關係中;二是不可論證性,因為論證必須依據特定原則來計算、推理,而一旦涉及這些就是對他者之獨異性的否定,犧牲也就不再是絕對犧牲。這種在不同他者間進行決斷的兩難及其秘密性、不可論證性,被德里達稱為“絕境”。絕境既非“通過”亦非“未通過”,而是在一個界限上的通過之不可能性。絕境不止在宗教語境中發生,它就發生在日常生活當中,不但涉及人,還涉及居所、動物、語言等一切事物。
德里達的這些論述有兩個要點值得關注。其一,自我與獨異體的關係是排他性的,所有他者都是絕對的、平等的,但他者之間是彼此對立的;其二,自我與獨異體的關係受製於其獨異性,因而是無法論證的,沒有一種語言、理性可以論證它。
我們以救助流浪貓為例進行更詳細的說明。如果現在因為某種原因只能領養一隻流浪貓,那麼就面臨一個選擇的問題。大部分人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貓身體是否健康,樣貌是否好看,品種是否高貴,性格是否合適,但衡量這些標準就意味著進行某種計算,貓之作為獨異體的身份便瓦解了。少數人會主動收養殘疾的貓,或大部分人在各種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選擇了這一隻而不是那一隻。在這些情況中存在著某種“不可名狀”的東西,它標示著不同的貓的獨異性。
德里達對獨異性的討論指向倫理決斷和責任生成。在進行倫理決斷時,各種文化中都能找到可論證的東西,比如血緣、國家、民族、年齡、性別等,這些都是通過訴諸普遍性來處理問題的;但還有很多不能用普遍性來解釋,這些才構成倫理決斷的難題。仍以領養流浪貓為例,領養就意味著責任的生成。選中這一隻,就意味著放棄其他的,也就得承擔其他貓的“犧牲”。這種要求看上去似乎太苛刻、太不切實際了,似乎我們對所有貓都同樣地負有責任。毫無疑問,德里達的這一觀點產生了巨大的爭議。《贈予死亡》的中譯者王欽也提出了質疑:如果我要對每個他者負責,這難道不是一種“受虐狂式的英雄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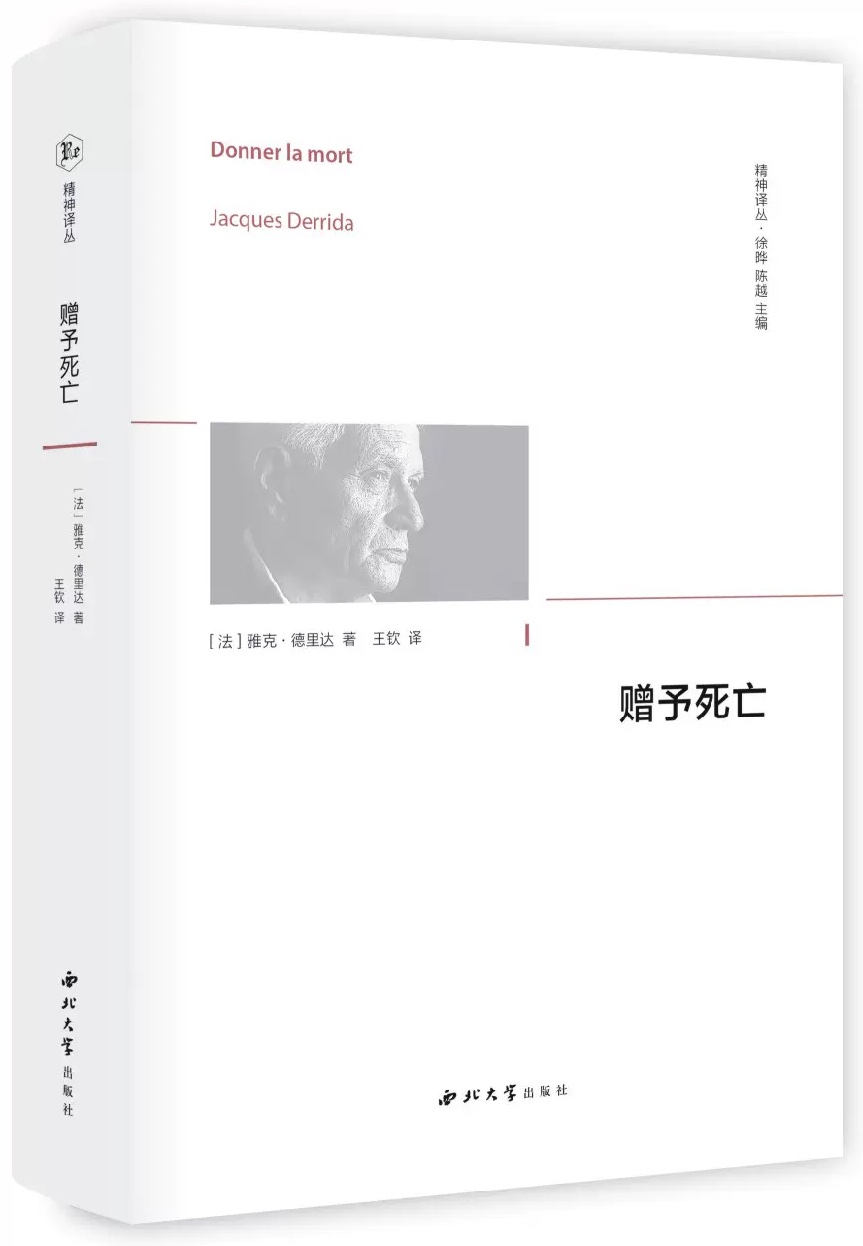 德里達著《贈予死亡》
德里達著《贈予死亡》雖然王欽給出了自己的解讀,也即不應將這種“絕境”理解為一種現實的、實踐的倫理指導,而應將其理解為對所有倫理法則的基本邏輯的反思:德里達並不意在提出一種特殊的倫理法則,而是呈現了奠基倫理法則的前提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譯後記》,見[法]雅克·德里達:《贈予死亡》,王欽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212-213頁)。這種解讀是有意義的,但還是繞過了德里達自身的立場。德里達特別強調正是通過“如此行事”,我們才履行著自己的義務。也即,正是通過這種決斷,通過這種對其他所有他者的無限犧牲、絕對犧牲,我們才能真正承擔自己的責任,履行自己的義務。該如何理解這一點?為什麼責任、義務與這種犧牲相交織?“絕對犧牲”的主張究竟是一種“受虐狂式的英雄主義”,還是另有玄機?
二
我在閱讀中意外地發現,《小王子》為這一問題的推進提供了絕佳思路。雖然布朗肖和聖埃克蘇佩里是同代人,但要說前者在獨異性問題上直接啟發了後者,似乎也難以成立。在我看來,《小王子》揭示了有關獨異性的另一層秘密。
小王子與玫瑰花的關係是書的重點。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只有一朵玫瑰花,小王子認為玫瑰花的珍貴正在於其獨一無二性、唯一性。但在書的第二十章,小王子走進玫瑰花園,他先前的玫瑰花觀點崩塌了。這裏不妨摘引兩段:
他的花對他說過,宇宙中僅有她一朵(seule de son espèce)。然而,這裏,單是一座花園里,就有五千來朵,朵朵相像。
他還對自己說:“我以為有一朵獨一無二的(unique)花,很滿足,其實只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法]安東尼·德·聖-埃克蘇佩里:《小王子》,馬振騁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70頁)
在這裏,個體的獨一無二性受到類(espèce)的概念的挑戰,類的普遍性、相似性剝奪了個體的獨一無二性。此時的小王子與玫瑰花的關係已遭受嚴峻挑戰,而平息這一切的則是狐狸。小王子與狐狸的關係是書的另一重點。當小王子向狐狸發出一同玩耍的邀請時,狐狸拒絕了,理由是它沒有經過小王子的“馴養”。什麼是馴養?簡單說來就是“建立聯繫”(créer des liens)。這裏不妨摘引一段狐狸的經典闡釋:
狐狸說,“你對我不過是一個男孩子,跟成千上萬個男孩子毫無兩樣。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對你不過是一隻狐狸,跟成千上萬隻狐狸毫無兩樣。但是,你要是馴養我,咱們倆就會相互需要。你對我是世上惟一的(unique)。我對你也是世上惟一的……”(《小王子》,71-72頁)
狐狸借助“馴養”,從類的概念中拯救了個體的概念:即使身處於類中,個體依然能在關係中保持其獨一無二性。雖然聖埃克蘇佩里沒有使用singulier這個詞,但使用了相近的unique,這兩個詞的內涵有很大的共通性,在南希等的闡釋中也經常一起出現。正是有了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用《小王子》討論獨異性問題。
 《小王子》馬振騁譯本
《小王子》馬振騁譯本具體言之,《小王子》生動地闡釋了獨異性的關係問題。這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獨異性,一種處在關係中的獨異性。所謂“建立聯繫”,正是這種關係的生成。沒有建立聯繫的兩個個體沉浸在類中,無法從類中掙脫;一旦兩者建立關係,各自的獨異性就顯現出來。由此,我們發現了獨異性的兩個層面——本體論和關係論。前者針對的是相對獨立的本體,描述的是每一獨異體的獨一無二性;後者則針對兩個個體形成的關係,強調關係中的獨一無二性。但又要看到這種區分只是大體上的,兩者之間還保持著緊密聯繫。毋寧說關係中的獨異性是激活本體上的獨異性的一把鑰匙:在每一獨異性關係中,相對於另一個體的此個體之獨異性,會隨著藉以參照的不同個體而發生變化,而在這一過程中保持不變的正是作為獨異體的個體本身。《小王子》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在這一點上完全能夠充當一部詩學著作、理論著作,其中蘊含著對獨異性詩學的深刻闡釋。
有了這種雙重的獨異性視野,重新閱讀《小王子》和德里達都會有新的收穫。小王子一開始認為類的概念與獨異性是不相容的,但狐狸說他的那朵玫瑰花也是世上唯一的。在這個意義上,小王子的玫瑰花早已準確表達了本體論的獨異性內涵。再看德里達的討論,其實亞伯拉罕與上帝的關係也是一種獨異性的關係,亞伯拉罕與上帝建立的關係不同於他與以撒的關係,而自我與一切他者構成的都是獨異性的關係。因此,獨異性的關係論也內在於德里達的討論中。
與德里達一樣,《小王子》也將獨異性與責任相聯繫,狐狸告訴小王子必須對他的玫瑰花負責。當自我與他者還未建立起獨異性關係時,就沒有產生任何責任或義務;而一旦建立起獨異性關係,責任和義務就隨之產生了。他者即使在我們沒有與之產生獨異性關係時也是存在的,但我們還未將其真正納入自我的建構中。因此,《小王子》對責任問題的啟示便是,我們並非要承擔對一切他者的責任,而是僅面向那些與我們建立聯繫的他者。相較於無邊無際的他者,獨異性的關係論縮小了自我所要承擔的範圍。
三
或許可以這樣簡單地概括上述討論:他者不因其本體論意義上的獨異性就理應得到自我的回應,這隻是一種潛在狀態;而一旦自我與他者之間建立起現實的獨異性關係,責任就真正誕生了。
這種獨異性的關係論與佛教的思想產生了某種對話性,具體說來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佛渡有緣人”,類似的表述在元末及明代的文獻中多次出現,如《琵琶記》《醒世恒言》等。《觀無量壽經》中有“有緣眾生,皆悉得見”的說法。除了“緣”,佛教中還有更具體的“菩提因緣”的說法。比如《大般涅槃經》卷九在論述“一闡提”的相關問題時言:“如人手瘡,捉持毒藥,毒則隨入;若無瘡者,毒則不入。一闡提輩亦複如是,無菩提因,如無瘡者,毒不得入。所謂瘡者,即是無上菩提因緣,毒者即是第一妙藥,完無瘡者謂一闡提。……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緣。”從這段經文看,“一闡提”即是暫時與佛無緣之人。總體而言,“緣”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本體論的界定,即眾生是否均具有內在的佛性,在這一點上不同宗派有不同理解;二是成道的具體機遇,即所謂“因緣際會”,正如經文中所述之“瘡”。其中,後一層面必然涉及度化之人與被度化之人的具體關係,這一層面的“有緣”呼應了《小王子》中的“建立聯繫”,它需要一種獨異性關係的建立。巧合的是,“緣”的兩個層面正好呼應了獨異性的兩個層面。
上述比較表明了獨異性關係論在不同文化中的普遍性,但同時要看到其中仍盤亙著獨異性的秘密性和不可論證性,它是理性和話語所無法穿透的,正如德里達的討論有著深厚的神學背景,這也許構成了獨異性哲學本身的魅力。
《贈予死亡》和《小王子》對獨異性、責任的闡釋都與其現代性批判有關。兩者都揭示出現代社會中一種普遍的責任缺失:隨著獨異性個體及關係的瓦解,人們只安於自己的特定身份去行事,淪為現代性機器的一個微小“齒輪”,現代社會充斥著不負責任的惡果。再次回到絕對犧牲的問題,該如何理解德里達的觀點,即正是通過對其他所有他者的絕對犧牲,我們才真正承擔自己的責任,履行自己的義務?
在我看來,正是備選項之間的互斥性和排他性,真正闡釋了責任的價值。正因為獨異性關係的建立是以潛在的犧牲為代價的,我們的選擇才是絕對的、至高的。他者的犧牲在自我的內部生成了一種罪的意識,它不斷提醒自我之決斷的或然性,警醒自我要珍重已建立的聯繫。德里達的用意不是要承擔起全部他者,而是要承擔起他者的犧牲,很難說這是一種“英雄主義”,它更強調自我反思、自我限制。
但也許還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英雄主義,可在各種文化中找到例證,比如儒家強調“平天下”,佛家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語,魯迅在《“這也是生活”……》一文中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624頁)。這種英雄主義直接以無數他者為己任,其均被納入自我的視域之中,自我欲承擔起對其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一種偉大的精神,但德里達提醒我們,即使是“英雄”也要面對絕對犧牲,以天下為己任就是將天下作為一個他者進行選擇,也就意味著會有其他的他者被犧牲。這正是獨異性的永恒“絕境”,也是一個將永續存在下去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