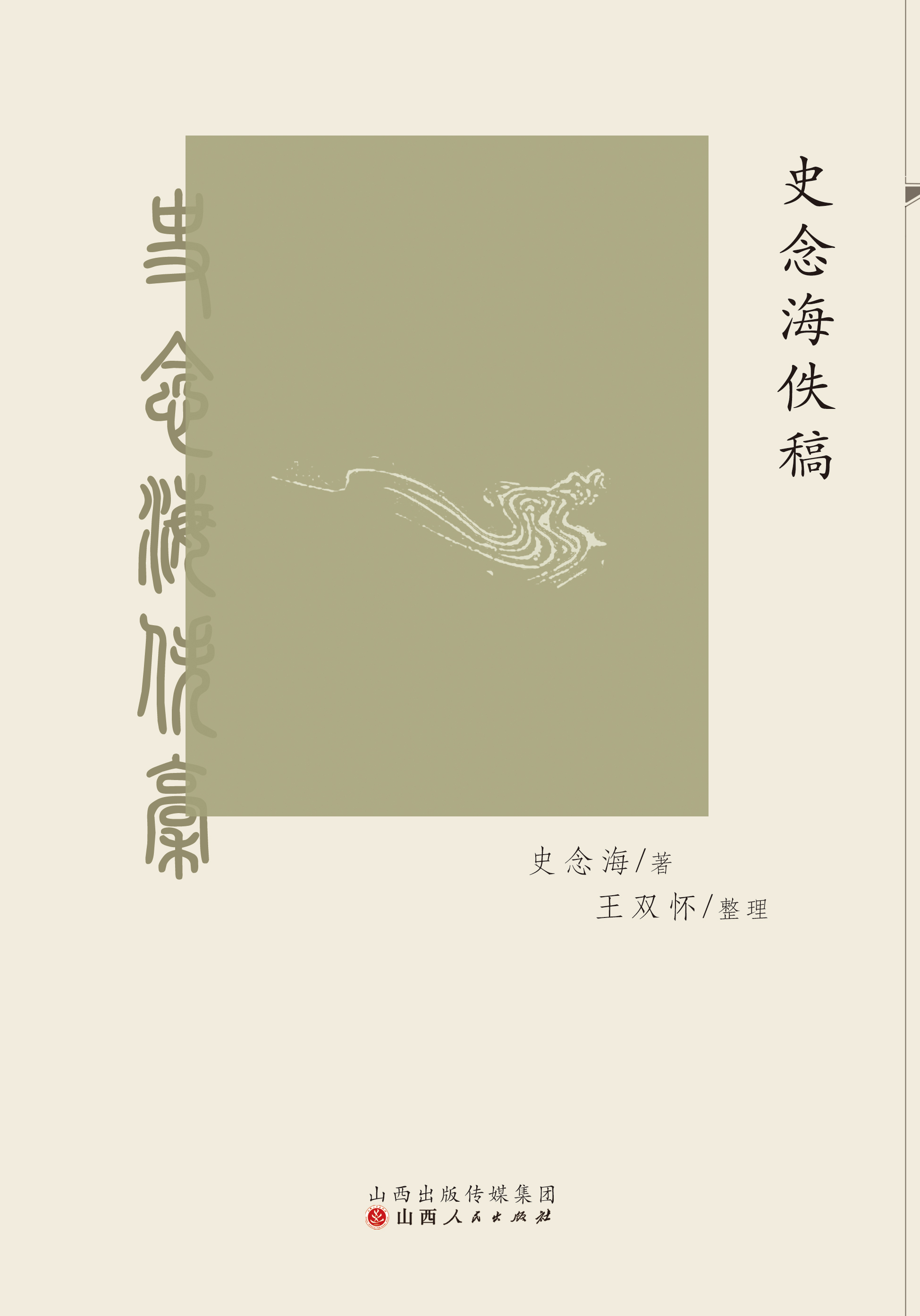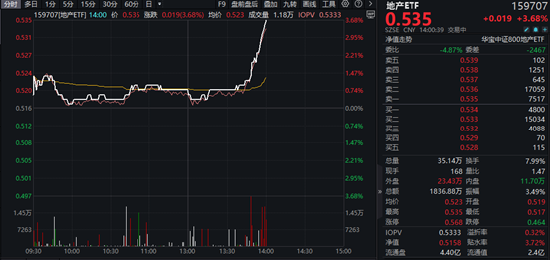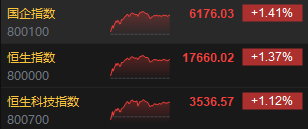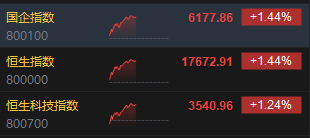史念海:秦漢時代關西人民的尚武精神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讚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鬱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襃,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班固這段話很可以看出當時人物的分野。因為地理環境影響的差異,所以各地人民的風俗習尚也就自然不同。關西人民的勇武有力和鄒魯人士的愛好文學,正是一個顯明的對照。這種區別不惟秦漢時候是如此,就是到了漢末三國之間也還沒有什麼大的變遷。《後漢書·虞詡傳》謂:“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由虞詡此言,也可看出其流風餘韻曆久不泯的盛況。
 秦朝弩箭
秦朝弩箭我們若由舊史的記載中實際考覈,當可知班氏此言並非過分的誇張。在戰國時,諸雄並爭,辯士縱橫,嬴秦也嚐羅致客卿,招納賢才,所以張儀、甘茂、範雎、李斯一般人皆以白衣干策而取卿相。但是嬴秦所羅致的人物,不過是這班遊說之士,用來折衝於樽俎之間,於其立國的精神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實在說來,嬴秦之所以威淩六國,六國之所以畏秦者,並不是這班輶軒的使節,而是其無敵的雄師。這些無敵的雄師,都是選自嬴秦本國的人民,和其所羅致的一般客卿倒沒有多大的關係。
到了楚漢之際,劉邦、項羽都是由東楚起兵,不用說他們的將士自然也以楚人居多。不過高帝的根據地是在關中,所以得力於秦人的幫助著實不少。《史記·蕭相國世家》說:“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嚐興關中卒,輒補缺。”這正是說明高帝的部隊實際已變了本質,和他初起兵的時候大不相同了。垓下之戰,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即以為漢已得楚。由這裏也可以看出這時漢軍的成分,已經沒有多少楚人了。後來高帝大封功臣,以曹參攻城野戰的功為多,列置第一,而鄂千秋就以蕭何由關中運糧遣兵為功最大,應該在曹參之上,高帝接受他的建議,因以蕭何居第一,而抑曹參居第二。這個固然由於蕭何的調度得宜,但是關中的糧秣和兵卒在楚漢戰中占著極重要的地位,則是無可懷疑的事情。
因為高帝起於豐沛,所以一班佐命的功臣,自然以豐沛的人為多,而執兵柄的韓信、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也都是豐沛附近的人物。但是時間稍久,這種趨勢也就慢慢消滅。西漢中葉而後,豐沛因為帝鄉的關係,容易攀龍附鳳,所出的人物仍是很多,而素質的變異,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時豐沛的人物除了一些與帝室有姻婭關係以外,大半竟然是寬衣博帶的經生儒者,而攻城野戰叱吒風雲的勇士不能不稱數關西諸郡了。
關西人民雖然在材力上壓倒關東各地,但在文事方面卻不能不低首於關東儒者之前。自嬴秦至於漢初,政府都未積極注意於文事,固不必說了。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進用,崇文學,講儒術,博士弟子為一般人的進身之階,而關西的人民在這方面卻不大聽說。《史》《漢》二書俱有《儒林傳》,專記一代經術文學之士,但是關西人民在其中並沒有占重要的位置。這很可以看出秦漢之世關西一般人的習尚。關西人在西漢時雖也曾登庸卿相,如武帝時的公孫賀、李蔡等,然而其所恃以進身的卻是汗馬的功勞,而不是尊前的對策。
東漢時這種差別慢慢減少,最著名的涼州三明(安定皇甫規字威明,敦煌張奐字然明,武威段熲字紀明),皆為一時名將,邊庭重鎮,但於材力之外,也都兼崇儒術。雖然仍是赳赳武夫,而勇武之中也還彬彬有禮。《後漢書·皇甫規傳》言:“(規)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吊、章表、教令、書、檄、箋記,凡二十七篇。”又《張奐傳》言:“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段熲傳》亦言:“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我們若不讀其全傳,究其身世,僅就這幾段記載來看,誰能說明他們不像鄒魯的儒士,又誰能想像他們是曾經威震邊庭、羌胡畏服的名將?
經過武帝和董仲舒、公孫弘一班人對於儒術的提倡,東漢一代明章二帝也都注意這方面,所以儒學大昌,關西受其影響,風氣也有點轉變。上面所說的涼州三明皆以一時名將,而授徒著作,堪為這時期的代表。然風流未泯,尚武的精神固仍保存而不失。譬如扶風馬融,亦為一代鴻儒,名重關西,盧植、鄭玄皆出其門下,但其請纓征羌的勇氣,雖千百年後,仍能令人景慕不置。《後漢書》融本傳載其請纓的端末說:“(融)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並,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雖然當時政府沒有允許他的請求,而這種武勇的精神不能不令人佩服,這絕不是普通人所想像的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所可比擬的。
 秦代銅鏃
秦代銅鏃上面所舉的不過是幾個特殊的例子,由這幾個特殊的例子很可看出一般的情形。實在地說來,秦漢時代關西關東的人民在素質上多少有點差異,尤其是邊郡的人民更為顯著。兩漢對徙民實邊的政策看得特別重要,實邊的事實更是史不絕書。實邊的人民雖然也和邊地人民一樣,染到尚武的風氣,但初至邊地,往往會受到邊民的欺淩,這其中自然免不了主客不和的關係,而實邊的人民體質荏弱,恐怕要占最大的原因。《後漢書·賈複傳》載:“建初中(賈宗)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仆役,不得為吏。”這正是關西人民和關東人民差別的地方。
至於關西人民所以崇尚武勇力的原故,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中已經指出一點。在《漢書·地理誌》中,班氏更作詳細的說明。他說:“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二千石治之,鹹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班氏此言乃就地理環境的影響,說明關西人民之所以崇尚勇力是由於地鄰邊庭、接近羌胡的原故。固然,羌胡的騷擾使關西人民不能不請求防禦的方略,因而養成崇尚勇力的習俗。但是,當時政府的提倡和社會的鼓勵,卻也相當重要,而不容輕易忽略的。
說到政府對於尚武精神的提倡,最早當然要數及秦孝公。本來嬴秦的立國,原是僻居西陲一隅,其初因為國小地僻,而為中原諸侯所輕視。繆公雖嚐稱霸,然其威力僅及於西戎,東則為晉所阻,不能一出函穀關。及孝公即位,頗思振作,乃任商鞅為相,風俗因之大變。秦人的勇武好戰,孝公和商鞅的力量最多。《史記·秦本紀》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複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商君傳》亦言:“定變法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秦國本來遠處西陲,與戎狄相鄰,其習俗素喜勇武,更加上孝公商鞅的一再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風俗的變化,是當然的事情。商鞅在鼓勵秦人尚武之外,還有更重要的設施,他設法招徠三晉之民使代秦人耕作,好讓秦人專心出去作戰。《商君書·徠民篇》中言:“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事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秦國得到這樣的調整根本沒有後顧之憂,秦人也得一心一意去從事戰爭,誠如商鞅所說“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秦兵愈戰愈精,而六國應敵不暇,無由再從容去耕作了。自此以後,一般人對於秦軍的勇武,都另眼相看,尤其是那些縱橫辯士,更是稱道不置。《戰國策·秦策三》載範雎說秦昭王之言曰:“大王之國,……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韓策一》又載張儀說韓王之言曰:“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史記·張儀傳》作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辯士的言辭雖然免不了誇大的成分和恭維的氣息,但他們所稱道秦卒的壯勇,卻有幾分的真實性,因為秦兵曆次東征的結果,證明這些話並非完全靠不住的。
 兵馬俑
兵馬俑嬴秦的兵製我們已經不大知道。漢代的士卒則多用關西的人民,這對於關西人民尚武的精神,實予以莫大的鼓勵。漢初兵製,大約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幾類,皆選郡國人民有材力者充之。樓船士多在江淮之南,為漢代的水軍。水軍在漢代效用極少,僅在對南粵朝鮮等處用兵時征發過,其他幾乎不再聽聞。輕車騎士大抵都是關西人民,而材官則多半是選自中原人民。《漢書·高帝紀》:“(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武帝紀》:“(元鼎)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由這幾篇帝紀中可以看出騎士與材官在征發地域上的分別。西漢時,騎士頗為一般人所重視,社會地位也相當之高,雖封疆大吏對於他們也不得輕易奈何。《漢書·趙廣漢傳》:“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竟坐要斬。”廣漢在當時身為京兆尹,京兆尹的位置非常重要,而廣漢在西漢一代中也算有數的能吏,為人又是極精明強幹,在地方官吏中曾經大露頭角,但竟因為斥除騎士的罪名,而受到腰斬的重刑。這雖是廣漢本人的不幸,由此也可看出騎士在當時受到的待遇是如何的優渥。至於材官,則沒有這樣大的福分,得不到這樣的青睞。其原因所在,想必是與關西士卒的勇武有關,或者因為材官是步兵,彼此之間遂有軒輊。武帝以後,兵卒的種類增多,有選募的勇敢、犇命、伉健、豪吏、應募、私徒,又有征自罪徒的譴民、惡少、亡命、徒、弛刑、罪人、應募罪人等名稱,但是騎士的地位,並沒有因之而減低。
騎士固是關西人民的進身之階,而拱衛宮廷的羽林、期門,更是關西壯士發跡之始。羽林、期門的選拔,率由六郡良家子。這裏所謂六郡是指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而言。至於良家子的限制,據如淳的註解,謂醫士商賈百工之人不得參預其間,其中的分子可說是相當純粹。若不是這六郡人民特別的勇武,何以會有這樣特殊的選拔?在當時由這羽林、期門兩部分出來的人才是相當的眾多,《漢書·趙充國傳》:“充國……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甘延壽傳》:“延壽……北地鬱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嚐超逾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公孫賀傳》:“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後漢書·董卓傳》亦言:“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這不過幾個顯明的例子。兩漢數百年間以羽林、期門出身而曆高位的,正不知有多少,利祿之藪,難怪要引起一般人的羨慕,因而都往這條路上想辦法。武帝提倡儒術,廣置博士,打動齊魯間儒生的利慾之心,研究章句的人,竟成了普遍的風氣,但是這種博士的頭銜,卻打不動關西人民的心理,因為他們另有進身之階,出頭之地,用不著摸索簡冊、尋章摘句。後來到東漢時,儒風雖然西被,而關西的人民仍然不願意驟違舊俗,所以尚武的風氣並沒有因之稍殺。
關西為產馬之區,也可以間接地助長關西人民的尚武精神。這話看起來很為奇突,實在當時的情形,正是如此。古代戰爭以車戰為主,到了戰國,車戰已經不能應付敵人,於是騎兵占到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秦漢時常和匈奴西羌戰爭,騎兵更是重要,沒有騎兵簡直不能和羌胡對壘。因為這種關係,騎兵在社會上的地位是要比步兵高過許多,上面所提到趙廣漢以斥除騎士而獲罪,就是一個證明。關西騎士無論在質與量上,皆為全國其他各地所不及,當然也可以歸功於關西產馬的優良。遠在嬴秦之時,關西產馬的優良,早已膾炙人口。《戰國策·秦策一》載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巴、蜀、漢中本是嬴秦的糧食倉庫,今以胡貉、代馬與此糧食倉庫並舉,可知其所占地位的重要了。又《韓策一》載張儀說韓王曰:“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其所產的馬,素質之佳,於此可見一斑。嬴秦之所以能掃平六國者,固然是仗著他的優越兵力,同時馬種的精良,也不能沒有關係。到了西漢,對於馬的養育,曾經做到最大的努力,李廣利的西征大宛,就是因為尋求天馬而起。並且又在西邊北邊諸郡大舉養馬,一時視為國家的要政。《漢書·百官公卿表》師古注引《漢官儀》說:“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可知漢代對於養馬的重視。武帝以後,關西各地盛植苜蓿,也是因為苜蓿為飼馬的最好草料。關西諸郡本來是宜於牧畜的,政府養馬之外,人民私馬的養育也有相當的數目。《漢書·地理誌》謂:“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後漢書·鄧禹傳》亦言:“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這種自然宜於畜牧的環境之下,畜牧事業的發達,是可想像得到的事情。《史記·貨殖列傳》說:“烏氏倮畜牧,……畜至用穀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這正是北地郡一位養馬的大家。而東漢馬援也是以在邊郡出牧而致富豪。《後漢書》援本傳言:“嚐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關西養馬如此之眾多,其人民對於騎射的工夫,當然可以日趨精良,關西騎士的質與量為全國各地所不及,也當然得力於馬的力量。我們再由曆次征伐匈奴對於馬的損失,因而影響到關西騎士的優越的地位,可知馬的關係是如何的巨大。《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複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複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其損失之大直可驚人,甚至對於整個的國策也發生影響,對於關西騎士的命運,自然也有重大的關係。大概關西的騎士受了這樣的打擊,其精神稍有降落,到了東漢初年,漁陽、上穀的突騎,竟也有名於時,而關西騎士反沒人提起,故《後漢書·吳漢傳》就說:“漁陽上穀突騎天下所聞也。”話雖如此,關西人民尚武的精神究竟濃厚,雖因一時的挫折而有降落的情形,但休養生息,仍然可得到原來的狀況,所以,涼州兵的英名,曆久不衰,一直到三國初年,涼州兵還是被稱為天下的勁旅。
誠如班固所言,關西諸郡因為迫近戎狄,所以其俗習修戰備。自嬴秦以至漢末,匈奴與西羌始終為西北二大邊患,侵擾邊塞,抄掠人畜,一直沒有止息的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關西人民實在得不到休暇的機會。《漢書·賈誼傳》所謂:“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複,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恰是一幅絕妙的戍邊圖。關西人民為了自衛,也是不能不講求尚武的精神。《李廣傳》謂廣世世受射,這種相習成風的訓練,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自秦漢迄今,曆時數千年,雖然環境屢易,而西北人民仍然有以勇武聞於世者,這不能不說是受舊俗的影響。班氏所謂歌謠慷慨,風流猶存,其實把這兩句話用在今日也未嚐不可。
(本文選摘自《史念海佚稿》,史念海著,王雙懷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