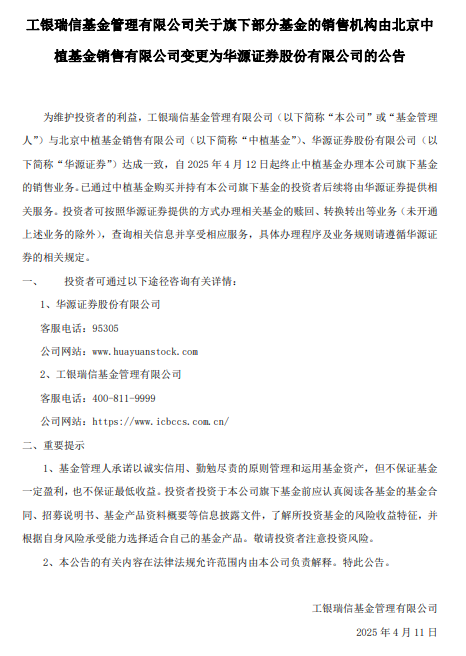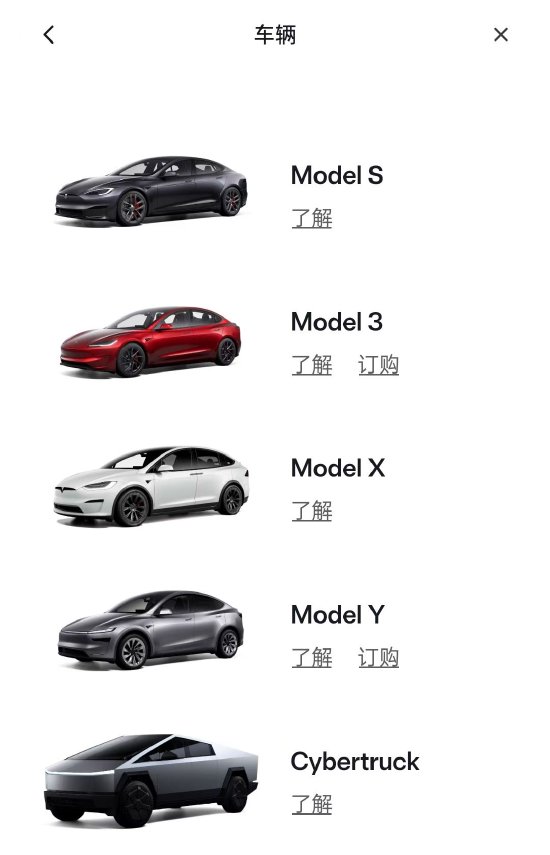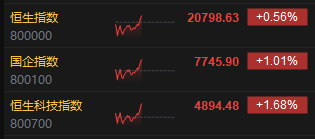南非行紀⑥︱南非鑽石和黃金開採業的經濟環境史
在人類曆史上,礦藏和採礦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採礦業中,貴金屬的開採雖然不像鐵礦和煤礦那樣將人類曆史帶入現代文明的工業化,但它以獨特的氣質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曆史的面貌。作為一般等價交換物的金和銀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金本位和銀本位的世界金融體系形塑和推動了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和發展。鑽石雖然沒有成為一般等價交換物,但作為被賦予了純潔和堅貞內涵的高貴之物不但在王冠上熠熠生輝,還在日常生活中散發美好。“鑽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正是這種寫照。然而,在南非曆史上,鑽石和黃金的發現和開採卻呈現出一幅愛恨情仇、傳奇與罪惡交織的複雜曆史畫面。
儘管殖民者自詡是為殖民地帶去文明,但華麗的說辭無法掩蓋其掠奪財富的真實動機和作為。殖民者到殖民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劫掠被打敗的皇室的金庫。在這個過程中,皮薩羅、科爾蒂斯、克萊武等表現出來的洋洋得意和貪得無厭成為世界曆史上最醜陋的一幕。然而,直接搶奪畢竟是一錘子買賣,為了持續掠奪財富,殖民者把目光轉向了土地和地下礦藏,或者按照世界市場需要建立牧場和種植園,生產能夠賺錢的畜牧產品和經濟作物,或者開採礦產資源,為宗主國獲取貴金屬和工業化需要的原料。南非也不例外,只是其進程稍晚於美洲,但也更為猛烈和狂熱。帝國主義時代和重商主義時代最大的不同在於大量賸餘資本迅速湧入殖民地,使一切賺錢的經濟活動都置於壟斷資本的控製之下,從而演繹出大魚吃小魚的悲歌。
 金伯利大坑博物館
金伯利大坑博物館金伯利發現鑽石礦後,來自世界各地的採礦者紛紛以非常低廉的價格獲得許可證,並用簡陋的工具在近萬個地塊上進行表層開採。但是,隨著開採的深入,所需要的技術越來越複雜,所需要的資金越來越多,個體開採者不但難以獲利,甚至很難生存。1870年,17歲的羅德斯追隨哥哥來到金伯利,加入開採鑽石熱。然而,讓他發跡的不是采到了很多鑽石(雖然每週都能獲得價值100英鎊的鑽石),而是他通過承包從深井抽水項目賺到的第一桶金。他用這些錢收購了德比爾斯農場的部分採礦許可證,進而與金融家、德裔猶太人拜特合作在1880年成立了德比爾斯礦業有限公司,並迅速上市圈錢(巴伯頓股票交易所),到1887年完全控製了德比爾斯採礦區,支付給股東的股息也從先前的3%上升到25%。與此同時,巴納托控製的金伯利中央礦業公司也迅速發展,雙方共同推高了南非的鑽石產量。南非的鑽石開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了人類鑽石開採史上的奇蹟。印度用2000年生產出2000萬克拉鑽石,巴西只用了200年,而南非僅用了15年。
 飛機上看到的金伯利大坑
飛機上看到的金伯利大坑 從觀賞天橋上看到的大坑
從觀賞天橋上看到的大坑如此高的產量在需求大致穩定的前提下必然導致鑽石價格的下降。為了保證公司獲得超額利潤,羅德斯一方面通過壓低勞動力價格降低開採成本,另一方面通過兼併其他公司形成對鑽石開採業的壟斷,從而把自主權掌握在自己手裡。面對掌握著全世界最好的鑽石產地“大坑(Big Hole)”的、巴納托的金伯利中央礦業公司的強有力競爭,一心要全面掌控金伯利鑽石開採業的羅德斯安排其歐洲代理人大肆購進巴納托公司的股票,然後通過自己的關係從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漢堡金融家各借款75萬英鎊,出價140萬英鎊從出售巴納托公司股票的法國公司買進,但這次購進不是用現金交易,而是用德比爾斯公司的股票支付,從而保證債權人和德比爾斯公司都能在股價上漲時獲利。這種一舉兩得的金融操作一方面反映了羅德斯高超的資本運作才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企圖從一頭牛身上扒下兩層皮的貪婪秉性。巴納托自然明白羅德斯的用心,企圖以更高的價格回購自己公司那些法國公司的股份。羅德斯再次展示出他機動靈活而又深謀遠慮的才幹。他提出以購買價把德比爾斯收購的巴納托公司的股份賣給巴納托的建議,但前提是巴納托不能付給羅德斯現金,而是金伯利中央礦業公司的股票。巴納托對羅德斯的盤算當然心知肚明,但迫於羅德斯背後龐大的、深不可測的金融資本的支持,不得不打破牙往肚子裡咽,出讓20%的股權給德比爾斯。羅德斯並不滿足,反而籌集更多資本,繼續瘋狂收購金伯利中央礦業公司的股票。雖然巴納托通過許以更高價格的方式企圖阻止收購,但隨著金伯利中央礦業公司股價的上漲,許多股民紛紛拋售套現,其結果是羅德斯和他的德比爾斯公司在金融資本的強力加持下最終控製了金伯利中央礦業公司,並與德比爾斯礦業公司合併,成立了一統鑽石業天下的德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該公司不但通過壟斷控製了全球90%以上的鑽石市場,還獲得了從事其它行業、組建自己的軍隊等權利,成為帝國主義時代的超級特權公司。
一如羅德斯所願,德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通過消減40%的南非鑽石產量把鑽石價格從每克拉20先令提升到30先令,同時由於縮減生產而節約了大量成本,這一進一出讓壟斷公司賺得盆滿缽滿。但是,這種壟斷也很脆弱,因為一旦發現了沒有被德比爾斯控製的鑽石礦,就會形成新的競爭。英布戰爭結束後,庫里南創建普利米亞鑽石開採公司,在比勒陀利亞附近開採鑽石。不到一年,其產量已達德比爾斯當年產量的1/3。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普利米亞公司在1905年1月開採出有史以來最大的鑽石(3106克拉),經過精密切割後,形成了舉世聞名的庫里南1號(530克拉,亦稱非洲之星)和2-4號,其中1號鑲嵌在英國王室的權杖上,其它三顆鑲嵌在不同的皇冠上。翌年,普利米亞的產量衝到200萬克拉,幾乎與德比爾斯當年產量持平。此後不久,德比爾斯的鑽石產量就僅占世界總產量的40%,其壟斷地位已經名存實亡。然而,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鑽石開採業不景氣的天賜良機,德比爾斯通過購買普里米亞股票等手段控製了普利米亞,再次成為君臨天下的鑽石之王。然而,江山帶有才人出,歐內斯特·奧本海默橫空出世。奧本海默在強大的家族關係和金融家摩根的支持下,創立南非英美有限公司,投身於蘭德金礦開採。在金礦開採中積累財富之後,它轉而在德屬西南非洲開採鑽石,逐漸在鑽石生產行業成為舉足輕重的公司。奧本海默並不滿足於自己賺錢,他與羅德斯一樣,要壟斷整個行業。他先把觸角伸向西非的鑽石生產,積累巨額財富之後就對德比爾斯進行滲透和控製。當他掌握了足夠多的德比爾斯股份後,就在1929年12月20日順理成章地、經過董事會選舉當上了德比爾斯集團的主席。比起羅德斯的德比爾斯,奧本海默的德比爾斯不但壟斷了全世界80%以上的鑽石供應,還整垮了倫敦鑽石集團,形成了供應和銷售一條龍的“單渠道銷售體系”,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把蘇聯的鑽石銷售也收於囊中。德比爾斯在世界鑽石和經濟市場上興風作浪,唯我獨尊,甚至形成了德比爾斯與鑽石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神話。
 金伯利礦的地下坑道
金伯利礦的地下坑道資本的本性是逐利增殖。1886年,蘭德發現了當時世界上最大、最集中的含鈾礫岩型金礦,黃金儲量達6.5萬噸。在這個地質學上稱為蘭德盆地的地區,先後發現了6個金礦田,而最早發現的露頭礦就在中蘭德金礦田上。易采的金礦發現後,世界各地的資本和淘金者都不遠萬里,趨之若鶩,金伯利的鑽石大亨怎會缺席?羅德斯和拜特都積極參與,但不同的追求和取向讓他們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1887年,羅德斯和魯德組建了南非產金地有限公司。1889年,拜特等組建了維納拜特公司。這些公司一方面到約翰內斯堡股票交易所募集資金,另一方面尋求國際資本的支持。前者得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融支持,後者有法國銀行支撐。除此之外,還有德意誌銀行支持的格茨公司等,但這些公司的實力不能與前兩者同日而語,在南非的黃金開採業中沒有佔據主導地位。雖然南非產金地公司實力雄厚,但羅德斯在金礦開採上並沒有顯示出與鑽石開採上同樣的敏銳嗅覺和經營才能,相反卻屢失良機,錯過一個又一個獲得富礦的機會,只買下了一些貧礦。然而,作為一個具有政治夢想的投機者,他通過買賣其它賺錢公司的股票大獲其利,同時鼓動操縱對德蘭士瓦共和國的兼併,企圖把蘭德礦脈完全納入英國囊中。雖然羅德斯沒有看到英布戰爭勝利的那一天,但他的德比爾斯公司在南非金礦開採業中仍然佔據了重要地位。在法國銀行支持下,維納拜特公司不僅從法國和約堡股市獲得大量資金,還兼併了蘭德的其它采金公司,開發了遠東采金地,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南非金礦開採的大勢。蘭德黃金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重持續上升,1886年占0.16%,1891年占10.89%,1894年占20.60%,1907年32.32%,1909年占33.05%,達729萬盎司,接近1/3。
 金礦脈
金礦脈 作者體驗淘金
作者體驗淘金與鑽石主要是貴重飾品不同,黃金是支撐金融體系的支柱性貴金屬。在世界曆史上,大型金礦脈的開採不但改變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走勢,還對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從1849年的加利福尼亞金礦到1850和60年代的澳大拉西亞金礦、1880年代的南非金礦、再到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金礦,莫不如此。毫無疑問,蘭德金礦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正當黃金產量迅速增加時,白銀產量卻相對下降。從1848年到1860年,金銀產量之比從1:16降到1:4,銀逐漸失去了可以主宰金融的絕對優勢地位,為歐美主要工業化國家過渡到金本位製奠定了物質基礎。從1850年到1896年,歐美國家相繼放棄銀本位製,改行金本位製,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提供了有利條件。
就國內影響而言,蘭德金礦的開採與金伯利鑽石礦開採以及德蘭士瓦和納塔爾煤礦的開採一起促成南非的礦業革命,進而帶動了南非的工業革命。按照經典的工業化模式,國家利用資本和技術,選擇某個產業作為突破口,並在其帶動下展開全面工業化,進而促成政治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然而,南非的工業化及其影響卻與眾不同。它的啟動不是由國家推動(德蘭士瓦共和國本質上是建立在牧羊業基礎上的農業國家),而是由渴望發財的投機者和資本家利用市場推動的;它的起飛主導部門不是紡織業,也不是製造業,而是貴金屬開採業;它的資本不是來自奴隸貿易的積累和農業的賸餘,而是來自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賸餘資本;它的深層開採技術不是來自工匠的經驗知識積累或大學實驗室的新發明,而是從先發工業化國家直接引進;它帶動的工業化並非在國內建立完整和平衡的經濟體系,而是以出口為導向和麵向白人統治者的獨特經濟體系;它的影響也不是社會和政治的全面進步,而是白人社會與非白人社會的完全隔離,白人的進步建立在非白人的被歧視基礎上。南非的現代化是畸形的現代化。
南非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典型的後發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政府(1910年前主要是德蘭斯瓦共和國,之後是南非聯邦)和壟斷資本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是採礦業還是製造業和商品化農業的發展,都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對南部非洲黑人實行種族歧視和隔離政策是製造廉價勞動力的粗暴而有效的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壟斷資本的需求和推動也不容忽視。儘管羅德斯聲稱要“打造世界上最富有、最偉大、最強大的公司”,但對公司工人採取的卻是最不人道的政策。剛到金伯利,在寫給母親的信中,羅德斯把近萬黑人採礦的小山丘比喻成螞蟻堆,把在上面勞作的黑人比喻成黑螞蟻。儘管他當時還是一個來南非討生活的小年輕,但骨子裡對黑人的歧視已是昭然若揭。在控製了德比爾斯礦區後,他把非洲勞工圈進孤立的混居區,一方面保證礦區的勞動力供應,另一方面迫使他們在混居區的公司商店消費,把掙來的低工資還給資本家。即使這樣,隨著壟斷程度的加強,公司不斷裁員,與此同時,工人的工作條件不斷惡化。金伯利爆發天花後,羅德斯故意隱瞞消息,導致751名工人在天花被控製之前死亡。之所以隱瞞,是因為他覺得一旦公開消息,工人會逃回家,影響礦區生產。另外,他也不願意負擔接種費用。由此可見,在羅德斯心目中,賺錢永遠重於非洲人的性命。羅德斯擔任開普殖民地議會議員和總理職務後,與阿非利卡人沆瀣一氣,不但要剝奪非洲人對土地的固有權利和少數非洲人享有的投票權,還主張通過有利於工業、不利於非洲人的法規。他在議會演講時說:“土著應該被當作孩童對待,應該剝奪其公民選舉權。在處理與南非野蠻人的關係時,我們必須採取專製統治。”為了獲得更多的鑽石礦和金礦,羅德斯利用南非公司,兼併了馬塔貝萊王國,奪占了黑人的土地,建立了羅德西亞殖民地。雖然羅德西亞的礦藏並不如預期,但製造出大量流動勞工,滿足了南非的鑽石礦和金礦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而對待已經到金伯利打工的非洲人,羅德斯支持實行通行證制度,支持剝奪黑人和有色人種獲得採礦許可證的權利,支持對黑人進行鞭笞或私刑。面對鑽石走私問題,羅德斯在議會領導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調查黑人走私和製定杜絕走私的政策。1882年通過的《鑽石貿易法》規定,嫌犯在被證明無罪之前被推定有罪,可以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判處最高15年的監禁。
在金礦開採中,需要的勞動力更多,然而,壟斷資本在金價基本穩定的前提下,為了保障獲得超額利潤,極力壓縮工人工資,降低可變資本比例。在礦業公司的推動下,南非政府在1911年頒布了礦山和工廠法,規定非白人不能從事技術工種。1922年蘭德罷工之後,窮白人的利益得到保障,而非白人的利益進一步被剝奪。1924年頒布文明勞工通令,規定非白人只能從事非文明工作,獲得非文明工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非製造業產值超過採礦業,成為第一大產業,採礦業中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擴展到其它產業。1953年通過的土著勞工法剝奪了黑人為改善工作條件而罷工的權利,黑人參加罷工即被視為刑事犯罪,可處三年監禁和罰款。1956年的工業調節法不但不承認黑人的僱員資格,還進一步強化了先前的職業保留制度。這種制度在1980年代之前確實促進了南非的白人現代化,但這種反人類的政策和實踐最終使南非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而難以為繼。雖然1994年民主新南非的建立創造了人類曆史上和平過渡的成功範例,但種族隔離制度的長遠影響及其與資本主義的複雜關係卻不是短期內能夠捋順的。
19世紀末的採礦業無疑是個髒活累活,尤其是在乾燥少雨的南非內陸地區。那時的資本家雖然不用像工人一樣幹體力活,但他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與工人的一樣髒亂艱苦。羅德斯初到金伯利時,那裡的環境非常惡劣。到處是死亡的馱畜,任其腐爛。蠅蟲寄生在食物、飲料和隨處排泄的便溺中,四處肆虐,傳染疾病,導致痢疾等流行。當地嚴重缺水,礦工長期不能洗澡,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迅速惡化。最可怕的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嚴重沙塵暴。無論是寒冷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天,被剝離了植被、堆滿了礦渣的地表一遇到強風,就會形成駭人的沙塵,掀翻簡陋的建築物屋頂和帳篷,帶毒的塵土直擊人們的身體,像海浪洶湧而來的塵暴好似要吞沒地面的一切。那時的羅德斯也只能因陋就簡,和朋友住在瓦楞鐵覆蓋的簡易住所中,經受著惡劣環境的考驗。只是後來積累了大量財富,才在金伯利建設豪華療養院,在開普敦蓋豪宅。他說,建療養院是他的個人愛好,而金伯利是那些心肺有問題的人進行療養的絕佳地方。換言之,他建療養院既是為了自己調養身體,也是為了展示自己的成功,在金伯利富人圈樹立自己的威望。發跡了的羅德斯不再像礦工那樣繼續遭受環境破壞和疾病流行的危害了。
此後,隨著資本的積累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白人資本家和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大大改善,而黑人勞工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因勞動負荷的加大而更顯惡化。肺炎和矽肺等疾病高發,從舊大陸傳來的結核病等在礦區傳播開來,既對黑人健康和生命造成損害,也影響礦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對南非礦工中肺結核病高發的認識經曆了曲折的過程。最初想當然地以為,肺結核高發是因為黑人不良衛生習慣和營養不良所致,是黑人不適應城市生活和工業化的產物。後來經過調查發現,這種從歐亞大陸傳入非洲的流行病對保留地黑人危害並不大,或者說保留地黑人對此病具有一定免疫力,但進入城市和礦區的黑人由於勞動環境惡劣和營養不良而逐漸喪失對此病的免疫力,環境惡化是造成結核病流行的關鍵因素。然而,進一步的調查研究發現,保留地也不是結核病的免疫地,相反隨著保留地環境的惡化,結核病在保留地也逐漸流行開來。蘭德金礦所在地植被稀疏,金礦開採對木材的需求導致地面植被大量被破壞,加之大量尾礦壩的出現使粉塵大量增加,當地的空氣質量急劇下降。隨著深井礦的開採,井下環境由於爆破和高溫高濕而越來越嚴峻,對礦工的身體健康極其不利,到1910年中央礦業集團的結核病發病率飆升到16‰。此後雖然有所下降,但隨著保留地人地關係的惡化和防病措施不足,結核病的發病率又創新高,1976年幾乎重回1910年的高位。這說明,黑人礦工中結核病告發不僅是一個環境產物,還是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建構。
在金礦開採和提煉中,會造成汞汙染。蘭德金礦本身的汞含量比較高,雖然在提煉時採用濕法冶金技術,但依然造成礦場廢水中汞含量超標。雖然當時沒有留下詳細客觀的資料,但現在通過採用科學調查和研究方法大致上可以探明汞汙染的環境影響。蘭德方丹金礦位於約翰內斯堡以西45公里處,是一個傳統老礦。從其豎井和鑽孔以及遭到尾礦壩滲漏的周圍小溪和濕地獲取的酸性廢水樣本中,可以發現蘭德方丹水的PH值介於2.9-5.0之間,汞含量最高的地方甚至超過平均值的四倍多,被環保署認為會對水生生物產生極為不利的慢性影響。另外,廢水中生物化的甲基汞含量越是離礦坑和提煉車間近越高,表土中的汞總量最高達到2581納克,濕地中的高於旱地,上遊的高於下遊的,沉積物中的汞總量表層高於底層。雖然土壤具有一定的去甲基化的能力,但並不能解決土壤和沉積物中過高含量的甲基汞的問題。無機汞變成甲基汞後,毒性大增,不但會造成水質惡化,還會在生物體內聚集,進而通過食物鏈影響人體健康。
在現在的蘭德礦田周圍,存在著與常規的城市環境很不協調的、引人注目的270多座光禿禿、白晃晃的梯形尾礦壩。尾礦壩是由提取黃金之後的尾礦砂構成,其中石英石占90%以上。這種土壤不適宜植被生長,缺乏植被就會加劇風蝕和水蝕,造成嚴重水土流失。更具危害的是流失的水土中酸、鹽、汞和重金屬(包括砷、鈷、鉻、銅、鐵、錳、鎳、鉛、硫、鋅等。)含量遠超正常值,這些物質經過化學反應形成更具危害性的化合物。它流經和所到之處土地荒蕪,影響動植物生長。另外,有毒物質不僅汙染了地下水,甚至深入到滲流帶,還汙染了表土,有些地方甚至深入到底土。雖然隨著技術進步,近年來有些含金量相對較高的尾礦壩被重新利用,但壩址所在地被汙染的環境並沒有得到有效治理。筆者在考察途中曾經遭遇沙塵暴,其中的顆粒物質和粉塵由一部分來自老的尾礦壩,這種次生災害擴大了尾礦壩的影響範圍,造成損失擴大化。更為恐怖的是,部分尾礦壩分佈於約翰內斯堡市內,影響著市民的身體健康和城市發展。在當地人的語言中,約堡就是黃金城。約堡因開採金礦而出生並茁壯成長,然而,約堡也深受采金後遺症之苦。尾礦壩是約堡不得不面對和需要花大力氣解決的環境問題。
其實,南非有相對比較完整的環境管理法律和政策體系,採礦業中的環境管理和技術標準也是其它非洲國家學習的模板。就採礦業中的水管理而言,根據1996年南非憲法中的權利法案、1998年南非環境管理法和南非水法、1996年礦業健康和安全法、2004年南非環境管理法之大氣質量法、1999年南非遺產資源法等規定的原則,南非水務部(原南非水務和森林部)出台了嚴格的採礦業水資源保護指南,包括礦業水綜合管理、水汙染防治和影響最小化、水的回收和再利用、污水處理等方面。在這些規定之下還有更為具體的分類政策指南。就跨部門合作治理指南而言,不但涉及水鹽平衡、暴雨雨水管理、閉礦水管理,還涉及水監測體系和水影響預測等。就礦山水管理而言,包括從開採到冶煉等不同環節,如小型礦、露頭礦、深井礦、濕法冶煉廠、尾礦壩、污水控製壩等。從理論上講,這些措施及其理念不能說不先進,不能說不全面,如果能夠得到嚴格執行,就不會出現水汙染問題。但現實情況是,在礦業生產中,對人身安全問題的重視超過環境管理,在成本效益核算中對短期影響因素的重視超過長期影響因素,更何況還有很多曆史遺留問題,還有很多非法采金者等。前者是礦業公司造成的問題,但經過曆史演變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公共問題,後者不僅是礦業的問題,更是非法移民和警察執法的問題。這些累積和疊加的問題使法規的適用性大為降低,而執法隊伍執行力不足進一步弱化了礦業水管理的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南非礦業既為南非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留下了必須克服的環境問題,但解決礦業環境問題在現實中因為牽涉各方利益而變得異常錯綜複雜,這在很大程度上考驗著政府、礦業公司和社會的聯動和互動能力。
俗話說得好,“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雖然早在上個世紀末就關注羅德斯和蘭德罷工,也閱讀了當時能夠找到的資料,但沒有現地體驗總覺得隔著一層紙。2019年夏天,藉著去澳州研究採礦業的全球環境史(主要是煤礦和鐵礦)之機,順便去本地戈參觀了Victoria山金礦遺址,觀察採礦造成的環境破壞和恢復環境的努力,下到中央德寶拉礦200多米深的作業面,辨認金礦石、體會采金業的工作環境,在地面上嚐試淘金作業程序,觀看冶煉過程。這種回到曆史現場、尋獲感悟的過程給我一種用內部人的視角對外國曆史進行同情之理解的體驗。而這種感受是從閱讀書面資料中得不到的,也是外國人研究外國史最需要的基本的能力。今年夏天終於有機會到南非,金伯利和蘭德自然不容錯過。
然而,鑽石和金礦開採畢竟是非常專業的領域,即使是研究它的曆史也不能忽視對專業知識的補充。南非大學名譽教授趙先生不僅是地質學和礦物學專家,還曾經做過金礦公司高管,是理論知識和管理經驗兼具的復合型”大咖“。在趙老師帶領下,參觀了地質展示公園,觀摩了他收集的各種礦石,登高俯瞰了約翰內斯堡的尾礦壩,途中還辨認了隨處可見的各種岩石和普通礦石。這次惡補無疑加深了我對礦業的理解,也啟發我從地質學角度認識南非曆史的演進及其獨特形態的形成背後的動力機制。
 威爾考姆金礦封閉礦區
威爾考姆金礦封閉礦區 威爾考姆金礦開放礦區
威爾考姆金礦開放礦區按照趙老師給出的參觀建議,利用姒總提供的、難能可貴的便利條件,從約堡一路南下,越過南非曆史上最重要的瓦爾河和奧蘭治河,先到布隆方丹再到金伯利。途中參觀了蘭德礦脈最南端的威爾考姆金礦。該礦由和諧金礦有限公司經營,有些礦區封閉管理,不進到場內無法看到任何生產過程,有些礦區基本上是開放式的,遠遠就能看到豎井和正在堆積的尾礦壩。當時正值礦工換班時間,發現礦工裝備齊全,面容乾淨,有些女礦工甚至還化著淡妝,他們升井後履行完相關手續就開車回家。這與我心目中的礦工形象大不相同。在公司人事部,相關人員介紹了公司的曆史和現狀,從中可以看出,現在的金礦公司與種族隔離時期的大異其趣,不僅僅是黑人進入管理層,從事決策和管理工作,而且還有白人工人與黑人工人一樣在井下第一線工作,同工同酬,真是換了人間。
 作者在麥克格雷格博物館查檔
作者在麥克格雷格博物館查檔金伯利是南非鑽石開採的中心地帶,那裡既藏有大量檔案資料,也是曆史發生的現場。在麥克格雷格博物館,查到大量金伯利和德比爾斯礦業公司的文字和圖片資料,對金伯利鑽石開採業、當地曆史和環境變遷產生直觀印象。在大坑博物館,不但看到了各種實物展覽以及拍賣等模擬實景展覽,還原了當時採礦業和其它產業發展的曆程,還看到了大坑和地下採礦坑道。在從開普敦飛往約堡的飛機上,就曾看到了大坑遺蹟,現場觀看更是令人震撼。大坑鑽石礦發現於1871年7月16日,1914年8月停采。40多年間,共開採了14504566克拉鑽石,最深處離地面1097米,挖出土石2250萬噸。現在大坑深215米,水面距地面174米。在坑道里,能夠體驗到黑人礦工勞動的艱難和困苦。這與拍賣廳和集市廣場上白人資本家和投機商亢奮喧鬧的情景形成鮮明對照。站在高高懸空的觀賞天橋上,俯視腳下的大坑、遠眺對面曾經的德比爾斯大廈,感慨曆史的弔詭和無情。當年羅德斯經常坐在礦坑邊緣發呆,當別人問他在想什麼時,他回答在尋找力量。羅德斯真是一位以金錢為力量推動曆史進化的人,至於他發揮了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還得由後人來評說。在開普敦大學,他的雕像被移走,但在金伯利,他的雕像依然矗立在市中心,雖然不遠處就是以反種族隔離而著名的普拉徹的名字命名的大學。
 世界上最深的金礦
世界上最深的金礦 姆寶嫩礦區
姆寶嫩礦區在和諧公司經營的姆寶嫩礦區,看到了世界上最深的礦井,離地面大約4175米,開採深度達3300米。該礦原由南非英美阿散蒂金礦公司所有,準備向5000米深度開採,但因成本太高而不得不出售。隨著開採深度的增加,礦道中的溫度升高,空氣稀薄,滲水增加,公司通過管道把在地表製冷過的新鮮空氣送入地下,用枕木和尾礦回填來穩定坑道。儘管開採條件已經大為改善,井下開採條件依然比較艱苦。幾千米的岩石壓力不僅會造成岩爆,還會引起周圍發生礦震,造成人員傷亡,儘管這個數字因為實行了嚴格的安全和環境標準在下降。在場區,還看到了種族隔離時期的混居區。雖然現在住在礦區的工人住房條件大為改善,但處在荒郊野外的這些集體住房仍然給人以與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印象。礦主和礦工百年來都不斷髮生變化,有些人甚至命喪井下,但利用黃金開採實現資本增值是唯一不變的邏輯,曆史就是在這個軌道上自行運行,其它都是這個軌道上的過客而已。
真正體驗采金工人工作環境和金礦大亨生活環境是在位於太陽城的金礦博物館。金礦博物館由地面和地下兩部分組成。地上主要是曾經擁有這一地塊的寡婦歐斯圖伊澤和金礦經營者的豪宅。從室內的擺設可以看出他們生活的奢華和講究,那些比較古老的高爾夫球杆彷佛昭示著他們的主人的榮耀和前衛。直到現在,在約堡看到整潔舒心的高爾夫球場,就不由得讓人產生天上人間的巨大反差感。井下完全是另一種環境。在這個開採了84年(1887-1971)的皇冠礦14號井,3萬多工人總共采出140萬克黃金,是當時世界上最深的金礦。博物館建立初期,參觀點在第5個工作面,位於地下226米處,現在的參觀點僅在地下75米處。即使如此,也能體會到當年黑人礦工在礦道勞動的艱辛。在用蠟燭照明的礦道上,在用枕木支撐的作業面,沒有耳塞的工人操作著鑽機打孔,填裝炸藥進行爆破,然後用驢子把裝滿金礦石的椰子鍋車拉上地面。由於使用明火,井下經常發生甲烷氣體爆炸事故,造成人員傷亡,長期操作鑽機的工人會耳聾。回到地上,可以觀看煉金以及製作金條的生產過程。在這金光閃閃的光鮮背後映現的是那些與礦石一樣黑的井下工人的面孔,在金礦大亨輕酌慢飲的葡萄酒之光怪陸離中折射著黑人礦工的血和汗。難道社會的進步只能是“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曆史的發展自有其冷峻的辯證法,但絕不是贏者通吃的曆史,研究曆史的也是有感情的人。面對南非獨特的曆史和急劇的社會變遷,曆史學家需要在探求真相、臧否曆史和情感好惡之間取得平衡。即使是涉及亮晶晶的鑽石和金燦燦的黃金,也不能把自我迷失在勝者流傳下來的文獻中,而是要在實地研究(是fieldwork,即把文獻研究和現地體驗結合,而不僅僅是到當地找文獻或走馬觀花的fieldtrip。)中既看到貴金屬產業的曆史貢獻,也不能忽視背後的資本邏輯和對黑人礦工的壓榨,還有它留下的環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