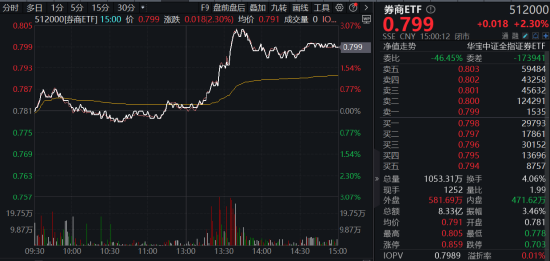“髒活”源自“好人”的無意識授權
【編者按】
為什麼有些職業既不道德又不體面,還有人搶著做?當工作不再享有尊嚴,我們是否有退出的選擇?在《髒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這本講述職業與不平等的非虛構著作中,作者援引了“髒活”的概念,即社會中不可或缺但被視為肮髒、下作的工作。這些崗位上的工作者無權無勢、朝不保夕,還會遭受羞辱與良心譴責。而公眾為了自己的良心安寧,寧願被蒙在鼓裡。本書作者埃亞勒·普雷斯(Eyal Press)是一位作家、記者,紐約大學社會學博士,曾獲詹姆斯·阿倫森社會正義新聞獎等,是《紐約客》《紐約時報》等媒體的撰稿人。他在書中敦促讀者:不要對我們肮髒的秘密避而不見。本文摘自《髒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望mountain2023年11月版,李立豐譯。有刪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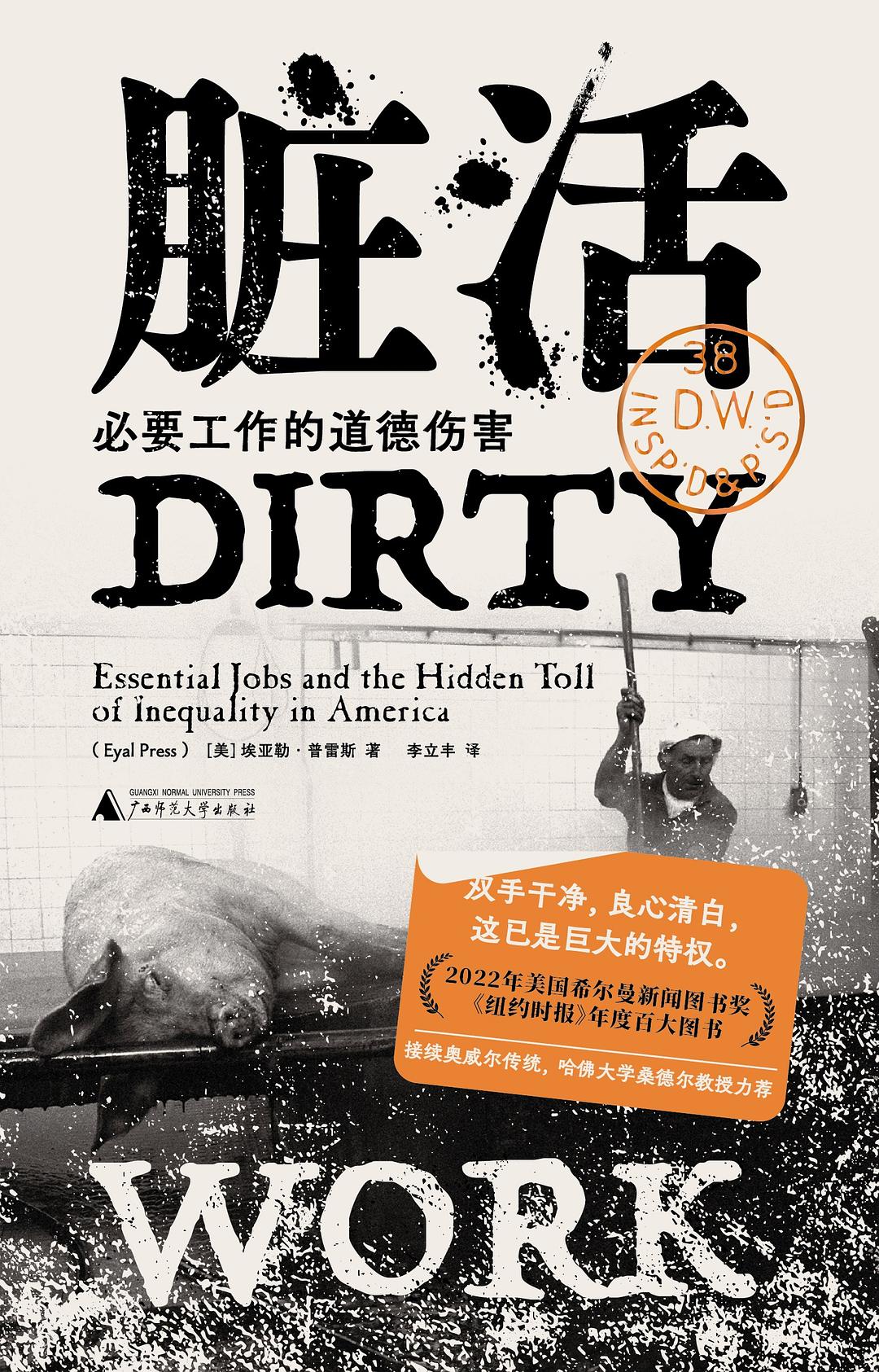 《髒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書封
《髒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書封休斯出生於1897年,是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高徒。帕克記者出身,曾擔任布克·T. 華盛頓的助手,也是芝加哥社會學派的掌門人之一,該學派強調直接觀察在帕克所謂“人類生態學”研究中的獨特價值。
……
在法蘭克福訪學期間撰寫的日記中,休斯描述了自己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交往,這些人“就總體的思想、態度和修養而言,與任何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無異”。造訪建築師的經曆便很有代表性。大家坐在偌大一個滿是圖紙的工作室,一邊啜飲香茗,一邊暢談科學、藝術和戲劇。“如果各國有識之士都能這樣面對面交流該有多好。”在座的一名德國教師如是說。那天晚上,這名教師抱怨自己在法蘭克福(當時仍處於美軍占領下)遇到的一些美國士兵很無禮,休斯順勢拋出了一個更為微妙的話題。他詢問這位女士是否瞭解德國士兵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
“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就為我的人民感到羞愧,”建築師插話道,“但我們當時並不瞭解,只是後來才知道了這些。您得清楚我們承受的壓力:我們必須加入納粹黨;我們只能噤聲不語,奉命行事。壓力之大可不是鬧著玩的。”
……
夜半時分,休斯起身告辭,離開了建築師的家。但這段對話一直在他的心頭縈繞。回到北美後,休斯在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做過一次演講,曾提及此事。十四年後,即1962年,演講的文字稿發表於《社會問題》期刊上。彼時,學界湧現了諸多理論,以解釋納粹統治下發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以及它們最終是如何導致種族滅絕的:德國獨有的“威權人格”,對於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熱崇拜。休斯則關注到另一個與狂熱分子以外的人都有關,且並非德國獨有的因素。他認為,在希特勒統治下犯下可怖罪行的兇手,並非完全遵從元首的命令被動行事。他們是“好人”的“代理人”(agent),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建築師一樣,這些“好人”對迫害猶太人的行徑視而不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樂見其成。
“大屠殺”“滅絕猶太人”,類似描述納粹消滅猶太人的術語有很多。休斯選擇的表達方式更為平淡。他稱之為“髒活”,這一術語意味著雖然肮髒且令人不悅,但並非完全不被社會中的體面人欣賞。休斯從那位建築師對“猶太問題”的思考中得出結論:受過教育的德國人即使不是堅定的納粹分子,也並非不歡迎清除“劣等種族”的做法。類似的態度,休斯在法蘭克福時參與的其他談話中也有體察。談到這位建築師時,休斯寫道:“他刻意與猶太人劃清界限,並宣佈他們是個問題,顯然也願意讓其他人來做自己不會去做的髒活,正是為此他才感到羞愧。”
正如休斯設想的,這就是髒活的本質:將某些不道德的行為交由代理人實施,再順勢對此矢口否認。與流氓不同,被分配干髒活的作惡者獲得了社會“無意識的授權”(unconscious mandate)。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納粹確實設法獲得了社會的授權。正如曆史學家羅伯特·格拉特利在2001年出版的《支持希特勒:納粹德國的同意與脅迫》一書中指出的,對於普通德國人來說,針對猶太人和其他“不受歡迎者”的暴力運動幾乎不是什麼秘密,大家都心知肚明,且經常為種族淨化運動推波助瀾。從這個意義上說,休斯在《社會問題》上發表的題為《好人和髒活》的文章可謂有先見之明。但正如他竭力強調的,他發表該文的目的絕不是要證實這一點。休其斯寫道:“在此重提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並不是為了譴責德國民眾,而是提醒大家注意始終潛伏在王我們中間的危險。”
……
休斯關注的是一種在他看來存在於所有社會的動態,在美國尤甚。可以肯定的是,戰後美國的不公與納粹時代的暴行在道義上顯然無法同日而語,休斯將後者描述為“世界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社會髒活”。但在不那麼專製的國家實施的不那麼極端的髒活,仍然需要“好人”的默許。事實上,在民主國家,這種同意比在像納粹德國這樣的獨裁國家更為重要,因為在所謂的民主國家,反對意見可以得到容忍,公職人員可以被投票罷免。與其他民主國家的民眾一樣,美國人有權質疑並可能阻止以他們的名義進行的不道德活動。
休斯寫道:“問題在於做了什麼,誰做的,以及實施者從我們這裏所獲授權的性質。也許我們無意識地給了他們授權,讓他們的行徑超越我們自己想做甚至希望承認的範圍。”
* * *
休斯的文章發表五十多年後,他提出的問題值得重新審視。當代美國出現了什麼髒活?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社會的無意識授權?有多少“好人”寧願不去深究那些以他們的名義做的事情?當這類事情可以委託給孤立存在的隱形“髒活勞工”階級時,實現起來有多容易?
自2020年冬季以來,美國社會的運轉對這群隱形工人的依賴性暴露無遺。新冠大流行期間,各州州長髮佈封鎖禁令,成千上萬個工作崗位隨即消失或暫時停工,真相也浮出水面。這場大流行無比真切地證明,擁有更多特權、可以奢侈地居家辦公的美國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超市收銀員、送貨司機、倉庫管理員等數以百萬的低薪工人,他們的工作被認為過於關鍵,根本不能喊停。這些工作通常留給女性和有色人種,長期處於全球經濟的陰影之下,幹的苦工與低廉的計時工資不成正比。大流行期間,這些工人履行的職責被賦予了新的稱號:“基礎工作”。但這並沒有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許多工人依然無法享受醫療保健和帶薪病假,即使必須承擔接觸潛在致命病毒的風險,也無法獲得個人防護裝備。然而,“基礎工作”的稱號強調了一個基本的真相,即如果沒人從事這些工作,社會就無法運轉。
 當地時間2023年7月7日,美國佐治亞州,美國聯合包裹(UPS)與卡車司機工會間的勞工合同談判破裂,卡車司機舉行罷工。
當地時間2023年7月7日,美國佐治亞州,美國聯合包裹(UPS)與卡車司機工會間的勞工合同談判破裂,卡車司機舉行罷工。但是,還有一種被很多人認為有損道德,甚至更不可見的隱形勞動,也是社會必需的。例如,在美國的很多州,監獄或看守所中的精神病房已經取代醫院成為當地規模最大的精神衛生機構,這也導致了無以計數的殘忍行為,且工作人員經常違反醫德,默許獄警虐待被監禁者。又例如,在美國發動的永無止境的戰爭中實施的“定點清除”,儘管在幾乎完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發動的致命打擊數量不斷增加,但戰爭已經無法成為頭條新聞。
批評者可能會認為,大規模監禁或無人機定點清除這類工作純屬多餘。然而,它們對於維持通行的社會秩序來說實屬必要,可以解決許多美國人想要解決,但又不想費神,更不要說親自處理的“問題”。比如,如何安置社群中得不到護理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只需要將成千上萬這樣的人關進監獄或者看守所,就可以很快將其忘在腦後。又比如,當舉國上下對代價不菲的武裝干預失去興趣、對酷刑和無限期拘留的爭論感到不安時,如何繼續進行無休止的戰爭,便可以通過大規模使用武裝無人機加以解決。
在過去的一年里,一些干髒活的工人不再隱形,其中最為惹眼的是在美國屠宰場“宰殺車間”工作的非裔及拉美裔勞工。為了滿足大眾對廉價肉品的需求,在消費者聞所未聞的惡劣條件下,動物被運送到屠宰場宰殺分割。新冠大流行使人們開始關注牛肉、豬肉和雞肉工廠生產線工人面臨的人身危險。儘管有數十名工人死亡,數萬人感染新冠病毒,但這些工廠仍被嚴令繼續生產。和許多幹髒活的工人一樣,屠宰場工人在工作中經常面臨極端的健康風險,這是行業的惡劣工作條件與從業者相對劣勢的社會地位共同造成的。但由於這類工作性質令人不快,屠宰場工人還更容易受到另一種鮮為人知的職業風險侵害。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在工業化屠宰場大規模屠殺動物,就像在監獄大規模羈押精神病患者一樣令人不適,甚至會引發厭惡和羞恥。這些負面情緒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公眾對於從事宰殺和羈押工作的人員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這些工人的自我認知。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和喬納森·科布在其經典著作《階級的隱性傷害》中,呼籲將階級分析的重點從物質條件轉移到工人們承受的“道德負擔和情感困境”上來。對於專事髒活的工人來說,負擔包括被汙名化、自責、名譽掃地、自尊受損。在某些情況下,工人們還會經曆創傷後應激障礙和“道德傷害”(moral injury),這一術語本來是軍事心理學家用來描述士兵在執行違反自身核心價值的命令後承受的痛苦。
工作可能會造成道德傷害,這一觀點並沒有完全被忽視。在新冠大流行的高峰期,很多文章細緻地描述了醫生和護士如何被迫做出痛苦的決定:在人滿為患的醫院,應該給哪些患者上呼吸機?誰能活下去?紐約市的一位急診醫生寫道:“我們再也不會和以前一樣了。”疫情期間,這位醫生身處一線,她對醫護人員的切膚之痛深有體會。但值得注意的是,是一場始料未及的危機才把醫生推向這樣的角色,而這場危機最終得以平息。對於許多幹髒活的工人來說,由於社會的組織方式以及工作的具體需要,他們每天都需要做出艱難的抉擇,遭受可能帶來的痛苦。此外,與醫生不同,這些工人並沒有從事被視為高尚的職業並受到同胞稱讚。相反,他們因被迫從事低下的工作而蒙受汙名與羞辱。
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那些僅僅為了掙錢而從事道德存疑的行當的人,應該為此感到羞恥。這正是許多移民權利倡導者對近年來執行美國非人道移民政策的邊境巡邏隊的感受,也是一些和平活動人士指責參與定點清除的無人機操作員手上有血的理由。這些人的觀點有其道理。在下文中即將登場的干髒活的工人,並不是他們供職的體制的主要受害者。對於遭受這些行動的人來說,干髒活的工人根本就不是受害者。他們是加害者,其履行的職責往往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和痛苦。
但是,將髒活的責任完全甩給具體的執行者,可能非常行之有效,足以掩蓋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使髒活常態化的層層共謀。這樣做還可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從而忽視了最終決定誰來幹髒活的結構性缺陷。儘管哪裡都有髒活,但在美國,髒活的分配絕非隨機。正如後文所示,髒活不成比例地落到了選擇和機會較少的人身上:來自落後農村地區的高中畢業生、無證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種。與其他薪酬微薄且存在人身危險的工作一樣,干髒活的主要是社會弱勢階層,他們不像生活相對富裕、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階層那樣,擁有技能和資曆、社會流動性和權勢。
這些工人的困境和經曆講述了當代美國更為宏大的故事,揭示了經濟學家們未曾注意到的不平等的面向。財富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工資中位數則停滯不前:這是衡量和描述不平等的典型方式,統計數字很形象地顯示出,近幾十年來很少有美國人從經濟增長中受益。這些數字確實很引人注目。根據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伊曼紐爾·賽斯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的研究,1980-2014年間,美國前1%的富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幾乎翻了一番,而靠後一半的人所占份額下降了近50%。另一項研究顯示,400名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所有非裔美國人的財富總和。
經濟不平等還反映並強化了道德不平等。正如富人和窮人居住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樣,在美國從事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陷入道德困境的人群,跟免於從事這些工作的人群之間,同樣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在一個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當中,像其他許多事情一樣,雙手乾淨、良心清白,日益成為某種特權:能夠將自己與干髒活的孤立之所隔離開來,將肮髒的細節留給他人。處於劣勢臨時工的群體不僅更有可能幹髒活,也更容易作為“害群之馬”被挑出來,當長期被容忍甚至得到上級慫恿的系統性暴力偶爾曝光時,他們就會受到指責。
……
當然,並不是所有干髒活的人都認為自己實屬無奈。有些人可以從這種工作中獲得滿足感。此外,還有觀點認為,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髒活,許多白領精英(例如兜售可疑金融產品的華爾街銀行家、設計隱藏跟蹤機制以便公司能夠在用戶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收集個人數據的軟件工程師)從事的工作也在道德上存疑。但對於這些精英來說,好處顯而易見:華爾街銀行家可以獲得豐厚的薪水和紅利;軟件工程師可以躋身於上層精英階層。在一個將世俗成功視為良好品格標誌的社會中,完成這樣的“壯舉”具有積極的道德價值,可以賦予攀升到社會秩序頂端的贏家以美德。成功的精英在需要做出有損道德的事情時,也會更有勇氣抱怨或乾脆一走了之。做出這樣的選擇自然存在風險,但對於擁有技能和資曆的人來說,找到其他理想的工作絕非難事。
本書著力刻畫的干髒活的人們,顯然無福消受這種奢侈的選擇。大多數人都牢牢地與手裡的工作捆綁在一起,為了生存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干髒活的人並不全是一貧如洗。對於其中一些人來說,這樣的工作確實可以提供擺脫貧困的門路,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可以獲得健康福利或略高於最低標準的薪酬。但是,享受福利或更高工資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感到自己被貶低和玷汙,為這份聲名狼藉、備受輕視的工作弄髒雙手。但凡干髒活的人要依靠這些工作討生活,他們就承受著雙重負擔:既要經受收入的不穩定,又要為有違道德的行當付出精神代價。
 當地時間2022年1月31日,美國印第安納州科里登,員工在肉類加工廠屠宰動物後清理屠宰場場。
當地時間2022年1月31日,美國印第安納州科里登,員工在肉類加工廠屠宰動物後清理屠宰場場。“髒活”在口語中多指吃力不討好或令人不快的任務。在本書中,這個術語指代的內容則與此略顯不同,且更為具體。首先,髒活通常意味著使用暴力對他人、動物和環境造成實質性傷害。其次,干髒活需要做一些“好人”(即社會中的體面人)認為肮髒、下作的事情。再次,髒活會對從事相關工作的人造成傷害,使他們要麼感到被貶低和羞辱,要麼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核心價值和信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髒活取決於“好人”的默示授權,後者認為這類工作對社會秩序不可或缺,但並不明確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還會將相關責任撇得一乾二淨。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將工作委託給他人,這就是為什麼授權乃基於這樣一項瞭解,即其他人會處理日常的苦差事。
……
幾乎所有形式的髒活都具備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避人耳目,使“好人”更容易視見而不見或者選擇性遺忘。不想目睹肮髒或令人厭惡的事情,這種願望並不新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一書中寫道:“對我們而言,任何肮髒都與文明不相容……即使把使用肥皂當作衡量文明的一個實際尺度,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受弗洛伊德的影響,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進程》中,追溯了西方道德和禮儀的演變,表明那些被視為令人不安或厭惡的行為(吐痰、暴力和侵略)是如何逐漸從公共生活中消失的。此書於1939年付梓,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幾十年來這本書一直被人們忽視:在許多人看來,西方文明在納粹主義的陰影下已露出野蠻的真容。但埃利亞斯並沒有將“文明的進程”等同於道德進步。像弗洛伊德一樣,他將其與日益增長的社會抑製聯繫起來,這導致人們在做不體面的行為時往往更加謹慎。理論上,這反而會使令人反感的做法更加普遍。埃利亞斯觀察到:“人們越來越注意把令人難堪的舉動置於社會生活的幕後”,“但是這種變得令人難堪的事情,或者把它‘置於幕後’的做法,很能說明被我們稱作‘文明’的整個過程的特徵”。
髒活在美國監獄和工業化屠宰場等偏遠機構的牢房暗室所代表的幕後悄然展開,這些機構往往位於貧困人口和有色人種聚居的偏遠地區。某種意義上,在這些封閉區域中辛勤工作的工人,可謂美國的“賤民”(untouchable),他們從事著不太光彩,又為社會依賴和默許,卻被掩蓋的工作。這種隱蔽性是通過砌築高牆等物理屏障隔離干髒活的場所來維持的,並通過設置限制公眾知情的保密法等法律障礙來強化。但也許,最重要的障礙源自我們內心。人類的心理過濾功能使我們無法認識到,自己讚同的事情有令人難堪的一面。
埃弗里特·休斯在法蘭克福期間,在日記的空白處為具有這種心理障礙的人草草寫下了一句話。休斯稱其為“消極的民主人士”。“消極的民主人士表面上態度十分開明”,他們“除了若無其事的愉快對話之外,什麼都不想做”。這些人的問題並不在於不知道周圍正在發生不合理的事情,而在於他們缺乏休斯所說的“瞭解的意願”。為了保持良心清白,他們寧願被蒙在鼓裡。
如果生活在納粹德國的消極民主人士更加積極,很難說能夠產生多大不同;畢竟,他們生活在獨裁統治之下,國家要求其絕對服從,根本容不下任何異見。但如前所述,休斯在撰寫關於髒活的文章時,主要考慮的並不是納粹德國。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美國同胞,生活在積極參與可以產生影響的民主國家公民,進而萌發了對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做法是否應該存續的辯論。
然而,在休斯的文章發表後的幾十年間,美國人的消極被動與日俱增。晚近的幾次總統選舉中,數以千萬的選民已不再關心前幾代人為之奮鬥和犧牲的權利。拜科技所賜,普通人無比輕易便可獲取海量信息。同樣,面對令人不安的事情時,點擊另一個鏈接來轉移視線變得輕而易舉。在一個注意力分散、連續專注時間縮短的文化當中,又有誰會費心費力地閱讀那些令人不安,或將引火燒身的揭秘爆料?又有誰會在網上衝浪時,長久沉浸於良心不安中,好讓自己在第二天記住此時的經曆?對大學畢業生的研究表明,近年來美國人的共情能力有所下降。設身處地的意願似乎與瞭解的意願一道在減弱。
在消極民主大行其道的國家,令人不安的做法在不遭遇太多阻力的情況下恣意發展。這令人遺憾,因為通過追蹤美國生活中髒活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瞭解到這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正如下文所述,我們都與這些髒活有所牽連,卻幾乎未曾察覺。哲學家查爾斯·米爾斯認為,西方社會賦予白人的優勢體現在無形的“種族契約”中。根據這個默示存在的契約,非白人是統治種族秩序的“下等人”,儘管許多受益者對此並未在意也不承認。這一默示契約同樣適用於髒活,它的條款確保那些容忍髒活存在並從中受益的白人不必深究。與種族契約一樣,這種協議在任何正式文件中都不見蹤影,使得人們很容易忽視。當人們注意到或提起這種協議時,他們同樣容易將其歸咎於他人,或歸因於無法改變的巨大外部力量。這顯然是一個錯誤。美國的髒活分配,儘管看起來一成不變,卻並不是預先註定,而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做出的具體決定(從理論上講,這些決定是可以改變的)的產物,包括製定的政策、實施的法律以及達成的決議,從如何發動戰爭到將最弱勢的同胞關在何處。對髒活的思考揭示了美國社會面臨的基本問題:美國人的價值觀、基於無意識授權建構的社會秩序,以及美國人願意以自己的名義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