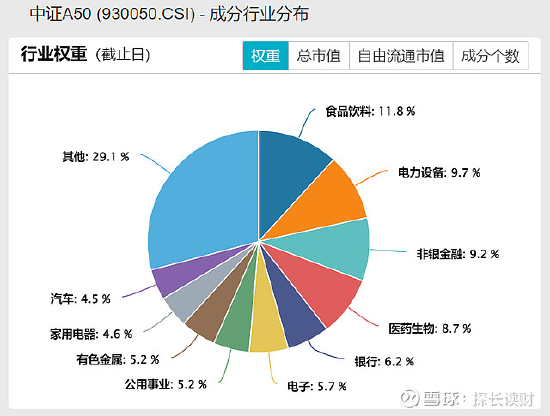範儉《人間明暗》:關注小人物在大曆史中的命運輾轉
《人間明暗》從2018年的5月12日寫起:
汶川地震十週年紀念日,四川省都江堰市郊外的寶山陵園里人頭攢動,煙霧繚繞。一陣鞭炮聲忽然炸裂開來,人們用這聲音呼叫著在這巨大災難中逝去的年幼生命的亡靈。
葉紅梅、祝俊生夫婦也在這人群中,他倆帶著七歲大的兒子祝葉桂川來祭奠女兒祝星雨。十年前,祝星雨上二年級,在5月12日的地動山搖中不幸罹難。失去了當時唯一的孩子後,夫妻倆開始漫長而艱難的重新生育之旅。年屆四十的葉紅梅想要再次成為母親,經曆了兩次常人難以想像的生育長跑——像她這樣的震後失獨再生育女性有五千六百多人。直到2011年5月20日,葉紅梅終於生下一個孩子,也就是祝葉桂川。
 葉紅梅和祝俊生
葉紅梅和祝俊生沒有冗長的關於書中內容的介紹與創作意圖的闡釋,《人間明暗》的內容也像紀錄片的鏡頭一樣,一下子切入到某一時間,某一現場,人物登場,故事徐徐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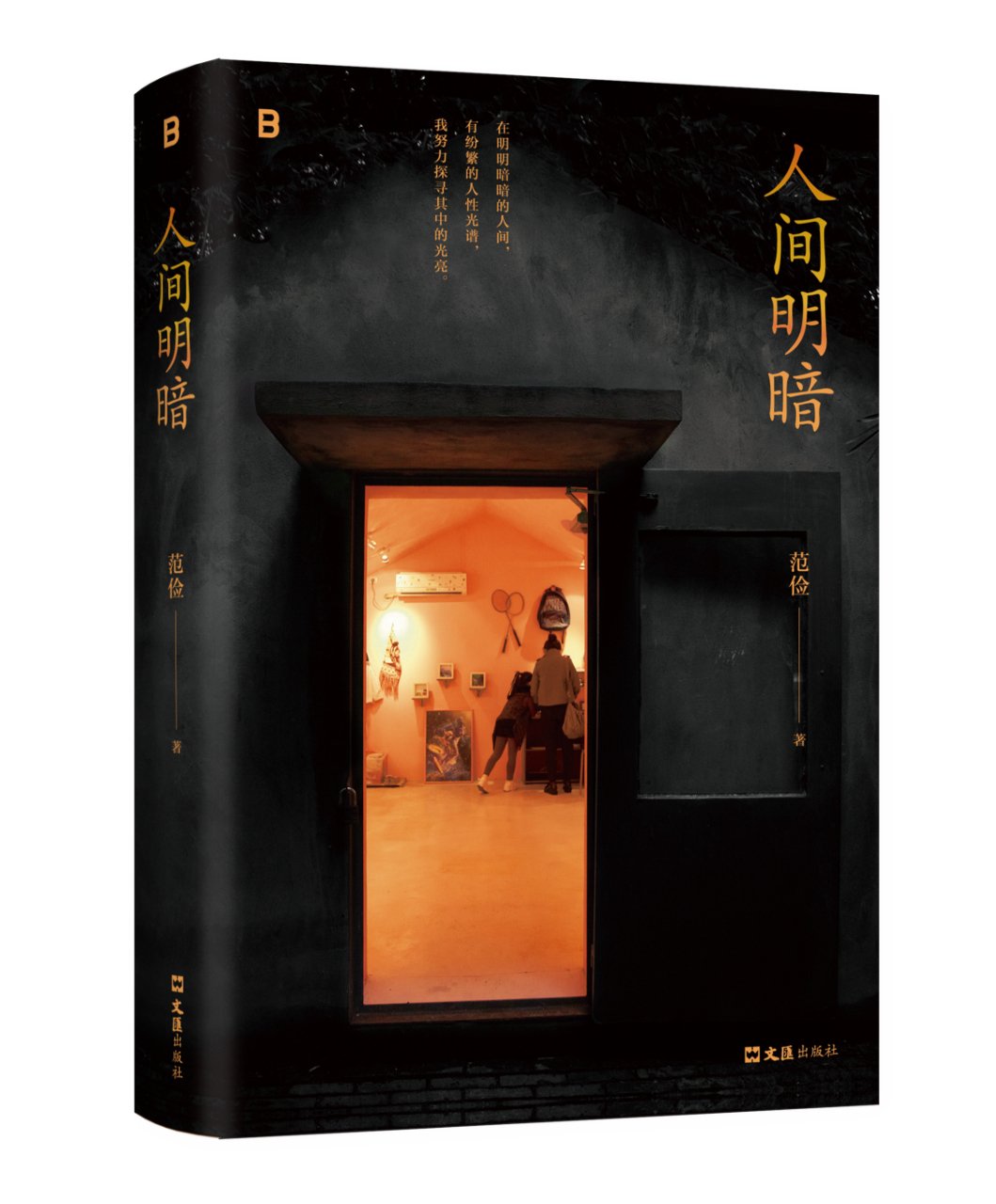 《人間明暗》
《人間明暗》寫作也的確並不是範儉的主業。他創作紀錄片二十餘年:《活著》《兩個星球》《被遺忘的春天》《搖搖晃晃的人間》……《人間明暗》是他的第一部非虛構文字作品。從紀錄片導演到寫作者,從一開始被好友餘秀華認為“寫得不咋樣”到最後完成時收穫其真心的祝福“你會成為一個好作家”——範儉經曆了身份和創作上的轉變。
《人間明暗》中,範儉寫作汶川地震以後一個個家庭“災後重建”的故事,寫作新冠肆虐期時武漢城市中一個個人的經曆與命運,也寫作始終在輿論漩渦中的橫店村和餘秀華。範儉始終在時代風暴的現場從未離開。
 範儉
範儉餘秀華本人因拍攝紀錄片與範儉相識,她說:“範儉記錄著小人物在大的曆史事件中的命運輾轉,他滿心悲憫地,用鏡頭記錄著這個世界。”
《人間明暗》是範儉的第一部非虛構文學作品,也是他對自己拍攝曆程的另一種形式的記錄——“寫這本書,是用見證者的目光寫下他們的故事。和紀錄片一樣,都為我所經曆的時代留下由普通人的樂章構成的曆史註腳。”範儉在盡己所能為未來終將被淡忘的一切留下存證。
最近,範儉攜《人間明暗》與詩人餘秀華、紀錄片導演陸慶屹進行了對話。
範儉坦誠了這本書創作的過程:“為了完成這部作品,我進行了各種嚐試和學習,參考同為紀錄片導演的陸慶屹的文字作品,從中把握如何將導演的畫面感構建為文字的畫面感”,範儉還特地去上了非虛構寫作課,以學習文字敘述的方法和節奏;為了保證細節和情緒的準確,他結合場記的文字記錄,一幀幀回看自己長達幾百個小時的海量視頻素材……修改多版文稿,曆經三年多,《人間明暗》終於得以成書。
至於嚐試文字創作的原因,除了有相熟的編輯鼓舞,認為自己閑暇的寫作有價值外,最重要的是:“想換一種方式拍的內容重新講述出來,用文字的方式延伸影像以外的、影像不一定能拍到的內容。”而當本書完成後,範儉確實意識到,文字有著更多的自由感和延展性,能補足紀錄片所不能夠抵達的一些細節,非虛構文字的記錄與紀錄片的記錄互補,共同完成了範儉“為小人物而譜的樂章”,成為“大曆史不可或缺的註腳”。
範儉還提到,在中國還存在非常多的優秀的紀錄片創作者,他們的作品是當代中國三十多年來社會變化與發展的極其有價值的記錄,有著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意義,但紀錄片受製於其觀眾與市場不為人所知——它們值得成書被更多人看見。
範儉畢業於武漢大學新聞學院,範儉本人將自己定義為一個“記錄者”,他認為:“從20多歲到40多歲,我能夠把記錄做下去的主要動力是使命感。我覺得應該用自己的方式為曆史留下一些記錄。”
《人間明暗》中的故事大多數關於生命的苦痛與沉重,書中範儉寫道:“我會主動去拍攝這樣的主題,投射很多情緒和思考在其中。……我又忽然想到,我的紀錄片工作的起點,是拍一個註定要死亡的人。1999年,我剛大學畢業,在山東電視台拍一名死刑犯從生到死的過程。這個死刑犯因搶劫被判死刑,之後決定捐獻自己的遺體器官來贖罪。……那時我才二十二歲,如此近距離地審視一個生命的消逝和另一個生命的延續,如此深入地思索善與惡之間的人性斑駁。當時我在拍攝中還不太會控製情緒,幾乎整夜失眠,大腦異常興奮,直到現在還清晰記得那個死刑犯輕聲說話的語氣,還有他非常羞澀的表情,以及他的母親目送我們離開時,我已熱淚盈眶、想扔掉攝影機的心情。”
這樣的紀錄註定是不容易的,範儉關注大的時代節點,而去到這些現場和找到合適的拍攝對象並不容易,因此拍攝屢屢受挫。使命感只是創作的前提,實際創作中,還不得不面對更複雜的問題,比如情感的尺度:是否要帶入自身的情緒與觀點?比如邊界的尺度:如何處理邊界感?對此,同為紀錄片導演的陸慶屹乾脆地指出“如果對方表現出一點不願意,那我就不拍了”。
範儉的答案是類似的,在其寫作中,他努力去減少和克製我的情緒介入,儘量用事實和場景描述的細節來表達,而非主觀地去分析、談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創作一定要真誠,要去面對自己的良知,要對創作的內容負責,要去展現對象最接近生活的樣子——這或許也是記錄者使命感的延伸。
陸慶屹談道:“我讀本書,尤其能感覺到範導的那種寬厚,像這樣的內容,如果不是一個被足夠信任的人,得不到那麼多信息;而他跟被拍攝對象保持了非常長的友誼,這也很了不起。”
《人間明暗》的書名來源於範儉本人的序言:“在明明暗暗的人間,有紛繁的人性光譜,我努力探尋其中的光亮。”本書的創作,也充滿著他尋求到的人性的光亮,這些光亮總是相互的,尤為動人。
如陸慶屹所提到的,範儉和不少記錄對象成為了朋友,比如他所記錄的汶川大地震後的失獨家庭葉紅梅一家,他見證了這家人失去女兒後如何再生育。甚至葉紅梅待產時,等他到了能拍攝才進手術室,如今,葉家的兒子川川已經13歲了,作為生日禮物,範儉送了他一整套科幻小說《沙丘》。
 《搖搖晃晃的人間》紀錄片中,餘秀華搖搖晃晃行走在雪後的橫店村
《搖搖晃晃的人間》紀錄片中,餘秀華搖搖晃晃行走在雪後的橫店村做客本次對談的詩人餘秀華是範儉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女主角”,曾開玩笑道:“一開始拍的時候一群人鬼鬼祟祟跟著你,很煩。”但最後,她已經和導演建立了持續至今的友誼。“我現在跟他之間沒有什麼忌諱或者不敢說的,這麼多年,他一直在我生命里佔據很要緊的位置。”談及拍攝中的感動,她尤其談及:“我記憶力很差,我對我媽媽的很多印像已經模糊了,很多我媽媽的事,我還需要看他的記錄才能想起來,在這上面我是真的很感謝。”
對於人性光亮的執著追尋,不僅使範儉收穫了友誼,還使其的文字帶上了人間的溫度,對於這些普通人的悲歡離合,他總是抱有認同與共情,成為記錄者,也是人間的一員。“我將終生銘記這樣一種情誼,一種溫暖。”範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