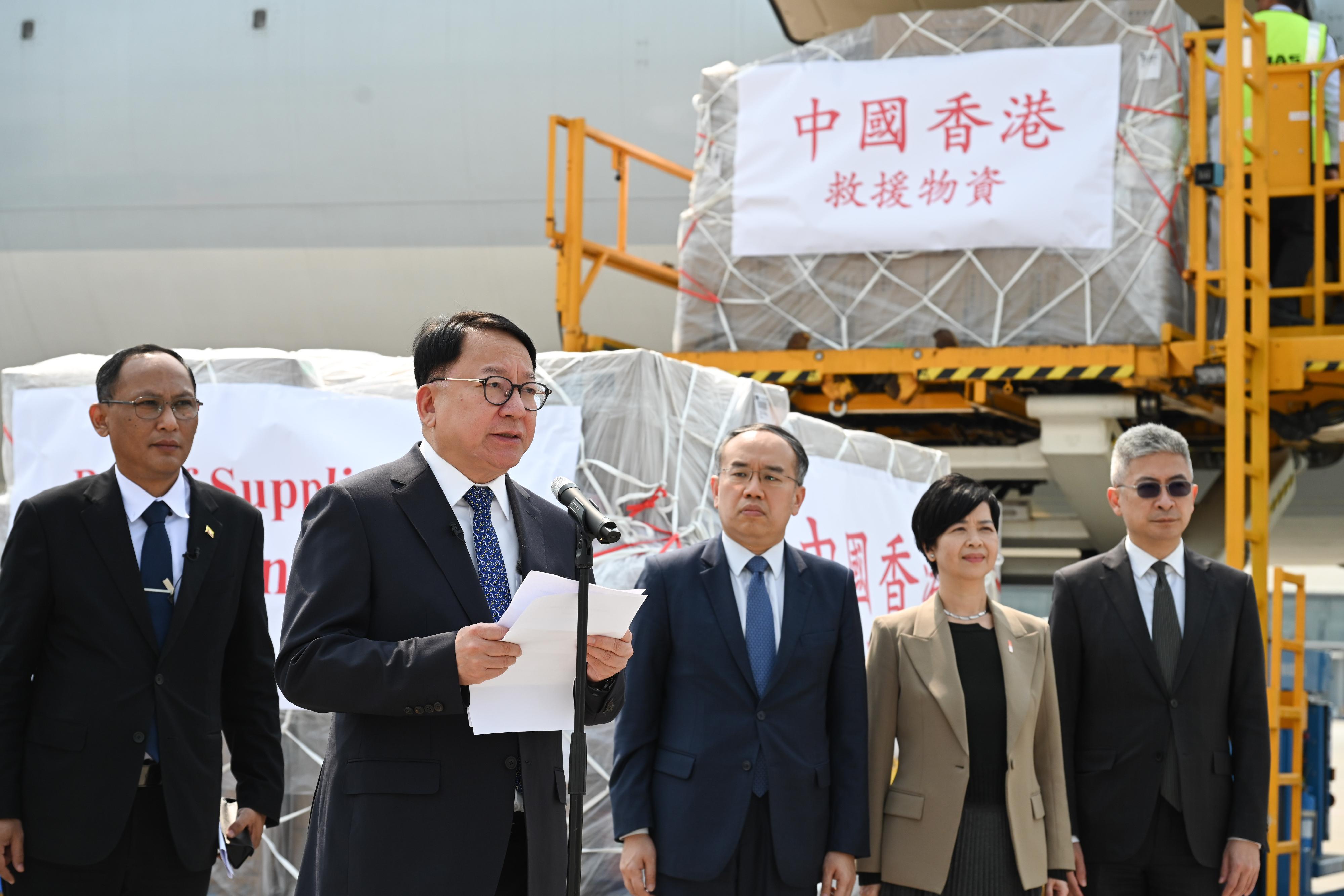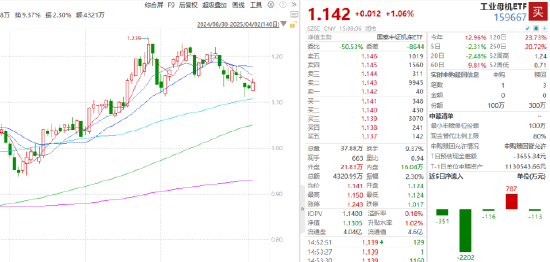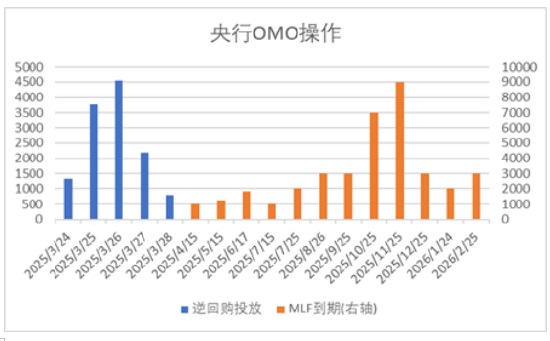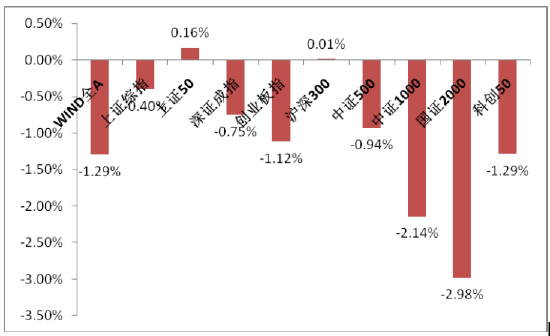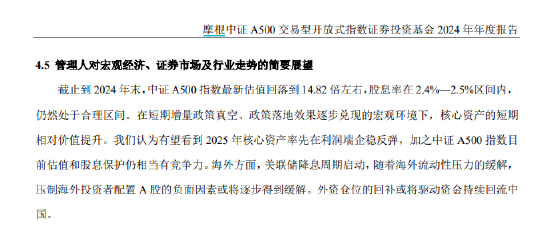詹丹|茅盾的《天窗》打開了怎樣的世界?
很久以前讀過茅盾的散文《天窗》,當時沒覺得理解上有問題,但此次打開統編義務教育教科書語文四年級下冊,看了該文所在第一單元的全部詩文,卻有了一些疑問。
 茅盾的散文《天窗》
茅盾的散文《天窗》該單元共編有4課,第1課是古詩詞三首,分別是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第二十五)》、楊萬里的《宿新市徐公店》兩首絕句以及辛棄疾的詞《清平樂·村居》,餘下的3篇都是散文,即第2課陳醉雲的《鄉下人家》,第3課茅盾的《天窗》,第4課劉湛秋的《三月桃花水》。
對於該單元,教材導語首先在內容上進行了高度概括,所謂:“純樸的鄉村,一道獨特的風景,一幅和諧的畫卷。”又進一步給出兩句學習提示,一句指向閱讀教學:“抓住關鍵句,初步體會課文表達的思想感情。”另一句指向寫作教學:“寫喜愛的某個地方,表達自己的感受。”
由此帶來的第一個疑問是,茅盾的《天窗》可以歸入“純樸的鄉村”嗎?雖然文章劈頭一句“鄉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把讀者帶入了鄉村環境,但隨後寫到的“風景”和“畫卷”,似乎都不是鄉村所獨有,那麼,把這文章歸到“純樸的鄉村”,有多大的合理性?對照其它的選篇,三首古詩詞寫農村的田野風光,有農作物、有農人的勞作、有農村孩子去田野遊戲自不必說,就是《鄉下人家》和《三月桃花水》兩篇,前一篇著重寫農居周邊種植的蔬菜花草和成群雞鴨,還有農人在院子裡吃晚飯等;後一篇則寫村邊溪流帶來的自然和農耕的聲響,還有水面倒映出的自然景觀。因為這兩篇定位在戶外,那麼《天窗》把描寫的視角基本定位在室內,是不是就顯示了特色呢?也許是,也許又不是。
如果寫的是鄉村人家的室內景觀,比如帶煙囪的大灶,堆農具或者茅草的雜物間等,那就有鄉村味。再如果從窗口向外平視,把看到的窗外周邊靜物或者路過的農人、小動物等一一寫下,也可以說是寫農村。但《天窗》卻是朝向天空的,這樣,能寫下的只有天空的景象,如雨天的風雷電閃,黑夜裡的星雲和飄過的陰影等。這樣的景象,透過城里的天窗(比如上海石庫門住所的老虎窗)也能看到,很難說這是鄉村特色。也許,可以解釋的是,文章里寫到的小孩子想像,從黑影中想到了蝙蝠、夜鶯和貓頭鷹,這是鄉村更有可能出現的,這是鄉村孩子想像的現實基礎。而房前沒有玻璃的木板窗,同樣是鄉村特色,這是讓小孩子被迫進入地洞一樣的屋內從而展開想像的前提。於是,把這篇課文歸入鄉村單元,因為鄉野風光的隱含性,使得該文章與同單元的其它文章比,顯出了與眾不同的特色。而文章從白日之雨寫到晚上,有一過渡句“當你被逼著上床去‘休息’的時候,也許你還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灘”,可能是唯一寫到的鄉村景色。這裏,簡單一句,把鄉村、把晴天、把孩子被逼著休息卻無法息下來的心,都一併交代了。儘管這一句作為過渡很重要,但一般不會被視為理解上的“關鍵句”。
由此帶來下一個疑問是,單元要求“抓住關鍵語句,初步體會課文表達的思想感情”,如何理解這所謂的“關鍵語句”?它是否可以是詞語,也可以是句子?比如題目中名詞性的“天窗”以及透明的“玻璃”、“地洞似的屋裡”在文中多次出現,這算不算關鍵詞語?還有動詞性的“看見”“想像”,這些詞語是否也算?教材的練習設計以及“教師教學用書”都把文章中兩次說到的——“這時候”,天窗是孩子們“唯一的慰藉”,視為關鍵句。那麼,怎麼“抓住”這樣的句子,來體會課文表達的思想感情?課文後面有相關的一處練習設計和虛擬的一位學生交流,拿來對照,可以提示我們對關鍵句的所謂“抓住”。
課後練習設計是:
在什麼情況下,小小的天窗成了孩子們“唯一的慰藉”?找出相關語句和同學交流,再有感情地讀一讀。
而在教材“語文園地”欄目的“交流平台”,虛擬了這樣的學生讀後感:
學習《天窗》時,我從“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的慰藉”這句話中,體會到天窗給孩子們帶來的快樂。
兩相對照,發現前面課後練習的設計指向才真是對關鍵句的理解,因為追問的是“成了”慰藉,而不是慰藉本身。如果追問慰藉本身,不過是對一個詞語的理解,這樣的理解,只是對心理狀態的理性概括。而虛擬的學生回答,恰恰是對這句話本身的理解,所以本質上沒有在抓關鍵句,也談不上“體會”,只是對一種抽像意義的詞語理解。但即使是抽像意義的理解,把慰藉的理解簡單等同於“快樂”,也是不精準的,否則作者直接說“快樂”,效果會不會更好?
順著教材中虛擬的學生交流,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為何作者不直接說快樂?說快樂跟說慰藉效果有何不同?如果直接說快樂,又意味著什麼?這樣,我們發現,也許值得讓讀者體會的,恰恰不是慰藉本身,而是課文說的“這時候”,這正相似於課後練習設計的“在什麼情況下”的追問。也就是說,所謂“抓關鍵句”,是借助“慰藉”這樣的抽像概括,把讀者帶回到“這時候”的特定場景。“這時候”,首先當然可以理解是小孩子仰望天窗的想像過程,但僅僅說這一點又不夠。簡單地說,先有小孩子不被允許出門的失落,轉而透過天窗而沉浸於想像過程的快樂,才可以用“慰藉”來概括。特別要強調的是,不是因為曾經想像,小孩才快樂,而是正在想像的過程中,在這同時,就伴隨著快樂。就像古人說的,不是你聞到了香味,判斷這個香味是讓人舒服的,你才喜歡上香味,而是在聞的過程中,你就喜歡上了。換言之,文章中短語“這時候”,是有多重指向性,既有不得出門的無奈和失落,也有沉浸於室內天窗下仰頭想像的快樂,更是站在一個已經成人的今天立場來回望孩子心靈而與之同情的慰藉乃至對其活躍想像力的讚歎。這種隱含的成人立場,才在通篇口語化的文章中,用了“慰藉”這麼書面化的一個詞語來總結。一如結尾段,用了成人的、更具哲理化的詞句,比如“從‘無’中看出‘有’,從‘虛’中看出‘實’” 來總結。
當文章中寫到的人物主體是小孩,又不可避免有隱含的成人立場時,帶出了我的第三個疑問,即,放在文章明面上的成人,跟小孩有怎樣的關係?
細細讀下來,不由得讓人驚訝發現,這是讓“天窗”成了孩子慰藉的兩個基本條件。雨天和黑暗,把孩子關閉在地洞的屋子裡,是成人;為屋頂開出天窗,讓孩子透過小小的玻璃,放飛自己的想像,也是成人。套用一句話來說,老天爺關上了門,卻又打開了窗。於是從開始似乎把成人視為孩子的對立面讓他們掃興,到結尾對成人的感謝,就不僅僅是因為拘管了現實中的孩子,才讓孩子不得不把自己的興趣轉移,讓想像盡情發揮出來,而是也確實以物質的構建——天窗的“發明”,讓孩子的想像有了展開的基本依託,大人與孩子的貌似對立在文章最後就和解了。這種和解,不妨理解為,寫作者的成人共情孩子立場時,又折返回來,對成人也有一份共情式的理解,讓孩子對成人不只是埋怨,也有一份感謝。
順便一提的是,從現實到想像的轉化,一個細節描寫可謂活靈活現。如“夏天陣雨來了時,孩子們頂喜歡在雨里跑跳”,而被大人關閉在屋內後,“從那小小的玻璃,你會看見雨腳在那裡卜落卜落跳”,孩子能跑且跳,雨卻不能跑只能跳,但重複用一個“跳”字,而且再一次寫到“跳”時那麼生動,似乎孩子已經移情於雨,隔著玻璃既在欣賞雨點的擊打和聲響,也讓自己在忘情地跳,類似的生動描寫,包括兩次描寫的仰頭想像的語句變化,那種由語言的內容也是形式帶來的力量和聯翩而來的畫面感,都是值得我們細細品味的。從這一點來說,《鄉下人家》《三月桃花水》和《天窗》在遣詞造句方面,都用了一些比喻擬人等修辭,《三月桃花水》幾乎達到了通篇都用修辭的地步。但在超越常規的句式變化方面,《天窗》是最具特色的,這樣的特色,可能是跟小孩子的超現實的想像世界相吻合的。反複誦讀這樣的詞句,是能夠把這種感覺、這種心靈世界觸摸到的。
走筆至此,突然覺得我開始提出的第一個疑問或許有點教條,為什麼非得把鄉村和鄉野景觀畫等號呢?也許是教材導語中的“風景”“畫卷”讓我產生了誤解,以為一定是指客觀的鄉村風景。但也許《天窗》本來的定位,就是要刻畫一個鄉村孩子的形象,現實的無奈和想像的活躍,都是在主觀化的“風景”和“畫卷”中,生動呈現了鄉村孩子的一個心理世界。不妨說,“天”,是自然,而“天窗”,就是開向孩子自然心靈的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