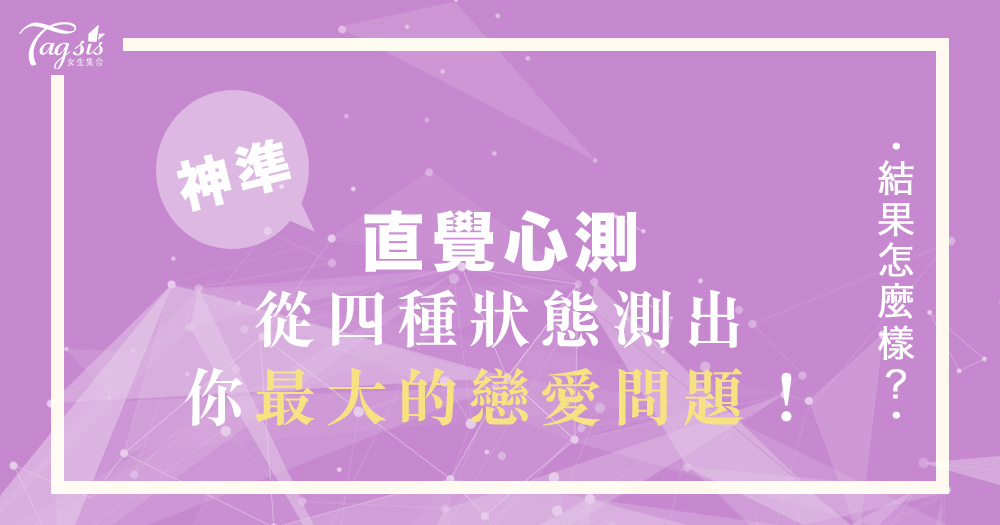戲裡人 | 《辯護人》:沒有法庭戲的司法劇 探討溝通和同理心
【橙訊】今年迄今為止,在香港最引起轟動、最多人討論的血淋淋刑事案件之一,非「荷里活廣場斬人案」莫屬:一名39歲男子手持利刀在荷里活廣場內施襲,2名遇襲女子被斬至傷重不治,現場地面遺下大灘血跡,令人震驚也令人歎息。犯案男子事後被證實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此案也引發公眾討論精神病患者治療過程是否有效、精神病患者重返社會後的影響。
此案令人想起2014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兇嫌鄭捷(男,21歲,當時就讀東海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二年級)在台北捷運車廂內行兇,隨後於江子翠站遭員警和民眾制伏,事件共造成4死24傷。在社會上眾多人憤怒聲討鄭捷時,被稱為「魔鬼辯護人」的律師黃致豪選擇為其辯護,而他本人也由此成為眾矢之的。
啟發自這一事件和黃致豪的訪問,中英劇團2022年推出原創話劇《辯護人》,當中的主角陳哲豪,便以黃致豪為原型。今年8月,經過修改調整的《辯護人》將再度上演,我們請來編劇郭永康與飾演陳哲豪的演員袁浩楊(魚旦),為大家拆解這部劇的內容,及探討對「魔鬼辯護人」的看法。

郭永康(左)、袁浩楊
「魔鬼辯護人」與「修復式司法」
「魔鬼辯護人」黃致豪以專為死刑犯辯護聞名,不少人質疑他的做法,但從他的訪問來看,與其是為死刑犯「辯護」,不如說,他認為哪怕是「罪惡的生命」也值得應有的尊重,希望理解犯案者背後的動機,體現的是對人本的關心。他的這種執著吸引了編劇郭永康,也讓他產生了創作《辯護人》這個故事的願望。
在「這樣反社會的罪犯就是無藥可救、應該嚴厲制裁」的沸反盈天聲音中,「魔鬼辯護人」默默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存在『教化可能性』?」誠然如同劇中所說,這樣的可能性一生都未必有機會了解,但願意相信犯罪的人能夠改變、甚至抽絲剝繭去探究對方犯罪的原因,比任由情緒審判、簡單粗暴給予懲罰,或許更有意義,這也是「魔鬼辯護人」寧可被千夫所指、成為社會意義上的「罪人」,也要不懈努力去堅持的正義。
劇中提到「修復式司法」這一概念,簡單說來,就是犯人、受害者家屬以及犯人家屬三方坐下見面聊天,現場也會有律師和其他相關促成對話的人士。雖然傷害已經構成,但起碼大家可以當面聊為何會釀成慘劇、聊心中的困惑和傷痛,以及探討如何彌補。這一方式旨在令犯罪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了解給他們造成的傷害,讓他們有機會自我救贖,並阻止他們造成進一步的傷害。比起傳統司法的應報理論,修復式司法是一種有效的補充,據不少研究表明,它也能降低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人和人的溝通,有時候沒有用?
《辯護人》劇中,三方見面一幕真切細膩,令人動容,觀看綵排的筆者也一度淚目。但聽到受害人家屬反復問著「為何要殺我的女兒」,加害人家屬反復道歉說「我也不知道他為何會變成這樣」,談話一度陷入僵局,筆者內心逐漸升起問號:「這樣的聊天真的有用嗎?」

圖:橙新聞
溝通是件何其困難的事,和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家人、經常一起玩耍的朋友尚且有難以溝通的內容,更何況是與和自己成長生活背景、價值觀迥異的陌生人了。林宥嘉在《想自由》中失望地唱「人和人的溝通,有時候沒有用」,發現頻道不合就轉台,漸漸成了社交常態。會不會「修復」反而成了浪費時間與二次傷害?
編劇郭永康想了想緩緩開口:「到底人和人之間是否可以互相溝通,然後明白對方……我以自己的經驗為例,這件事其實很難講百分之百。但某程度上來說,我們做劇場的,無論是演員也好,編劇也好,我們寫作,我們有些東西講出來,其實都有一顆想與人溝通的心。」
他強調,「溝通」不是「說服」:「他們未必需要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但起碼嘗試過坐在一起,有一個聊天溝通的機會。其實就算大家未必完全理解或明白,只要有一個人肯講出來,然後有人聆聽,可能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的紛爭就會少很多。」

不開庭的司法戲
看到《辯護人》這個題目,相信很多人都會聯想到去年爆火的兩部司法主題電影《正義迴廊》與《毒舌大狀》,但如果想看律師在法庭上舌戰群儒的場景,你可能會失望,因為《辯護人》全場都沒有設置法庭戲。
袁浩楊(魚旦)亦有參演《正義迴廊》,在他看來,《正義迴廊》聚焦「何為真相」,尋找「真正的答案」,《毒舌大狀》試圖展示「何為正確,何為正義」,而《辯護人》則著眼溝通:「就算兩方立場很對立,但是他們有沒有嘗試過互相理解,溝通后會不會生出第三個想法,令他們走在一起呢?」

圖:橙新聞
比起法庭上確切的辯方,《辯護人》中陳律師的辯方,其實是從受害人家屬、到整個社會輿論對他的不理解,甚至連犯人家屬,都未必有耐心配合他一次次的上門拜訪。除了他為了心中的正義而戰,偏執勇敢的一面外,魚旦直言更吸引自己的是角色的「黑暗面」:「其實他也會很累,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可能也會有質疑,他幫死刑犯辯護,但喪失了自己和家庭的關係,甚至讓家人身陷險境」,這種回歸日常生活、作為普通人有可能失控的一面,讓角色更加有血有肉。

圖:橙新聞
比起去年的首演版,此次的版本根據之前的演出反饋、以及郭永康身邊家人朋友的意見進行了不少改動,除了讓陳律師的語言更自然貼地外,他的家庭戲比例也有所提升,還展示了他與太太相處時幽默的一面。
「我總覺得劇本最重要的兩個東西,一是台詞,二是衝突。雖然和之前的大致方向一樣,但我希望透過台詞的改動,讓陳律師不再是一個法律的工具,只會講一些法律名詞,而是讓觀眾進入他的世界,理解他的執著」,郭永康說。

圖:橙新聞
在進行創作前,郭永康及創作團隊與原型人物黃律師有過細緻的對話,他發現黃律師比起訪問上略顯咄咄逼人的形象,私底下很感性,甚至會聊著天落下眼淚。他也想透過《辯護人》請觀眾思考,是否大家要讓已經被定罪的人走向萬劫不復的境地,是否可以嘗試多一些溝通的方法,而這種思辨屬性,也與他早前大受歡迎的作品《原則》一脈相承。
魚旦補充表示,「同理心」不應只用在受害人家屬身上,對犯人家屬的攻擊有時也是一種傷害:「現在網絡時代真的很方便,我按幾個按鈕,就可以罵別人全家,但當你有同理心的時候,質疑一下自己,或者就不會做出這些事,因為除了宣洩你自己的憤怒之外,你又沒有幫忙解決這件事,沒有意義。」
「其實我們的社會應該是多元化的」,郭永康說,「我們的社會由不同的人構成,所以大家需要有一個意識,每個人都要有願意質疑自己想法的心。一個有理性的人其實就是喪屍片中還在生存的人類,他可能覺得很痛苦,甚至很艱難才能生存,但如果我們放棄理性,就會變成喪屍一群,所以要學著質疑自己。當人願意去想為甚麼,願意去質疑自己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向前行。」

《辯護人》(重演)
日期及時間:
8月18日至19日,8月23日至26日,下午8時
8月19日至20日,8月26日至27日,下午3時
(8月27日下午3時為通達專場,設粵語口述影像)
地點:中環愛丁堡廣場5號香港大會堂劇院
門票現於art-mate及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