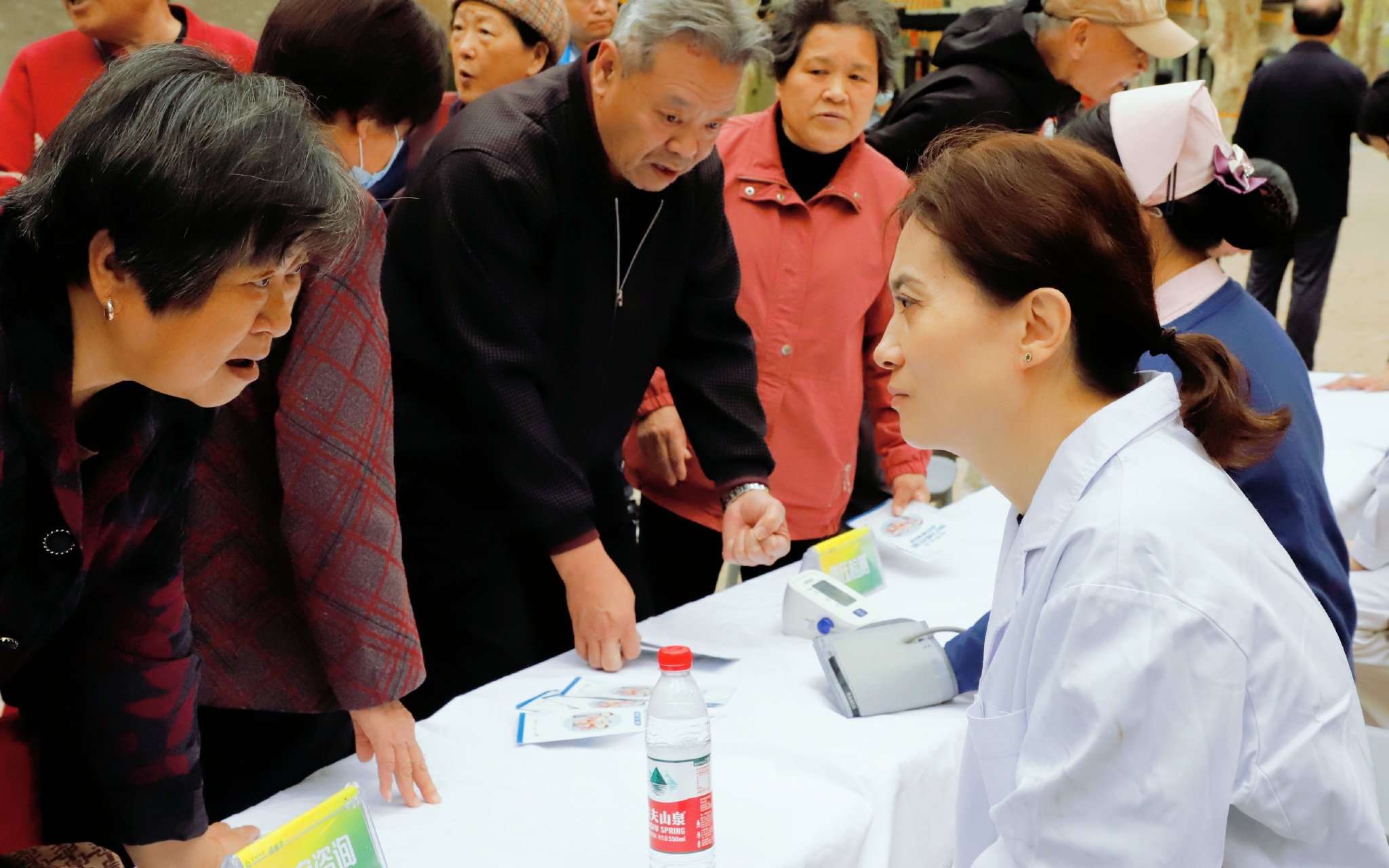何以至此:明清淮北衰敗的曆史溯源
|
||
|
||
|
||
|
淮北地區位於黃淮海平原的中心地帶,地理位置與氣候條件極佳,古有“江淮熟、天下足”“魚鹽之邦”等稱呼,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區之一。隨著經濟中心南移與政治中心北移,淮北成為連結南北的交通樞紐。但是,明清以降,淮北生態環境惡化、民眾生活困苦、社會秩序失範,以至成為民國前期的著名匪區。這既令人惋惜,又引人深思:淮北何以至此?究其根本,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修訂本)一書中指出:“淮北社會問題的根源,曆來是權力積累的不平等,從而導致經濟積累方面的不平等,並由此造成社會的不公。”這一不平等廣泛體現在前現代中國的不同區域和人群之間,而淮北及其普通民眾則是其中被犧牲一方。該書討論了淮北地區自明清至民國的變遷,運用“行政權力統治社會”理論,描繪了一幅令人惻痛的曆史畫卷。
朝廷大計的區域惡果
與大運河益於國計民生的一般認知不同,馬俊亞以淮北地區為例,揭示出這一善政造成的區域悲劇。大運河作為交通動脈,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承擔著輸送漕糧、供養京師、溝通南北的使命。由於淮北為其必經之地,“保運保漕”便成為這一區域明清治水政策公認的“大局”。明萬曆初期,為維持京師及北部邊境的糧食供應,潘季馴採取“蓄清刷黃”“刷黃濟運”治水方略,興修高家堰(位於今江蘇省淮安縣)截斷淮河,在地勢平坦的淮河中遊形成洪澤湖水庫,逼迫全部淮水從清口湧入黃河,衝刷泥沙入海,保障黃、運暢通。後世大致沿用這一方略,直至1855年黃河再度北徙,不再奪淮入海。
由於黃高淮低,黃強淮弱,“蓄清刷黃”過程中,洪澤湖底日漸淤高,水位漸增,高家堰亦不斷加築,周圍地勢低平的淮北地區常有洪水威脅。這也客觀上導致了高家堰修築百餘年後,古代繁華的泗州城永沉湖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位於州城東北的明祖陵,這一頗為虛懸的明王朝象徵,反而為明代泗州士紳增加了一些與中央博弈的大局籌碼,即“祖陵水患為第一義,次之運道,又次之民生”。
高家堰水利工程帶來的洪水隱患,只是“保運保漕”對淮北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顯著一例。除此之外,作者還指出,運河本身即破壞了淮北的水系和自然生態環境。更糟糕的是,為保障自身安全,淮北內部規避水災,以鄰為壑的水利設施造就了難以化解的地域矛盾。而且,不止淮北,運河對某些地區而言可謂百害無一利。運河河堤經常潰決,淹沒周邊地區,船行其中亦需大量人力以纖繩拉動,船隻因河道艱難、遇到大風等因素而經常翻覆。河道不僅需要極高成本來維繫,且滋生出各種勢力爭奪使用權的衝突。因此,作者認為明清兩代統治者堅持河運,從本質上看是封建統治者的重大決策失誤。
令人深思的是,“保運保漕”導向的治水政策使淮北地區常被水患,而朝廷鹽政竟使淮北地區更加貧困。兩淮鹽場是明清最大的產鹽區,亦是重要稅收汲取地。富可敵國的淮北鹽商,從未像無錫等地精英們帶動本區域經濟發展。作者認為原因在於,為維持自己的壟斷利益,鹽商不得不把大量的經濟資源用以交換政治支持,從而保持了對煎丁和其他平民的超經濟剝奪。多數煎丁本人甚至全家依附於占有生產資料的鹽商,不啻朝廷鹽政體制內的生產奴隸。食鹽專賣和嚴峻鹽法之下,普通民眾只能通過走私甚至暴力對不公正的鹽業分配規則發起挑戰。或許,我們可以把鹽政理解為鹽商與朝廷交換利益、相互博弈的綠色通道。鹽商職責主要在於滿足朝廷提出的賦稅、報效等財政需求,來換取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不在地方建設、鹽業生產改良和滿足民眾需求上。
淮北社會環境的衰退
馬俊亞認為,自然生態、經濟生產、社會風氣的全方位退化,是淮北成為被犧牲“局部”更為深遠的體現。中古時代,淮北稻米種植極為普遍,乃是富庶的魚米之鄉,以至於當時有著“走千走萬,比不上淮河兩岸”的民諺。明清以來,黃淮水患頻發、水資源無法利用,使淮北無法種植水稻,改為玉米、高粱、蕃薯類粗糧。而水利工程的修築、被淹州縣的營建、木材盜伐猖獗,更加劇了淮北地區森林稀缺,導致水土流失,水災愈甚。桑林稀缺,絲織業因此難以發展,最終使淮北從“桑麻之境”演變成為“不蠶之土”。總之,作者認為淮北惡劣的生態條件無法滿足農業經濟、手工業經濟的發展需要,陷入“地廣而不得耕”“男耕女不織”的困境。及至清末以降,家庭手工業因現代工業和交通發展而重獲生機,淮北地區才重建了男耕女織的農家經濟。而同一時期的江南,則從原來經營副業為主的經濟模式,邁向工業化道路。其後,江南與淮北的發展差距,則已不啻天壤之別。
作者還注意到,女性的家庭地位和文本形象與其經濟生產能力密切相關。由於明代以後,淮北女性無法在絲織業中獲得收入和實現自我的機會,其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亦較為低下。同為官方意識形態設立的“列女傳”,不同區域具體描述亦大有不同。鬆江、蘇州地區,依靠紡織業供養親屬和自己而列入傳記的女性較多,而徐淮揚地區載入傳記女性的事蹟,多為“刲股”療親。更意味深長的是,明清時代已淪為文化瘠土的淮北,“節烈”之風卻不遜於理學興盛和傳統文化發達的地區。可見傳統意識形態只是壓製女性的一種工具或具體表現形式,其背後的專製皇權才是實質。
不止女性地位,隨著專製權力的強化和經濟環境的惡化,淮北地區的社會風氣整體上急劇下降。古時淮北不僅是詩禮之鄉,更是奇才劍客輩出之地。而明清以降,貧窮、教育資源匱乏,是淮北地區的常態。百姓一面擔負著災害的惡果,一面承受著強勢群體的掠奪,逐漸產生消極的社會心理。為了對抗權力或攫取權力,民風剽悍的淮北人或裝神弄鬼、或為匪為盜,摒棄倫理和道德,以求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生存。與江南相比,淮北大部分百姓宗族觀念極為淡漠,人際關繫緊張,面對盜匪橫行、水患不斷的現實,深感無能為力。這或許是淮北地區賭博、鴉片和酒盛行的原因之一。在這樣急劇衰變的社會生態之中,淮北終究淪為一個弱肉強食的從林世界。作者認為,正是由於不公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和惡劣的生存環境,淮北一般民眾為獲得應有利益,只得成為“刁民”與“奸棍”。
政策滋生的利益群體
馬俊亞觀察到,即使是對淮北產生惡劣影響的河務、漕運、鹽政,其內部各關卡處,亦滋生出大量受益群體。這些人雖然生活在被犧牲的淮北,卻以朝廷大計賦予的行政權力,犧牲其他人。直接支配巨額治河經費的河務官員,內部盛行貪汙腐敗。加之善於做假賬的“外工”協助,從事治水實務的河臣及有關官員因此中飽私囊。他們不怕水患,反而怕水不為患,一旦朝廷停止投入治水資金,官吏們也就失去了生財的機會。
不僅治水如此,漕運中的閘夫、漕丁亦藉機謀求私利。這些細節揭示了一個頗為典型的政治過程。朝廷通過重大工程下沉權力,行使政府職能。工程所吸取的國家財政和它所提供的控扼普通民眾生活資源的機會,使工程鏈條上的諸色行政人員可以兩面受益,成為政策滋生的受益群體。作者認為,正是漕糧河運產生的利益集團,才使明清兩代大體上拒絕改走海運。
對於鹽政問題,作者更是認為,其實質是“把民眾生活必需品加以控製,使之產生壟斷暴利,作為皇恩君寵賞賜給利益集團”。獲得專賣權的鹽商們,所售食鹽質量問題較大,甚至到民國時期,南京仍有專商販賣毒鹽之事。正式途徑之外,各種勢力紛紛參與鹽業走私,如漕私、船私、梟私、商私,更有軍私、警私和官私。與朝廷嚴懲一般民眾走私不同,這些人的行為往往得到容忍。其中,清初滿洲軍兵公然載運私鹽,引起中央政府震驚。而至民國前期,淮北軍隊販私則已極為尋常。鹽業成了上至皇帝,下至鹽商,外至有權勢走私者的制度性分潤平台。
對於近代以來鹽業市場化浪潮的作用,作者給予了較低評價。一方面,鹽業表面上的市場化,背後可能只是權勢相爭的一種手段。正如民國初年,原本屬於淮北鹽場運銷區域的安徽、河南都督,以開放鹽業市場的方式,改為當地辦理鹽政,分取部分利潤。另一方面,在行政權力沒有受到程序化約束之前,推動鹽業市場化的商人,仍要收買相應的政治權力。作者指出,20世紀30年代初,淮北七大鹽業公司均受累於巨額招待費而瀕臨破產。這些現象大概源於鹽業與行政權力糾葛過深的實質並未改變,而這又與鹽稅仍為民國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有關。
淮北社會結構的異化
明清以降,朝廷政策形成的利益群體,只是淮北地區“權力統治著財產”的部分體現。馬俊亞認為,淮北所有軍政人員和行政權力支持的強勢群體,均極易積累財富。甚至經商本身在傳統中國就是一種特權。所謂“抑商”是指對普通商人的抑製,對鹽商在內的權商,政府則極盡優待之事。淮北商業的凋敝,恰恰是因為普通民眾經商之難。而商人的實際地位和影響力要高於農、灶等階層。商人與農民利益發生衝突時,往往會受到官員們的偏袒。所以“重農”和“抑商”並無關聯,而我們討論政府和“商”的關係時,亦應按照與權力的關係對“商”有所分疏。
與強勢群體壟斷資源相對應,平民則只能淪為當地的農奴、盜匪,或流落江南的底層勞動者。作者認為,這使淮北社會貧富分化過於明顯,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啞鈴形社會結構,強勢群體、貧困平民多,中產階層極少。這種結構不同於一般認知的金字塔形,平民人身依附關係極強,頗具“封建”色彩。即使富裕集團,也要利用和收買行政權力,以保護其超經濟掠奪或減少對自身利益的侵害。不論貧民、富民,他們只能改變所依附的行政權力的類型,而無法改變其依附本質。
由於能夠規避農業稅和其他各種風險,強勢集團往往成為大土地占有者。他們控製當地糧食市場,操縱價格,獲取暴利。這些受益的強勢群體,不僅拒絕承擔地方建設的職能,反而積極打壓試圖興利除弊的官員。及至民國中央權威衰落時,強勢群體更是以各種時興的政治話語“地方自治”“村政建設”“民主政治”等,擴張自己的勢力。淮北更有圩寨這一社會結構的具體範本。寨主們集行政、軍事、政治、經濟、司法等權力於一身,對佃戶擁有生殺予奪之權,亦對佃戶妻女隨意侮辱,甚至擁有對其妻的初夜權。這頗類似於封建領主與其屬民之間的關係。淮北豪紳帶領佃農反叛,對抗朝廷的事件亦層出不窮。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近代以來國家及其新式地方代理人和淮北舊有強勢群體之間的衝突。在政府近代眼光的審視和國家權力的下沉中,後者內在於舊有王朝秩序中的生存規則,遭到衝擊。或許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只得努力跟上時代形勢,尋求新的合法性資源或揭竿而起。總之,對於民國尤其20世紀20年代末黨國時代來臨之後淮北地方勢力的境遇,似乎應作更為細緻的討論。
總而言之,作者認為,正是因為淮北自然生態遭到治水破壞,其經濟、社會結構被迫退化,才最終造成這一區域迥異於江南的近世命運。這一結果則又源於行政權力支配社會之下的區域和人群不平等。
中國的淮北與江南
馬俊亞深刻認識到傳統時代政治權力對自然、社會環境的影響。他將政治史、環境史、社會史、經濟史等各領域相結合,不僅多維度探討了明清以降淮北社會的變遷,還嚐試將這些維度統合起來,展現出曆史變化之間的複雜關聯。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嚐試以各種具體的切入點,如人群、區域,重審宏觀曆史進程的實際影響。當他以淮北經驗解釋宏觀政策或中國形象時,往往得出頗具新意的結論。對傳統中國做出貢獻的大運河,對淮北地區卻不啻罪魁。近代以來,江南邁向工業化之時,淮北卻成為一個更“封建”的地區。
無論是明清以來國家工程對淮北的成本轉嫁或資源汲取,還是強勢集團對地方社會的支配,其實都說明了傳統時期中央政府對淮北地區重視程度不足。從行政區划來看,清初以來這一地區大多屬於四省交界,朝廷直接統治力量相對薄弱,這也致使清末民國時期以及當下不斷有人倡議建立以徐州為中心的省。但另一方面,國家對某一地區的重視亦非只有積極作用。作為中央財政核心來源的江南,明清時期的重賦政策對當地普通民眾產生極大壓力。明清江南出現以家庭手織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乃至後來的工業化,本身可能就與國家對此地的財政汲取強度有關。換言之,淮北與江南的發展皆與朝廷需求有密切關聯,兩地各司其職的過程中,都有著“被犧牲”或顧全大局的一面。
近世江南和淮北之所以出現不同的發展軌跡,與其曆史傳統、國家需求、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等諸多因素有關。兩地的不同演進路徑表明,曆史並非發生於真空之中,而是具有某種“疊加”效應。同一宏觀進程,會因作用區域的社會傳統和內部結構不同,呈現出多樣性與非同步性。而學者們基於某一區域得出經驗範式時,極需注意其背後普遍脈絡和特殊境遇的區別。從這個角度而言,區域的異質性或又為曆史發展的常態,覺察某種特殊經驗便可能是一次突破舊有認知模式的機會。因為史料數量及開放性、地方重要性及曝光度的差異,被研究區域亦存在著中心-邊緣之別。當人們聚焦於江南、華南研究時,作為另一種曆史脈絡的淮北,其研究意義也就得以凸顯。
□薛克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