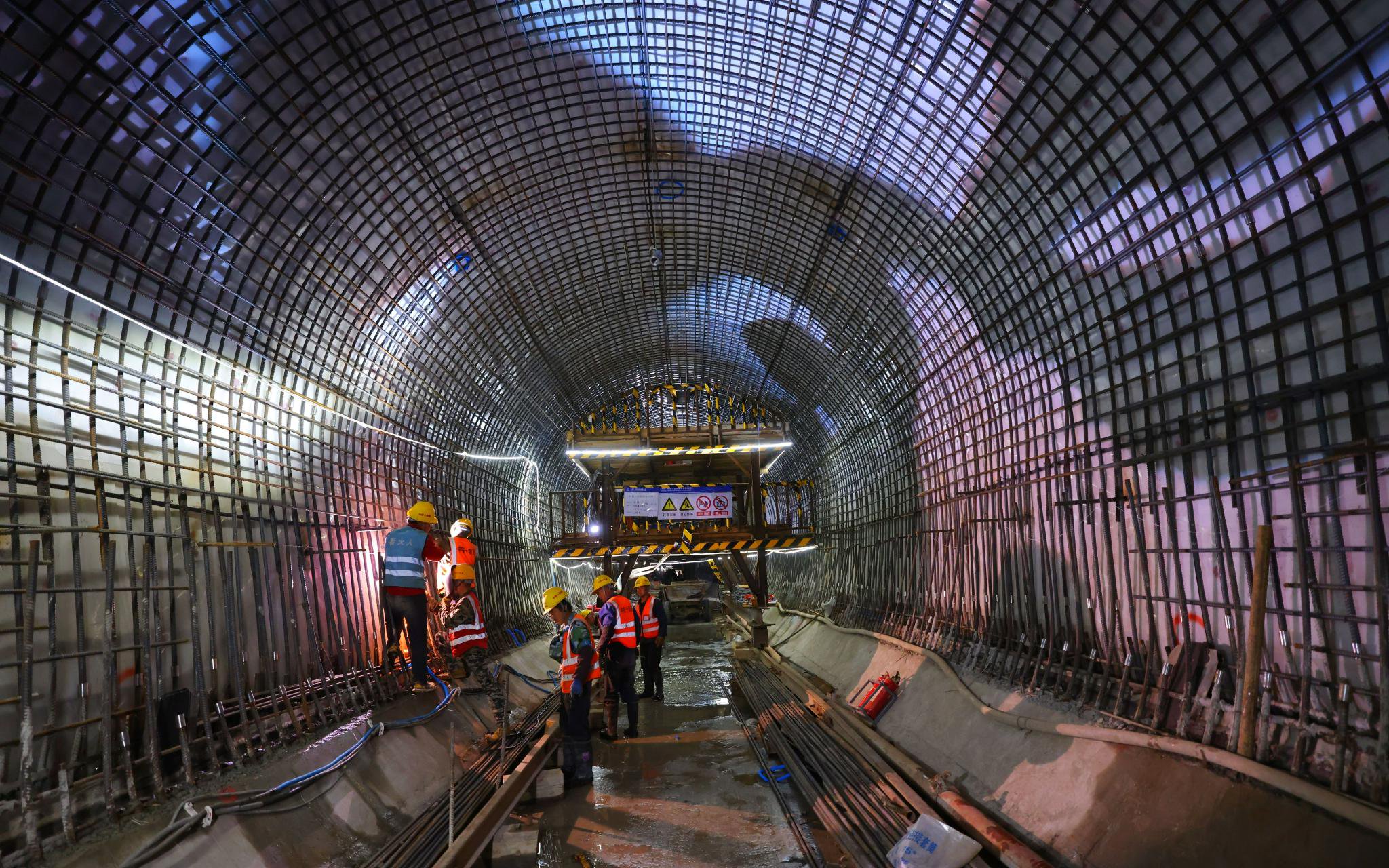嚐試為人文學科“辯護”,關鍵在於咬緊牙關,保持鎮定
人們如今談及大學,總是難以確定人文學科的教學與研究的性質,從而難以解釋人文學科的價值。在這方面,衡量科學、醫學和技術等學科的價值要容易得多。事實上,公眾對後一種學科的理解,未必一定比其對人文學科的理解更全面、更準確,但就“發現”自然界的真相,並將這些發現應用於改善人類狀況而言,人們總能舉出一個大家耳熟能詳且容易理解的例子。當然,我們也可以拋出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例子,證明理解人類世界同樣重要,但若只從“發現新真理”的角度來證明這一點,那就會引人誤解。況且,人們對人類世界認知水平的提高所帶來的直接好處,難以言簡意賅地說明。因此,人們就人文學科所做的公開聲明,往往依賴一系列抽像名詞,儘管這些詞語在某種意義上是恰當而準確的,但聽起來難免給人一種虔誠而乏力之感。
 雅典學院
雅典學院此外,人們對人文學科的理解,還面臨另一重困難。目前形勢下,讓人們描述人文學者的工作,無異於要求他們為之辯護。誠然,所有的描述都內含評估成分,因此任何描述行為都可以達成辯護的目的。但正如我所指出的,所有證明某一活動的正確性的企圖中,都必然存在防禦成分——辯護者往往假定,要求自己做出辯護的人是冷漠無情的,與自己有著截然不同的看待問題的出發點,並預料自己的辯護將遭到對方的抵製或蔑視。這一章的書寫,並非本著這種防禦的心態。相反,它試圖以相對輕鬆的方式,探詢人文學科在做些什麼,以及(至少某些)人文學科的實踐到底是什麼樣的(我要集中討論的實踐,是學術活動而非教學活動,儘管兩者的界限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分明)。在探詢的過程中,我將對一些常見的錯誤觀念發起挑戰。在對人文學者的工作進行一番描述之後,我將在最後一節闡述如何更好地“捍衛”人文學科這一棘手問題。
在當前的背景下,關於人文學科的工作最值得一提的也許是,它在許多方面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工作沒有太大區別。所有學術研究和科學探索的核心,都是力圖達成理解、做出解釋,這些活動大致遵循類似的準則:準確性和精確性、論證的嚴密性和表述的清晰性、對證據的尊重及面對批評的開放性,等等。生物學家與曆史學家一樣,會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系統而冷靜地審視相關證據;物理學家與哲學家也一樣,會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使用抽像而精確的概念和符號。各門學科之間、各個學科群之間,可以從方法、主題、結果等方面,劃分出各式各樣的區別,但這些區別並不都能嚴絲合縫地映射到各個學科和學科群上,從而使之成為兩個相互排斥的對照組。歸根到底,所有學科都有一種衝破學科界限、實現開放式理解的相似內驅力。出於這樣的原因,所有學科都與大學的繁榮發展休戚相關。現如今,人們通常把人文學科拎出來單獨討論,對此我們應該秉持謹慎的態度,以免助長人們形成一種懶惰的觀念,即認為只存在“兩種文化”,而這種陳詞濫調的大多數版本都具有誤導性,阻礙人們理解各個學科之間的內在關聯。
當然,出於各種機構的目的和實際的理由,某些學科必須組合在一起——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意識到:首先,不僅在不同的國家,甚至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大學,學科界線的劃分標準都不盡相同;其次,這些學科組合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目前,“人文學科”(the humanities)正好代表了這樣一個語用組合。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組合安排,以及這一標籤的使用,都是新近才出現的。19世紀,人們主要使用幾個更傳統的詞來指代人文學科,譬如“文學”(letters)或者(在更為理論化或更具自我意識的背景下)“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s);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大學逐漸使用“文科”(arts)作為“理科”(sciences)在組織結構上頗為合宜的反義詞。“人文學科”這一術語在19世紀並不被廣泛使用,它通常指的是古典學研究,而其單數形式(Humanity)可以當作拉丁文學的同義詞來使用(譬如,在蘇格蘭的幾所大學,拉丁文學教授到了20世紀下半葉還被稱為“Professor of Humanity”)。到了20世紀中葉,複數形式的“人文學科”才以其當代的意義在美國流行起來。該詞的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回應彼時咄咄逼人的實證主義,後者提倡將所謂的自然科學方法作為所有真知的基礎。20世紀40—50年代,“人文學科”的使用在英國越來越普遍。1964年,“鵜鶘經典叢書”(Pelican Original)中的《人文學科的危機》一書的出版引發熱議,書名中使用的“人文學科”在當時卻並未受到爭議。然而,這段簡史顯示了兩個相關的主題,它們現在仍然是許多關於人文學科話語的特徵:首先,人文學科基本是處於被動處境,因此往往具有強烈的防禦或辯護意味,而大多數關於“科學”話語則不然;其次,人文學科幾乎總是處於“危機”之中。在過去的十年里,美國出現了大量關於人文學科危機的文章,而在英國大學的人文學科院系中,為了響應政府最近出台的政策,也明顯存在著與美國類似的嚴陣以待、抵禦威脅的衝動。
根據最新版的《牛津英語詞典》,“人文學科”有如下定義:“與人類文化有關的學科門類,包含曆史學、文學、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法律、哲學、藝術和音樂等學術科目。”如此定義,恰如其分地凸顯了這一術語的學術地位,它所列舉的學科也不會引起太多質疑,不過可能需要說明的是,藝術和音樂通常只有被當作學術研究對象(例如,藝術史或音樂學)而不是創意實踐時,才屬於人文學科。在詞典編纂學的角度之外,“人文學科”這個標籤現在也囊括一系列其他學科,這些學科試圖跨越時間和文化的障礙,理解作為意義承載者的人類之行動和創造,重點關注的是與個人或文化獨特性有關的問題,而不太關注那些易受統計學或生物學所影響的問題。相比人文(研究人類世界)與科學(研究物理世界)之間的迂腐區分,一種更好的表述方式或許是:人口統計學或神經心理學這樣的學科雖然是研究人類的,但只是偶然地把個人或群體當作意義的承載者,所以我們通常不會把它們歸入人文學科。這樣的定性方式,不允許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做出硬性的區分:通常被歸入後者的一些學科,不僅表現出鮮明的理論特徵或量化特徵,還顯露出人文學科所特有的闡釋維度或文化面向——政治學、人類學、考古學都屬於此類社科學科,儘管它們有著各不相同的人文屬性。有時,同一主題可能同時屬於(被假想的界限劃分出來的)兩個相鄰學科:譬如,政治思想不僅由政治學家來研究,也由思想史學家來研究;過去的社會行為不僅對社會曆史學家有用,對社會學家也同樣有用。對於思維縝密的分類者來說,語言學是一個特殊學科,它既與語言史家乃至文學評論家的研究興趣有一些共通之處,也與實驗心理學和聲學在方法論上存在共同點。
面對“人文學科”邊界的多孔性和不穩定性,有人設法將這個詞限制在某種不容置疑的中心地帶,將這個標籤局限於對西方思想精華和文學經典的研究。這種反應在美國近來針對人文學科所扮演的角色的討論中,尤為清晰可見。在美國,人文學科的焦點一直是教育教學法,傾向於為研讀文史哲經典文本的“偉大之書”課程(“great books”courses)辯護。但是,以這種方式限制“人文學科”的意涵,不僅完全違背了業已確立的慣用法,而且一些現實理由也導致這種做法不可取。這個標籤須涵蓋完整的古今學問和學術積澱,比如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研究,以及曆史、藝術、音樂、宗教和文化等領域的包羅萬象的研究,而絕不僅限於研究偉大作家和哲學家的作品。
 意大利錫耶納,在古羅馬遺址中被挖掘出來的青銅雕像
意大利錫耶納,在古羅馬遺址中被挖掘出來的青銅雕像這看似只是一個分類學的問題——對於那些因從屬於某一範疇(而非另一範疇)會帶來利害得失的人而言,分類問題很重要,但從大處著眼,這樣的分類問題難免顯得枯燥無味、毫無生氣。儘管如此,最好在一開始就提醒讀者,統攝在“人文學科”這一標籤下的作品類型是豐富多樣的。人們就此範疇而做的一般性陳述,往往產生扁平化的效果,將人文學科的知識探索描繪為整齊劃一的活動,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只需去藏書豐富的學術圖書館逛一圈。速覽圖書館的人文學科書庫,我們會發現,這些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如此千差萬別,光看書的外觀就能感受到這一點。哲學期刊上的短論文,有數字編號的命題或佈滿符號的句子;一部500頁的曆史著作中,對經驗證據所做的密密匝匝的翔實腳註隨處可見;文學評論集收錄了風格獨特的各式文章。總而言之,人文學科的作品,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幾乎與其題材一樣,隨著文化的變遷和時間的流逝而呈現出不同樣貌。
面對一書架又一書架的書籍和文章,外行讀者很容易嘀咕,這些書和文章的內容都是對有限話題的不斷重複,好像再沒有什麼新東西可說。當然,到目前為止,學者們對莎士比亞、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支持自由意誌的論據都已瞭然於心,應知盡知。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真正的新證據可能會被發現,比如一位幸運的學者偶然發現一件因為被錯誤分類而迄今無人知曉的作品,或者在某位名人後代的滿是灰塵的閣樓里找到了一隻手提箱,裡面裝著揭示真相的信件。但大多數情況下,外行讀者若有所思地說,當代的人文學者似乎與他們一代又一代同行前輩多年來所做的是一樣的事情,書寫同樣的文本,使用同樣的材料,處理同樣的問題。那麼,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他們——我們——大部分時間所做的是憂心忡忡。人文學者的常態是對智識的永不滿足。無論發現了多麼令人振奮的新證據,或做出了多麼富於啟迪的恰當描述,人文學者永遠不能(也許也不應該)完全消除這樣一種感覺:他目前所做出的成果只能算一份臨時報告,總是容易遭受挑戰、被人糾正,乃至無人問津。他會在腦海里尋找一種模式,尋求一種秩序,但這是一個躁動不安、永無休止的過程。對於人文學科而言,最可能產生影響力的作品通常是書籍,因為它相當於一塊尺寸極為寬廣的畫布,可以通過令人信服的細節,來充分展示其所繪製的圖案。要想使一本人文學科的著作產生影響力,作者必須提出典範性的模式,使之成為該領域諸多後續研究的框架。就此而言,在剛過去的一代或更久以前出版的書籍中,能夠塑造整個子領域的範例包括:E. P. 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或弗蘭克·克莫德的《結尾的意義》(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7),或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在某些方面,這些作品從未失去切合現實的相關性。不過,它們幾乎一直受到批評和修正(有時系作者本人所為)。而且,人們感覺,這些著作所歸屬的學術共同體仍在向前推進——或轉移到其他話題,或採用不同的方法,或提出新的問題。學術共同體能做到這一點,並不完全是發現新的經驗證據的緣故,也不完全是學術風尚的運作,亦非來自外部世界不斷變化的壓力使然,儘管這些因素都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更根本的原因是,任何知識的起點都需要被重新思考,任何假設(關於社會如何變化、人們如何行動、意義如何表達)都需要被質疑,任何詞彙都不具有排他性的壟斷地位。這裏,學者對知識不滿的生存狀態,演變為一種方法上的準則。在實踐中,它需要經驗豐富的判斷,以決定何時提出不同類型的問題能有效推動知識的進步,何時只會起到無關緊要乃至阻礙性的作用。但原則上,任何問題都不能被事先否決。別人總是可以重新出發,另起爐灶,找到新的切入角度,從他處入手——那麼我們也可以。學者所做的工作永遠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
……
![[英]斯蒂芬·科利尼 著,張德旭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http://n.sinaimg.cn/sinakd20230623s/297/w1080h1617/20230623/dae4-a3fc9a4afdd26d9aae9c61a8c113ac0e.jpg)
[英]斯蒂芬·科利尼 著,張德旭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因此,在某些情況下,面對真實或假想的質疑,捍衛人文學科的最佳策略可能是說:“看,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情,太棒了,不是嗎?”如果坐在桌旁的那位衣著莊重、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行政人員回答說,他根本看不出哪裡很棒,那麼與其費力使用來自工具性話語世界中的術語來重新描述人文學科活動的價值,莫不如讓正經的討論退化為滑稽的拌嘴:“哦,是的,真的很棒 / 哦,確實不怎麼樣”。當然,現實中的討論往往不會完全遵循這種模式,但是想像這種交流爭吵背後的邏輯,可能是一種有用的啟發方法(heuristic),它可以使我們想起,社會對“具體成就”(concrete achievement)這樣乏味的抽像概念的常見呼籲,背後隱藏的是怎樣的現實。談及細節,我們應該注意到“具體成就”一詞的潛意識能力,它能喚起令人不安卻極為貼切的畫面:為了回應人文學科“正當化”的官方要求,一排排自卸卡車在相關部門的台階上卸下一大堆優秀的學術書籍,這種幻想既令人愉悅,又生動有力。
嚴肅地講,這裏的要點是,當有人(可能冷漠地)要求我們對人文學科進行定性和辯護時,我們所能做出的任何回答,其有效性可能不僅取決於我們所做的種種定義和論證,也取決於我們所透露出的語氣和信心。有人說得好,人文學科“探索生而為人意味著什麼:詞語、思想、敘事、藝術和人造物,都有助於理解我們的生活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也有助於理解我們是如何創造這個世界的,又是如何被它所創造的”。歸攏在“人文學科”這個標籤下的各種探究形式,記錄了最為豐富多彩和千變萬化的人類活動。人文學科所從事的工作,試圖加深對人類活動的某一方面的理解,以訓練有素又易於理解的方式,表達人類的好奇心和求知慾——這種努力本身就是目的。顯然,我針對人文學科所發表的這番執拗言論,意在對抗悲觀絕望的勸退言論。人文學科所錘煉的那種理解力和判斷力,與生活中需要的那類理解力和判斷力是一致的。分析至此,我們只能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人文學科感興趣並認可其價值的原因,然後必須認識到,我們已經行至單純的辯護所無法抵達的境地。嚐試為人文學科“辯護”,就像嚐試過一種生活,關鍵在於咬緊牙關,保持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