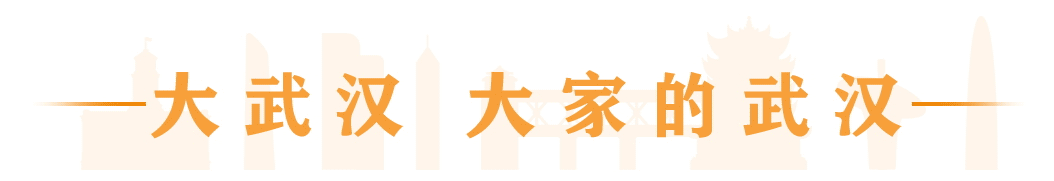專訪|《不完美受害人》編劇:漫長而艱難的女性之路
任寶茹和高璿,二人在電影學院就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姐妹,畢業前後,老師給了一個寫劇本的機會,兩個人互相拉扯著就去了,然後一搭就搭到現在,整整26年。
2017年開始,國內外女性受性侵害案件的報導和女性平權事件層出不窮。編劇觀察生活和社會是創作習慣,又是與女性相關的事件,兩位編劇自然關切,任寶茹和高璿看了許多新聞之後開始討論,討論焦點集中在“這麼多受害者,為什麼都是很多年以後才說出真相?”
“當時,我們都認為這是因為女性困於性的恥感。”任寶茹說道,“但有一天,高璿推給我一篇文章,裡面有句話讓我們醍醐灌頂,它說‘職場性侵的本質不是性,而是權力,它是權力的不對等’。”隨後,兩位編劇開始思考,在性侵事件中,受害者的心態是如何的百轉千回,一波三折,又是怎樣的想要反抗,卻不敢反抗。
“為什麼漫長的時間里,一個女性她的身心都已經成熟了,她完全可以正確的看待性了,但她還是無法面對自己受到的傷害?其實是因為權力的不對等,弱者被碾壓的感覺更屈辱,更慘痛,就算你有一天強大了,你都很難自洽。”高璿說道。
任寶茹越來越覺得,應該去呈現在模糊地帶髮生的性侵案中,受害者的心態變化。“受害人為什麼懼怕權力?權力能給她帶來的正面利益是什麼?一旦違抗權力後,你失去的是什麼?”她聊道,“把這些東西說清楚,我相信能讓很多人對‘不完美受害者’有一個認知,認知‘不完美’存在的合理性。”這便有了電視劇《不完美受害人》。
 《不完美受害人》海報
《不完美受害人》海報《不完美受害人》,講述了一場處於模糊地帶的性侵,一個並不猙獰甚至魅力十足的施害者,一個並不純善甚至滿身瑕疵的受害者,各方視角和敘說之中,一點點鋪開人物和事件的皺褶與暗面。故事有深度的同時,對社會現象和問題提出了質疑,毫不掩飾作者表達上的鋒芒,在當下電視劇市場上,是罕見的勇氣十足的作品。二位編劇表示,從大綱階段開始,平台方就已經進入,但整個創作階段沒有任何外力的干擾,兩位編劇的表達被充分保護和尊重。
澎湃新聞採訪了二位編劇,暢聊了這部作品的創作故事,以及二位編劇在自身成長中,對於女性處境的思考和經驗。
【對話】
趙尋和林闞
澎湃新聞:目前觀眾對於劇情有個很大的爭議點:趙尋有沒有從跟成功的關係中獲利,一旦她獲利過,是否就改變了事件的性質?這個爭議,二位是有所預料的嗎?
高璿:我們完全預判了目前社交媒體上所有爭議,包括大家說的趙尋收下的88萬信用卡和禮物。我們只能說,禮物是強迫給予并包裝了溫柔的面目,其實是成功圍獵趙尋的手段。以交際需求為理由,給高級助理配備50萬額度的黑卡,讓趙尋陪同他參與社交場合時去做一些支付工作。當然,趙尋被告知有權使用這張卡給自己買點東西,但從咱們第一場戲就能看到,趙尋平時就是襯衫牛仔褲帆布包,她逃走的時候,也是脫掉了成功給她購置的大牌服裝。
拍攝的時候,導演要求“88萬”相關道具,一定都是未拆封狀態,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只要這些禮物是打開過的,立刻會導致觀眾對趙巡的道德判斷髮生變化,所以我們為了讓觀眾準確捕捉到趙尋到底接沒接納利益這件事,我們在拍攝和道具準備上進行了精確的執行。
 林允 飾 趙尋
林允 飾 趙尋澎湃新聞:另外關於林闞這個人物也有很大的爭議點:她作為成功的律師,卻送趙尋去報案。也想跟二位聊一下這個人物的創作?
高璿:我們這個戲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司法和情感兩層邏輯。林闞前期所有行為都出於司法邏輯和職業倫理。前期作為代理人,她是在成功的授意和授權下,代表他去跟趙尋溝通和解決問題的,這時,他倆並沒處於對立的立場。在這個過程中,她看到了法律事實之外的另一種真相,但這個真相對定罪毫無意義,因為定罪只看證據和客觀事實。
而她跟趙尋的關係是動態的,當她建立起對趙尋的共情和理解後,她送趙尋去報警,注意,不是“慫恿”她去報警,這個行為從林闞的情感邏輯上是完全沒問題的。當趙尋走向派出所時,林闞依然只是代理人,履行的是代理人職責;當警察來給成功拘捕證時,她的身份才正式轉化為辯護律師,這是有法律上的嚴格規定的。
而後,這兩個女性即使處於司法對立的立場,情感依然在推進。林闞身上體現的是兩種邏輯,一個是職業倫理,一種是情感邏輯,隨著事件推進,她的職業倫理和內心情感越來越撕裂,越來越無法忍受,當最後成功要絞殺趙尋時,她才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
 《不完美受害人》劇照
《不完美受害人》劇照為什麼連承認“受害”都如此艱難?
澎湃新聞:趙尋前期對於自己被性侵的否認,除了她自己還沒理清思緒,除了對於權力的恐懼,她是否有一種不願承認自己被性侵的心情?
高璿:有。一是她自我認知還沒理清,也不願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這讓她羞恥。二是她其實在遮蓋她人性的瑕疵,因為她也不能100%面對自己的選擇和猶疑,所以她第一時間是想遮蓋自己被侵犯的這種羞恥的烙印。她後來的撒謊,也是為了掩蓋自己過去三個月無法解釋清楚的內心的小九九,但後來這個過程被披露在公眾面前,她就為這三個月的猶疑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到那一刻她才完全清楚了自己內心真正想要和不想要的,才完成了最後的成長。
她雖有私慾,卻不是唯利是圖,出了這件事,她是站在十字路口的,往一邊走,她會成為李怡,往另一邊走,她會成為林闞。在選擇的過程中,有懦弱畏懼算計,但同時也有反抗和勇氣。
我們也呈現了她遭受蕩婦羞辱的內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她受到的傷害,以及經受蕩婦羞辱的程度,和她自身的瑕疵是否對等?她是否罪有應得?當然你可以繼續審判她,你也可以選擇共情她,都可以,這是觀眾的選擇。
澎湃新聞:為什麼對於一個女性來說,連承認自己是受害者,都是一件這麼艱難的事情?好像涉及某種“不願成為弱者”的尊嚴?
高璿:我覺得“慕強”跟“恐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每個人都有“慕強”的本能,我們是崇拜權力的,只要權力不傷害我們,我們是希望能沾權力一些光的,社會中走走關係找後門,難道不就是想抱權力的大腿嗎?趙尋在暴露“恐弱”的一面時,也暴露了她的“慕強”不是嗎?如果她承認自己是受害者,她就必須面對過去三個月她“慕強”的一面,她如果沒有慕強的一面,可能一開始就直接拒絕成功了。
澎湃新聞:所以她確實是有沾光的心理,她在“走鋼絲”,但她並不想真的掉下深淵。
高璿:對,所以有人說她又當又立,或者“糖衣吃下炮彈打回”,也沒錯。她自我辨識是有過程的,我覺得這裡面有一點是我能體會的,我二十多歲時是見識過捷徑的,雖然後來我堅持用實力成就自己的事業,絕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二十多歲時,一個在北京沒有家,沒有事業也沒有錢的年輕女性,能突然靠捷徑獲得穩定的居所或者一個工作,那我要不要?最後雖然沒走捷徑,但回想起那時我心裡有過的搖擺,依然如鯁在喉,非常羞恥。
澎湃新聞:不能面對曾經想要自我物化去置換一些資源的自己?
高璿:對,那個“自己”存在於林闞的過去,也存在在趙尋的當下。所以後來林闞有一段話,她最不能忍受的是自我厭惡,厭惡在自己不強大的時候,曾經掂量過——我是不是該拿自己換點什麼?
澎湃新聞:可是我們在影視劇里,在曆史書中,對於男性拿尊嚴換利益的敘事並不陌生,只要達到目的,就是成王敗寇。怎么女性哪怕有這種想法就會羞恥和自我厭惡?
任寶茹:當然了,你想《紅與黑》於連這個人物,評價他是野心家,這要換成個女性,會是什麼評價呢?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的審判,絕對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把趙尋這樣一個人物掰開了揉碎了,放在大家面前,讓大家去評價她,去審判她,是為了什麼?是希望大家看了以後想想,當一個人一身的大窟窿小眼睛,瑕疵像篩子一樣時,她有沒有權利反抗?我們認為她仍有反抗的權利,因為她再有錯,也是受害人,我們還是該把質疑加害人放在第一位吧。
 劉奕君 飾 成功
劉奕君 飾 成功我們的善意和幫助是否有道德門檻?
澎湃新聞:趙尋這個人物有著非常複雜的面相,因此引起爭議是正常的,但在所有的爭議中,一個讓我覺得需要警覺的論調是把她開除出女性隊伍,“她現在的不反抗,讓其他女性的抗爭化為烏有”?
高璿:每個人骨子裡都有懦弱和貪婪,面對權力高位者給你的利益時,是否能完全不動搖?當誘惑你的條件和砝碼足夠大的時候,你是否能無慾則剛?當一個威權的代表,以溫柔的方式誘惑和施壓,你能否明確拒絕和立即割席?當然有很多道德感很高的女性,我為這些女性喝彩。但我們想提供一個不完美到極致的範本,把一個女性的貪婪也好,懦弱也好,把她的褶皺全部打開,任人去討論和批判。
如果這樣的受害者也能獲取到理解,都不用共情,就理解就行,就可以幫助更多女性在受到侵害時,不會由於自己已犯下的道德瑕疵,由於害怕面對惡劣的輿論環境而不敢舉證。而且其實社會多一點包容和理解,她們在說出“不”的時候,猶豫的時間也會短一點,這就是我們寫這部戲的意義。
澎湃新聞:所以,我們的善意和幫助是否該有道德門檻?
高璿:道德門檻之下,哪怕她千真萬確是受害者,也要被討伐,可我們不願意給受害者設置這樣的雙標。我就在想,大家一寸一寸地分析受害者,怎麼就沒人分析施害者,怎麼沒人給施害者劃邊界?我們審視受害者因何受害,而不問責加害者為何加害?
咱們先不談法律,拿公序良俗道德衡量,在道德上,趙尋還會比成功更無恥嗎?成功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不知道嗎?一已婚男性,利用自己的權力“閱女”無數,怎麼不討論他的道德?成功口口聲聲自己沒犯罪,如果你們都不去討論一個權力上位者,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以及邊界在哪裡,那我們就想拆除對於不完美受害者身上的邊界劃定,為什麼要劃定?給成功先劃一個啊。
 《不完美受害人》劇照
《不完美受害人》劇照任寶茹:第一場戲從酒局出來,趙尋明顯是喝醉了的狀態,雖然她嘴上說我沒醉,但在場的人都心知肚明。怎麼不討論:你成功憑什麼不送人回家,而是把人帶你那去了呢?大家是覺得這很正常嗎?包括在現實中,男性出軌,我們看到更多的也是對“小三”的攻擊。
趙尋這樣一個人物的複雜性,只有大家心態平和的情況下,你才能真正的去理解她。她從一個管培生突然被不合規地調到董事長高級助理的位置,她知道這件事反常,但這個位置誘惑嗎?誘惑,那怎麼在第一時間拒絕?我要辭職嗎?或者我不肯調動?都不是容易做出的決定。那到了這個位置上,董事長沒有直接傷害她,送禮也是說“因為你要跟著我工作,你必須要像樣”,“這些東西體現的是我的面子”,你怎麼拒絕?也很複雜。那這麼複雜的處境,最後有人能簡單粗暴的說,她是一個“接受了88萬的妓女”,這種評價我只能說是一種語言暴政。
加害者背後的女人們
 董潔 飾 李怡
董潔 飾 李怡澎湃新聞:李怡這個人物也很有意思,作為成功的情人,她卻對趙尋毫不留情地貶低和羞辱?
高璿:李怡進入這個公司的軌跡跟趙尋一模一樣,年輕貌美,進入了成功的圍獵範圍內,你可以把她理解為:多年前她就是趙尋的處境。不同的是,當她受到這種誘惑包裹下的侵害後,她迅速辨識了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她選擇去攀附、接受成功給予她的一切,並且為了自洽,她把自己的情感也調動起來,不去分清,也懶得分清到底愛的是成功的人,還是他的權力和地位,總之這個人整體讓她迷戀。
所以我們也有過一個設問,當成功被辛路趕回家,褪去一切光環並身敗名裂後,李怡還會不會像從前那樣?我覺得會變化,她至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肝腦塗地為他做一切。我們覺得這就是李怡,她一定是迷戀權力本身。
澎湃新聞:所以,成功的性侵害隱蔽和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受害者要不要認定它是一種侵害?
高璿:對。但不能因為李怡選擇了接受,就改變了他侵害的本質。對於李怡也好,對於趙尋也好,成功都是施害者。但確實比較困難的是:只有受害者的主觀感受才能去追究他是否違法犯罪。成功侵害的方式就是這樣,柔軟的、含情脈脈的,還讓你覺得“為你好”,偽裝得好像你還該對他感恩戴德似的,實際上他的行為都是利用錢和權對年輕女性性資源的掠奪。他在春風得意的時候溫柔如水,但我們也會讓大家看到他濫用權力時,那種傲慢碾壓,無理蠻橫,淩駕於所有人之上。我們只寫了一個李怡,但用其他員工的嘴說了,他身邊有好多這樣的女高層,誰給他這樣的權利?
 陳數 飾 辛路
陳數 飾 辛路澎湃新聞:那麼辛路和林闞導師的妻子,都是侵害者背後的妻子。她們在這個故事中存在最大的價值和作用是什麼?
高璿:辛路跟成功,他們倆是勢均力敵的。當她對婚姻和丈夫失望後,她做的不是討伐,而是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你哪兒涼快哪兒待著去。這不光是精神上的獨立,情感上也完全獨立了,所以後來他們倆從屬關係變化了。我們想通過這樣一個角色說,如果一個女性在婚姻里無法實現自己對於情感的理想,無所謂,只要你自己是完整的,不失去你自己就好。
另外一個妻子,師母,她問林闞兩句話,“你愛他嗎?你恨他嗎?”她期望聽到肯定的回答,因為這樣她才是勝利者,是她“擁有”這個男性,而別的女人沒能“搶走”。其實她特別迷戀她老公的權力,哪怕這種權力包括了掠奪性資源,她也能接納,只要“你們都愛他,是你們主動勾引的,他就是可以被原諒的”。
但一旦說她老公是加害者,而且還被人家拒絕了,這就傷害了她迷戀的男性形象,也傷害了她的自尊。她的個人尊嚴跟她老公的男性權力,直接畫了一個等號,她完全維護自己丈夫的體面和尊嚴,可以作為戰士去“絞殺”同性以維護她老公權力和體面,而這個體面和尊嚴是多麼的虛妄。生活中這樣的女性也不少,我們就把這種觀察放在了她身上。
“社會洞察劇”
澎湃新聞:成功這個人物設計很有意思,我很難看到一個性侵者,網上許多評論都是“心疼成功”,“有魅力”,“正常男人”。
高璿:我告訴你,如果網上都是這樣的言論,我就真的會懊悔,我們為什麼不簡單片面地把這個施害者寫成一個猙獰邪惡的形象。但確實,生活中我們看到很多處在權力高位的人,外表是如此體面,我們想說的是:即便他包裝如此,這種行為依然是侵犯;即便這種行為有99個女孩可以接受,有一個女孩說“我不願意”,這種行為依然是侵犯。
任寶茹:社會好像預設,男性想占領占有大量的異性資源是正常的,如果是一個有權有位的人就更正常了,這叫什麼,“多吃多占”“能者多得”,有人預設這個規則。所以你看有什麼辦法,這劇播出的時候,簡直照見現實。
澎湃新聞:這部劇的創作有兩個難點,一是對性侵犯罪的大量法律知識和案例的調用;二是模糊性,不管是人物的模糊,還是案件的模糊,都會帶來整個創作過程的難度。想聽二位聊一下?
任寶茹:法律方面肯定是巨大的難點。如果法律部分不堅實,這個故事就不成立了。從一開始構建故事,在落筆之前,我們就跟兩位法律顧問開始溝通了,他們會在關鍵情節的法理方面幫我們做推演,如果有些方向走不通,給我們提建議。我們也觀察和瞭解大量國內外類似案件,從裡面找人物的合理性,可以說,正式落筆之前我們的儲備就長達兩年的時間。
說到模糊性,為什麼這個劇宣傳團隊定位“社會洞察劇”,其實就是因為,熟人性侵,職場性侵,很多都在模糊地帶,人性的複雜也全藏在裡面,想把這個寫清楚的確是很難。我們為什麼能一個案件寫了29集,因為我們寫的不只是案件,而是案件前後,每一個在案件中的人,他們人性的複雜,只有這樣才能把模糊性寫清楚。當把一個人物的模糊性寫出來後,我們並不是提供給觀眾一個評斷:好與壞,是與非。我們只是想說:你看,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複雜性和模糊性。當然,審判是觀眾的權利。
高璿:另外,趙尋本身就是一個從認知模糊到逐漸清晰的辨識自己的過程,林闞年輕時其實也有這個過程。戲里這個案件司法上給出了清楚的定義,法律定義接近客觀真相,但不是我們最主要想表現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趙尋從模糊地帶走向清醒認知的過程,所以前面我們就要把所有的模糊攤開。並且劇中幾個女性,趙尋、林闞、米芒等,是有共同的心路軌跡的。
澎湃新聞:女性要走過一條好長的路,通過漫長的自我馴化、自我說服、自我掙紮,可能才能面對和接納全部的自己。
高璿:這就是我們倆為什麼要寫這個題材,因為我們清楚自己走過什麼樣的路,一談這個題材,我們就感同身受。女性創作者當然不用彰顯女性的標籤,完全不用局限在任何題材類型中,只是在《不完美受害人》里,以女性視角輸出觀察視角和價值觀,是我們的責任、義務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