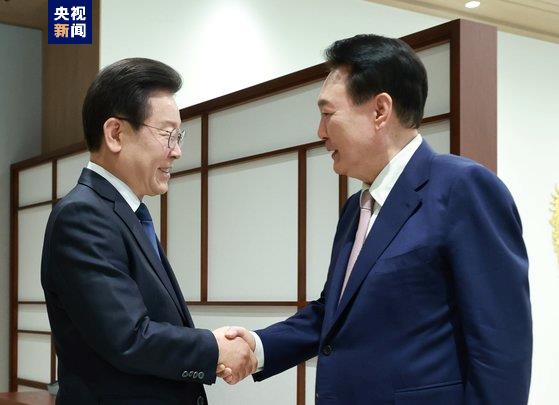許倬雲93歲仍立新說:「天地之間應有如此的中國」
來源:北京晚報
一生為常民寫史,93歲仍立新說
過去一年,九旬許倬雲八易其稿,以考古學為基石展開論述,考察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係,完成新書《經緯華夏》。他感歎道:「我已老邁,大概再無餘力撰寫如此較具規模的專著。」


《經緯華夏》 許倬雲 著 南海出版公司
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
歷史學家許倬雲一生主張「為常民寫史」,他的著作也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許倬雲教研與著述歷史。截至2022年,他共有中文專著58種、英文專著6種、中文合著及編著26種、英文合著2種,共計92種、212個版本行世。
2006年,《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同步在海峽兩岸出版,不僅獲得國家圖書館文津獎,在海峽兩岸銷量也超過百萬冊。2019年7月,清華大學向新生發送錄取通知書的同時,一併送上《萬古江河》,校長寄語新生「從歷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2006年至今,他在大陸出版新作近二十種,如「中國三部曲」、「文明三書」、「從歷史看管理」系列等,自選集、演講集、舊書新版絡繹不絕,成為這個時代最具公眾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近年來,他的線上課程、演講、談話頻頻「破圈」,受到年輕群體的喜愛。
最新出版的《經緯華夏》與《萬古江河》一樣,有著一以貫之的「大關懷」。許倬雲在新書別冊中闡述了為何要在多年後再寫華夏歷史,並在末尾《餘白》中描述這般繼承性:「我平生著作,其計劃與開展的過程,以《萬古江河》最有特色。……這本書稿即將完成,本打算作為《萬古江河》的續編,以補充過去陳述的分析以外,又在別的層面進行一些討論,以說明中國這一華夏共同體,如何可以經歷數千年而不敗。這本書寫作過程中,我的想法逐漸改變,終於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線。」
在《經緯華夏》中,許先生跳脫出中國文化內部演變的敘述,以「大歷史」的觀看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他讚歎中國文化經歷多次調整磨合後,呈現出來的包容性:「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過程中,甚為罕見——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間,作為族群融合的場所。於是,從本書陳述的時間看,中國文化跨度近萬年,少說也有六千年。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這一個例極為獨特。」他希望經由這本書,讓國人知道——「天地之間應有如此的中國」。
許倬雲先生一生著作頗豐,93歲仍立新說。幼時的戰爭經歷,讓他有了一般知識分子不曾有的豐厚的人生體驗,因此對生命格外敬重,關心民間疾苦。他的關心方法,在持續一生的寫作治學當中,也在從不中斷的對他人、對世界的關注中。
許先生一直主張:讀書固然重要,更要讀「社會」這本大書——制度、規章、書本,往往與當下發生的社會現實存在相當程度的距離。九十多歲了,他還保持著少年時的習慣,每天看《紐約時報》《大西洋雜誌》等英文報刊,以及兩岸的中文資訊,為這個變化劇烈的世界心懷憂慮。限於身體他已經三年足不出戶,但不妨礙他對新技術的關心、思考。對於個人主義之下日漸疏離的人倫關係,他顯得憂心忡忡。「人工智能會對包括歷史在內的人文學科造成什麼改變?」他回覆道:「我不擔心AI超越我們,我擔心我們忘了別人——人跟人之間不再有面對面的接觸,人把自己封鎖在小盒子裡邊,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別人。」
全書結尾,是這位常年心懷憂慮的鮐背老人對這個世界的殷殷屬望:希望《禮記·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早日在中國乃至世界落實。
他希望喚起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真情與連接。在一個日趨分裂的世界里,他始終盼望人們不要離散,相愛,互助,開出個新天地。
「抗戰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
許倬雲的學術成就,與其大時代下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
1930年,許倬雲與胞弟出生在廈門,適逢戰亂時期,母親生了一場病,雙胞胎營養不夠,在腹中的許倬雲骨肉沒有發育完全,一出生就是高度殘疾,完全不能行動。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許倬雲與家人一起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也是從那時開始,死亡的陰影籠罩了他的生活。在逃難的路上,他目睹了無辜的百姓屍橫遍野的慘狀,日本軍機無差別的掃射,上午還一起玩耍的小夥伴,下午已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無法行走的許倬雲只能由挑夫挑著趕路,但在某個深夜裡,挑著許倬雲的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另一個挑夫去追離開的隊伍。荒山野嶺中,年幼的許倬雲動彈不得,只能無助地倒在死去的挑夫旁,等到家人來找他。
他後來回憶說:「抗戰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看見人家流離失所,看見死亡,看見戰火,知道什麼叫饑餓,什麼叫恐懼,這是無法代替的經驗。」
到了二十八歲,許倬雲才終於能夠開刀做手術,矯正雙腳,直立行走。在這之前,他都只能在椅子上坐著。面對命運的不公,許倬雲仍堅強地表示:「我的不幸(殘疾),變成我的幸運,因為我能專心唸書。」
與其說是他選擇歷史,不如說是歷史選擇了他。父親教他認字,弟弟把上課學習到的知識講給他,許倬雲不敢放鬆一刻地學習,最終考上了台大外語系,校長傅斯年對他說:「你應該讀歷史系。」
他在台大的恩師有:考古學家李濟之,曾主持河南安陽的殷墟發掘,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歷史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是西洋史研究的開路者;考古學家董作賓,是民國時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學「四堂」之一;文化人類學家李宗侗,經常派三輪車接學生去家裡上課;民族學家淩純聲,完成中國第一部民族學調查……
「我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終身仰慕的楷模。我也沒有專挑哪一位老師的路線,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個人對我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1956年,許倬雲從研究所畢業進入「中研院」史語所。在胡適的幫助下,他獲得紐約華僑提供的1500美元獎學金,得以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1957年夏,他坐船遠航美國東海岸。不同於其他留學生坐飛機或快速客輪,他是廉價貨船的「附帶乘客」。這艘船裝載著菲律賓出產的鐵砂,慢吞吞地駛向目的地。
1962年,許倬雲拒絕了五份美國工作的邀請(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學),選擇回到台灣。之所以作此選擇,是出於三個承諾:對母親、史語所、台大錢思亮校長。回來後,他同時在史語所和台大工作,後來在台大擔任歷史系主任。
「因為我一輩子不能動,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這跟我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大的關係,歷史學家也做旁觀者。」這使得他終身的歷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視角,而非傳統的政治史或帝王將相。
不是「歷史在變」,而是人的眼光變了
「歷史在變」,這是許倬雲一貫的主張。不是歷史本身變了,而是人們看過去的眼光在變,看到的東西也就不一樣了。作為歷史學家,他認為人類在歷史的樹林里,每次只能多看見一點點,前面的道路是慢慢走出來的,要隨時修正,隨時體諒別人。
許倬雲每寫一部書、一篇論文,不是簡單地排比時代的先後、人事的更迭,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國文化的本質。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學術專著為例,《西周史》是在探尋中國文化秩序的本源,寫到西周亡國,他會聯想到抗戰時期同胞的慘狀而落淚;《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關注的是一個社會的分層與流動機制;《漢代農業》則關注人口壓力、市場網絡、政府和工商關係,給近代以來的三農問題帶來了很多啟發。
70歲之後許倬雲致力於為普通人寫作。他說:「中國的歷史常常只注意到檯面上的人物,能為常民寫作、與大眾講話的人實在不多,我願意承擔起這個責任。」此後的十多部著作,其範圍不出大型集合體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縮,還有社會節奏的變遷,都是為了給普通讀者提供一種切實的歷史參照物,從而讓他們有所思,有所得。
對於許倬雲來說,歷史從不僅僅是冰冷的知識和研究對象,歷史是大群知識叢中最貼近人心的部分。它可以是文化的歷史,可以是一個家庭的歷史,甚至可以是每個人內心的轉變。
在這本他額外珍視的《經緯華夏》,許倬雲說,這本書里有自己的歡笑與眼淚。所有的歡笑與眼淚,「都是因為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的芸芸眾生幾千年來的掙扎和奮鬥;或者輾轉於艱難困苦而沒有出路。但是,其實是有出路的,會有出路的;有時候,他們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沒看見而已」。
如果大家都能保持一種時刻在局外又在局中的視角,養成這種觀察世事與往事的習慣,那他作為歷史學家數十年來對公眾說話的目的便算達到了——「我盡了我的力,讓人家知道歷史是這麼一個項目,對你的人生尋找意義、尋找自己,都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