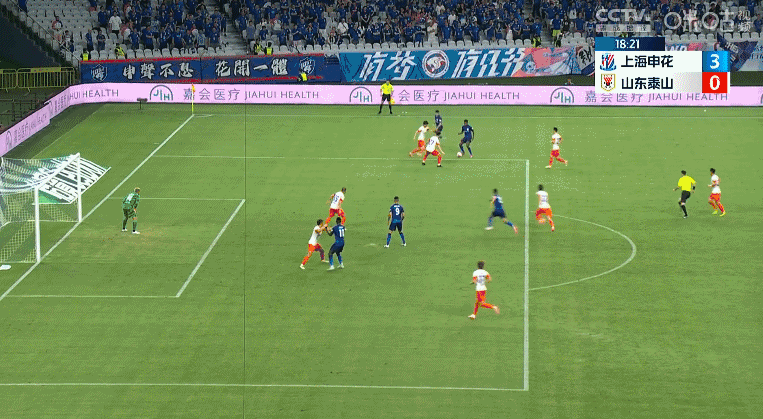做文博戲劇,對場地環境、創作心態有要求|業內說
正如北京李大釗故居、宣南文化博物館等一系列名人故居、博物館一改往日莊重、嚴肅的形象,紛紛推出沉浸式導覽解說、劇目,真正讓館尼雲物活化起來的同時,也重新定義觀眾觀展的體驗感。與傳統的戲劇相比,沉浸式導覽劇充分發揮故居和古建築的優勢,打破傳統舞台與觀眾間的「隔牆」,觀眾置身於場景氛圍之中,能夠與劇中角色「零距離」——忽而是欣賞劇作的看客,忽而又化身為劇作中的角色。
 沉浸式導覽劇《宣南往士》。 新京報記者 劉臻 攝
沉浸式導覽劇《宣南往士》。 新京報記者 劉臻 攝創作目的:輔助觀眾記住展覽內容
宣南文化中最輝煌的一章,應該是曾居住在這裏的士人們,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國家的興亡,為了民族的昌盛所表現出來的報國情懷、變革精神和犧牲勇氣。自明清以來,這裏聚集的士人眾多、活動空間緊湊、延續時間長久,是地處京師、士鄉所形成的文化學術平台。
《宣南往士》導演袁子航回憶創作之初時坦言,當接到西城區文物保護管理中心給到的這一命題時,倍感壓力。當自己第一次沉浸到宣南文化博物館「風聲、雨聲、讀書聲——北京宣南士鄉歷史文化展」的展覽之中,又覺得最初的壓力瞬間便轉化成了動力,創作狀態變得興奮起來。「長椿寺作為一座有著四百多年歷史的古建築,這裏先天的空間優勢對於創作者而言,無論從藝術展現空間,還是創作空間都是無比巨大的。同時,宣南士人文化中,近代以來影響中國歷史前進的人物莫不與此地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裏出現過的歷史人物,發生的歷史故事數不勝數,因此以什麼樣的形式詮釋‘宣南士人文化’這一主題都不是問題。」
袁子航認為,雖然士人雅集作為傳統士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交流方式,推動了北京宣南士鄉文化的形成,但到了晚清時期,宣南士人雅集更重要的目的是闡發經義、傳播學術,進而改變社會風氣。若站在觀眾的角度,創作者一開始並不需要深究歷史上那些著名士人的一言一行。「如果觀眾能通過看展覽記住一些歷史人物,再通過我們將這些人物故事演給觀眾,哪怕觀眾能記住一句話、一個片段、一個事蹟,或許當他們再來看展的時候,就會產生一種全新的心理狀態。」
近年來,宣南文化博物館一直在文物活化、沉浸式感受宣南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不斷探索與嘗試,從去年的「雙節」期間,舉辦「月滿長椿 梨韻仲秋」沉浸式遊園活動,到2024年世界讀書日期間特邀「宣南往‘士’」演出團隊化身NPC,打造深度參與式的文化體驗活動,其實都給袁子航以及《宣南往士》創作團隊巨大的創作空間。推翻傳統劇作諸多線性敘事的創作模式,根據劇情需要融入了相聲、曲藝、彈琴說唱、流行歌曲等表現形式,主創希望以一種歡樂的姿態將宣南文化展現給觀眾。「通過演員的表演,不僅將部分展陳的內容進行了還原,觀眾還能深刻地記住某些瞬間,在自媒體時代下,再通過他們的手機短影片進行二次、三次的傳播,也讓更多人知道《宣南往士》與宣南士人文化。」
同樣作為李大釗故居沉浸式導覽講解《守常先生》的導演,袁子航則認為,與《宣南往士》相比,李大釗先生作為當之無愧的革命領路人,這部作品的創作從內容上,首先要遵從史實,創作態度需要極為的嚴謹。《守常先生》集中展現的是1920年-1924年,李大釗在北京家中生活期間,最集中且充滿戲劇衝突的事件濃縮,讓觀眾在故居看完展覽之後,通過沉浸導覽解說再進行一次情緒上的提升。
 博物館中的表演能讓觀眾更立體體驗展陳內容。 圖/IC photo
博物館中的表演能讓觀眾更立體體驗展陳內容。 圖/IC photo創作手法:「潛入深出」的表達形式
相較於傳統戲劇,沉浸式戲劇在觀演元素空間、觀眾、演員這三個方面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宣南往士》這部沉浸式導覽劇中,觀眾、演員,以及宣南文化博物館的展陳,三者要融為一體,在觀劇時,觀眾作為觀賞者或者暫時的表演者存在於戲劇中,不論是什麼身份,觀眾與演員之間會存在交流,只是這種交流有時是間接的,有時是直接的。
《宣南往士》與《守常先生》這兩部沉浸式作品,演出過程中都會距離觀眾非常近,因此很多觀眾都察覺不到身邊的那個人就是演員。而演員常常需要在戲中跳進跳出,既要照顧角色的需要,又要隨時應對觀眾的反應,進行即時的互動,「當我們演員習慣了這種演出中的互動交流方式,反而覺得這種方式深受觀眾喜歡。我們也會選用一些當下流行的熱梗來與觀眾交流,當他們記住了這些梗與一些片段後,也就記住了劇中的人物,這種‘潛入深出’的方式,會吸引他們主動拍攝一些互動小影片,發給身邊的家人、朋友,由此又會吸引一批新的觀眾預約來到博物館感受我們宣南文化。」
《宣南往士》涉及歷史人物與事件眾多,也被袁子航看作是一部多樣式的劇本。據他透露,這部作品的劇本創作前期,沒有動筆寫之前,便進行了兩個月之久的討論——劇中人物的時間背景從明末跨越至民國,如何讓觀眾在一個視角下將整個展覽逛完,這是最初擺在主創團隊面前最大的問題。
最終,《宣南往士》以由宣武門石額幻化的白鬍子神仙「石額公」為主要講述者,另一個視角則是進京趕考的晚清舉子「弘生」,兩個虛構的角色引導觀眾走入各個展廳。觀眾在石額公和弘生的引領下,看學論道,賞筆墨丹青,聽公祭楊椒山,瞭解清末「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等歷史事件,讀宣南報業發展變遷史,沉浸式感受文人才子及熱血青年的家國情懷。袁子航解釋,「石額公」在宣武門城樓之上將近六百年,一直俯瞰著這片熱土,而歷史上所有的士人學子來京,也必須經過宣武門,因此宣南的士人,「石額公」都認識。而時間點以1895年為起點,在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影響中國近代史的事件:如甲午戰敗簽署《馬關條約》;康有為入京會試聯同十八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並組成強學會;在宣南的後孫公園創辦《萬國公報》,成為北京第一份由中國人創辦的近代報紙,以此為起點,石額公和弘生帶領觀眾開啟跨越百年的宣南文化之旅。
袁子航認為,由於宣南文化博物館展陳內容太豐富,即使每一輪《宣南往士》演出都有全新的角色加入其中,但截至目前,劇目相關歷史內容的挖掘工作,甚至還不到博物館展陳的十分之一。「就算《宣南往士》在宣南文化博物館里再演十年,都不一定能把這裡面的人物與故事挖掘完。」袁子航表示,以個人的能力肯定不能完成如此龐大工作,但在他身後還有一支龐大的演出隊伍——西城區文保劇社,《宣南往士》中的數十名演員均來自這裏。
據袁子航介紹,文保劇社的構成主要由國家一級演員、職業演員以及一部分對戲劇感興趣的群眾演員組成,目前已擁有1000多人,而想在劇社深度體驗,挖掘《宣南往士》這部作品文化內容的演員,目前有100人以上。為此劇社還推出了一個「士人喚醒計劃」,將宣南歷史上出現過的數百位士人歸納起來,讓一些對某位士人感興趣的社員將其「喚醒」,帶回家中進一步地深入研究。「很多士人在網上的資料非常有限,學員便會主動走進圖書館查古籍,自行購買一些書籍去研究這個人。未來我們計劃將他們研究的成果以影片的形式推出,讓更多人瞭解宣南的士人文化,同時,通過這些資料的研究,也為我們《宣南往士》的故事不斷地更新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宣南文化博物館內在進行沉浸式導覽講解。 劉臻 攝
宣南文化博物館內在進行沉浸式導覽講解。 劉臻 攝創作挑戰:成為趨勢同時也有許多限制
沉浸式導覽劇可以一舉改變傳統博物館講解「你講我聽」的參觀模式,把展覽內容用戲劇體驗的表現形式,通過創新方式,將其建築價值、精神價值與文化價值一一傳遞給觀眾。
博物館裡面的「沉浸式」演出成為一個熱詞,但從專業的角度來說,在博物館里進行沉浸式戲劇演出,還是會受到一些客觀限制。在宣南文化博物館館長張麗娜看來,宣南文化博物館之所以能夠將《宣南往士》這部沉浸式導覽劇做成功,其實是將博物館的劣勢變成了自己的優勢。她進一步解釋說,相較於很多大型的專業博物館而言,宣南文化博物館的劣勢在於自身的文物展品非常有限,如果按照傳統博物館參觀模式運營,其實不太容易吸引更多的觀眾。把這一劣勢轉化成為優勢,推出《宣南往士》這樣一部沉浸式導覽劇便彌補了原有的不足,進而還成為區別於其他博物館的一大特色。「隨著博物館熱,讓很多人開始喜歡博物館,這裡面肯定也會有因為戲劇走進博物館的群體,從而又進一步地感受瞭解到宣南文化。」
從博物館遊覽體驗的角度,張麗娜認為,博物館里看沉浸式演出未來肯定會成為一種趨勢,但同時一定也會受到很多的限制。「相較於以文物展品為主體的傳統博物館,側重於讓參觀者更多地沉浸於文物,宣南文化博物館則本身就擁有全北京最好的‘舞美’——長椿寺,與其他博物館將文物活化,演出與文物分開相比,我們的演出都是由真實場景構建而成,觀眾只需站在展陳的文物旁邊,便可觀看一部沉浸式導覽劇,這種體驗對於走進博物館的觀眾而言,無疑是最好的。」
 觀眾對沉浸式導覽劇的評價。 新京報記者 劉臻 攝
觀眾對沉浸式導覽劇的評價。 新京報記者 劉臻 攝從創作者的角度,導演袁子航則認為,「博物館里看戲」的趨勢一定是存在的,但想要在短時間內實現大範圍普及,或許這中間還是需要一定的過程。若想真正在博物館里做一部戲劇,其實對於環境以及舞台設備的要求非常高,像《宣南往士》這部作品,需要在長椿寺2000平米空間完成無死角的音響覆蓋,幾十人的服化道都要具有專業性與可考性,這些除了演職人員自身的決心與情懷外,自然離不開上級領導要把《宣南往士》這部劇持續做下去的決心與魄力。
「通常博物館里的導覽類作品,一場表演下來,音響覆蓋最多一個房間30到50人。若以此為標準,像在宣南文化博物館這類博物館進行演出,就得進來一批觀眾,演員就要給他們演一遍。一個房間里的一段劇情重覆地演,便不可能形成一部完整的戲劇作品,因此這就需要博物館下更大的決心,將劇目與博物館設定成一個整體,在固定時間段,讓演員從頭到尾引領一撥觀眾完整地享受劇目的觀演,這個難度可能是目前很多博物館很難達到的,也需要他們進行更多的嘗試與探索。」
新京報記者 劉臻
首席編輯 田偲妮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