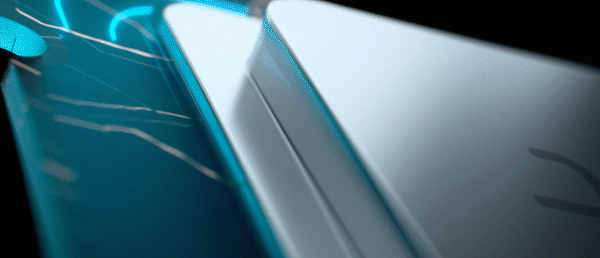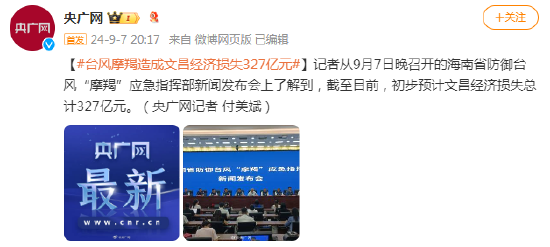史鐵生:當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間清醒」
 地壇銀杏大道。視覺中國供圖
地壇銀杏大道。視覺中國供圖對我來說,無論何時看到「史鐵生」3個字,就像看到一串開啟時空隧道的密碼,持有這串密碼,就可以自由穿越時空。不對,不是自由,而是每次穿越,都只能回到一個荒蕪的故園。那裡也許是地壇,也許是清平灣,也許是孩童嬉鬧的某條小胡同,但總歸是內心深處一個清澈、柔軟的地方,還有淡淡的絃樂流淌。
第一次有這種穿越感,是2010年12月31日,史鐵生在那天淩晨告別了人世。到了白天,消息傳開,就有報社編輯給我打電話,說史鐵生去世了,讓我準備採訪幾個他的生前好友,寫篇「逝者」文章吧。
我當時在做文化記者,領到任務就開始行動。文章似乎不難寫,但「史鐵生」這名字讓我開始恍惚,什麼時候集中大量讀他的文字?大概是中學時代吧。20世紀90年代,史鐵生作品在中學生的課外推薦讀物里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坐在輪椅上的形象,被貼上了「身殘誌堅」或者「不向命運屈服」的標籤。寫作就是對抗命運的一種方式嗎?少年時代的我真正讀進去,發現這些標籤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誤讀。史鐵生的文字沒有那麼鬥志昂揚,而是溫情的,憂鬱的,困惑的。他像每個年青人一樣,即使不是病痛纏身,對這世界也有太多的問題,找不到明確答案。
這樣一位無數次思考過死亡的作家去世了,我才把他關於生死的文字彙集起來重讀,最後把他的這句話放在悼文的開頭:「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是2010年的最後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在翹首企盼新年,而史鐵生的「節日」提前降臨。
一晃10多年過去,再次重讀也再次恍惚穿越,就是現在了。短影片時代,「史鐵生」這個名字竟變成了新的流量密碼。《2024年抖音讀書生態數據報告》顯示,史鐵生成了抖音最受歡迎的作家,今年上半年,史鐵生作品銷量同比增長44%,其中《我與地壇》的銷量就同比增長了357%。要是按年齡段看讀者數據,最愛史鐵生的是00後,也就是現在十幾歲到20出頭的年青人。
贏得年青人的心,為什麼是史鐵生?或者,為什麼不能是史鐵生?知識界和文藝界的討論像是自問自答,又像是中年人試圖理解青年人的一場群體心理測驗。
史鐵生是1969年去陝北插隊,1972年回到北京。雙腿癱瘓的時候,他只是個20歲出頭的青年。「插過隊的人想寫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寫插隊。」史鐵生把知青故事編排了很久,設計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諸葛亮式的人物、張飛式的人物,「結果均歸失敗」。小說不好寫,生活本身比寫小說更難,回到北京的史鐵生也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半個世紀前的年青人也想要一份穩定的工作,或者說,那時候的年青人尚不知「內卷」為何物,也無從想像更多元的選擇。「我仍然沒頭沒腦地相信,最好還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進一家全民所有製單位,一生便有了依靠。」
這是不是這屆年青人共情史鐵生的密碼之一?史鐵生無法書寫的知青歲月,梁曉聲寫成了,時代的一個切片就此進入文學史。文藝評論家解璽璋說,史鐵生的文學不是知青文學,完全不是,他甚至連知青文學特有的那種熱情洋溢的理想主義都沒有,完全沒有。史鐵生只能去寫失落,寫生存困境,他的身體被禁錮在輪椅上是一種殘疾,而他書寫的是精神領域的另一種殘疾。「在史鐵生的作品里,人的有限性,都是人的殘疾。」
「回去再等等吧,全須全尾的,我們這兒還分配不過來呢。」史鐵生寫當年的勞動局庭院深深,他和母親奔走多次,得來的只有這麼一句例行公事的話。母親是史鐵生最重視的人,她直到去世之前還在一趟一趟往勞動局跑,每次回來都向兒子表示歉疚。史鐵生不說什麼,依他的意思,再不要去找那些人。
他決定寫作。寫作意味著他不再幻想一種來自社會層面的堅實保障,這又像極了如今年青人說走就走的旅行。不同的是,史鐵生的活動半徑不過那時荒草萋萋的地壇,他並無別的地方可去。別人上班,他上地壇。「地壇的每一棵樹下我都去過,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過我的車輪印。」史鐵生寫道,「我一連幾小時專心致誌地想關於死的事,也以同樣的耐性和方式想過我為什麼要出生。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後事情終於弄明白了。」
史鐵生就這樣成了當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間清醒」,拜網絡無遠弗屆的力量所賜,有比當年多得多的讀者,來史鐵生這裏尋求情緒價值。短影片並不是吞噬時間的黑洞,而是讓更多「心裡有事情」的年青人重返書本,重讀經典。只是在他身後,時光如水,人潮如虹。年青人一茬接一茬長大,那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卻像地壇的老樹,沉默地矗立在每個遊人必經的路旁。曾在荒園老樹下長久靜坐的那個人已經走了,但只要你帶著問題回到這裏,你就一定會再遇到他。
武雲溥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7月26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