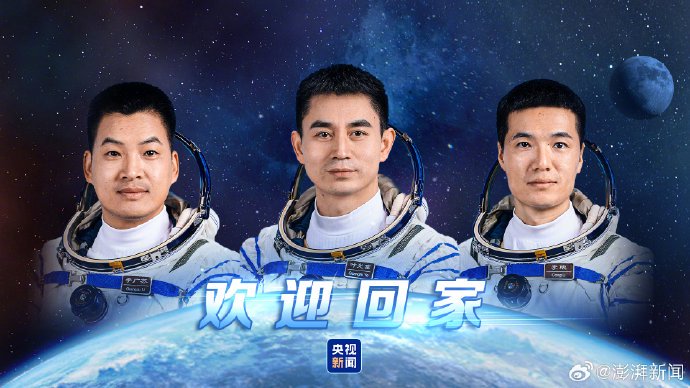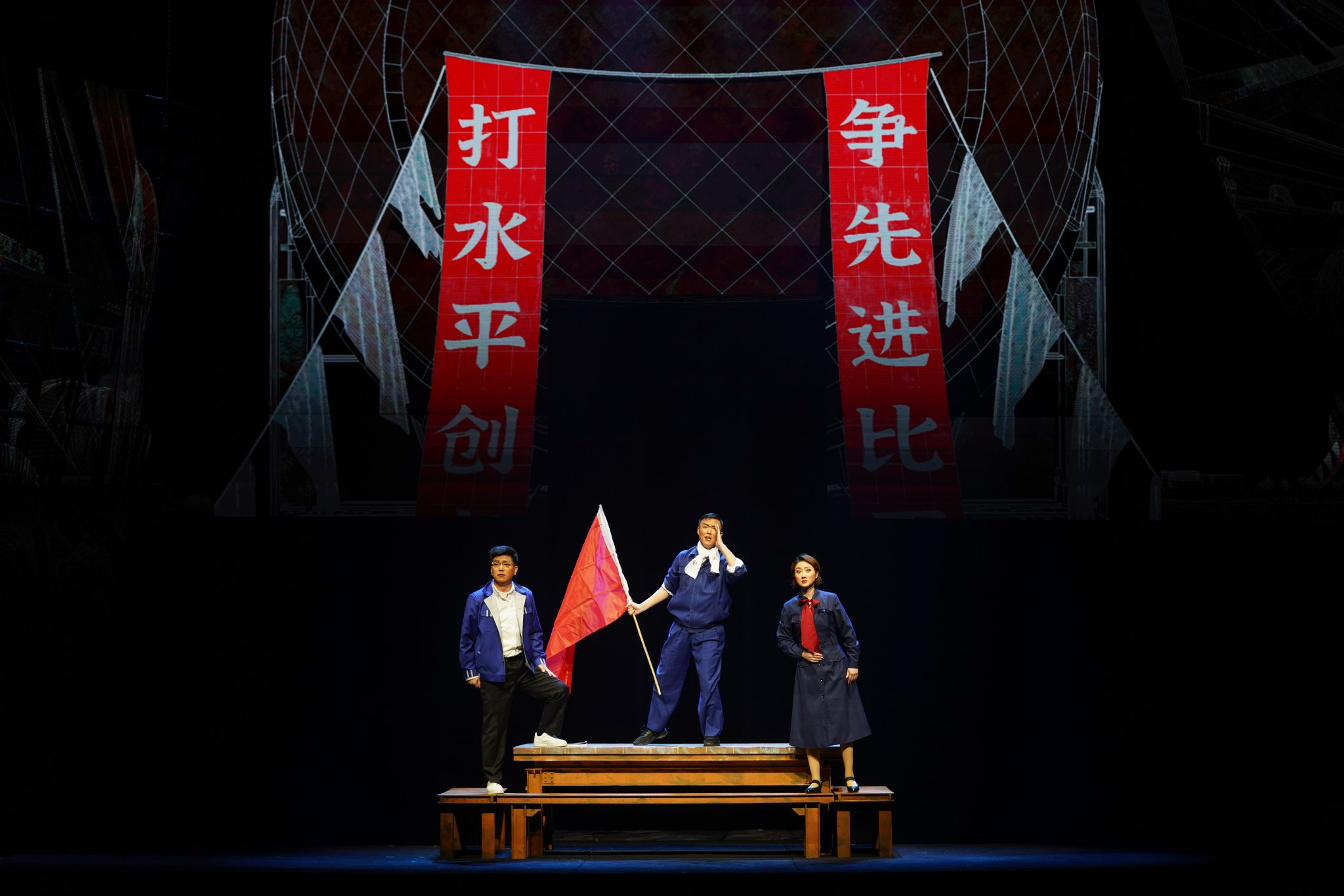醫院是座動物園
 書封。出版社供圖
書封。出版社供圖《難得糊塗|綿羊一家》《壞人我來當|烏龜的殼》《八面玲瓏言部長|蛇的身段》《最熟悉的陌生人|不是同林鳥》《小乙與小文|橘貓的最後時光》……《醫院是座動物園》是一部神奇的短篇故事集,每個故事的標題分為兩部分,前面是人或事,後面則是動物,但讀完會發現,人,也是動物。
這本書的作者本碩都是新聞專業,「陰差陽錯」入職了一家醫院,先在辦公室工作,後來調到宣傳部門,這讓他有更多機會和醫生們打交道,記錄下那些與人性和命運有關的故事。
每個故事往往只有兩三頁,就已經完成了對一個人「病」與「死」的書寫。極致的簡短,刻畫出人在醫院這個空間中的極端性。作者以動物喻人,在那些生死攸關的場景下,患者和家屬的各種表現,總讓他不由心生悲憫;那些狀態、那些姿勢、那些神情,在與一些動物形象的重疊中,甚至有了一些神性。
《社會活動家李大郎|薛定諤的貓》中,醫生讓大郎住院做穿刺取活檢,以判斷是不是肝癌。但大郎夫妻倆一合計:如果是,沒得救,無非掛著管子延長幾年壽命;如果不是,那就白檢查,還有因檢查而發生感染的風險;乾脆,辦理出院,開始旅行,想著不能延長生命的長度,就拓展生命的寬度。
「只要不檢查,他就永遠不知道那是不是癌症,他永遠不知道自己會短時間內死去還是繼續活著。」幾年後,大郎媳婦給醫生打來一個電話,說大郎過世了,因為喝了場大酒,心梗。
在醫院里發生的很多故事結局都是死亡,走向死亡的過程有的曠日持久,有的猝不及防。如何好好活著,反而成了病人最認真思考的話題。
醫院里人來人往,每個人一生中不出意外一定會進醫院,既然是每個人不得不去的地方,那自然收集了關於人性最廣泛而深刻的切面。比如,《重刑犯|鱷魚也流真眼淚》中老謝的故事。
老謝是個重刑犯,因患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從監獄直接拉到醫院急診。做完手術那天,老謝半夜醒了,轉頭叫陪護的李警官,卻發現李警官的身體佝僂成了一種奇怪的樣子,在劇烈地扭來扭去。老謝想用手推醒他,可一隻手被銬在病床上,想用腳,腳也被銬上了;扯開嗓子想喊,可是手術插了管,聲帶受損……老謝拔去針頭,用盡全身力氣從床上滾了下來,一隻手支著地,往病房門口挪動。
護士聽到巨大異響,趕緊跑過來,看到李警官昏迷在陪護床上,老謝半掛在床邊,嚇了一大跳——這可是重刑犯啊,趕緊叫醫生和保安。最後,李警官被搶救了過來,急性心梗,當時是發病初期,搶救的黃金10分鐘以內,再晚上幾分鐘,就不好說了。第二天,甦醒的李警官買了罐頭給老謝,問他為什麼要救自己;老謝說,我幹了壞事情,政府逮我、判我,這和你又沒關係。
有人覺得醫生不能共情,有些「冷酷」,其實他們也是普通人,在生活中也有七情六慾,但職業特點決定了他們必須冷靜,必須站在一個超然的位置看待這一切,才能更好地救治病人。事實上,年長的醫生往往人情練達,患者說一句話,他們就知道後面要說什麼,話背後隱藏的又是什麼。
《就是想和你聊聊天|燕雀與鴻鵠》中,值班醫生淩晨兩點接到電話,一個老太太說自己發燒37.5℃。醫生請她先在家物理降溫,不行再來醫院,但老太太問這問那,而且問題逐漸離譜,比如小夥子你多大了,成家了沒,孩子多大……
在聊天中得知,老太太今年70多歲,一兒一女都非常爭氣。兒子20多歲留學後就留在了法國,女兒到北京讀書後也留下工作。兒子從出國後到現在總共見過三四次,女兒多一些,一年見3次。老伴兒過世後,老太太就一個人生活了。最後一直聊到了早晨6點,老太太說,沒什麼事情,就是睡不著,找人說說話。
醫生下班回家,晚上輔導兒子作業,突然想到,如果孩子以後去遠方念大學,自己不就和那位老人家一樣。「鴻鵠可以去遙遠的西伯利亞,飽覽美景,而燕雀也挺好,兒女們棲息在平原、山間,能經常廝守,其樂融融。」
書中有的故事有些晦暗。《不值得的一生|老牛沒好命》講的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老張,22歲本科畢業,不到30歲副處,等了20多年才剛提拔成正處。生病之前,他懟天懟地懟空氣,生病之後,反而放下執念,開始知道如何生活。可是,世界只留給他四五個月的時間。
作者說,其實醫院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情況更多;患者來院就醫,醫生盡力,家屬配合,才是臨床的常態,否則醫生每天就不用看病了,忙著處理醫患關係的時間都不夠用。但也正是因為這些「另一面」的存在,才能讓我們更審慎地正視自己的內心。
一個放逐自我的乞丐,也有著駿馬般驕傲的一瞬;一位多年前弄丟孩子的老人,最終如白鶴一般歸去……把醫院比作動物園,毫無不敬之意,而是生死之下,萬物芻狗。老子說,老天看待萬物是一樣的,不對誰特別好,也不對誰特別壞。但人終究不是天地,不會「不仁」。我們面對深淵的時候,其實看到的都是自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世界很幽遠,但幽遠不過人心,即使是星空,比起人心也如透明一般。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慎獨」,關門那一刻,你才知道自己是什麼。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7月26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