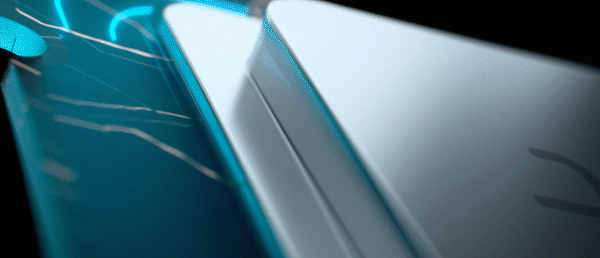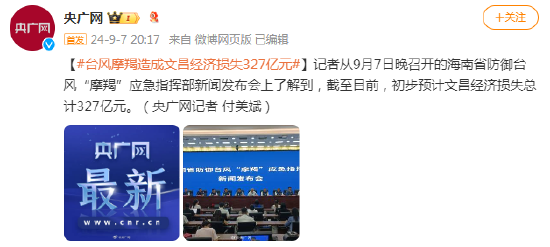「三辭桂冠」的季羨林 中國學問家的典範
 季羨林。視覺中國供圖
季羨林。視覺中國供圖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
「曾經的紅衣少年,如今的白髮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雜憶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筆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貧賤不移,寵辱不驚。」這是「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給季羨林的頒獎詞。一介布衣,是他的人生起點,也是季羨林的自我定位。
近日,為紀唸著名學者、北京大學終身教授季羨林先生逝世15週年,由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聯合舉辦的「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第五講「季羨林:中國學問家的典範」開講。本次講座的主講人鬱龍餘教授於1965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師從季羨林,現任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是國際著名印度學家。
季羨林研究的梵學、吐火羅文專業,早年間能懂的只是極少數人。晚年,隨著他聲名遠播,「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成為世人冠在他身上的稱號。他卻「三辭桂冠」,並說:「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季羨林一生不慕名利,潛心研究,在印度學、東方學、比較文學、散文研究等眾多研究領域,都作出傑出貢獻。不過,鬱龍餘認為,「印度學研究是最基礎、最重要,開展最早、堅持最久的」。
中國和印度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但古代的中印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東傳為主,印度的主流文化經典——《吠陀》《往事書》《奧義書》及兩大史詩等,並沒有傳到中國。所以,真正從梵文原典將印度文學的主流作品,翻譯介紹到中國並進行學術研究的,季羨林是第一大家。
在《梵典與華章》中,鬱龍餘這樣評價:「季羨林正是憑著自己豐碩而精湛的印度學研究成果,和其他學者一道,真正建立起了中國的現代印度學。他不僅是當代中國的首席印度學家,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印度學家之一。」在季羨林逝世後,時任印度總理的曼莫漢·辛格致函表示:「季教授是世界最著名印度學家之一。」
季羨林不但是中國印度學的創建者,還是中國東方學的奠基人。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羨林終於歸國,在北京大學與金克木、馬堅等一起創立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東方學。他所建立的中國東方學和西方恰恰相反,以人類全部歷史為考量,客觀、公允地評價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給予認真分析、理性批判和充分借鑒,旨在為建立以「世界大同」為特徵的人類新文明貢獻力量。
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比較文學在中國複興並蓬勃發展時,自幼學習古文、精通多門外語的季羨林對此產生濃厚興趣。1981年1月,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學會正式成立,會長季羨林,顧問錢鍾書。
季羨林從事比較研究文學,主要聚焦於中印文學的比較研究和批評。他始終認為,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有著古老文明的大國,在文學上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他作為一位研究印度語言文學的學者,有責任向讀者展示中印兩國沿襲至今的文學關係。
鬱龍餘認為,季羨林對比較文學的理論貢獻,主要表現為一個總綱——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以及八大觀點:批評西方中心論,讚同印度故事中心說,百姓是故事文學的創造者,本土化和民族化是故事流傳的必然,文化交流是源、比較文學是流,文學交流促進世界各民族友誼,一國之內可以有比較文學,東方綜合、西方分析。
在比較不同的文化和文學後,季羨林開始思考,在一個西方中心主義佔主導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如何向世界展示厚重的中國文化。為此,在季羨林的散文創作、學術專著中,存在大量文化交流內容。他的《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正是關於中印文化交流的名著。
季羨林喜愛語言研究,也精通翻譯。縱觀中國現代翻譯事業,季羨林譯作不但數量驚人,而且大都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難譯之作。所譯「二劇一詩一故事」(劇本《沙恭達羅》《優哩婆濕》和大史詩《羅摩衍那》、寓言故事《五卷書》),是印度主流古典文學的代表作,質量與品相極佳。
他總結自己的翻譯實踐,提出了自己的翻譯理念。後來,這被學者們稱為「季氏譯論」,主要有三條:反對重譯即轉譯,主張直譯,提倡以詩譯詩。這「季三條」是對古代中國譯論「五失本」「三不易」(道安)、「十條」「八備」(彥琮)、「五不翻」(玄奘)、「六例」(讚寧)的繼承與發展。
當時,季羨林為了以詩譯詩,尋找一個韻腳,「失神落魄、其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又說,「時間經過了十年,我聽過三千多次晨雞的鳴聲,把眼睛熬紅過無數次,經過多次的心情的波動,終於把這本書譯完了」。
著名學者袁行霈在2007年5月《明報月刊》上發文說:「一個沒有典範的社會是悲哀的,一個雖有典範而不懂得尊敬的社會更是悲哀的。我們還有季先生這樣一些典範,而我們也知道應當如何敬之愛之,用他們的人格和學問來規範自己。」
季羨林一生治學嚴謹、一絲不苟,對學問孜孜以求。然而在生活中,卻是個性情中人,敢說敢言。他在《清華園日記》中寫道:
「腦袋里亂七八糟地滿是作文的題目,但是卻一篇也寫不出——今天只想作一篇《自咒》。」(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以前我老覺得學生生活的高貴,尤其是入了清華,簡直有腚上長尾巴的神氣,絕不想到畢業後找職業的困難。」(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實際上,出版社在刊印他的日記前,提議「做適當刪減」,但季羨林的意見則是「一字不改」。
他說:「我考慮了一下,決定不刪,一仍其舊,一句話也沒有刪。我七十年前不是聖人,今天不是聖人,將來也不會成為聖人。我不想到孔廟里去陪著吃冷豬肉。我把自己活脫脫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悅 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7月26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