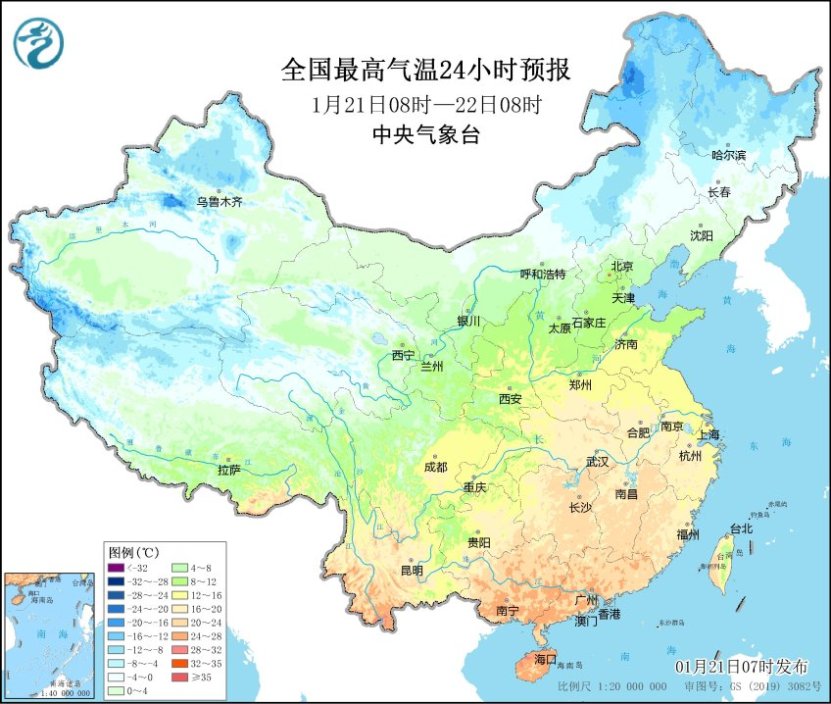北京文化守護人|邢軍:尋源白浮泉

 8月20日,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昌平區博物館原館長、文物專家邢軍站在白浮泉遺址前。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8月20日,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昌平區博物館原館長、文物專家邢軍站在白浮泉遺址前。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北京文化守護人邢軍,昌平區博物館原館長,文物專家,從事文物保護工作三十餘年,先後參加了張營遺址的發掘、京西工業遺產調查、長城資源調查、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2017年後,邢軍從昌平區文化和旅遊局退休,此後仍然在文保工作中發揮餘熱,為大運河白浮泉遺址文保工作提供建議,在遺址公園建設過程中,提供文物保護利用的思路,由他編著的《白浮泉水入運河》已於2022年出版。

邢軍講解的白浮泉,和大眾印象中的不太一樣。
2023年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開園前後,邢軍那段時間來得最勤。他頂著一頭花白的頭髮,背著一個深色的挎包,站在人群裡,向媒體記者、相關單位來客、慕名而來的遊客,講述白浮泉與大運河的關聯。
邢軍不僅會講述七百多年前,元代水利學家郭守敬為滿足元大都的漕運需求,從現在的昌平龍山白浮泉引水,連通京杭大運河的往事。他還會在講述過程中,看似不經意地彎下腰,從地上拾起一塊陶片,向人們展示上面的繩紋紋飾,說那是西周古墓陪葬品的碎片,以證明白浮泉一帶早有人類活動。除了白浮泉水入運河的高光時刻,邢軍也喜歡說說這裏的前塵過往,展現歷史與文化的連續性。
如今,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正式開園已一年有餘,邢軍便很少再去了。畢竟,他講述的那些歷史與故事,會隨著這座公園的對外開放,被更多人熟知。
記憶中源頭往事另有一番模樣
京密引水渠以北,龍山腳下,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的蟬,到了夏末初秋也仍然不知疲倦。白浮泉畔已對外開放一年有餘,汩汩水流會從鬚髮畢現的石龍首處湧出,流入鋪滿荷葉的池塘。泉畔一側,龍泉禪寺內的展覽講述著運河往事。山頭上,北京唯一一座以「都」字冠名敕建的保殊廟內,民間的求雨壁畫環繞牆壁,一如幾百年前。
 邢軍查看九龍池龍首。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邢軍查看九龍池龍首。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邢軍說自己家距離公園不算遠,「沿著東沙河,走路四十分鐘就到了。」過去幾年,邢軍是白浮泉畔的常客,公園正式對外開放後,他來得少了。再次踏入園中,邢軍的衣著打扮一如往年——長袖外褂加一條長褲。他說這套「工作服」能防戶外的蚊蟲,也能抵禦室內的空調冷氣。深色的斜挎包像是長在身上,隨手總拎個水壺,即便夏天,裡面的水也總是熱的,邢軍說,不服老不行。
「上歲數了之後,就發現有時候昨天的事情都忘了,但自己小時候的事情倒都還記得。」與當下呈現在市民遊客眼前的景象不同,邢軍記憶中的運河源頭,另有一番模樣。
走到白浮泉邊,邢軍緩緩說道,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白浮泉遺址曾一度頹圮荒廢,九個石雕龍首空張著口。
現如今龍首上那座仿金元時期的臨水榭亭是九十年代後建的,亭子四周幾根中間粗兩頭細的「梭柱」、頂部碩大的斗栱,都是金元建築的風格特徵。
 邢軍正在觀察「梭柱」。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邢軍正在觀察「梭柱」。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山腳下的龍泉禪寺,最早建於明代。邢軍聽附近村莊的老人講起,這裏新中國成立前還曾有僧侶梵音。後來因年久失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完成過一次落架大修,還保留著建築的整體格局。
山上坐北朝南的都保殊廟,邢軍與它的緣分更深。五十多年前,這裏曾是市屬單位的退休職工養老院,年僅七八歲的邢軍曾隨家中長輩到這裏拜訪老友。他還記得那時候,屋內掛在頂上的葦簾作為隔斷,將正殿分割成幾個區域,裡面住著十幾到二十多位老人。唯獨不見牆上壁畫——邢軍想起當時,興許是為了讓整個屋子看起來更亮堂些,牆面上刷有「大白」,正殿東西牆的壁畫還不分明。
最近二三十年間,白浮泉與兩處寺廟經歷多次修葺。邢軍退休前在昌平區博物館下屬的文物管理所任職,其中也有多次修復項目經由他手,「具體修復是由專業人員去做的,修復期間我與同事也經常來,也為留存一些照片和資料。」
等到能清晰地觀察這組壁畫,時間已經來到了2020年。那年秋天,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由有壁畫修復資質的公司實施,壁畫表面的塗層被慢慢剝落修復,專業人員修補補充缺失的部分。殿內這幅最早畫於清晚期,記錄民間求雨故事的作品才重新完整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
 邢軍在都保殊廟觀察房頂,身後便是複原的壁畫。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邢軍在都保殊廟觀察房頂,身後便是複原的壁畫。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運河源頭來自歷史與文化的積累
在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尚未對外開放之前,龍山的廟宇和泉眼對於周邊村民來說,依然充滿神秘。邢軍解釋說,這是因為1956年,龍山一帶被市屬單位接管,與外界隔絕了一甲子。
 邢軍站在白浮之泉的牌匾下。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邢軍站在白浮之泉的牌匾下。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但對於這塊地界兒,昌平人並不陌生。白浮泉位於龍山,在十三陵盆地南側。山南曾有「鹿場」,養殖梅花鹿和烏雞,而南側的京密引水渠曾被當地村民稱為「運河」。
與邢軍一般年歲的附近居民,或許大多記得,鹿場的梅花鹿和在水渠中戲水的夏天。但泉畔與寺廟,還是因為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更多地被人關注。人們重提七百多年前的往事,講述古人由白浮泉引水,讓本沒有大河補給的元大都城得以與通州運河對接,延長京杭大運河的北線,成就曾經北京城積水潭內舳艫蔽水的過往。
1292年,元朝水利專家郭守敬啟動了引水工程。每當邢軍講述這一段故事時,他總會將時間軸拉得更久遠一些。
邢軍熟悉龍山,又已退休,時間充裕。因此在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開園前後,但凡有記者或是相關單位到訪,邢軍總是隨行。每次拾級而上,邢軍會在山頂平台的土地上尋覓一種細小石塊,它們有的不足拇指大小,上面展露著或深或淺的規則紋路,邢軍說這是「繩紋」。
 邢軍總會在地上尋找一些小石塊,並研究其歷史淵源。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邢軍總會在地上尋找一些小石塊,並研究其歷史淵源。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1957年,在龍山南麓,人們無意中發現了三座古墓,後被命名為「昌平白浮西周木槨墓」。出土的隨葬器物包括甲骨、青銅器以及陶器。其中,陶器上的繩紋裝飾在商周時期非常流行。邢軍認為,龍山頂部發現的陶片與這些古墓中出土的繩紋器物屬於同一類型,說明龍山周邊可能還埋藏著更多早期的墓葬,但由於時間久遠,這些墓葬已被毀壞,繩紋陶片隨棄土成了山頂的填充物。
在邢軍看來,這些過往歷史,是白浮泉故事的一部分。他提到古墓出土的青銅器中,尤以馬首、鷹首短劍為代表,「青銅是中原青銅文化時期的重要特徵,而動物的頭型則是草原民族所崇尚的造型。」代表著這裏地處草原民族與農耕民族交會處,曾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在這裏共榮。
 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里,邢軍對許多地磚都能說出歷史故事。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里,邢軍對許多地磚都能說出歷史故事。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儘管人們經常會談論郭守敬如何選擇白浮泉引水,強調其對元代大都城內運河的重要作用,但邢軍認為,白浮泉之所以成為引水地,正是因為這裏早已有著豐富的人文歷史和人類活動積澱,白浮泉畔從來不是古人與文化的未竟之地,恰恰是因為這裏的歷史深度與文化積澱,甚至是勞動力的積累,才使得這裏成為古人開鑿引水之地。
做歷史文物研究也是性格使然
聽邢軍講白浮泉歷史,是一件很放鬆的事。
在他的口述里,聽眾們幾乎聽不到晦澀難懂的專業詞彙,碰到實在避不開的術語,邢軍會掰開揉碎地解釋每一個詞組,告知是哪幾個字,該如何書寫,他像家裡的長輩,端不了一點專家的架子。甚至聽到有人稱呼他「專家」「老師」,他會趕緊不好意思地擺擺手,「可別這麼說,我這哪兒算得上。」官方資料中稱他是「昌平區博物館原館長」,邢軍聽了又會一口否認,說,「那是人家給面子才這麼寫的。」
 一個挎包,一壺水,組成了邢軍戶外勘察的裝備。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一個挎包,一壺水,組成了邢軍戶外勘察的裝備。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出生於1957年的邢軍,與歷史文物的緣分來得有些晚。直到1986年才進入原昌平縣文物管理所,當年成人高校開始了全國統一招生入學考試,包括夜大在內的成人教育開始快速發展。
1987年,邢軍進入當時的北京大學分校歷史系。雖是夜校,但專業課老師多是在行業內有名望的「老先生」——比如講青銅器的是著名考古學家杜廼鬆,講瓷器的是北京文物局研究院李宗揚,考古課的老師是趙福生。這是一段短暫,卻值得長久回味的時光。「每週六下了班就趕緊往學校跑去上課,夜大隻有三年,也確實學到了很多實實在在的本事。」邢軍說。
解讀歷史留下的信息,捕捉器物呈現的故事,邢軍喜歡這門學問。他說自己本身不擅長與人打交道,更不用說處理人際關係,所以很大程度上,選擇「向後看」,做歷史文物的研究,是自己性格使然。對於文物工作者來說,文物器具會「坦誠交代」它們所承載的歷史,而能收穫多少信息與素材,憑本事,也靠機遇。
在文物管理所任職的30年里,邢軍還曾先後參與張營遺址的發掘、京西工業遺產調查、長城資源調查以及多次文物普查。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與解讀記錄下來,也出版了《長峪城》《昌平文物普查資料彙編》《昌平博物館藏品識讀》和《石語昌平》等與昌平文物相關的書籍。
這些書籍基本是在2017年退休前完稿的,出了書之後,邢軍似了卻了幾樁心事。但要說起這些書的意義和價值,邢軍卻搖了搖頭。
「我的書沒什麼學術性,寫的就是我所能看見的事情。」邢軍說自己的這個行當,需要不斷地傳承,不只是技藝,也包括見聞,「寫成的東西,就好像一塊磚頭,放在這裏了。要說意義和價值,我意識不到,給後面研究的人,當本參考資料吧。」
又補全了一個歷史的角落
2024年是邢軍退休的第7年。
7年前,邢軍前腳剛一退休,後腳龍山便整體移交至昌平地方,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開工建設。邢軍開始為大運河白浮泉遺址文保工作提供建議以及文物保護利用思路。
他說,那時候自己對運河文化瞭解得還不算太多,只好邊補課邊探訪。邢軍的隨身挎包里,總裝著一台巴掌大小的數碼相機,相機右上角印著「40X」的光學變焦標誌,「退休那年買的,就是為了腳力所不能及時,能靠相機變焦把場景‘拉過來’。」相機拍攝的照片,最終都用上了,收錄進2022年邢軍編著出版的《白浮泉水入運河》。
 邢軍隨身攜帶了一個40倍變焦的小相機。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邢軍隨身攜帶了一個40倍變焦的小相機。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寫書的兩年,和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正式開放前後,這段時間里,邢軍跑白浮泉畔跑得最勤。有時是為了推進工作,有時是為了陪同相關人員介紹歷史,公園開園後的一段時間,他也來當過義務講解,給年輕的講解員傳授些經驗。做完這些自己能做的事,對於邢軍來說,「白浮泉」這個知識點也就「翻篇」了。
最近這段時間,他又開始專注於爬長城,看古建,「特別是對於長城的瞭解,這一塊知識我差得多,得多走走,補補課。」有時候週末,他還要跟著驢友去外省,67歲的人了,一天下來也要徒步十幾二十公里。
上一次邢軍來到白浮泉邊,還是一年多前的事。
今年夏秋之際,再來公園,邢軍還會惦記龍山西北側的「鷺影台」。每年四月,鷺鳥會按時北遷,回到龍山腳下,開始新的繁育週期。幾年前,在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建設的推進會上,邢軍曾建議保留這片可供白鷺和灰鷺繁衍築巢的林地,到現在,這裏已經成為昌平觀賞鷺鳥的最佳點位之一。
公園里許多點位的安全員都是「老人兒」,認識邢軍,都會和他打招呼,知道他是專家,還要拉著他問一些遊客經常提的問題。邢軍站住腳,聊起來三五分鐘都打不住。年紀大了,上週末出去徒步的具體路線可能不記得,但人問他,寺廟建築的年代,泉畔龍首的尺寸,邢軍回答起來從未含糊。
走著走著,他說起了都保殊廟正殿的屋頂。在脊檁與檁枋的平面下,還保存著幾行明代的題字:「香火地五十畝山,果樹兩千餘株。」這些文字記錄了都保殊廟一次修繕的情況,還提到修繕廟宇時購置的財產。2002年都保殊廟進行落架大修時,邢軍和他的同事們意外地發現了這些題字。後來,廟頂重新修補了天花彩畫,這些題字連同脊檁又重新被封存於廟頂之下。
 邢軍在都保殊廟前。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邢軍在都保殊廟前。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邢軍說,這可能是他多年來最令人欣喜的發現。原本沒有人會想到,在脊檁之上竟藏有這樣的文字,正是那次大修才讓這些珍貴的歷史痕跡短暫地重見天日。邢軍將這個發現寫進了關於白浮泉的書中,「從事我們這行,最大的願望就是多發現、看到一些來自過去的文字和痕跡。」在他看來,這彷彿意味著,在自己所能觸及的歷史中,又補全了一個或許微不足道但真實存在的角落。
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