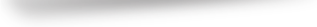千古詩文里的鄱陽湖美到你了嗎

在江西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有一片令無數人魂牽夢繞的水域,這就是江西的母親湖鄱陽湖。為探尋這片湖水的出處,我們需要遠赴一萬年前的「番」地。
那時候,祖先們尚在混沌神話中漫步,那片區域,還是「荒服之地」。直到最近一次亞冰期結束,廬山的「起立」與旁邊盆地的「臥倒」,如盤古開天,發育出鄱陽湖地域的雛形。


開場詩:
洲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
《尚書·禹貢》記有「彭蠡」,《漢書》則記為「彭澤」,都權作這片湖水的乳名。
時光的步伐本質上就是水的形態,川流不息,勢不可擋。三國時,彭澤湖水逐漸南侵,至南朝時湖水直抵豫章,鄡陽和海昏兩縣一路被淹。「沉海昏,起吳城」的歷史畫面,對應的並不是1400年後的那句閩南歌「人生好比一場波浪,有時起有時落」,而是坐在船頭彈琴長嘯的南朝詩人謝靈運。
雖然鄱陽湖還待字閨中,但大謝的這首《入彭蠡湖口》為這湖水的敘事開了個氣象開闊的序曲:「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詩寫於元嘉八年,是個值得存記的時間刻度。
謝靈運當時並非以詩人的身份赴彭蠡湖採風,而是一個由京城建康外放臨川的官吏在跋涉,命運與情緒的疊加註入寬闊的湖面,才自然恢復了其詩人的真身。兩年後,謝靈運便以「叛逆」罪死在「元嘉草草」的桑治文帝劉義隆手中。所幸,這位中國「山水詩派」鼻祖的地位千古聳立,他為這片湖水書寫的開場詩千古在場。
 鄱陽湖濕地。歐陽衛民/攝
鄱陽湖濕地。歐陽衛民/攝
盛唐潮聲:
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
繼續,我們跟上湖水的腳步。到了隋代,湖水逼近鄱陽山,相遇就這樣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產生了,湖水的身體已然成年,鄱陽湖之名塵埃落定。無論真相如何,我們相信大抵總是遇見了鄱陽之名的地界,這湖水才得名「鄱陽湖」,而不是其他名字。
而鄱陽湖這個名分,在戀舊的文人筆下還得熟悉一陣子。好在接下來氣象萬千的盛唐不會顧及這些枝葉,豐腴的鄱陽湖似乎正合那個時代的審美,張九齡、王勃、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紛紛登上各自人生的舟楫,過江州、入彭蠡、望廬山。
真不知當年,坐著搖晃的帆船駛入鄱陽湖的浩渺空間,詩人的心裡是否也會發慌。
去交趾探親的青年才俊王勃途經鄱陽湖,在南昌被邀請參加宴會。端坐在臨江渚的滕王高閣上,聽歌觀舞,自是不慌;提起筆來書寫一篇華美宏闊的駢文,自是不慌;待「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千古名句出,都督閻公已經慌了。
而王勃的「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不僅讓鄱陽湖有了比詩歌更宏大的敘事方式,也給85年後才見鄱陽湖的李白帶來壓力。面對這滔滔湖水,李白恍惚又回到當年他站在黃鶴樓崔顥題詩下的境地。不過,此時的「詩仙」已經是流放夜郎遇赦後的一個六旬老人,他的詩意依然宏大,但已接近尾聲:「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下尋陽城泛彭蠡寄黃判官》)。
 成群的越冬候鳥在鄱陽湖湖口鞋山水域上演壯觀的「鳥浪」奇觀。圖源湖口縣融媒體中心
成群的越冬候鳥在鄱陽湖湖口鞋山水域上演壯觀的「鳥浪」奇觀。圖源湖口縣融媒體中心兩年後,李白送從弟李昌峒赴任鄱陽司馬,他又一次闖入鄱陽湖的道場,氣宇竟然勝過前詩:「桑落洲渚連,滄江無雲煙。尋陽非剡水,忽見子猷船。飄然欲相近,來遲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我們似乎可以想像到詩成之後老「詩仙」臉上的得意,他的詩,怎麼可能配不上一片湖水!
沒料到的是,過鄱陽湖登滕王閣都不曾發慌的王勃,次年從交趾返程時竟然溺水而亡。史料記載:「渡海溺水,驚悸而死。」
沒料到的是,送昌峒弟的那年,「詩仙」也離世了。傳說很多,但大都與酒、月、水有關。聞一多有一首寫李白之死的長詩,把孤獨與月光融進酒中,釀出了一個只屬於李白的審美表達。
所幸,古代優秀的兩位文人在離世前都與鄱陽湖有了惺惺相惜的會面,有了宏闊真誠的交待。所幸,在兩位巨星筆下,鄱陽湖一出場就是宏大敘事,寬袍大袖,石破天驚。
而對於此湖,還有一個詩人值得記住——晚唐的貫休,他的詩《春過鄱陽湖》首次將鄱陽湖的名字公之於眾。
 鄱湖鶴韻。葉學齡/攝
鄱湖鶴韻。葉學齡/攝
宏闊敘事:
鄱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
當然,翻過了隋唐的鄱陽湖會以它的方式繼續等待,等待後面的文人,後面的帝王將相與漁樵耕讀,甚至鱗潛羽翔與蒹葭蒼蒼。
鄱陽湖是一泓碧水,更是一艘巨輪,航行穩健,從容淡定。鄱陽湖又像一位宰相,宰相肚裡好撐船,於是許多船和宰相踏湖而來——漁船、商船、戰船,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鄱陽湖的敘事方式從不單一,觀照事物的眼光永不迷離。
除了等待與迎候,鄱陽湖也主張派出使者。洪邁出發了,他的《容齋隨筆》中有近30篇書寫了饒州鄱陽,表達了作者濃鬱的桑梓情結。薑夔也出發了,「長與行雲共一舟,零落江南不自由」,帶著鄱陽湖的生命氣質,去了五湖四海不歸。
對於元末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擺開的龐大陣仗,鄱陽湖的方式只有負重、隱忍。而與洪武占士推行的「江西填湖廣」移民活動中載滿瓦屑壩移民的船隻相比,從昌江、鄱陽湖一路運著景德鎮瓷器的商用貨船,才是鄱陽湖內心暢快淋漓的方式。
在煙波浩渺的鄱陽湖上,難道除了戰爭、奔波、魚米、瓷器,就沒有浪漫的愛情?
當然有!浪漫的鄱陽湖人不打魚不打仗的時候,就去寫詩;不寫詩的時候,就去編織愛情。鄱陽湖畔的望夫岡故事,忠貞癡情的梅小姐化成一座永恒的山岡,就是中國最早的愛情傳說——早在1700年前,就被東晉史學家干寶收集到他的傳世之作《搜神記》中,更被當代的學者們譽為「對世界文學的貢獻之一」。
 鄱陽湖邊最溫柔的荻。李哲民 /攝
鄱陽湖邊最溫柔的荻。李哲民 /攝
大美鄱湖:
長江之腎,候鳥天堂
今天的鄱陽湖,中國最大的淡水湖,已然是我們地球母親懷裡一個無法忽視的自然體系和底蘊深厚的人文世界。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片平淡的水域,平淡卻見證自然的高明,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被自然的湖水演繹得貼切無比。
於萬物而言,鄱陽湖的方式其實就是自然的方式,萬物都在踩著自然的節奏,或流動,或生長,或飛逝……我們需要在這種節奏中逐漸找到自己的步伐,追尋真正眷戀的心的家園。
早春,江南綠漸被鄱湖紅搶去風頭,成片的紅花草在鄱陽湖濕地上抹了濃烈的俏色,彷彿給濕地的臉龐打上胭脂。氾濫的桃花汛是夏季的先鋒,而長江的反哺更讓湖水誌得意滿。秋水也滿,只在王勃眼中的盈盈一水間。
但秋水終究有些黯然神傷,一路陪著蘆花荻草搖曳,望大雁南歸,濕地盡顯秋草枯黃,如塞上般蒼茫。隆冬,無數珍稀的候鳥們從遠方相約而來,這裏的水域已經瘦身成功,在最淺最美的春晚舞台上,人類只配做觀眾,觀望那萬羽翔集的仙境,也觀望自己迷離已久的內心。
等待春又來,汀洲漸綠,候鳥北飛,鄱陽湖的宏闊敘事將以美好如斯的方式一直進行下去……(張新冬)
 直衝宵漢。葉學齡/攝
直衝宵漢。葉學齡/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