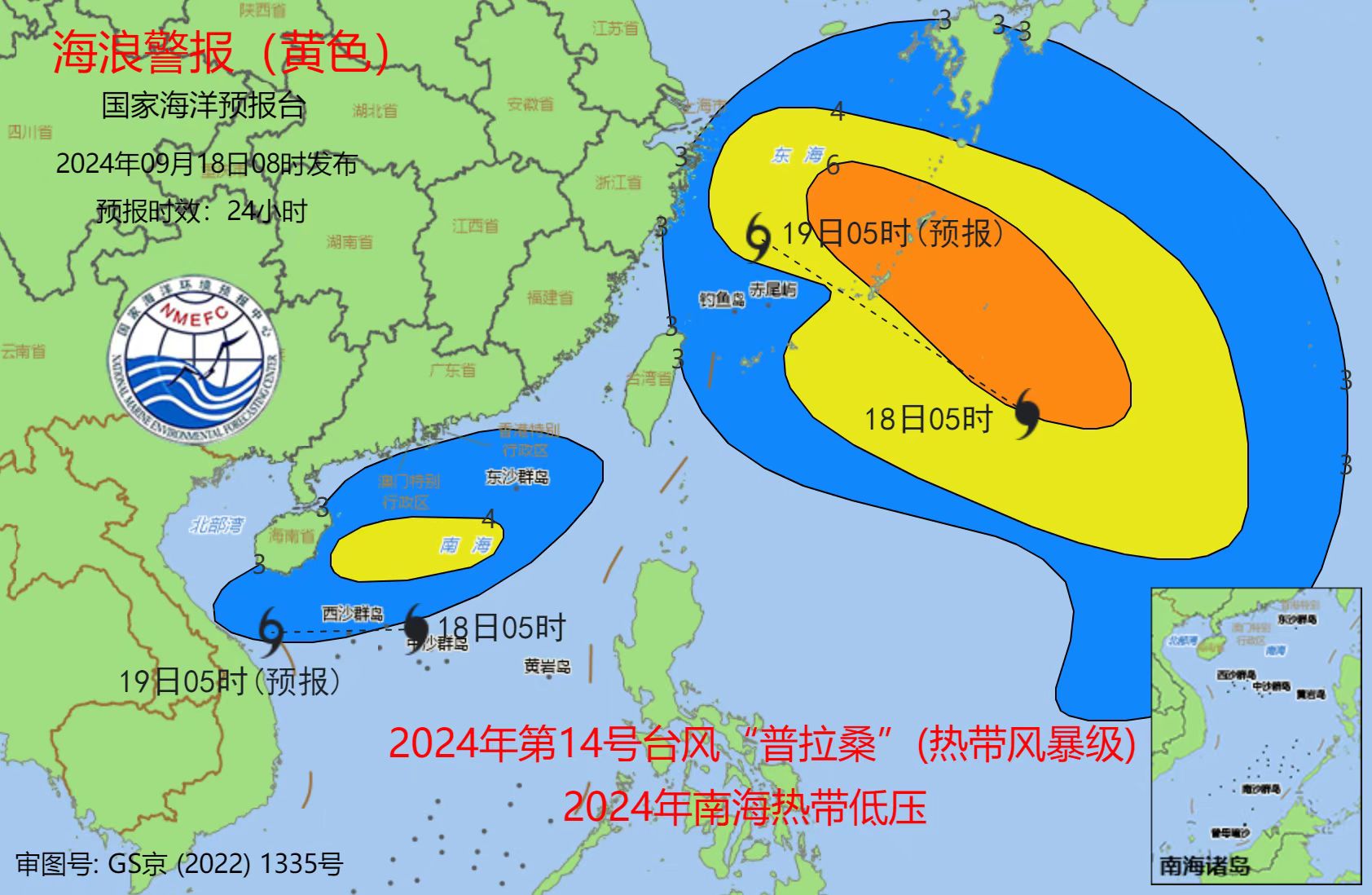對話《雪迷宮》編劇:為了這部劇差點翻爛《禁毒學導論》
正在優酷熱播的《雪迷宮》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講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東北,禁毒警察開展禁毒工作的日常,展現了無名英雄有血有肉的鮮活形象。該劇編劇張鳶盎、麥利雅斯此前曾經創作過《冰雨火》等緝毒題材作品。在《雪迷宮》中,除了展現禁毒警察和犯罪分子鬥智鬥勇,也用了大量篇幅去描繪禁毒警察的日常生活。日前,張鳶盎、麥利雅斯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希望觀眾看到一些生動鮮活、落地一點的公安英雄,他們也是普通人,這些人有朋友、家人、愛人,也會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去操心,「他們的生活也充滿了喜怒哀樂,和我們沒有什麼不一樣。但當他們穿上警服走進禁毒戰場的時候,卻能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兇惡的罪犯,守護普通老百姓千千萬萬人的生活。這是他們身上最動人、最閃耀的地方。」

黃景瑜飾演警察鄭北。
刑警也需要用自己幽默的方式平衡情緒
新京報:近些年來禁毒題材的影視作品很多,但其中大多是展現近當代,《雪迷宮》為何選擇集中展現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禁毒故事?
張鳶盎:在整個九十年代,冰毒的犯罪集團是日益猖獗的。劇中選定的1997—1998年的時間段也比較特殊,1998年8月公安部剛剛成立禁毒局。1999年9月在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設置了禁毒學的專業方向,這時候才招收了國內第一批禁毒專業的本科生。劇中故事1997年在禁毒局成立的前夕,很多地方的警察是非常缺乏禁毒相關的專業知識。對於毒品案件的偵破是摸著石頭過河,對他們來說特別難。剛開始,禁毒理論的薄弱和禁毒形勢的嚴峻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反差,這是我們調查過程中發現禁毒工作最大的難題之一,所以我們特別想把故事聚焦在特殊的時間段,去集中寫一寫這些困難,以及禁毒英雄們英勇無畏的精神。還有就是,九十年代刑偵手段比較原始,沒有辦法通過像監控攝像、手機定位等現代科技去輔助破案,就更需要一線刑警最大程度動用腦力和體力對抗犯罪分子,所以也會呈現出比較直接的戲劇衝突。
新京報:劇中將故事背景設定在東北的虛構城市哈嵐市,其中又設置了一個來自南方的毒品專家,這樣的地域搭配是出於什麼考慮?
張鳶盎:近幾年來禁毒題材影視劇基本都集中在金三角地區,或者滇緬邊境這些地方,觀眾是比較少能看到在北方禁毒前線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我自己是一個東北人,我們編劇團隊3個都是北方人,有2個是東北人,所以對家鄉這一片土地是更感興趣,也更有創作熱情的,這是(故事背景)選擇東北的原因之一。在重案組設置里加入一個來自花州的毒品專家,不只是為了製造南北差異的戲劇性,也是為了讓本身劇情合理化。對於1997年哈嵐的警察來說,一個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和冰毒打過交道,帶著非常先進經驗的廣東專家是必不可少的。
新京報:在你看來,劇中的「東北元素」主要展現出來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氣質和風格?
張鳶盎:我看網上有一個說法,叫「東北不養i人(內向的人)」。其實本身沒有那麼誇張,但東北人確實有獨特幽默感。因為東三省緯度高,冬天特別長,基本上大家是沒法出門的,所以只能窩在家裡嘮嗑,在炕頭上說訪問節目。再加上東北方言喜歡用一些擬聲詞和萬能動詞,很普通的一句話說出來也自帶喜感。我們在東北地區去採風交流時,刑警們在講述當年那些大案、要案破獲的過程中,會不自覺流露出這種幽默感,可以把刑警工作講得生動有趣。他們當年經歷的那些故事是驚心動魄的,但現在談起來都是談笑風生的。我們當時也明顯感覺到,即使再勇猛的警察,他也不是銅牆鐵壁,跟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尤其是在禁毒前線特別凶險的戰場上,他們隨時可能出現流血犧牲,他們也需要用自己幽默的方式平衡情緒。

刑警們日常對話自帶喜感。
新京報:與其他地方相比,那個年代東北的刑警有什麼明顯的特徵?
張鳶盎:我們在寫故事時有一個想像,會覺得東北警察特別硬漢、硬核,很凶悍。但真正去採訪的時候發現很多老刑警,尤其是經歷過九十年代一線工作的刑警,他們反而很和善,有他們自己的氣場,同時也很有幽默感。他們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能夠用樂觀、積極陽光的態度消解一些苦痛,這也是我們在整個創作時比較著重去渲染的一種氛圍。
新京報:除了展現禁毒過程,劇中加入了很多刑警們生活化的日常,看上去工作和生活基本是融在一起的?
張鳶盎:因為禁毒警本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業,不像大多數人上班打卡、下班回家。對於他們來說只要有毒情、有案件發生,他們隨傳隨到,所以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很緊密地捲在一起。這也是我們在故事里加入很多日常生活的原因。

該劇加了很多生活化場景。
有一本書叫《禁毒學導論》,我們快翻爛了
新京報:在採風過程中,有什麼事情留下了深刻印象?
麥利雅斯:我們採訪了幾個老刑警。其中有一個當年的刑事警察,負責大案、要案、兇殺案,但他看見賣毒品或者販毒的小罪,也去抓。還有一個警察,他當年是掃黃的,他說遇到了(販毒)也會抓。當時他們是不分的,販毒也是刑事犯罪,他們全一鍋抓,沒有專門的禁毒警察,刑警或者民警,只要看到犯罪行為就去抓。我們也寫過現代的禁毒劇,比如《冰雨火》,都是有專門禁毒的單位,但當年沒有。作為編劇來說,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點,所以我們就深入瞭解了一下在禁毒局沒有成立之前,當年遇到毒販是一個什麼情況。
新京報:劇中有比較緊張的禁毒工作,也有喜感比較強的日常生活,如何形成統一的風格?
張鳶盎:觀眾對懸疑劇和刑偵劇的節奏要求比較高,希望劇情不要磨磨嘰嘰,能快速地強情節推進。但與此同時,也能感受到很多觀眾的日常工作、生活壓力很大,劇情如果過於有壓迫感,沒有喘息的時間也會看得特別累,一個懸念沒有接上,他可能就棄了。這兩種需求怎麼融合我們思考得比較多。我們加入了很多生活戲,跟破案、懸疑強情節節奏做一個對衝,讓很多比較緊密的劇情堆積在一起的時候,觀眾能在中間有一個喘息的時間。同時也加入很多喜劇元素,大家再看強情節,去看快速推進的時候,也會覺得更鬆弛,更輕鬆一些。
新京報:劇中展現了當時對比指紋、恢復指紋等刑偵手段。也包括一些化學知識、毒品知識的介紹,在創作時做了哪些案頭工作?
麥利雅斯:主要還是採風,去專業的禁毒單位諮詢刑偵人員、禁毒警察,包括當年他們對禁毒方面知識是怎麼獲取,怎麼學習。我們也會買一些專門的書籍去看,比如說有一本書叫《禁毒學導論》,我們已經快翻爛了,這個也是警察同誌推薦的。
張鳶盎:因為先有了人物基本關係和故事框架,我們在採風之前從各種專業書籍,包括大量相關案件的新聞里去找素材、找靈感,選取一些有原型的真實案件。我們帶著這些框架再去採風,去和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一線禁毒警察聊,這些案件我們理解得對不對,這些細節有沒有出入。這個過程中他們又講述了很多在東北發生過的,他們經歷過的,和禁毒相關的案件,我們再添加到更多劇情里的細節中。我們也瞭解到很多真正的毒販,尤其是所謂大毒梟,他們不是我們刻板印象里的大佬風範,一出場就走路帶風,他們很多時候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走在路上是可以非常完美融入到所有普通老百姓里的,對於禁毒工作者來說是很難辨別的。
張雪瑤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女性角色
新京報:雖然是九十年代的故事,但讓當下的觀眾能夠共情的部分有什麼?
張鳶盎:比如張雪瑤這個角色,她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女性角色,我們設定她曾經是被英雄救美過的。但她沒有因為被「英雄救美」而愛上「英雄」,反而說我要當這個英雄。我覺得比較符合當下女性觀眾獨立自主的表達。其實在九十年代,女刑警出外勤相對少一些,除了坐辦公室,更多是化裝偵查這一類的工作。張雪瑤作為一個武力值很高的角色在專案組里出現,她有一個綽號叫「瘋狗」,這個角色很渴望用自己的能力去懲罰、懲治犯罪分子。再比如鄭北這個人物,他就是有血有肉、有勇有謀,但特別沒「溜」的一個人,我們把鄭北設定在一個相對圓滿的家庭中出生。包括他的父母是普通的下崗職工,重新創業開小飯館,開雞架店,他妹妹也活潑可愛。他的生活中有真實的、普羅大眾能感受到的生活煩惱,而不是苦大仇深的感覺。

張雪瑤是個人設鮮明的女警察形象。
新京報:在一些刑偵懸疑劇中,反派的張力和受歡迎程度可能會壓倒正面角色。創作中,應該如何保持正反角色之間的平衡?
張鳶盎:一旦這個故事中存在對抗,有所謂的正派、反派,這個難題就存在。我們希望反派聰明厲害,因為如果反派很弱,會顯得正派也很弱;但反派如果特別聰明厲害,又會擔心他是不是壓過正派,這是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創作難題。作為編劇能做到的是去控制講述的視角,本身《雪迷宮》不是單線敘事,有刑警、專案組這邊破案的過程,同時也有毒販、反派,他們一些作案的計劃變動,兩邊都有描寫。但我們更希望觀眾代入到專案組,以鄭北為代表的團隊視角去撥開整個故事的迷霧。我們如果想做出懸疑點,那就要控制反派行動的篇幅。如果我們直白地寫反派是怎麼犯罪、怎麼銷贓、怎麼銷毀證據、怎麼交易,對觀眾來說也不存在懸念了,因為所有的真相都看到了。讓觀眾儘可能感受到一些懸疑,去享受破案的過程,視角肯定不會特別多放在反派如何作案這方面。
新京報:在劇情展開以及人物搭建上,創作中會有一些什麼新的思考嗎?
張鳶盎:不管好人壞人也好,可能都經歷過一些傷痛,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因此而去選擇犯罪。犯罪更多的是個人選擇,而不能把原生家庭或者童年創傷當成自己的藉口,我們希望這方面能有探討引發觀眾的思考。包括我們的主角,警察或者一些好人的角色,他在整個劇情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思考正義和邪惡的對立關係,也在思考一些執法的方式等。
新京報記者 劉瑋
編輯 佟娜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