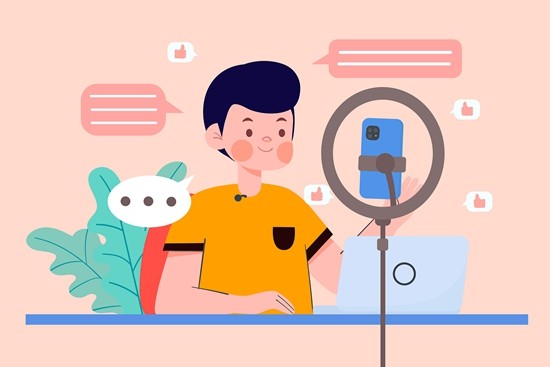詩歌的江河,湧向民族的心靈地平線
 視覺中國供圖
視覺中國供圖中國傳統詩歌的核心要素中,河流始終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不必說謝靈運與王維這樣專意從事山水題材的詩人,任何一位能夠在科舉考試中規範寫作應製詩的士子,「兩岸曉煙楊柳綠」的蒙書基因,都將在其寫作生涯中長久地發揮作用。
「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是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設計的理想寫作狀態。信步可及而無須刻意攀援的河濱水湄,不僅是詩人吟詠的對象,更是創作的現場。他們的目光伴隨唼喋的河豚感受著春江水暖,在無人野渡中發現橫臥的扁舟,透過潮落夜江的蒼茫搜尋彼岸的兩三星火,但最終,往往凝聚於河流指引的遠方——這是河流中泓線與上下遊地平線交彙的地方。
遙遠的江河源頭,是杜甫逝去的理想
公元766年,偉大的詩人杜甫徘徊在今日三峽邊的夔府孤城(今重慶奉節),不盡長江是他最常見的風景。此時,距離他在成都平原體驗「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的閑適已隔有年,而在江漢平原沉浸「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歲月則尚未到來。週遭峻拔的叢山,每每攔住他順著江水而逐漸遠移的目光,卻攔不住他追隨江水奔向遠方的心緒。一個關於木筏漂流的典故便被寫入《秋興八首》:「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南朝文獻《荊楚歲時記》記載,漢武帝命張騫到西域去尋訪黃河的源頭。張騫在黃河上乘木筏(浮槎),漂流一月後到達一處城郭,看見河邊有一女子織布、一男子飲牛。後張騫回到中土,拜訪佔卜者嚴君平,被告知所到達之地是天上之銀河,遇見的二人就是牛郎與織女。
這一傳奇故事在唐代有著巨大的接受度,黃河與銀河的聯繫在文學作品中被反復強調,如李白《將進酒》詩中「黃河之水天上來」、羅隱《黃河》詩中「解通銀漢應須曲」,都由此生發。不過,唐人在用典中似乎忽略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缺陷:張騫尋訪河源理應逆流而上;而在這個沒有縴夫的故事里,木筏只能順河漂流。
事實上,中國人對於河流的地理學認知,很早就達到了極高水平。在甘肅天水放馬灘墓群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地圖實物中,公元前300年前後的古人,就能於木板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渭河上遊各河流的分佈情況。公元6世紀,酈道元寫作的《水經注》中,對全國河流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令人歎為觀止。不但記載河流數量高達1300多條,不同河段的清濁、緩急、寬窄、豐枯等細節,都有明確記載。
只是,古人的河流知識在空間方面並不均衡。雖然在理性認知中,唐人不會真以為黃河與銀河連通,但黃河源頭的確切位置則模糊不清:究竟是《尚書·禹貢》中的「積石山」,還是《山海經》中「崑崙山」,抑或是唐人曾親自到達的「星宿海」,長期沒有定論。這無疑使黃河源頭蒙上某種神秘色彩,「張騫浮槎」的浪漫主義要素,也更容易被人所津津樂道。
《秋興八首》是杜詩名篇,但「奉使虛隨八月槎」一句的確切含義眾說紛紜。結合杜甫親眼所見與唐人的河源認知,或許可以試作如下理解。
有著強烈經世情懷且一度接近中樞的杜甫,只能困守在遠離長安的西南一隅「每依北鬥望京華」。杜甫其實不害怕偏遠,只要能繼續為君王效力,哪怕是受朝廷指派(奉使),像張騫那樣乘坐木筏遠至江河源頭;但在現實的高江急峽中,杜甫絕對看不到一隻可以自行逆流而上以達江河的木筏(虛隨八月槎)。神話破滅,江河的遠方源頭遙不可及,「致君堯舜上」的理想也只能任隨江間波浪,漸行漸遠。
秦觀的相思,沿著郴江付予誰
晚年杜甫的心境與筆力,一如深秋的江水,沉鬱浩蕩,浸透寒冷。同樣的寒冷,也出現在300年後的湖南,湘江二級支流郴江的水波中。這大概是一個初春天氣,從東京(今河南開封)被一路貶黜至郴州的才子秦觀,寫下著名的《踏莎行》: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秦觀逝後,他的老師蘇軾讀到「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在句後親書:「少遊(秦觀字)已矣,雖萬人何贖。」這兩句詞由此著名。現代讀者無疑能感受到蘇軾對弟子的讚歎傷感之情,但這兩句詞究竟妙在哪裡?近人唐圭璋謂其「情韻綿邈、令人低徊不盡」,仍覺費解。
倒是一個古老而俚俗的故事,對我們的理解有所幫助。桑治人筆記雲,秦觀被貶赴郴州途中路經長沙,迷戀一妓,但因害怕被舉報彈劾,不敢攜至郴州,只能借郴江湘水送去深情。為經典詩文編製俗豔「本事」,是某種源遠流長但未能脫離低級趣味的傳統,一如要把《洛神賦》說成《感甄賦》。但對《踏莎行》的此種解釋路徑,卻正確地指出前人在河流與情感之間所建構的一種經典關係:河流是情感的載體,情感沿著河流奔向對方。
借助天然江河與運河,中國很早即形成連接核心政治經濟區的發達水運網絡。每個人或者書信,皆可經由天然或人工河道,達至親人戀人友人的身邊。秦觀在詞中提到的「驛寄梅花,魚傳尺素」,即指書信。折梅花以寄遠人、托魚雁以傳書,這是漢魏六朝時期已經成熟的著名掌故。
把書信放在郴江之前,不禁令人想到唐人雍陶的故事。雍陶是成都人,恃才傲物,對自己的親人疏於問候。其舅李敬之寫詩譏諷道:「地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這也從側面反映,在唐人眼中,水脈構成的物理聯繫是相當可靠的。
秦觀的貶所郴州離衡陽不遠,《踏莎行》的下半闋或許可以這樣理解:「我居住在偏遠的地方,想給遠方的親朋寫封信,其中滿滿都是我無盡的遺憾與愁緒。這裏所幸還有一條郴江,應該能把我的心意傳遞出去吧!可是,還有親朋能夠或願意收到我的信嗎?」
更早一些,蘇軾已有「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的名句。秦觀顯然比他更進一步,彷彿在說:「我有相思,可以流到,可誰在那裡呢?」可見蘇軾所對《踏莎行》結尾二句的欣賞,是一種河流與心靈高度契合後無法排遣的密密愁緒,並不是王國維所批評的流於「皮相」。
在「廣陵客」的指尖,淮水展開千里雲山
杜甫看不到遙遠的江河之源,被朝廷遺忘在蕭森的巫峽;秦觀看得到郴江在遠方彙入湘水,卻依然被拋棄在迷濛的霧夜。無論看見或看不見,河流的遠方除了感傷孤獨以外,能安放一種從容靜謐乃至優雅閑和的情緒嗎?不妨讀一讀李頎的《琴歌》:
「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木風入衣。銅爐華燭燭增輝,初彈淥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唐代詩人中,李頎是描寫音樂的高手,曆代皆激賞「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明清之際戲劇家、評論家黃周星謂其「妙處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至於本文的結尾兩句,曆代著墨不多,一般以為作者要到千裡外的淮河流域公幹,聽此曲後頓生歸隱「雲山」之意。
此種解釋不能令人滿意。此詩運用一系列形象化的方案,運用明暗、冷暖、動靜等方式極寫琴韻之悠揚,處處緊扣於琴,已經水乳交融、渾然一體,不當於收束處忽然抽離。
作為當代人,我們大可以借助我們時代的文藝方式提出一種新思路,即末二句實為一種「音畫」。在這「音畫」中,「奉命出使」的並非詩人自己,而是淮水本身。在琴聲的驅使下,清澈的淮水緩緩東行,兩岸的千里雲山如畫卷徐徐展開。這畫捲開啟處並非地理上的淮水源頭桐柏山脈,而是撫琴者「廣陵客」的指尖。
為什麼詩人用淮水而不是其他江河呢?這大概是為了遷就「廣陵客」的典故。嵇康臨刑前彈奏《廣陵散》的典故十分著名,以此來類比琴師,足見技藝高超。地理上的廣陵(今江蘇揚州)長期被認為是淮河南岸的重要都會,即所謂「淮左名都」。「廣陵客」的琴聲中流淌著淮水,字面意義極為貼切。淮河流域雖多平原,但「淮南木落楚山多」也是唐人共識,秀美的風景當得起「雲山」之謂。
在沒有飛機與攝像機的時代,由雪山冰川涓滴交融的源頭,到彙入大海時黃藍相隔的尾閭,以及俯瞰視角下曲折蜿蜒的河道,是大多數先輩不可能目睹的河流遠方。令我們驚異的是,先輩們用他們瑰麗的想像、豐沛的情感、高卓的才思、細膩的筆觸,超越了他們時代感官與技術的局限,不斷追尋河流的遠方、拓展詩意的遠方,為我們留下了比真實的遠方更為深廣的文化空間,足以承載個體與家國、柔情與理想。
河流與詩歌,是定義我們民族心靈地平線的重要坐標。
(作者係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張景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10月2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