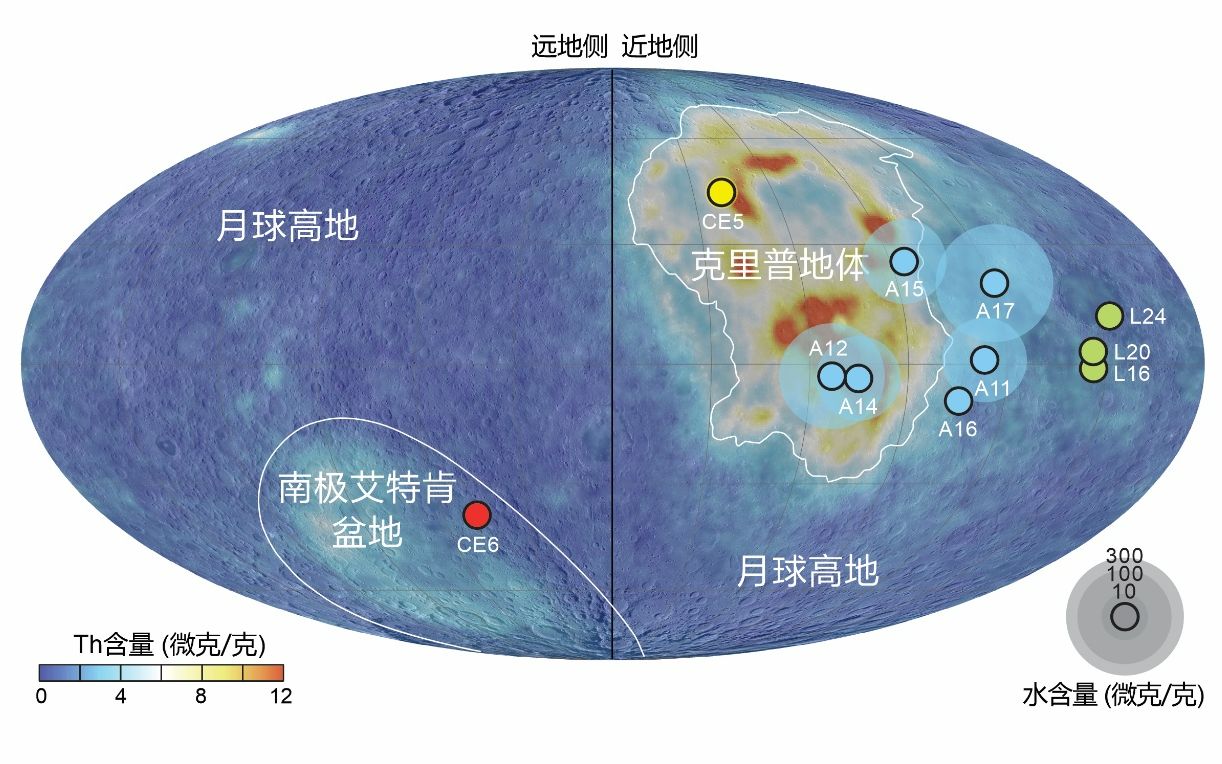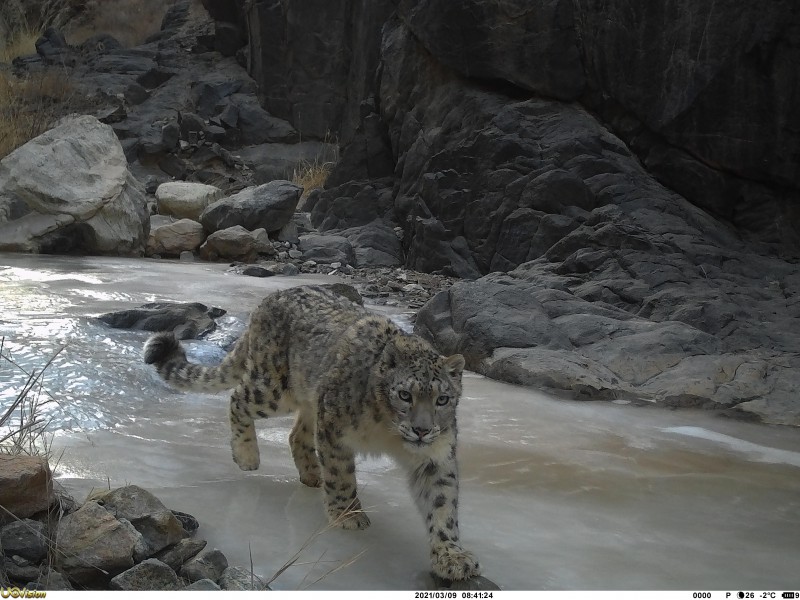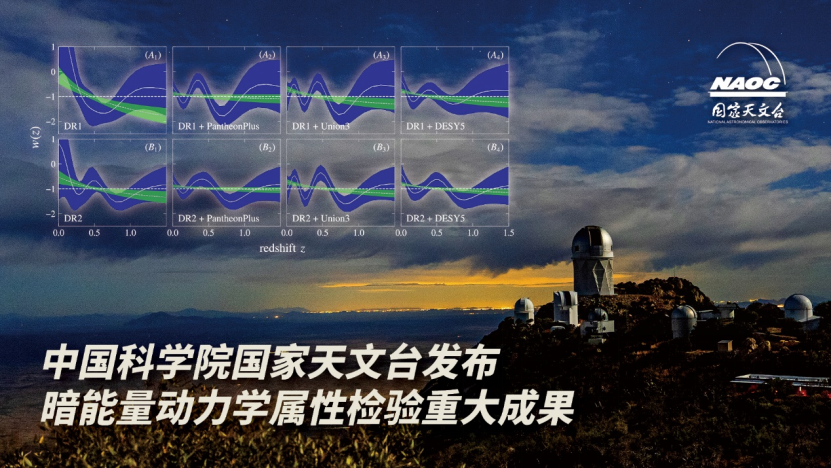陳繼明:站在敦煌面前,起一個自己的「空中樓閣」
 陳繼明。受訪者供圖
陳繼明。受訪者供圖 小說《敦煌》書封。受訪者供圖
小說《敦煌》書封。受訪者供圖寫小說是一場探險。
——————————
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敦煌都不只是一個地名。每個中國人讀到這兩個字,內心都會升騰起無限的敬畏和感喟。它的絢爛輝煌、破敗落寞和重生永恒,都帶著巨大的隱喻。這種隱喻讓作家既無法抗拒「敦煌誘惑」,又不敢貿然涉足。
陳繼明決定開始自己的敦煌探險。
小說《敦煌》以唐代貞觀年間為時間背景,以李世民的禦用畫師祁希為主人公,寫王朝征戰、凡人開窟、宮廷畫師造像;以瓜州、沙州為空間背景,書寫河西走廊上吐穀渾人與漢人的融合;以漢人村莊令狐家的動盪,書寫盛世到來之前,普通人的犧牲和反抗。
「我不太願意寫已成結論的東西,我想讓寫小說成為一個探險的過程。我把敦煌當鏡子,也把藝術當鏡子,為的是照一照人間的圖景,照一照男男女女的愛恨情仇。」陳繼明說。
陳繼明是甘肅天水人,但從2007年開始就在廣東珠海生活,他的上一部長篇小說,是寫華僑「下南洋」的《平安批》。從西北到東南,從大漠到海洋,無論是生活環境,還是創作題材,跨度之大,他似乎都能出入自如。
近日,陳繼明在北京舉辦的《敦煌》新書發佈會後,接受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
中青報·中青網:是什麼契機讓你創作長篇小說《敦煌》?
陳繼明:早在7年前,長篇小說《七步鎮》出版後,我就在責編的建議下,開始考慮寫敦煌。《敦煌》中的令狐昌,也是《七步鎮》中一個尚未展開的人物。
30年前,我就接觸過吐穀渾的故事。我是甘肅天水人,再具體一些,我們縣現在叫甘穀縣,以前叫伏羌縣。吐穀渾人從陰山往西遷徙的過程中,第一站到了隴山山脈的腹地,就是我們那一帶。我在查閱甘穀的文史資料時,很容易就看到了吐穀渾的故事。但我一直沒寫,所以當責編提出這個建議後,我就把吐穀渾的故事也放了進去。
中青報·中青網:敦煌題材的圖書非常之多,類型豐富,知識的、研究的、非虛構的……你的《敦煌》有什麼不同?
陳繼明:在開始創作之前,我定下兩個「不寫」。第一,不直接寫藏經洞的故事,因為這類故事被寫得太多,難以出彩;第二,不把敦煌當作圖騰來寫,我想寫一個新的敦煌,而不是一個已經成型的、不容想像只能叩拜的敦煌。
同時,我定下了兩點「要寫」。第一,要寫人。過去寫敦煌的小說,對人的關注不太夠。在敦煌面前,人不能渺小,而是應更偉岸,所以,要在這部小說里恢復「人」的重要性。第二,要好好寫一寫動物。馬、駱駝等動物在小說中都不被看作人的工具,而是成為小說的角色,和人平起平坐。小說中,鳴沙山的正面是千佛洞,而反面是一窩狼,狼窩旁邊又是羊塚。強和弱、善和惡、生和死、神和魔,就是這麼在敦煌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中青報·中青網:敦煌有各色各樣的人,為什麼選擇畫師作為主角?
陳繼明:這是一個技術問題。我想進入敦煌的內部,進入石窟開鑿前的年代,誰開窟的、為什麼開窟、請誰做畫師、畫什麼內容……我想寫這個過程,那麼,畫師就是一個最好的視角,可以把各種元素以他為中心來展開。此外,畫師來自長安、來自宮廷,這部小說基本結構的一部分,是關於廟堂,那麼畫師看敦煌的視角,也意味著廟堂看世界的方式。
中青報·中青網:為什麼在小說中設置了一條當代的故事線,還出現了第一人稱「我」?
陳繼明:我很明確,我不想將這本書寫成一部歷史小說,我希望小說有當代感,就把「我」寫進去了,其實是「偽自傳」。
「我」的朋友、自稱吐穀渾人後代的慕思明也是完全虛構的,我想在慕思明身上寫出一個已經消失的民族的性格的延續。民族的發展如忒修斯之船,經歷過修補重建,此船早已非彼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書中的人物和情節,其實是敦煌的「反射物」。漢人、吐穀渾人、粟特人,他們如果不在敦煌,可能不是這個樣子,是敦煌激發出他們性格中、生命中的某些特質。這可能是我寫這部小說的探險成果。
中青報·中青網:小說中的一些細節是真實的,比如壁畫上留下了匠人的指紋。你為寫作做了哪些準備?
陳繼明:我下了很大功夫,買的關於敦煌的書就有兩三百本,一邊讀,一邊做筆記,有的史實就用到小說里了。
其實寫之前我只去過一次敦煌,還是1992年的一次旅行;原本創作前打算去住至少半年,房子都租好了,沒能成行。但小說家有時候需要想像,比如,我印象中在敦煌城能看到祁連山的雪,我在小說中也是這麼寫的;但是當我寫完小說再去敦煌,發現連祁連山都看不清。幸好沒去,這是一部虛構的小說,我想站在敦煌面前打量她,然後起一個自己的空中樓閣。
中青報·中青網:你1984年畢業於寧夏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這是你的第一誌願嗎?
陳繼明:是的,那時候幾乎每個人都有作家夢,所有人都是詩人。
我的老家陳莊是一個偏僻的山村,我爸算半個知識分子,家裡還有幾本書,《古文觀止》《封神演義》《三國演義》……這些書有幾本我現在還保存著,《封神演義》翻得多了都只剩半本了。從小學到中學,我的作文都是班里比較好的,經常被老師表揚。
上高中時,大家忙著複習,我還在寫詩。高考時,我的語文考得不好,政治考得不錯,招生辦就問我要不要上政治系,我竟然很明確地拒絕了。我當時想,一定要讀中文系,不行就明年再考。其實那時候家裡很窮,上一年學要花費很多。幸好,隔了一星期我就收到錄取通知書了。
大二時候,我在寧夏一本如今已經停刊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了處女作,是一首詩,模仿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40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題目是《大學——我的保姆》。
中青報·中青網:你年輕時喜歡讀什麼書?
陳繼明:我真正的文學閱讀是從大學開始的,瘋狂「補課」,整天泡在圖書館,大部分書的閱覽卡上都有我的名字。我不僅看書,還抄書,比如《歌德談話錄》《懺悔錄》。當時最喜歡的作家,外國的是海明威、川端康成,中國的是蕭紅、鬱杜夫。他們的文風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但我都特別喜歡,我的文風可能是綜合的結果。
中青報·中青網:你一般在什麼時間寫作?
陳繼明:我一開始總是早起寫作,早晨四五點起床,寫兩三個小時,在上班之前就把一天的寫作任務完成了。但這樣寫作進度比較慢,我就有緊迫感,於是開始探索一種作息方式。我把每天的睡眠分解成3-4次,一次睡兩個小時,每次醒來就像一個早晨,寫一兩個小時,然後再睡。這樣寫作,其實睡得不少,寫作時間也比較長,而且兩次寫作之間的間隔比較短,狀態容易延續。
中青報·中青網:你從天水到珠海,適應嗎?地理跨度對創作有什麼影響?
陳繼明:剛來的時候不習慣,天氣熱,飲食偏甜,我都有回去的衝動。人文環境也不一樣,在西北,大家都是哥們,時不時要見面、喝酒、聊天;在廣東,大家都在忙事業,平時不打麻將不喝酒,我都有「失血」的感覺。但是待久了,就覺得挺好,從作家角度,我也應該到開放的沿海開闊眼界。現在我完全適應了。
魯迅在北京寫紹興,比在紹興寫紹興更清晰、視野更廣,大概我也是這樣。我在珠海寫敦煌,覺得很多東西都打開了;而一個西北作家寫華僑,其實也沒什麼障礙,只要對語言、細節下功夫,典型人物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塑造致廣大而盡精微。
中青報·中青網:你現在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教授,對當下的年青人有什麼閱讀建議?
陳繼明:在閱讀方式上我比較傳統,建議我的學生讀紙質書,也經常在課堂上辦讀書會。我還要求他們抄書,抄一些散文、詩歌、思想類的書。
我自己幾十年從來沒有停止過抄書,積攢了三四十本本子。我會用小楷抄,字還不錯,有的本子就被朋友要走了。抄文章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
中青報·中青網:你有什麼業餘愛好?
陳繼明:一個是寫字,我喜歡書法,會臨帖,能讓我從寫小說的狀態中跳出來。另一個是足球,可惜有時看得要「氣死」,一點都不長精神。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11月08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