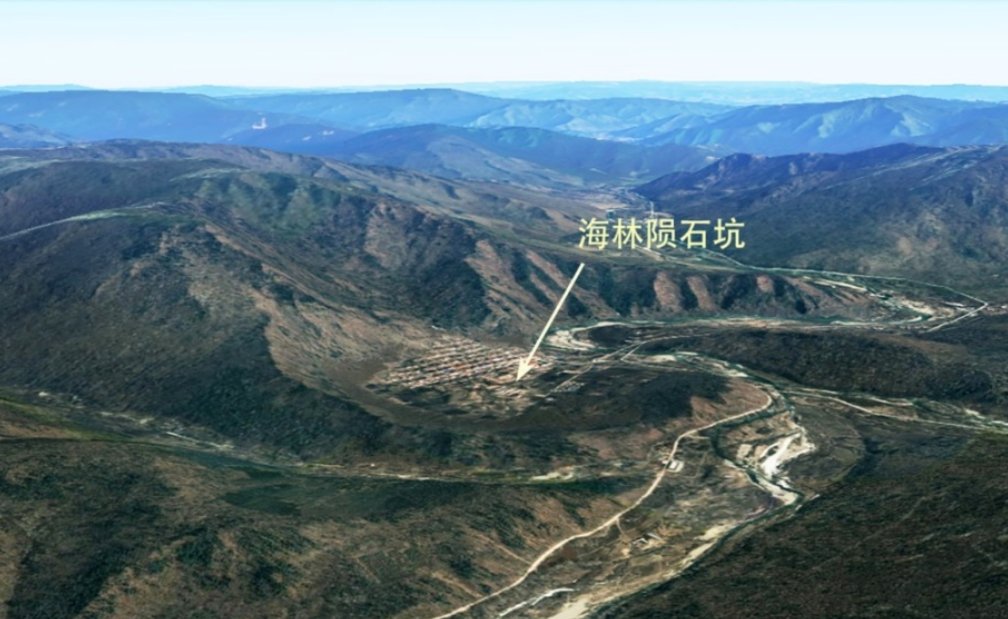古典文學研究學者葉嘉瑩逝世:詩詞的女兒,風雅的先生
原標題:古典文學研究學者葉嘉瑩逝世:詩詞的女兒,風雅的先生
據央視新聞消息,總台記者從南開大學獲悉,古典文學研究學者、南開大學講席教授葉嘉瑩,於2024年11月24日去世,享年100歲。
葉嘉瑩1924年7月2日出生於北京的書香世家,從小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與中國古典詩詞早早結緣,而她與古典詩詞的緣分一生從未中斷,成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十幾歲時即可填寫詩詞,借此表達自己的生命經驗,後又開始古典詩詞的教學與研究。在研究方面,葉嘉瑩已出版眾多相關書籍,如《唐桑治詞十七講》《人間詞話七講》《北桑治名家詞選講》《小詞大雅》等,成為中國古典詩詞研究領域的佼佼者。而作為一名教師,葉嘉瑩更注重古典詩詞對學生和讀者們的啟發,將詩詞之美以及背後的文化底蘊與當下讀者的生命經驗相結合。
2020年,以詩人葉嘉瑩為主角的文學紀錄片在國內藝術院線首映。與其說是《島嶼》系列的延續,導演陳傳興更願意把《掬水月在手》與《鄭愁予·如霧起時》《周夢蝶·化城再來人》一起,合稱為「詩人三部曲」——「鄭愁予是詩與歷史,周夢蝶是詩與信仰,葉嘉瑩是詩與存在。」

葉嘉瑩紀錄片《掬水月在手》劇照。葉嘉瑩,號迦陵,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1924年7月出生於北京,1945年畢業於輔仁大學國文系。現為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
新京報書評週刊記者曾就此採訪《掬水月在手》導演陳傳興,總製片人廖美立,製片人、副導演沈禕等片方主創,共同解析文學與影像碰撞背後的故事,現重發此篇,以示紀念。
撰文|肖舒妍
所謂詩人,也是凡人
葉嘉瑩先生雖然早已聞名,在大眾心中卻始終和她傳播、創作的古典詩詞一樣,留存著「陽春白雪」一般的形象,高雅、美好、可遠觀而不可褻玩。但《掬水月在手》一片,卻將鏡頭拉近,展現了她作為「凡人」的一面。
開篇的一串空鏡之後,葉嘉瑩在影片中出現的第一個鏡頭是工作人員幫她量血壓、別耳麥,工作人員小心翼翼把耳麥藏在她後頸衣領之下,她卻帶了點著急笑嘻嘻催促:「不用藏啦,又拍不到我背後。」而另一個鏡頭,在工作人員輕輕別過飄到葉嘉瑩眼鏡上的髮絲時,她順勢捋了捋頭髮,驕傲地說:「我頭髮多吧?這可都是真發,上回還有人問我是不是戴了假髮,我本來頭髮還要多,上個月跌跤摔到後腦勺掉了不少。」
人前的葉嘉瑩端莊,也愛美。鏡頭中她總是穿著得體,一條高領旗袍搭一件對襟開衫,為了整體服飾的和諧,兩個小時的影片中,她不同顏色、不同材質的眼鏡鏈就出現了三條。
 《掬水月在手》劇照。
《掬水月在手》劇照。但離開學生和友人的目光,私下的葉嘉瑩,96歲還帶著些孩子氣。製片人兼副導演沈禕記得,一次接葉先生到北京錄音,工作結束之後,葉先生邀請陳導演到房間里聊天。因為在拍攝之外,團隊關掉了所有攝影機,而葉嘉瑩就坐在床尾,放鬆地晃著腿,「像個小女孩在蕩鞦韆」。
導演陳傳興最遺憾沒有剪入成片的,也是一個相似的畫面:葉先生回想起自己兒時的夏夜,她和父親鋪著涼蓆躺在老宅四合院的樹下,在航空公司工作的父親就教她認識天上的星座和星辰,講到這一段時,她手指著天空,眼睛癡癡看著上方,「哇哦,你就覺得她似乎回到了小時候的夏夜,她面對的星辰星空,其實也是她之後的生命歷程,詩的星辰、詩的宇宙,就在她的手指裡面。」
《掬水月在手》在北京的一場點映結束之後,一位觀眾悄悄告訴製片人廖美立:「這部電影讓我想到了我奶奶,我奶奶和葉先生一個年紀,等影片上映,我一定要帶我奶奶一起來看。」
這部紀錄片,讓我們意識到,葉嘉瑩是著名詩人、是博士生導師、是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也是一個普通的老奶奶,有自己的小心思,不是坐在不食人間煙火的神壇,而是活在凡塵里經歷和我們一樣的喜怒哀樂。
所謂詩歌,是詩人生命的流淌
文學紀錄片,自然離不開對文學的講述。但《掬水月在手》不是對詩歌的文本分析、逐字解讀,也不是葉嘉瑩詩詞的風格概括、名篇推薦,而是把詩歌,還原為詩人生命的流淌,通過對葉嘉瑩生命歷程的展現,試圖以此更深刻地理解她的詩詞創作。
「淒絕臨棺無一語,漫將修短破天慳。」
——(《哭母詩八首》)
這是葉嘉瑩17歲失去母親,親耳聽到母親入殮時釘子釘在棺材上的聲音,悲痛欲絕後地質問蒼天:為何這樣吝嗇,讓母親在44歲時便撒手人寰?
「室邇人遐,楊柳多情偏怨別;
雨餘春暮,海棠憔悴不成春。」
這是葉嘉瑩上世紀50年代在台灣遭遇白色恐怖,帶著尚在哺乳的女兒被抓、丈夫入獄三年、幾多漂泊後在夢中浮現的聯語,是她潛意識中對離合聚散不由人、海棠憔悴好景難常的感傷。

《掬水月在手》劇照。
影片特別呈現了兩句詞跨越兩岸、相隔十餘年的佳話。葉嘉瑩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時,師從顧隨。一次在課堂上,顧隨引用雪萊《西風頌》中「假如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詩意,寫下了「耐他風雪耐他寒,縱寒已是春寒料」兩句詞,卻並未完成全詩。
葉嘉瑩課後借這兩句湊成了一闕《踏莎行》:
燭短宵長,月明人悄。夢迴何事縈懷抱。
撇開煩惱即歡愉,世人偏道歡娛少。
軟語叮嚀,階前細草。
落梅花信今年早。
耐他風雪耐他寒,縱寒已是春寒了。
多年以後,顧隨之女顧之京整理父親遺作,發現在1957年同樣用這兩句次填了一闕《踏莎行》:
昔日填詞,時常歎老。如今看去真堪笑。
江山別換主人公,自然白髮成年少。
柳柳梅梅,花花草草。
眼前幾日風光好。
耐他風雪耐他寒,縱寒已是春寒了。
師徒二人相隔十餘年的兩首詞,選用了同一個詞牌,同一個韻腳,所用意象也隱隱相似,竟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唱和。在電影中,導演選用了一男一女兩個人聲,分別吟誦這兩首詞,錯落地剪輯在一起。筆者彷彿看到葉嘉瑩和顧隨先生跨越時空在推杯換盞、吟詩作賦,師生的默契體現在了詩詞之中。
但副導演沈禕提醒道,這也完全可以理解為與葉嘉瑩、顧隨毫不相幹的兩位後來人,在多年之後重讀他們的詩詞,在詞中尋找自己的感受。
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都能從一首詞中窺見自己,這可能也是詩歌本身雋永的魅力。
葉嘉瑩曾提到,自己在五十年代生活最艱難時期,是王安石《擬寒山拾得》中的一句「眾生造眾業,各有一機抽」猶如當頭棒喝,讓她猛然驚醒,意識到人世間的因緣、業緣和遇合都各有因果,於是她決定坦然承受,不再計較。時隔多年,她再去查這首詩,才發現當時是自己的誤讀,王安石的原句為「眾生造眾惡」,但這全然無改她從詩歌中獲得的慰藉。

「你是否曾在葉先生的某首詩中看見過自己?」我問導演陳傳興這個問題,他遲疑了一下,給出了《向晚二首》這個答案:
向晚幽林獨自尋,枝頭落日隱餘金。
漸看飛鳥歸巢盡,誰與安排去住心。
花飛早識春難駐,夢破從無蹤可尋。
漫向天涯悲老大,餘生何地惜餘陰。
這兩首詩作於1978年,在電影中亦有出現。彼時身居加拿大的葉嘉瑩向國家教委寫了一封信,申請回祖國教書,但尚未收到回覆,去留未定。散步時的歸鳥激起了她無盡的思鄉之情,想到自己年過半百卻不知何時才能歸鄉,她寫下了這兩首絕句。
而陳傳興曾留學海外多年,在法國的第十年,他必須要作出決定,是留在國外,還是回到台灣。最後,他選擇回到故土,因此對於葉嘉瑩的感受,他可謂心有慼慼。
詩詞帶來的強烈共鳴,可能正是《掬水月在手》與一切詩歌的魅力。
所謂詩意,是慢節奏的「燒腦」
儘管有這樣的親近與共情,真正「看懂」《掬水月在手》卻並不容易。
長達兩個小時的電影看似雲淡風輕,葉嘉瑩的講述也始終笑盈盈、慢悠悠。儘管她的人生遠非如此波瀾不驚。但即使提到女兒女婿的車禍,葉嘉瑩也是淡而化之。
 2018年,葉嘉瑩在天津。
2018年,葉嘉瑩在天津。「經歷了那麼多,她是怎麼挺過去呢?她女兒女婿走了那陣子,有人在亞洲中心見到她,說葉先生來上班了。她迎面走來,看見大家,眼眶一紅,但也就是那樣了。」紀錄片中,葉嘉瑩加拿大的鄰居回憶。
葉嘉瑩本人曾以玩笑的語氣提到,自己這輩子沒有談過戀愛。可這看似輕巧的埋怨背後,是一段從頭到尾都不幸的婚姻,幾十年來葉嘉瑩不但要忍受丈夫趙鍾蓀暴躁孤僻的性情,還要獨自工作養家。當年她倉促決定留在加拿大U.B.C任教,也是因為肩負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可她一邊忍受用磕磕巴巴的英語講授中國古典詩詞,下台還要回來逐字逐句地翻字典查生詞備課,一邊還要遭受待業在家的丈夫的謾罵與嗬斥。這些委屈她從未向他人訴說,只有在長達40萬字的口述自傳《紅蕖留夢》最後,用了寥寥數頁講述,是告解也是和解。
 《紅蕖留夢》,作者:葉嘉瑩 口述 /張候萍 撰寫,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9月
《紅蕖留夢》,作者:葉嘉瑩 口述 /張候萍 撰寫,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9月但在影片中,趙鍾蓀僅在最後借葉嘉瑩的好友劉秉鬆之口出現一次:「哎,那個趙鍾蓀。」更多情感,只能從葉嘉瑩避而不談、欲言又止的地方細細體味。
葉嘉瑩曾提出,詩詞之美,是「弱德之美」,是在外界強大壓力之下,不得不自我約束和收斂以委曲求全的一種品質。而「弱德之美」也是葉嘉瑩本人品格的最好概括。
葉嘉瑩本人「弱德之美」、「淡而化之」的性格,也是導演陳傳興選擇如此講述的原因,「當你穿透了人生的顛沛流離、週遭的親人傷亡和情感上的不悅,走過這些非常大非常大的困難,最後終於都放下了。既然都放下了,我們卻要回過頭用一種濃重的、濃厚的大筆觸表現,那不是太牴觸了、也太不真實了、也太殘酷了嗎?」
整部紀錄片,陳傳興用四合院的結構串起,由門外、脈房,到內院、庭院,一層一層直到廂房。同時也把葉先生和詩詞的關係,疊影在這座巨大的回憶宮殿之中。
陳傳興希望借《掬水月在手》來討論「詩與存在」的關係,也即赫特格爾「詩作為存在的居所」,於是採用了葉嘉瑩在北京察院胡同、現已拆除的四合院老宅,來一進進講述她的人生。影片開頭,葉嘉瑩翻看相冊中的舊照片,指認老宅的方位:「這是大門……這是踏馬石……這是西廂房……」其實就已定下了影片的結構。
另一方面,四合院又疊加著更多的隱喻。1948年葉嘉瑩隨丈夫渡海來台後,常做「回不去」的夢:夢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院子卻門窗緊閉,她怎麼都進不了門,只能長久地徘徊於門外。四合院於她,是美好的童年、是記憶的安全港、是回不去的故鄉。
 《掬水月在手》劇照。
《掬水月在手》劇照。此外,陳傳興運用了大量的空鏡。從寺廟到古蹟,從壁畫到浮雕,看似無意又實有所指,《嫦娥》一詩配了洛陽的雪景,《錦瑟》則是陶器,觀眾儘可能從中作出自己的投射和想像。
於是,《掬水月在手》成了陳傳興有意搭建的一座迷宮。至於對這座迷宮的解讀,有人樂在其中、津津樂道,也有觀眾認為這導致了紀錄片主角與影像之間的斷裂。
「這其實是高度危險的,講難聽一點,咬起來傷牙,很硬、很生,而多數人只愛吃鬆軟甜膩的食物。人們評價一些電影‘燒腦’,‘燒腦’其實只是一種遊戲、一種商業操作、一種燒錢。真正的‘燒腦’,不是短短90分鐘、120分鐘可以燒完的,而是電影結束之後你還會帶著燃燒過的燒焦痕跡入睡,這才叫做可拍,可是這也正是迷宮里好玩的、高度挑戰的地方。」
這樣看來,陳傳興或許不太在意《掬水月在手》是否能讓觀眾足夠喜歡,但他無疑希望發出一次邀約——「在這個手機屏幕支配一切、動漫文化橫掃一切的環境下,我想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去壓著年輕世代說,你們必須要讀、你們必須要看。我們只能說,你看,我向你發來了一張邀請函,這是一場舞會的邀約,僅此而已。」
撰文/肖舒妍
導語撰文/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