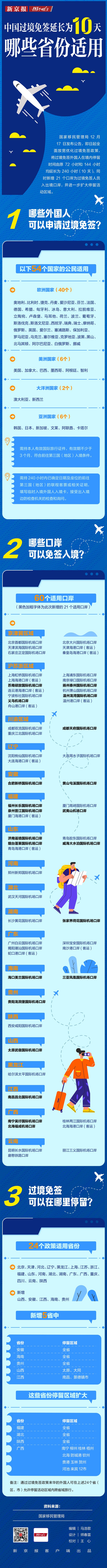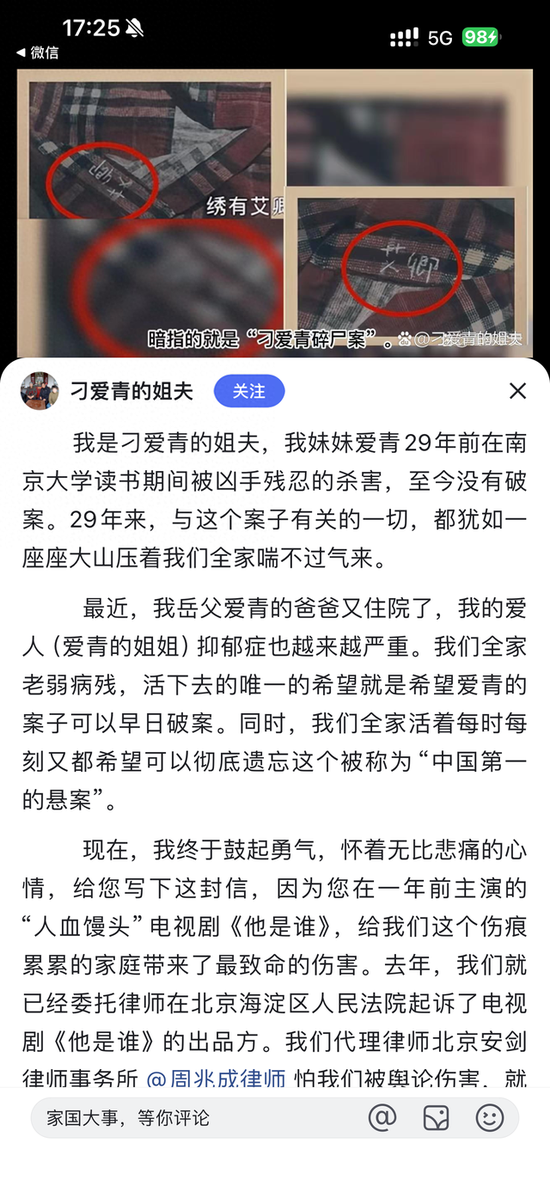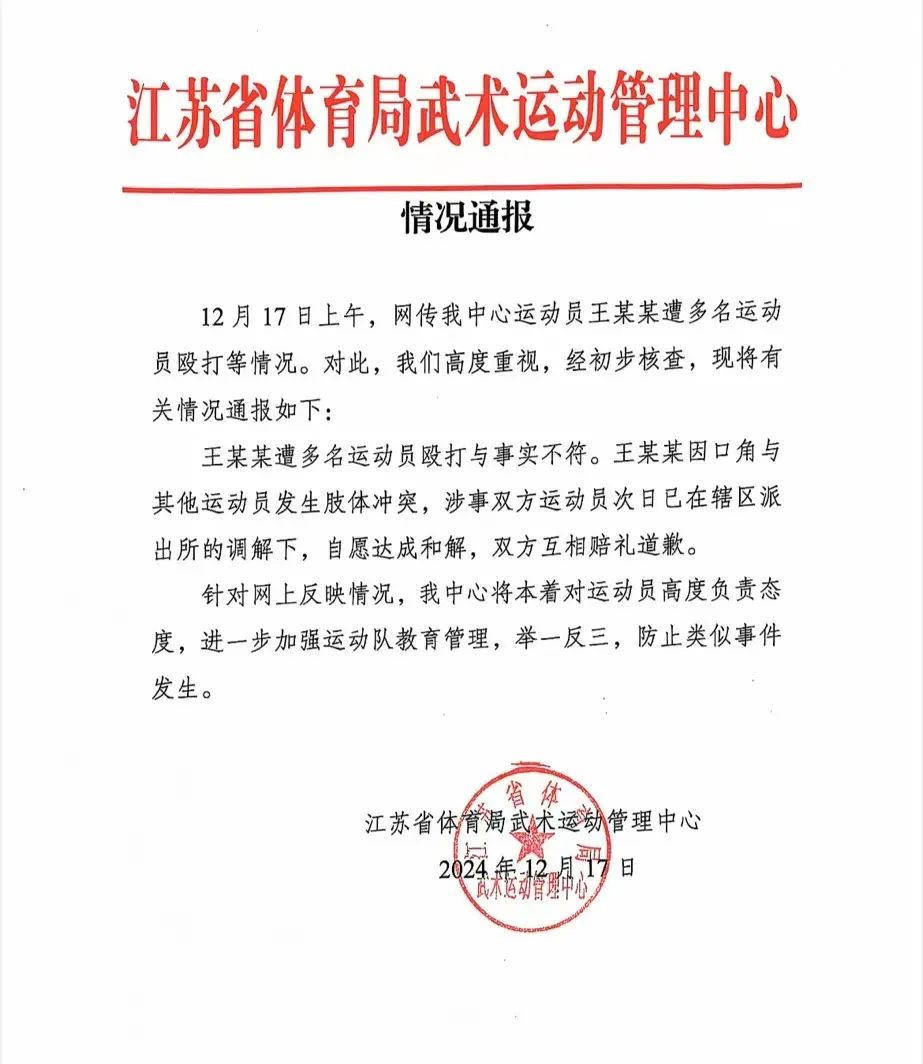《我是刑警》富大龍:角色出場,何談早晚丨對話
刑偵大劇《我是刑警》跨度30餘年,用一線刑警的辦案歷程與成長軌跡,串聯起我國基層刑偵的發展脈絡。富大龍在劇中扮演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陶維誌,灰頭土臉、兢兢業業、不修邊幅。日前,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富大龍表示,現實生活中他認識不少刑警,他們工作辛苦、枯燥,時刻處在危險之中,但卻並不為人所知。也因此,他希望可以攝取刑警們的工作、生活日常,展現「冰山一角」給大家看。
《我是刑警》全劇演到第30集,富大龍飾演的基層刑警陶維誌才「姍姍來遲」,被網民戲稱為「最晚登場的男主演」。在富大龍看來,如果大家過度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影響了劇情和對陶維誌的觀感,他會覺得有點遺憾。富大龍此前演繹過《紫日》《天狗》《大秦帝國之縱橫》等經典影視作品,他8歲出道,卻始終保持著不急不躁的拍戲節奏,平時喜歡寫字、音樂、畫畫,極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被稱作「不拍戲就消失」。富大龍表示,迄今為止他都認為自己不懂表演,或者說只是一個在學習過程中的演員。「一部戲演完了,這個角色也還在進行,有時候我也還在想,當時這個地方要是那樣處理就好了。對於塑造角色,我認為我一輩子都是在ING(進行)中。」

在《我是刑警》中,富大龍飾演基層刑警陶維誌。
最起碼要從真實的刑警中體驗生活
新京報:接演《我是刑警》之後有做一些什麼特別的準備嗎?比如體驗生活,去和真實的刑警接觸、聊天?
富大龍:有的。現實主義題材在拍攝手法上要求每個演員塑造的角色回歸到一個傳統、紮實、貼近生活,甚至最好能達到「以假亂真」的表演狀態。對演員而言,這是最難的一種挑戰。最起碼要從真實的刑警中體驗生活,去觀察一個刑警都不夠。我之前也演過一些警察的角色,相繼接觸過警察內部的各種領域,也有很多警察朋友,我初中同學就是一名刑警。在我的人生當中,我認識、觀察到的警察不是一個兩個,在這個過程中做了很多功課,對他們的生活、工作狀況,我還是有一個相對深入的思考。
新京報:像陶維誌這樣現實中的基層刑警,給你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富大龍:我得非常慎重地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每一個職業內部也存在著差異,同樣叫刑警,不同地域,比如浙江和內蒙古的刑警氣質上可能就不一樣;有的刑警是從警校畢業,有的來自其他專業領域,都不太一樣。總體來說,我個人接觸過的刑警,絕不是在一般偶像劇或者商業片里看到的樣子。我舉個例子,也許你家門口賣了大半年白薯的老大爺就是一個刑警。當我瞭解到他們的具體事蹟之後,那種崇敬不是嘴上說說的,他們真的是捨棄了自己大部分的家庭生活,執行任務的時候也不能告訴家人,甚至一失聯就是半年時間,風餐露宿,幹著隱蔽工作,絕不是帥氣、威風八面,甚至007那種風流倜儻的樣子。如果在一列火車上,你一眼被看出來是警察,那麼也意味著可能就要有危險了。
新京報:《我是刑警》最初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富大龍:用影視專業上的說法,在近些年像《我是刑警》這樣幾乎是半紀錄式的作品比較少見。
新京報:近幾年可能會出現某一種潮流或者特別熱門的影視類型,在你自己的審美標準和大眾流行趨勢之中,你有矛盾的時候嗎?
富大龍:搞文藝的人始終面臨著一個悖論,我們常說的「潮流流行」和「你自己」。你固守自己的某一種觀念是不行的,需要發展、需要開放;但是反過來,什麼流行你就幹什麼,又是藝術的大敵。所以個性和流行之間永遠存在矛盾。這些年,我一直保持自我,我不希望自己是一個潮流流行什麼我就跟什麼的人,我有自己的主張和審美;但我一直也在提醒自己,不能固步自封,一直在學習,至少希望自己是在不斷提高的。
說陶維誌像村幹部,一點都沒錯
新京報:劇中陶維誌作為縣級的刑警隊長,在行為舉止上會跟市里的刑警有所不同,更樸實一點,甚至有網民說他的氣質更像一個「村幹部」?
富大龍:像陶維誌這樣級別的警察,我自己認識的不下十個,有南有北。陶維誌來自山西一個小縣城,你說他像村幹部,一點都沒錯。他們日常所幹的事情,更多時候和居委會村幹部是一樣的,脫了警服,你確實完全認不出來他是一個警察。昨天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說,他舅舅就是一個小縣城的刑警,他說跟陶維誌特別像,每天血紅著眼睛,蓬頭垢面,鬍子拉碴,離老遠就聞見他一身的煙味,甚至臭味,因為他工作的時候很長時間不能洗澡,他說,他舅舅脫了警服,你會覺得他就像一個「行走的臘肉」。我覺得他形容得特別準確。真正執行任務的時候,這些刑警們可能需要蹲一個點,十天半個月不洗澡,窩在一個屋子裡,靠一堆方便麵過活,這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

《我是刑警》中,展現了基層警察為了破案,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調查工作。
新京報:陶維誌作為一名縣城刑警雖然有「質樸」的一面,但是他也會彈吉他,還挺文藝青年的。你如何把握這個人物氣質?
富大龍:比如像你們記者,有愛好文藝的,也有喜歡打麻將的,還有擅長廚藝的。我所接觸的這些警察朋友也是這樣,有的人愛打遊戲,有的人愛踢球,什麼樣的人都有。如果從藝術創造角度說,在非常緊張的偵破案情之中,這個人不能不透氣。案情非常焦灼的時候,他們總要有自己的排解。在拍戲時,正好我手邊有一個道具吉他,我就想,為什麼陶維誌不能很喜歡聽音樂呢?但他的吉他水平非常差。所以設計了他一直在彈《致愛麗絲》,這是我小時候親曆的,在七八十年代這是一個著名的梗,所有的吉他少年入門曲都是《致愛麗絲》,追女孩子什麼的全都是彈這首曲子。
新京報:為了三個女童追兇六年,「執拗」是大家對陶維誌的形容。在你看來,陶維誌是一個什麼樣的刑警?
富大龍:他是有溫度、有毛邊兒,有生活氣息的一個人。我個人一直在和概念化在作鬥爭。我塑造角色主要的一個命題就是,要把某一個人物去概念化。他是活生生的人,允許他有各種各樣的層次。具體說到陶維誌的執拗,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是職責所在,他有任務、計劃,盡忠職守;第二點就是,我認為能堅持下來做警察的人,需要具備起碼的善惡觀。比如陶維誌一直掛在嘴邊的話,「這個案子我可以放,可以擱置,但是我為什麼放心不下?」後面的劇情會有展示,他不僅見過那三個女孩子的屍體,而且他見過她們的家人,他每次都提,「那三個媽媽都瘋了,三個家庭都完了。」這些都是他真切見到的,因此最基本的惻隱之心會使得他堅信,一定要為死者討回正義。所以在我看來,陶維誌不神奇,他也並不偉大,他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刑警,同時他也是一個真實、有正義感的人。
演繹陶維誌,最重要的在於對真實的還原
新京報:劇中市裡面的警察,比如秦川對DNA的運用已經挺熟悉了,但是對於陶維誌來講,這還是一個很新鮮的技術手段。對於一個縣級的刑警而言,那個時候是不是更多還是要依靠「人肉式」的方法去尋找破案線索?
富大龍:是的。我是1976年出生,在我中學以前沒有智能電話,也沒有網絡。劇中那個時候,就算是市里的人也沒有聽說過什麼DNA。像秦川所掌握的已經算最高的偵查技術手段了,除了他們,很多人都沒聽說過DNA,更不要說小鄉村,確實是很封閉。而且DNA測試到今天為止都是做一次花一次錢,這個花銷是很巨大的。
新京報:陶維誌作為最終破案的中流砥柱,在你看來,他「踹開真相大門」的「那一腳」是什麼?
富大龍:這個案件最終能偵破,不是靠陶維誌一個人,秦川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秦川所代表的是高端的技術支持,先進的思想理念、偵破觀念,破案依靠的是集體的力量。而且在劇中你能感受到這些刑警的工作非常枯燥,同時他們也非常寂寞。他們需要忍受一年、兩年,甚至十年去查一個案子,這其中可能還會經歷不被人所看到和理解,他們也只能苦中作樂,背後很酸楚。
新京報:演繹陶維誌,對你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富大龍:我覺得最重要的在於對真實的還原,而且需要掌握它的度。這部作品畢竟是藝術創作,它是一個虛構的故事,陶維誌也是虛構的人物,在把握人物的時候,從他內心到行為舉止、一言一行,所有的部分我都在找度。怎麼樣讓他既忠實於真實,又能夠有個體的特色。在陶維誌負責的三個女童案件,一個特徵是沒有強情節。這裡面沒有悍匪、槍戰,也沒有所謂的高智商犯罪,沒有這些戲劇衝突,破案几乎靠的就是走訪、排查。他的人物設定又是一個基層的鄉土小警察,說話不能長篇大論,對演員來說這很可怕。它是一個平鋪直敘,沒有律動,沒有節奏的樂章。只能靠人物的生活氣息來填充,挖掘生活細節,他的日常生態。

陶維誌為了調查三個女童案件,屢屢碰壁,靠著一股韌勁兒和破案決心堅持了下來。
和於和偉會在現場產生很多即興表演
新京報:劇中你的搭檔是於和偉飾演的「秦川」,這也是你倆第一次合作嗎?
富大龍:《我是刑警》是我第一次和於老師(於和偉)合作,劇中陶維誌和秦川之間亦師亦友,我在生活里跟於老師的關係也是這樣。從演員角度來說,我非常享受我們拍戲的過程,因為於老師是我最喜歡、敬佩的一位表演藝術家,我從他身上學習了很多。我們到現場當著導演對戲的時候,在一些特別的創作點上,我們的想法一模一樣,不謀而合。我倆會在現場產生很多即興表演。就像咱們現在聊天一樣,你的問題方向我大概知道,但具體還是要依靠咱們現場隨時的即興問答。劇中陶維誌和秦川第一次相見,恰恰就是我倆拍攝的第一場戲,我倆也很激動,對彼此都有一種欣賞和默契。
新京報:此前很多網民也都在等你出場,都覺得你30集才出來,等得太著急了?
富大龍:我覺得這挺有意思的,驗證了原來我說過的一句話,對一個演員本身的關注度最好不要太高。這次很多人都說一邊追劇一邊在等我,對我來說有點糟糕。如果我是一個大家完全不知道的演員,大家就正常看戲,該誰出來就誰出來,何談早晚。
新京報記者 劉瑋
編輯 佟娜
校對 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