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上的守寶人|文化中國行
來源:南方日報
南澳島,中國大陸北迴歸線唯一穿過的海島。其所屬的汕頭市南澳縣,是廣東唯一的海島縣。這裏四季溫暖,海水蔚藍,漫山疊翠。
饒宗頤曾在《南澳:台海與大陸之間的跳板》中寫道:「這是一個蕞爾小島,面積只有一百零六平方公里,在歷史上卻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起了重大的橋樑作用。」
他所說的「橋樑」,就是今天常常提及的海上絲綢之路。
「南澳是航線上的望山,是海舶的補給點,絡繹往來的海舶帶動著繁榮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館長黃迎濤指向展廳里的一幅地圖——16世紀開始,西方地圖中就已經有南澳(Lamao)的名字。
如果說,黃迎濤和文物考古之間也有一座「橋樑」,那一樣也是南澳島。
黃迎濤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在島上已經生活了50多年。過去33年里,他像「開盲盒」一樣,跑遍了南澳島的每個角落,拚湊出了關於南澳的文保版圖。

對他來說,守島是「苦中作樂」,更是責無旁貸。他守護的,不只是家鄉的寶藏,還有海絲的記憶。
島上文物有了「戶籍檔案」
12月初的清晨,三澳漁民基地,黃迎濤帶領南澳縣文物普查隊一行四人,背著測繪儀器登上了漁船。
海風簌簌,當天的風浪不小。此行目的地是虎嶼,位於東北方向的一座獨立島嶼。

他上一次到虎嶼,已經是15年前。那時正值「三普」,他帶隊走遍了南澳全縣38個村居,登上包括虎嶼在內的4個獨立無人島嶼,調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63處。
「30多年前做‘二普’,我們只能劃竹筏過來。到了‘三普’,我‘蹭’漁民的船,他們送我過去,捕完魚再來接上我。」在他記憶里,虎嶼的石頭多,植被少,沿著礁石可以一路攀爬,直達頂部的龍門塔。
但這回,當漁船努力迎著風浪靠近虎嶼的邊緣時,黃迎濤才看清,眼前的虎嶼已經變了個樣——鬱鬱蔥蔥,樹根猛紮入山體,帶刺的荊棘擋住了為數不多的石頭縫隙中的小路。

黃迎濤聳了聳肩:「只能硬爬了。」——就在兩個月前,他下鄉調查時不慎摔傷,爬山再不如之前穩健。
他身著夾克,穿休閑鞋,脖子上掛著一台單反相機。頂著呼呼作響的大風,他一路上扯著樹枝,手腳並用。在數次驚險滑倒後,他和隊員們終於抵達龍門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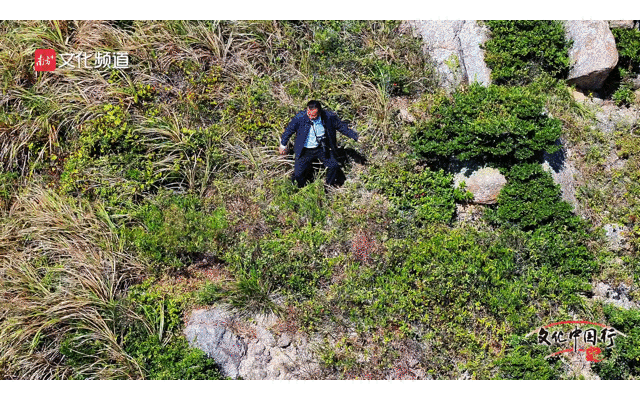
他氣喘吁吁地進入塔內,端詳四周,猶如故友見面。「古人真厲害!全是用石頭砌成的,一點水泥都沒有,沙也沒有。」他興奮地用相機記錄下眼前的這座清代文物。
一旁的年輕隊員正在用無人機進行航拍。「飛到頂上,先繞一圈,要記錄每個門的正面。一些石條還有地震導致的裂縫,要看看有沒有變化。」黃迎濤細緻地叮囑。

上世紀80年代末,黃迎濤入職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在此之前,南澳島上還沒有建立過真正的館蕆文物檔案,博物館里僅有十餘件從民間徵集來的兵器。老館長告訴他:「如果真的要做這行,你先把這個島走一遍。」
他二話不說,背起挎包,拎著照相機,開始「環島尋寶」。南澳地形複雜,丘陵起伏,他白天趕路,晚上記錄。因為條件簡陋,他只能根據日照投影來估測島上古塔的高度。「二普」期間,他摸清了整個南澳大體上的文物分佈,手繪了一整疊文物建築圖。

回到館里,黃迎濤立即著手對館藏文物進行清理,並完成第一本文物原始登記冊——相當於文物的「戶籍檔案」。泛黃的牛皮紙上,墨跡依然清晰。文物的時代、尺寸、重量、來源,都被工工整整地記錄下來。
第二年,他又對館中文物賬冊進行了整理,健全入庫手續。2010年後,博物館引入藏品數據化管理系統,但他依然保留著手寫記錄的習慣,170多件在館文物都有手寫檔案。他說,這是「雙重保險」。
守護被盜撈的瓷器
如今的南澳島上,盤山公路蜿蜒於山海之間,多部電影都曾在此取景。隨著韓寒執導的電影《四海》的上映,一道寫著「四海」字樣的海堤,成了熱門打卡地。
對於黃迎濤而言,這片海堤意義非凡。
那是在2007年5月25日下午,他突然接到通知,說有三艘漁船正在水下擅自盜撈「古董」。他急忙騎著單車,馬不停蹄地往海堤趕。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南澳漁民對於撈到瓷器就已經司空見慣。「當時還沒有水下考古的概念,南澳發現的第一艘水下沉船——許厝礁沉船就被盜撈過,我們很痛心,這次必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他越想,心裡越急。
等他到達時,漁船已經被公安和海警控制,船上載著一些盜撈的瓷器。眼前的海面,位於烏嶼與官嶼之間,島民稱之為「三點金」。看似平靜,暗藏玄機。

黃迎濤的首要任務,是守護水下沉船,等待省里派專業打撈船和考古專家到來。
現場風浪很大,他就睡在碼頭上,方便隨時和公安、海警、漁民一起巡邏,整整12個晝夜,不讓可疑船隻靠近海域。
6月初,省里的打撈船到達接班時,他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此後五年間,他多次隨水下考古隊員乘小艇前往沉船打撈地點,進行摸查定點,對沉船遺物進行跟蹤拍攝記錄。

這艘沉船,就是2010年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南澳一號」,也是國內考古界首次在水下完成考古發掘的項目,具有標杆意義。
今年「四普」期間,也是在同一片海域,「南澳二號」的水下發掘工作順利完成。黃迎濤數次找到老漁民,帶著專家一起,在附近搜尋其他古沉船的跡象。
紅綠彩花卉紋碗、青花蘭花蓮紋小口罐、青花太陽花海水紋粉盒……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的展櫃里,像這樣的明安蘭(今越南)窯瓷器,有100多件,都是5年前漁民在青澳灣海域無意撈起的。
直到去年,黃迎濤才給這批瓷器全部做完脫鹽處理。他想知道,這些越南燒造的瓷器是怎麼來的,又要被運到哪裡?南澳在這條航線里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黃迎濤還有兩年就要退休了。他說:「希望我在退休前,能解開這些謎題。」
習慣了「折騰」的一輩子
黃迎濤越發忙碌了。他每天往返於家、博物館還有南澳島上各處。前些年,博物館展陳更新,黃迎濤不僅承擔了展覽的設計和解說文字的撰寫工作,還摸索著用電腦剪輯了一段7分鐘的「南澳一號」發掘專題片。
用他的話來說,「折騰」了一輩子,習慣了。
雖然不是考古科班出身,但他從小就對歷史很感興趣。1990年8月,他從縣廣播站的職工那裡偶然得知一個線索——對方說,在隆澳東坑仔幫親友挖土時,發現了一些碎瓦片,泥地燒的,中間夾黑。
到了現場一看,「滿山的陶片把我嚇壞了!」黃迎濤憑直覺認為,這可能是一個人類聚居遺址。
他輾轉聯繫到了同是潮汕人的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騏。當年國慶期間,曾教授專程趕來南澳,手把手教他怎麼看文化層,怎麼採集文物標本和繪圖……
這是黃迎濤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田野考古。一年後,兩人合作在《東南文化》雜誌上發表了《廣東南澳東坑仔古遺址考古報告》。隆澳東坑仔發現商周時期人類聚居遺址,改寫了史書上關於南澳桑治代才有人類居住的記載。

南澳中學的一位老師又向黃迎濤提供了在象山上採集到的一些小燧石,上面還有清晰的打擊痕跡。經過近三年採集,這些燧石核、石片、細小石器足有100件。
隨後,由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縣文化局、汕頭市文管會辦公室、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等單位聯合組建的韓江流域考古調查組,有針對性地對象山進行考古調查,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個距今約8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是粵東地區迄今發現最早的人類生活遺址。
至今,島民的「爆料」源源不斷。今年12月,有村民把一件在路邊發現的石器帶到館里,請黃迎濤鑒別。

這是一件用於磨製的石斧,年代可能是新石器中晚期。但經過黃迎濤現場勘驗,發現地點所在的山坡表土層非常薄,底下是風化土和岩層,石器的來源還需要調查。
儘管如此,他依然對這些線索樂此不疲。他還打算把曆任南澳總兵的生平梳爬一遍,總共有183位,目前已經完成了1/4。每到深夜,他都窩在書房裡,翻看一本本書脊比手臂還厚的誌書。這些古書,有不少都是曾任南澳中學校長的父親留下的。
母親常常勸他不要太辛苦。他直言:「哪個行業不辛苦呢?苦中作樂吧!」
南澳島於他而言,既是家和故鄉,也是漫長歲月中的「遠方」。太多的謎題還未解開,太多的故事等著有人書寫。
而他,仍像他的名字一樣,迎著風濤前行。

編者按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廣東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邁開新步伐。
廣東省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正全面啟動,以縣域為基本單元,實地開展文物調查。
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南方日報、南方+聯合推出「問脈南粵·文保日記」系列報導,記錄廣東基層文保人「不平凡」的文保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