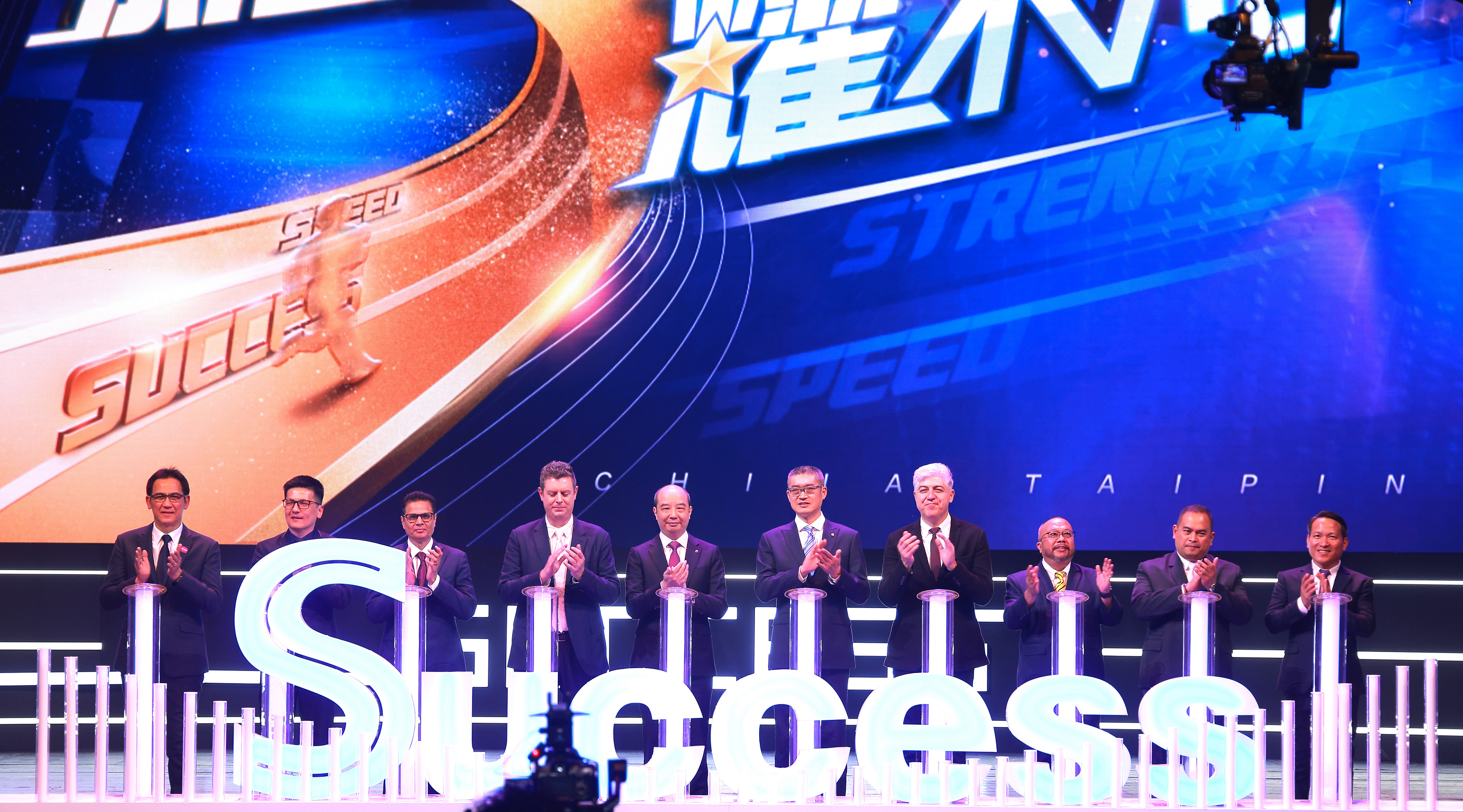故鄉里的中國|父親的自留地

1
不知從何時起,「自留地」已經成為了一個高級詞彙。它通常與精神生活有關,意指乾淨、純粹,與世俗相對。時間久了,很多人已經忘了它原本的含義: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之前,分給農民的小塊可自由支配土地。
在父親眼裡,它從來都沒有多餘的引申義,自留地就是一塊不足半畝的「場邊上的地」。作為一個地道的農民,這塊地有太多讓他偏愛的理由。
場,在魯中南山村的方言里,是指用來晾曬、堆放糧食的開闊平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父親還小的時候,這裏是村人民公社的麥場,人們為集體忙碌,掙工分。
整個麥場是一塊不規則的方形,鋪開在南山腳下。它的北側靠近河流,土壤含水量高,東北角有一眼泉水和一汪像沼澤的澇灘,夏天,那裡會長出兩米多高的蘆葦。南側土壤乾燥,靠近通往南山的大路。
父親的這塊自留地位於麥場的東南角,面積不到半畝,準確地說是四分半,還不如現在的一塊籃球場大。
1997年,村里重新分地,整個麥場被劃成七八份。我們家三口人,每口可以分到三分山地,這塊地作為其中一塊,被分到我們家。
作為這塊地的主人,父親有播種的自由。近三十年間,這塊地上開出過大朵的棉花,結出過圓胖的黃豆,養育一茬茬玉米拔節開花、一茬茬麥子抽穗灌漿,土裡也埋藏過顆粒飽滿的花生、個頭兒勻稱的地瓜。
 父親站在場邊上的地裡。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父親站在場邊上的地裡。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父親喜歡這塊地。南山上的泥沙被衝下,經年累月沉積在這裏,形成沙土,俗稱「沙窩包」。
「沙窩包」吸水性和透氣性極好,種出來的花生和地瓜更大;刨地時,一钁頭下去,土又鬆又軟,花生和地瓜不費力氣就被撬出來。
父親提起花生秧,晃一晃手腕,整棵花生帶著泥土被揚起來,展示在我們和過路的人面前,「你看看,這花生,滴溜搭掛的。」
鄰居也會誇讚:「了不敵(得)!老十你這花生真好啊。」
父親笑著露出他常年抽煙燻黃的牙齒,黝黑的臉上褶子一道道堆起,像花生殼上的紋路,夾著黃色的泥土。
2
老十是他的諢名。他在東山的趙家排行老十,同輩中年齡最小。
我們的村子過於微小,省、市、縣、鎮、村一路數下來,才是我們這個只有15戶人家、聚居在山窩裡的東山大隊。自清朝末年老祖先逃荒到這裏,已經繁衍了6代,生老病死是這裏最大的變化,其他的,一切如舊,面朝黃土背朝天,祖祖輩輩在地裡刨食。
 東山上的小隊,還有15戶人家。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東山上的小隊,還有15戶人家。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我一度羞於提起它,它總是和「土」離不了關係。
帶著口音的方言很「土」,在社交媒體上,說著山東話的男人被稱為「性縮力」十足;村里的穿著打扮很「土」,回到家,我會再成為穿著花襖的大妮兒,這在城里是要被笑話的。
但這裏的人愛土地,他們把溝溝角角都開墾出來,種上蔬菜、糧食和果樹,站在南山放眼望去,包圍著屋頂的,是一片片綠色、黃色、紅色的,整齊又分明的土地。
他們會認真對待手裡的每一分土地。
比如,父親的這塊自留地裡,每季都會安排上至少兩種作物。花生壟的盡頭,總會被點上幾粒山豆角,夏天路過捎上一把回家,就能做一頓晚飯。
土地養育了我的父輩和我。
爺爺曾是一個包地大戶,年輕時,靠著蠻力,他在屋前屋後開荒種地,後來承包下後山大半個山坡,種地瓜、花生、玉米,甚至栽種各種果樹,給父親攢下了蓋房子的錢,把生活支棱了起來。上世紀90年代,父親成了隊里第一個買電單車的人。
一輩子,爺爺都沒有捨下他的地。60多歲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大好,父親和奶奶勸他不要種這麼多,他總會生氣罵人。
好像不種地,就違背了他的立身之本,忤逆了祖宗和老天爺。
3
爺爺去世後,父親接替他繼續種地,以此養活一家人。
秋天孩子開學前、過年前,以及開春後需要買化肥等農資時,是農民需要用錢的時候,也是賣糧食的高峰期。
對於土地的產出,父親瞭然於胸。在這塊自留地,四分半地的麥子,能打出五六百斤麥粒,收穫約千元。種玉米、棉花,也大多是這個收入。
收穫的季節是喜悅的,但也是勞累的。
小時候我總跟著父母去這塊地裡收麥子。他們心疼孩子,不讓我動手,夏天日頭毒辣,我躲在橫穿馬路、直徑約一米粗的排水管道里,玩著自己的遊戲。
收割機上不去山地,只能人工收割。麥子已經沒到大腿,父親、母親和爺爺奶奶,每個人脖子上掛一條毛巾,彎腰揮著鐮刀。割好的麥子捆成一抱粗,碼在推車上,走過一條長長的上坡路後,碼成垛堆在大門口,等待脫粒機上門。
 山坡上的麥田。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山坡上的麥田。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這裏沒有關於豐收的浪漫想像,只有被麥芒刺得泛紅的手臂,毒辣的日頭曬出汗,殺得皮膚上的血口疼。推車拉車時手上總會磨出血泡,還有五六十斤的成捆麥子,它壓彎了一個男人的腰。
重擔背著背著,人就到了中年,又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同輩里最小的父親,也已經五十二歲了,種地已顯吃力,母親勸他少種點兒,他像他的父親一樣發脾氣。
留在村里種地的人越來越少,我們這一輩的兄弟姐妹,已經沒有人再扛過鋤頭。沒有人種,地只能撂荒。這在農民父親看來,是萬萬不能做的事情。
他說,以前負擔重的時候,講「三提五統」,種地要交錢納稅,他和爺爺都把地種了下來。現在,種糧食還有補貼,一畝地國家補貼一百多元,說什麼也得把這地種下去。
4
或許是因為收的那一把「沙窩包」里的花生被人稱讚,或許他靠種地供出一個大學生,令他驕傲。
也或許,是他習慣了做一個農民。
即使在農忙時,去「上坡」(到地裡幹活兒)也是一件頗具儀式感的事情。父親會用大容量的塑料水桶,灌滿涼白開,挑選一件趁手的農具,穿上一件外套,再揣個蘋果。休息時,他和母親會坐在自留地邊的陰涼地,吃上一個。
風吹過來,整個場里青綠色的麥田翻湧,發出「刷刷」的聲音,成熟的麥田,則多了「沙沙」的硬朗。
場邊的地離家不遠,母親做好飯後,在門口的斜坡上喊一嗓子,在田里的父親就會聽見應一聲。
等到太陽掛在西山頭上,一天的勞作結束,該「放工」了。回家的路上,父親的語調都會輕快很多,一路上招呼著鄉鄰,「走啊,放工啊。」有時,他們會蹲在地頭,吃上一顆煙再走,相互交流下今天的鋤地進度。
 父親站在地邊。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父親站在地邊。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土地連著土地,也連著生長在土地上的人們。
耩麥子要用耩子(一種人力播種工具),需要後面一個人扶住,一邊掌握住方向,一邊搖動耩子漏下麥粒,前面要有人用繩子往前拉,需要幾人合作。因此,種麥子時,大多要幾家一起選定日子,同進同退。
扶耩子的一般是經驗豐富的老人,麥粒漏下去的多少,掌握著來年麥子的稀疏程度。爺爺在世時,他總是扶耩子的那個人,後來,這個人換成了父親。
種地需要相互幫襯,但鄉鄰之間又是界限分明的。比如,土地的界限必得清清楚楚,種地瓜的田壟開到相鄰的地界,必須得往自己地裡挪個一兩拃,好不越界,這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但站在各自的自留地上,大家又總能把距離拉近。
每年翻土時正值春夏交接,氣溫升高,父親常常會脫了鞋,光著腳踩在涼地裡,揮舞著钁頭。一同勞作的村人會扯著嗓子聊天,誰家的羊賣了多少錢,誰家的狗生了多少隻小崽子,誰家又有了新鮮事。愛聽戲的四大爺提著女兒給他買的唱戲機,安放在地頭兒,黃梅戲、二人轉能唱一天。
鬆土,上肥,提前打出壟,一場雨過後,播下花生種子,或栽上地瓜秧苗,疏苗、翻秧,耐性等待,它們會隨著時令自然生長。
農民總是萬分感恩土地的恩賜。每年正月初十,父親都要帶著香和紙錢到場邊上的自留地裡,祈求土地神保佑土地肥沃,五穀豐登。
5
土地像一個橋樑,連著家鄉和我的精神世界。
每年,我會離開這裏,走出村道的水泥路,駛過柏油馬路,來到看不見黃土地,也看不見麥子和玉米的城市,兀自生長著,步履匆匆,疲於奔命。
假期回家,總會路過這片父親的自留地。它有不同的顏色,麥子和夏玉米在這塊地上輪播,青黃也在交替;幾年後,棉花的花會開得五顏六色,再過幾年,綠色的花生葉間,會冒出星星點點的黃色花。等到種下地瓜,深秋,幾場霜打過秧苗,地裡一片青紫。
從小在土裡打滾的土孩子,好像只有在重新踏上這片土地時,才會有徹底的踏實和心安。
我想,父親或許也是如此,閑的時候,他總要跑到他的地裡,去轉轉看看。
 後山上的土地,以前爺爺在這裏承包了大半片山。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後山上的土地,以前爺爺在這裏承包了大半片山。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作為一個農民,他有他對土地的親近和尊重。
前年,隊列特高望重的大爺去世,葬在了他家的桃樹林里。他是村里的小學老師,一生教書育人,生前他常常在清晨,或者下班後的黃昏,蹲在桃樹林的地頭,吧嗒吧嗒地抽菸。如今,他蹲的那個地方已經是一座墳塋,墳前的鬆樹,已經長到兩人高。
場邊的地依舊是父親的自留地。他早早打算好,百年以後,他也想安頓在那裡。現在他能做的,就是種好每一顆莊稼。
十年前,他在這塊地上種了名為「早黃金」的桃樹,一種在春末秋初生長成熟的金黃色的桃子。每到下雨的時候,父親就得扛著鎬頭,去把排水溝挖好,以防水流到地裡,或者帶走更多的土。
去年,麥場北側的澇灘被填平後,水湧到地裡,桃樹澇死了大部分,僅剩了幾棵。父親請來了挖掘機,挖走死掉的樹,平整了土地,來不及傷感和遺憾,他得為下一個播種季做打算。
無論經歷了什麼,都得往前走,這是土地教給他的,也是教給我的。
新京報記者 趙敏 編輯 楊海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