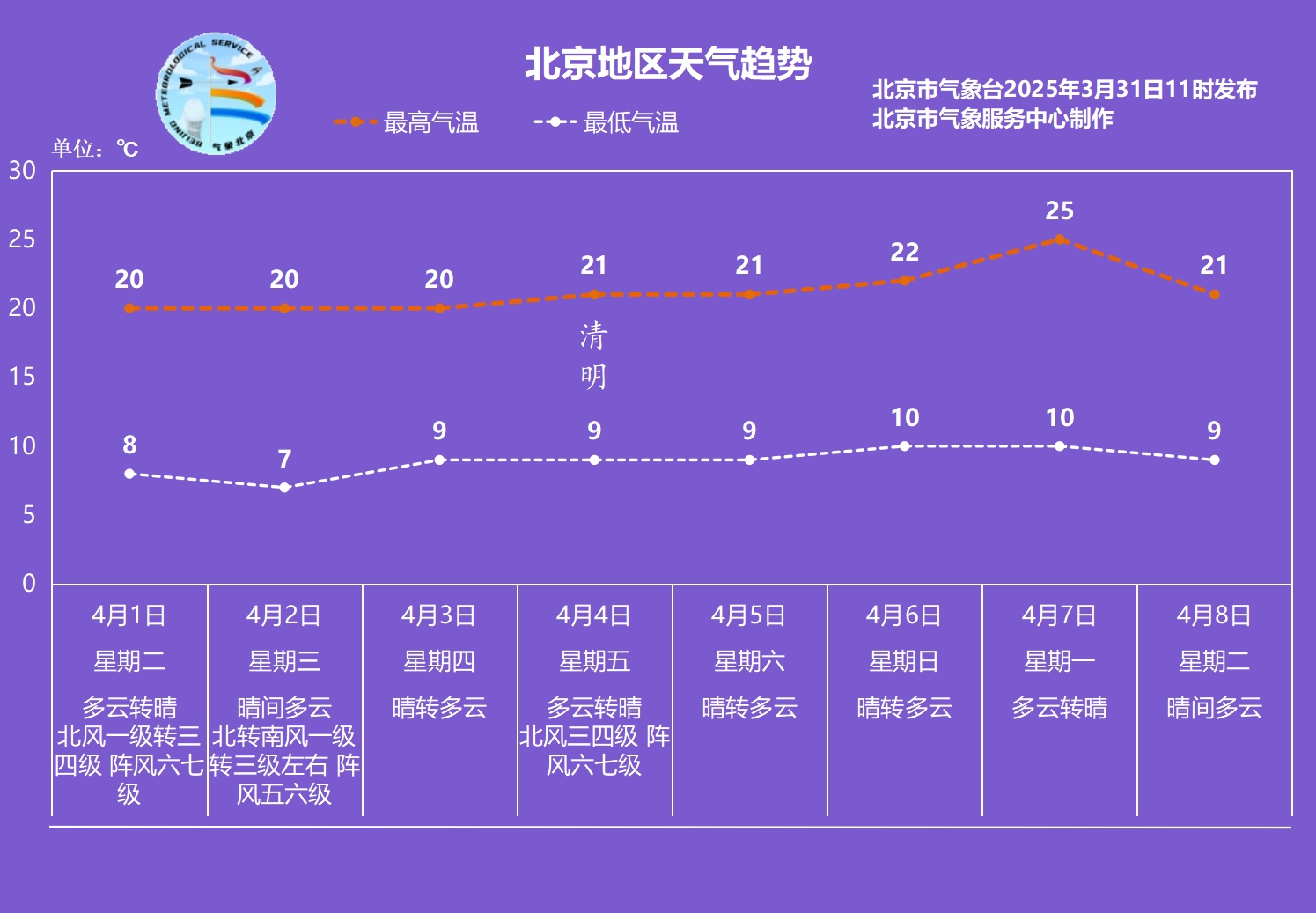「結婚」七八次,女孩出租自己,看盡酸甜苦辣
來源:南風窗

「95後」成都女孩曹玫又「結婚」了。最頻繁的一年里,她「嫁」了七八次。
這些婚禮散佈在不同的地區,有的在城里,有的在農村。每一次婚禮現場,曹玫都像初次結婚的新娘那樣,穿著婚服,融入喜慶的氛圍。
其中一次,現場宴請了300多桌賓客,整個村子的人都來了。不過流程很簡單,甚至沒有請司儀。婚禮現場有個大檯子,男方父親上台致辭幾句後,直接開席了。
台下來賓不知道的是,這是一場「假結婚」宴席。台上這對新人見面不過幾天,而曹玫是租來的「假新娘」。
扮演他人現實生活中的角色,是曹玫的職業。「女友」是她最常扮演的角色。聯繫上她的人,大多說著實在沒有辦法,而後委託她以假「女友」身份回家見父母、拍婚紗照、訂婚,或是辦儀式。
行業內,這份「出租自己」的工作也被稱為「生活演員」。他們進入僱主的現實生活,根據僱主的需要,扮演各種身份,如父母、伴侶、朋友、領導等,滿足來者在特定場景的需求。
租來的「幸福」
第一次見「家長」時,廈門人張赫緊張得不行。那五天,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保姆」。
他每天一早起床,白天做飯,晚上煲湯,還幫忙做了不少家務活。行動上勤快的同時,他沒忘記關心「女友」,叮囑對方穿暖和,不要著涼感冒。
這些行動明顯奏效。在「女友」的母親眼裡,張赫是一個符合標準的「女婿」,所以她安心回到日本,把女兒「交付」給他。
這位母親不知道,她登機以後,張赫趕忙買機票飛回福建,不帶一點猶豫。
那些噓寒問暖,只發生在「女友」母親在場時。回想起那幾天,張赫甚至覺得「有一點受不了」,因為太過勞累。

「90後」的張赫是名兼職生活演員。對他來說,這是在主業「汽車陪練教練」之外的一份 「額外收入」。他偶然接觸到了這一行,並在社交平台上發帖出租自己。後來,上述「女友」找到了他。
女孩出生於1995年,東北人。七八歲時,她隨父母去了日本生活,一家人定居日本,直到不久前才回國。女孩想留在國內工作,但父母不放心她一人,希望她回到日本。所以她謊稱在國內找了個男朋友,甚至已經懷孕。
在編織的生活劇本里,生活演員們總能討得僱主家人歡心。因為這種時候,他們並不完全是其自己。那些「完美形象」,通常由僱主和演員雙方合力堆砌而成。
正如見面當天,張赫會提著女孩提前準備的禮物登門,表現得禮貌謙遜。在家長面前,他會主動幫廚,盡顯貼心。
面對提問,他就按照事先商量的劇本回答,比如家長問家鄉習俗,按真實情況說;問什麼時候結婚領證,必須留餘地,說「等事業穩定」。張赫強調,每一句話都要給僱主「留退路」。

曹玫的準備更細緻。一些僱主會給曹玫安上全新的身份,比如年齡、職業、學曆,甚至是姓名。赴約前,她會提前背誦好這些基本信息。很多任務並非一次就終止。她甚至建了客戶信息檔案庫,每次合作前都會溫習「人設」。
每次見家長前,曹玫會提前根據僱主要求調整穿衣風格。若無特別要求,她會穿得文靜些,儘可能迎合長輩的喜好。見面時,她會按照提前商量好的劇本應答,遇到超綱的話題,「儘量轉移,或者不給明確的答案」。
一些時候,父母們也知道這些「幸福」是假象,但世俗觀念推著他們加入隊伍。
曾有家長找到曹玫,希望幫自己的兒子租個女友。那位母親說,自己的兒子曾交過一任女友,兩人交往一年,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後來,兩人因男生家境差而分手,但他們的戀情早已傳遍鄉里,且婚期早已定下。無奈之下,男方家只能租個假女友頂替完成婚禮。
「租人」生意
「一場戲能把份子錢收回來,何樂而不為?」28歲的陸荏說出自己找生活演員的想法。
事實上,陸荏的父母很開明,鮮少催婚。讓她困擾的是親戚的催婚話術——可以談戀愛了、該找個對象了,這些聲音總試圖提醒她「到年紀了」。不過比起催婚,她更在意的是那些隨出去卻還沒收回來的份子錢。
陸荏於是萌生了租演員辦酒席的想法。在她看來,這是場「各取所需」的交易,演員賺薪金,她收回人情債。
和陸荏類似,大多數客戶在現實生活中面臨著各種壓力,卻無法找到合適的方式解決,於是選擇找生活演員來扮演自己的伴侶或父母,以暫時緩解家庭的矛盾,滿足家人和社會的期待。一些時候,父母是婚姻的「門檻」,跨不過去的孩子也會找生活演員當「跳板」。
40來歲的肖曉霞在昆明兼職做生活演員。她曾「以母親」身份,坐在陌生女孩的男友對面,故作自然地詢問對方的工作、家庭。

找上門的僱主多為年輕女孩。有人因父母反對其遠嫁,希望她假扮母親與男方家長見面結婚;有人雙親離世,但結婚前要見家長,擔心男方家介意,委託肖曉霞來假扮母親。
這些需求,也讓生活演員這個行業逐漸有了市場。曹玫便看到了其中的商機。2018年,朋友因被家裡催婚,請曹玫假扮女友見父母。這次經歷讓她發現了生活演員這一職業,並進入了相關的群組。
這八年來,曹玫幾乎每年都在「結婚」,估算下來,大約「結」了20次,見父母的次數更是數不清。這些訂單多集中在過年過節,老僱主居多。
在生活演員的業務里,扮演男女朋友是「重頭戲」,尤其在過年期間。「年前我們有1000多單,基本上就是扮演男女朋友。」某經紀公司負責人李宇說。
當有需求出現,李宇會通過兼職群匹配合適的生活演員。這些群組成員大多為群演,平時也會去拍短劇、跑龍套。要是群裡沒有合適人選,他就會通過別的「中間商」再去找人。他號稱能匹配任何需求,「目前全國所有城市都可以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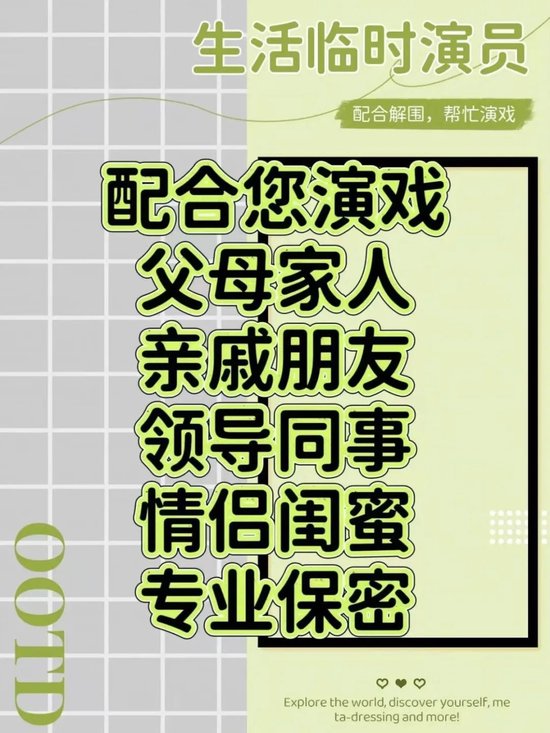
一則生活演員宣傳廣告
不過,這個行業並沒有具體的收費標準。另一「中間商」陳熙說:「就像殺豬一樣,肥的可以多搞點肉,瘦的少搞點,覺得不合適了就放棄。」他通常會根據僱主的朋友圈或對話,瞭解其需求和經濟能力後「看人報價」。
他說,在雲南當地,最低收費大概是1000元/天,一線城市則可能漲至1500元/天,甚至2000元/天。這些錢經中間商轉手,到生活演員手上的份額也各不相同。
曹玫剛入行時,收費通常是600—800元/天,如今漲到1500元/天。若遇上節假日,價格則可能更高,同時,報價也根據拍婚紗照、訂婚、辦酒席等不同需求變化。
但隨著市場供給增多,競爭也愈發激烈,出現了幾百元一單的低價競爭。僱主開始「貨比三家」,同行則靠「話術」搶單,騙子也混跡其中,這讓曹玫接單變得越來越困難。
謊 言
想要採訪生活演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主要出演影視劇、短劇的演員告訴南風窗,很少有人願意向陌生人講述這份經歷。在他看來,生活演員類似「當托」,若被外界知道,會影響個人聲譽。
李宇也表示,生活演員若暴露身份,可能會影響後續接單。
與普通演員不同,生活演員演的是現實中的真實角色。一次任務結束,他們還可能與僱主多次見面、電話、影片保持聯繫。身份一旦暴露,下次接單就容易穿幫。所以他們只能藏在「暗處」,不斷變換身份。

即便不是專業演員,從事這份工作的普通人也會有顧慮,畢竟它並不完全符合「正常三觀」。陳熙直言,「本質上它屬於欺騙」,而且訂單售後難保障,演不好「最多就是收不到尾款」,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生活演員群體人員複雜。陳熙管理的群裡有200多人,有五六十歲的長者,也有年青人。他們職業各異,有人平日兼職做保安、充場,還有人四處打零工,「只要給錢什麼都干」。
僱主付定金後,陳熙會按照需求提供照片供僱主選擇,直到活動當天,雙方才能互留聯繫方式。
他認為這種「信息隔離」能規避一定風險。但被問及如何保障僱主安全時,他也只是建議「一般還是不要找」。中間商們通常無法保證自己挑選出來的演員是否真的完全可靠。
早年租友就曾出現過性交易亂象。一些人表面接正規單子,到僱主家就變了樣,甚至威脅僱主「不加錢就揭發」。事情也是兩面的,部分顧客一上來就提過分要求。
曹玫還遇到過這種情況:她和僱主談好規矩,陪對方回家見父母,結果半夜卻收到是否可以「非綠」(即發生性關係)的詢問。她果斷拒絕,卻被認為是嫌錢少。最後,她只能放棄尾款,半夜拖著行李離開。
曹玫是個i人,這份工作被她形容為「i人地獄」。每次「結婚」、見「父母親戚」都讓她疲憊不堪。任務一結束,她就只想趕緊回家宅著。她將工作與生活分得很清,但頻繁的「演出」仍改變了她的婚戀觀。
她曾經期待一場獨屬於自己的婚禮。可參與多次婚禮後,她開始對婚禮流程感到麻木。期間,她窺見了許多家庭的代際矛盾,以及僱主們在催婚壓力下的痛苦。

這份工作的「出租」性質,更讓曹玫無法向家人坦白自己的職業。她覺得說了會引發誤會和矛盾,畢竟她自己第一次聽說「租女友」時,也曾將其與性服務聯繫起來。她只能謊稱在普通企業上班。
曹玫高職畢業後當過群演。那時為了幾十元的薪金,一整天耗在劇組。現在,她也放不下心態回歸普通職場,因為做生活演員接幾單的收入「都比上班一個月多」。
在這個行業,謊言往往一個接一個。
比如去年,那個東北女孩的母親回日本後,張赫的任務還沒完全結束。時至今日,對方仍以為女兒與張赫是夫妻。他說,女孩P了假的結婚證騙過母親,懷孕的謊言是以「流產」收場。
女孩母親得知女孩流產後很傷心,他的心裡也不好受。「可是行有行規」,他只能繼續配合。
「換一個角度來,這也是一個善意的謊言。」肖曉霞說。看到「女兒」們因此收穫幸福,她不希望自己的行為被定義為「騙」。
有時,她感覺自己真的多了個女兒。她曾假扮母親參加「女兒」的訂婚宴。女孩結婚時,她雖在國外旅遊沒能趕上,但她們的聯繫並沒有因此中斷。之後,女孩認肖曉霞作「乾媽」,逢年過節總打來電話。
曹玫也因這份工作結識了不少朋友和友善的「假公婆」。有些「戲」陸續演了好幾年,「假公婆」不時會和她聯繫,她也會給對方寄去成都特產。
曹玫說,在很多僱主家裡,善意的謊言比直白表達更有用。如今,她仍徘徊在真假交織的生活,面對僱主的家庭和自己的家人,不得不編造一個又一個謊言。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