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研究方式,如果可以改變
《經濟學家,請回答》是一本經濟學家對話經濟學家的集子。採訪者是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生於1924年,2023年去世,他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著稱,在1987年獲得盧保經濟學獎。
迪爾德麗·N.馬克洛斯基認為,索洛在20世紀是最懂得如何修辭、如何寫作的經濟學家。這本集子讓讀者知道了,索洛也是懂得如何提問的經濟學家。
晚年的索洛決定向他的同行們發起徵集,請他們從各自的研究專長回到一個經濟學問題。得益於索洛在經濟學界的號召力,此番徵集的受訪者陣容規模堪稱罕見,包括約瑟夫·斯堤格利茨、讓·梯若爾、堅尼斯·阿羅、阿比吉特·班納吉等。在年齡上,除了同齡人如佐治·舒爾茨,大多為索洛的晚輩。

《大空頭》(The Big Short,2015)劇照。
遺憾的是,因為這本書的形式是徵集,並沒有展開連續的對話。不過我們仍然能在90組回答之中讀到這些經濟學家如何理解當今世界,如何認識收入、女性、中產、工作等諸多議題正在發生的轉變。除了與現實經濟世界密切相關問題,索洛也向他們徵集對經濟政策以及對經濟學這門現代學科的看法。下文摘選內容,即是關於經濟學學科自身的看法。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經濟學家,請回答》第4、41、69等篇章。
標題為摘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文。
原文採訪者|[美]羅伯特·索洛

《經濟學家,請回答》,[美]羅伯特·索洛編著,許可譯,文彙出版社·貝頁,2024年10月。
為什麼全世界對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預測都如此不可靠?
以賽亞·安祖斯(Isaiah Andrews)
預測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無法用實驗驗證。政策製定者通過實施財政刺激政策或改變利率,來應對經濟形勢的變化。因此,當我們同時觀察一段時間內的政策和經濟狀況時,很難確定究竟是政策的實施影響了經濟走向,還是經濟變化影響了政策製定。
為瞭解決這個挑戰性問題,我們可以挑選出歷史上一些政策變化與經濟狀況無關的時期,然後研究政策變化後的經濟表現。然而,此類事件相對少見,本質上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以這種方法開展研究,只有較少的數據可供使用,而且可能會產生與正常時期的經濟政策效果差異很大的預期結果。

《大時代》(1992)劇照。
另一種方法是,我們可以通過將數據擬合到一個模型中來估測政策的效果。如果通過這樣的擬合模型 預測出的政策變化對經濟的影響,與我們預期的經濟自然演變的模式有所不同,那麼我們就可以從模型出發觀察數據,分析出其中的因果關係。但不巧的是,許多現代宏觀經濟模型並不能達成這一目的。即使我們假設這些模型是正確的,可用的數據量也不允許我們對政策的效果作出精確的預測。因此,在許多情況下,這類模型只能為我們理解因果關係提供十分有限的幫助。
由於模型充其量只是對現實的近似描述,因此,如果在估測政策效果時只追求模型對數據的擬合優 度,可能會加大錯誤建模的風險。只有能在數據中捕捉到經濟模式與政策之間關係的模型,才能夠幫助我們預測政策的效果。在實踐中,宏觀經濟模型與數據的某些方面擬合得很差,而且通常我們並沒有弄清楚這些建模誤差對模型預測結果的影響究竟如何。這樣一來,即使模型給出了精確的預測,我們也不確定是否應該相信這些預測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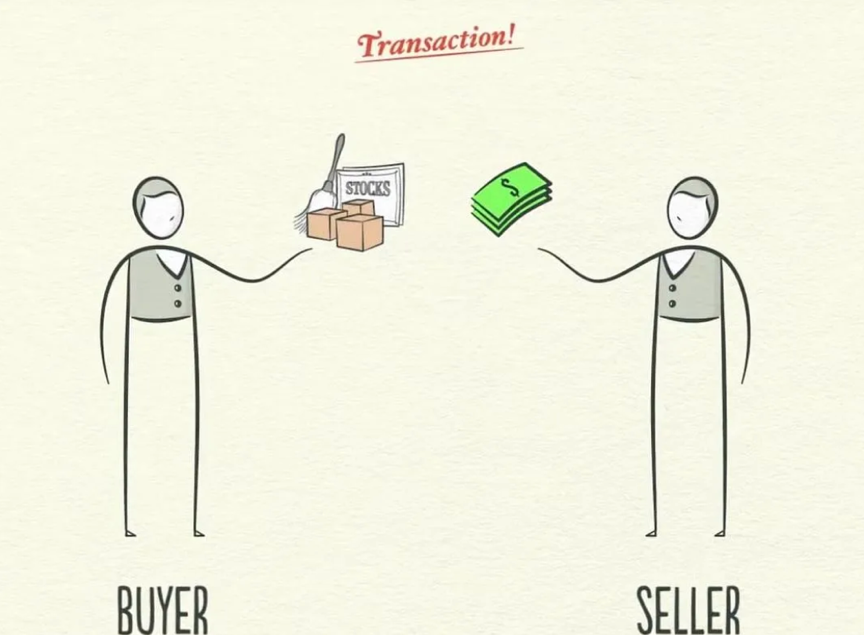
紀錄片《經濟機器是如何運行的》(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2008)畫面。
即便不考慮因果關係的問題,預測宏觀經濟的走向也並非易事。基於數據驅動的預測方法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即從過往模式中觀測出的信息有助於預測未來的狀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狀況也會發生變化,同樣的模式並不一定會持續下去。宏觀經濟學家必須認真思索應追溯多久以前的數據,這限制了可供分析的數據量。數據稀缺加大了宏觀經濟分析師面臨的挑戰。不過,最近的研究方法中使用了地區和個人數據,從而擴大了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時可用數據的範圍。
考慮到這一問題的困難程度,可以說即使我們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數據,對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預測 也乏善可陳。也就是說,這一領域在未來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一位心理學家在經濟學領域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在我與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於1974年左右開始研究賀拿悖論(Allais paradox)後,我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效用理論應用中一個奇特的假設所吸引,而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這一假設都是風險決策領域的主流理論。
我們所質疑的假設是由耶高比·伯努利(Jacob Bernoulli)在1738年首次提出的一項著名理論。他提出,在賭局中,人們是通過對可能出現不同結果的期望效用來評估選擇的,而人們心中認為的「結果」即賭局結束後的財富狀態。根據伯努利的模型,如果一個人有50%的可能性贏得100美元,或者確定能夠贏得40美元,那麼這個人會依據「我現有的財富」「比我現有的財富多100美元」和「比我現有的財富多40美元」這三種效用來評估賭局中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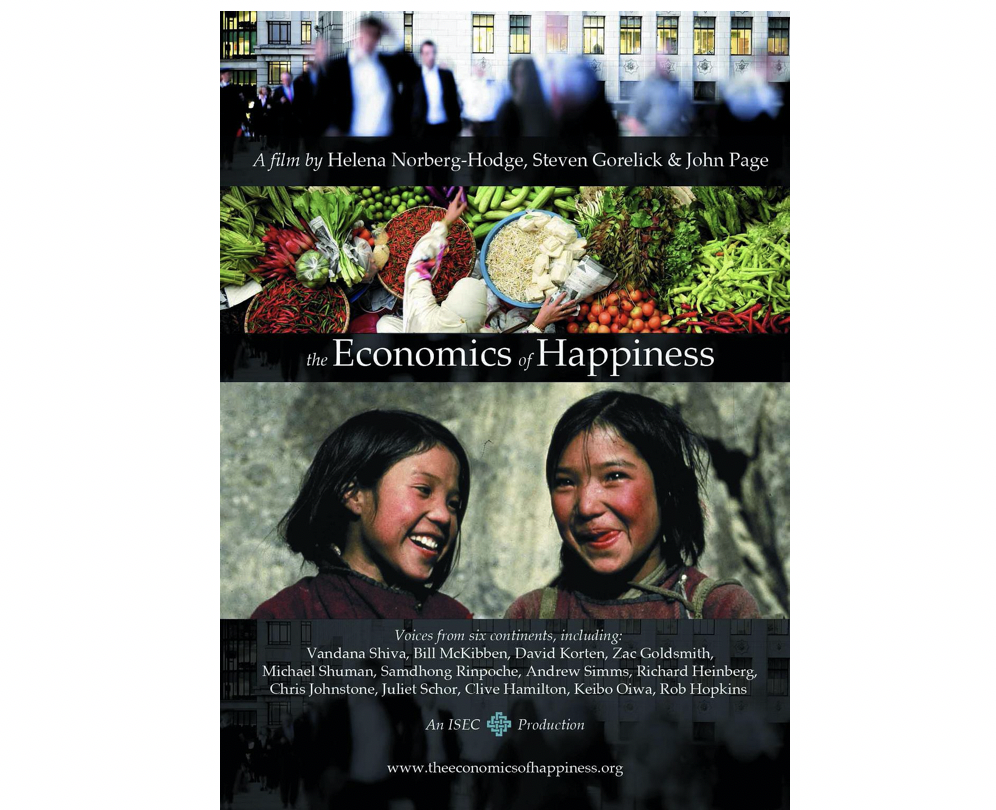 紀錄片《幸福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11)海報。
紀錄片《幸福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11)海報。伯努利在構建這一理論時針對的是體量巨大的金融決策,他的理論在解決商人把一艘裝滿香料的船從 阿姆斯特丹運到聖彼得堡的風險決策問題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在這個經典的船運案例中,已知損失船隻的可能性為5%,商人想要計算出自己能接受的保險費用。很自然地,商人會首先比較自己當前財富的效用和船隻沉沒後自己賸餘財富的效用。此例中,認為「財富狀態」等同於「結果」的假設是合理的,但如果不同結果體現在財富上的差別十分微小時,這種假設就顯得很牽強。
此外,在效用理論的應用中並沒有區分高風險和低風險的情況。因此,阿莫斯和我很快就決定提出一種全新的期望理論,將評估的對象定為「收益」和「損失」,並在小額或中等損失的情景下測試了理論的有效性。哈利·馬科維茨(Harry Markowitz)也曾在同樣的領域進行過嘗試,但我們的探索更為全面徹底。

《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劇照。
為什麼伯努利的不合理假設能沿用如此長的時間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被我稱為「理論誘導的盲目性」的現象。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學者是某一成熟理論的堅定支持者,就很難承認甚至很難去思考該理論存在的嚴重缺陷。
另一部分原因是,如果不使用伯努利假設,而選擇其他替代假設,人的選擇會很快被導向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方向。如果人們從收益和損失的角度思考效用,那麼特定財富狀態的效用將取決於與之相比的參考狀態效用。舉個例子,如果現在賭局中的兩個選擇是,有相等的概率獲得300萬美元或400萬美元,以及確定獲得350萬美元。這種賭局中產生吸引力的一項重要特徵就沒有體現在效用理論中,那就是當前的財富狀態。如果當前的財富為400萬美元,那麼相比當前的財富是300萬美元的情況,選擇冒險賭博的吸引力更大。財富狀態的價值似乎取決於賭局的結果,會因結果是輸還是贏而顯得不同。
還有其他觀察表明,損失的痛苦大於收益的快樂。但這合理嗎?這種差異似乎是短視的:一個理性人在作出財務決策時,不應該由近期財富變化的情緒反應所主導。在標準的經濟人假設中,理性的行為人是以財富狀態作為預期結果,進而作出評估和選擇的。
「理性人假設」在使經濟學問題變得易於數學化處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使在行為經濟學中,也有充分的理由繼續使用「理性人假設」。當然,簡化假設仍然適用的情況並不少見。然而,以李察·塞 勒為首的行為經濟學家在研究財富變化的短視效用時使用的競爭性假設就十分有趣,且令人耳目一新。以上,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卻混跡於與自己不同領域的學者中。
市場和語言的相似之處
艾雲·路斯(Alvin Roth)
市場和語言都是古老的人類智慧的產物,是我們人類為了更好地合作、協調、競爭和組織各種活動而 創建的工具。就像語言有許多類別一樣,市場和交易平台的種類也有很多。

紀錄片《經濟學大師》(Masters of Money,2012)畫面。
一提到市場,我們通常會想到商品市場。在這類市場中,出售的對像已經被標準化為商品,你在市場 中交易時便無須關心自己在和誰打交道。舉個例子,每塊麥田都各不相同,但芝加哥期貨交易(CBOT) 出售的是2號硬紅冬麥的合同,這是一種無須進一步考察就可以買賣的商品。所以在商品市場中,所有工作都圍繞價格來完成。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工作就是整天為它所銷售的每一種商品找到能實現供需平衡的價格。
但不是每個市場都是商品市場。在某些市場中,你會關心自己在和誰打交道。在匹配市場中,你不能簡單地挑選自己想要的東西(即使你能負擔得起價格),因為你也必須被選擇。史丹福大學在招生時, 不會採用把學費定得足夠高,以使學生人數剛好等於教室的容納量的方式;同樣,Google也不會降低軟件工程師的薪金,直到剛好有足夠多的工程師想在Google工作。
事實是,除非你被史丹福大學錄取了,否則就不能在史丹福讀書;除非你被Google聘用了,否則也不能在Google工作。所以,大學錄取和勞動力市場的本質是匹配市場。我們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些關口都會遇到匹配市場(如你不能簡單地選擇配偶,你也要被其他人選擇……)
我設想,如果有一位火星科學家飛來觀察地球人(假設這位科學家的研究重點是人類)的活動,那麼 其發回火星科學基金會(MSF)的第一份報告可能會這樣寫:人類總是在交談,而且總是在交易、協調、合作和競爭。也就是說,火星科學基金會將瞭解到,語言和市場是人類的基本工具。
一旦我們把市場看作工具,就可以開始思考如何充分地理解市場,以便在市場出現問題時進行修復,並建立起新的、更好的市場。這些都是市場設計的任務。
敘事經濟學是什麼?
羅伯特 · 施拉(Robert Shiller)
在1896年 的《 帕 爾 格 雷 夫 政 治 經 濟 學 詞 典 》 (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有一個關於「敘事經濟學」(Narrative Economics)的條目,但詞典中給出的定義並不是最新的,它寫道:「敘事經濟學或歷史經濟學中,不僅包括按縱向的時間順序敘述的過去事件,還包括對同期或不同期社會的比較。」根據這個定義,敘事經濟學與針對經濟事件的年代學或地理學研究就相差無幾了。
2017年,我在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演講中,針對「敘事經濟學」提出了一種不同的定義:敘事經濟學應該是將流行敘事作為經濟力量本身進行的研究。也就是說,敘事經濟學並不構建敘事,而是研究吸引公眾注意力的敘事—這些敘事其實在歷史事件的形成過程中一直有活躍的影響。敘事經濟學應該關注廣為傳播的敘事,這些敘事通過口口相傳或社交媒體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開來,並影響了數百萬人的經濟決策。過去重大經濟事件的敘事可以在早期報紙數字化的材料、書籍、講稿、日記、社交媒體和其他傳播途徑中找到。
我們應該記住,「敘事」這個詞不能與「故事」畫等號。敘事是敘述者從個人對世界的看法出發,講述故事、傳達理論或動機的過程。一個單一的客觀故事—比如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的故事—可以從無數個不同的角度來講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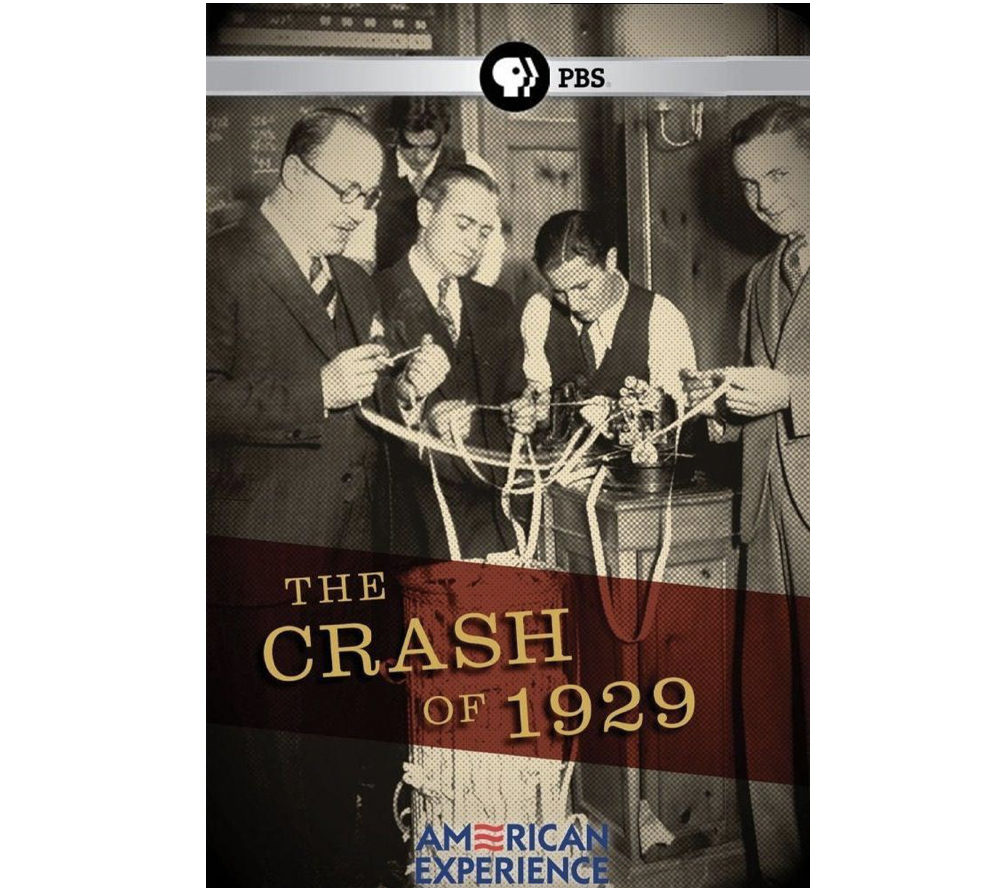 紀錄片《1929大蕭條》(The Crash of 1929,1990)海報。
紀錄片《1929大蕭條》(The Crash of 1929,1990)海報。1929年之後,一些觀點佔據了主流,大家遍相信「股災預示著即將到來的糟糕時代」這一故事敘述,導致人們對自己的未來切實地感到恐懼,並停止了消費。1929年至1932年,福特新車的銷量下降了近80%。大多數人認為他們完全可以在幾年內不買新車,直到不再恐懼。但由於人們普遍推遲購買車輛,汽車廠被迫關閉、工人遭遇解僱,大蕭條局面因此產生。
上述「敘事」甚至被銘記至今。現在,電視新聞廣播在每個交易日都會盡職盡責地報導道鍾斯工業平 均指數的變化,而《華爾街日報》在每個頭版的橫幅下方都會刊登這一信息。在1929年之前,道鍾斯指數並沒有這樣的市場影響—1929年的大蕭條讓道鍾斯指數知名了。今天人們仍然認為道鍾斯指數也許能夠預示另一次大蕭條。這是一種不會消亡的敘事,它在公眾思維中根深蒂固。有關大蕭條的說法在2007年至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再次出現,可以說,如果不是它重新點燃了公眾的恐懼,蕭條也不會如此嚴重。
與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相比,經濟學家對敘事的興趣要小得多,而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敘事的興趣相對較大。部分原因是經濟學家很難確定敘事和經濟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想知道如何證明一些流行敘事是否真的有效地影響了經濟行為。他們希望看到所有經濟活動影響因素的量化證據,這樣才能確定其在統計學上的意義。
而量化敘事影響的問題在於,敘事是複雜而模糊的。某一敘事的影響可能只取決於其中包含的幾個關鍵詞語。而敘事中細微差別的含義和對當時的人的意義,似乎需要依靠個人判斷才能解釋。
但是,如果我們要理解和預測經濟事件,嘗試系統地研究不斷變化的流行敘事是一條必經之路。
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學的方式,假如可以改變
李察 · 塞勒(Richard Thaler)
標準經濟理論最基本的特徵是,人們通過優化的方法來作選擇。也就是說,消費者在面對所有自己能夠負擔得起的商品和服務組合中,會選擇其中「最好的」一種。企業同樣採用優化方法,選擇最有效的生產過程並製定合適的價格,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別除了對市場的關注外,正是體現在其關於優化方法的這一假設上。但經濟學的這種特徵也是一個關鍵問題的核心:經濟學家會將最優化假設應用於兩項不同的任務,而它只適合解決其中一項任務。這兩項任務分別是:(1)描述一個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2)預測大多數人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實習生》(The Intern,2015)劇照。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考慮一個找工作的問題。假設查理失業了,開始找一份新的工作。他偶爾會得到 一些工作邀約,而他必須迅速地回覆是否接受邀約。如果查理回覆「是」並接受了這份工作,那麼他會停止找工作(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為了使問題更易於處理,經濟學家會作一些額外的簡化假設,通過建立模型來確定查理的最佳策略。解決方案會根據當前的經濟環境,準確地評估查理的市場價值。查理可以採取的一種策略是,確定一個合適的最低薪金(在已選擇了其他工作標準的基礎上)後開始找工作,直到找到這樣的工作機會,或者直到他意識到自己應該降低期望值。為這類問題尋找好的解決方案是一項相當有成效的工作。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會經常面臨類似的困境,例如,企業會面臨招募新員工或尋找新的供應商的問題。
而預測查理在找工作時實際會怎麼做,就是另一項完全不同的工作了。比如,查理可能過於在意對標 自己以前工作的薪資水平,即使他工作過的公司已經倒閉了,類似的工作選擇也很少;或者他可能對自己的工作前景有誇大(或貶低)的看法。再如,他可能會過分壓縮自己的求職範圍,錯誤地認為只要某一份工作與自己上一份工作差別很大,就完全不考慮,等等。在實際情景中,查理不採用優化方法而選擇其他策略的可能性不勝枚舉。但在一個僅僅基於最優選擇的模型中,上述所有因素都將被忽略。
因此,我對經濟學界的一個期望是,我們需要明確認識到一種理論不能同時滿足兩種目的。之所以存在錘子和螺絲刀兩種發明,就是因為不同的任務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來完成。研究描述性理論的學者仍然要掌握優化的藝術,但也需要發散思維,瞭解人們在實際中會採用的各種次優策略。社會科學其他分支的研究結果以及一些處理大數據的新工具(如機器學習)可能對完成這項任務有所幫助。此外,抽出一些時間,觀察現實中人們的行為,也會對研究有所幫助。
原文採訪者/[美]羅伯特·索洛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