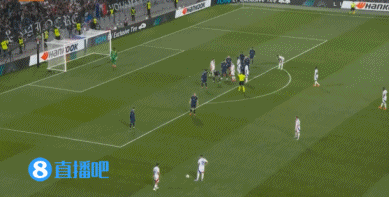為陌生孩子捐母乳
三月末的晨光斜照進西北婦女兒童醫院采奶室,何曉靜正將電動吸奶器的旋鈕調到第五檔。機器細微震動,她在捐贈卡的背面空白處寫下:「給不知名的小朋友,祝你早日回到爸爸媽媽身邊。」
這是她本月第二次捐贈。
五天前醫院公眾號推送的招募文章里,嬰兒蜷縮的姿勢讓她想起五年前,保溫箱里三斤二兩的女兒像只小蝦米,護士用1ml注射器喂下第一滴捐贈乳,那個瞬間曾被丈夫用手機錄下。如今二胎小女兒已經能抱著奶瓶「噸噸」直灌,她便把每月兩次的捐乳寫進日程里。
采奶室外的登記簿上,記錄著不同軌跡的溫暖。
寫字樓里的白領媽媽利用午休時間匆匆趕來,尚在月子裡的新手媽媽裹著厚圍巾來捐乳,最遠的捐贈者來自距離醫院24公里以外的灞橋區,天不亮就起身,換乘兩趟公交和地鐵,抵達醫院。她們穿過晨霧而來,只為給保溫箱里早早降生的孩子們送一口生機。
這些帶著體溫的液體正在實驗室玻璃器皿中流轉。
被採集的母乳經過細菌學檢測後,進入巴氏消毒流程,消毒後按量分裝,分配給不同需求的患兒,幫助他們抵抗壞死性小腸結腸炎、視網膜病變,以及其他感染性疾病的風險。
2013年,國內首個母乳庫在廣州誕生,此後十二年間,三十餘處生命驛站在全國九省紮根。微小而普通的故事,逐漸擴散成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愛心接力,而再往前一步,仍需整個社會的共同托舉。
 近日,西北婦女兒童醫院新生兒科重症監護室里接受捐贈人乳的早產兒滿月。 受訪者供圖
近日,西北婦女兒童醫院新生兒科重症監護室里接受捐贈人乳的早產兒滿月。 受訪者供圖「孩子們不怕任何困難」
3月16日,新生兒重症監護室里,安靜得只能聽見監護儀規律的滴答聲。護士長王茜把聽診器在掌心焐熱了,才輕輕貼上30周早產兒巴掌大的胸膛。孩子體重剛過800克,青色的血管微微跳動,皮膚薄得像浸過水的紙。
針管里的乳汁泛著琥珀色,順著鼻飼管慢慢遊走,這樣的孩子暖箱里還躺著十四個,最輕的400多克。王茜數著推注器的刻度,一毫升足足推了三分鐘,早產兒的腸胃薄如蟬翼,鼻飼喂養每天要進行多次。
三十二周前降生的低體重嬰兒們正用未發育完全的腸道對抗世界。由於無法耐受配方奶,而母親們又因為術後併發症導致泌乳延遲,早產兒們不得不依賴母乳庫中的捐贈乳。
在新生兒科,母乳庫是專門保管愛心母乳的「銀行」。工作人員從健康的哺乳期母親那裡收集多餘的母乳進行儲存。檢測合格的母乳將會分發給有需要的患兒。
母乳庫的歷史可追溯至1909年的維也納,美國與德國於1919年也相繼建立母乳庫。中國第一家母乳庫成立於2013年5月,位於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截至目前,全國約建立了35家母乳庫。
王茜的登記簿里記錄著更精確的數據。
西北婦女兒童醫院的母乳庫成立於2022年4月,曾接受過490位愛心媽媽捐贈的母乳,總量469819毫升,這些珍貴的母乳已為703名早產寶寶提供生命營養支持。其中,獲益的早產寶寶最低出生胎齡僅24周,最低體重僅有400多克。
其中,九成的捐贈母乳優先供給了體重不足1500克的早產兒。這些特殊醫療用乳需憑醫師處方使用,主要針對腸道發育不全、術後恢復或伴有先天免疫缺陷的新生兒,成為他們抵禦感染的關鍵支持。
「以前早產兒數量沒這麼多,庫存的捐乳夠用,充裕的時候,冰箱里都是滿的。」過去一個月,西北婦女兒童醫院新生兒科收治的早產兒數量激增。王茜清點著所剩無幾的儲奶瓶,按當前日均消耗量計算,現有的母乳存量,只夠15個需要捐乳的新生兒再吃三天。
 西北婦女兒童醫院母乳庫。 受訪者供圖
西北婦女兒童醫院母乳庫。 受訪者供圖但問題遠比數字更緊迫。
從事新生兒護理工作多年,王茜深知,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早產兒的萬里長征就開始了。她說,早產兒因器官發育不全面臨多重生存挑戰,想要存活下來,要過很多關,呼吸關、感染關、營養關,尤其是對於30周前出生的早產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敗血症都是他們要抵抗的危險。
2017年,由中國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兒童保健學組和中國醫師協會兒童健康專業委員會母乳庫學組共同發表的《中國大陸地區人乳庫運行管理專家建議》中指出,科學研究已證實母乳含有早期嬰兒生長所需要的所有營養成分和重要抗體,是新生兒最理想的天然食物。
但當各種原因導致親母母乳分泌不足或母親由於疾病影響不能直接哺喂時,捐贈人乳可作為替代喂養的最佳選擇。捐贈人乳不僅是新生兒的營養來源,甚至已成為臨床醫生治療性藥物的選擇,其對早產兒的近期和遠期影響毋庸置疑,如降低喂養不耐受、減少壞死性小腸結腸炎、膿毒症以及其他感染的患病率和病死率,縮短住院天數,提高精神發育行為評分等。
情急之下,西北婦兒醫院新生兒科啟動了緊急預案,他們決定在網絡上公開呼籲愛心媽媽前來醫院捐乳。
王茜逐字核對即將發送的稿件:「需哺乳期10個月內」「無菸酒史」「通過血清學檢測」,這些嚴苛條件曾勸退過無數熱心人,但現在,他們必須把網撒向整座城市。
推文在3月16日上午9點40分發佈。王茜守著後台,閱讀量從幾百跳到兩千,她不確定會有多少媽媽來捐獻母乳,但在她看來,「孩子們不怕任何困難,只要你幫他(她),他(她)就往前闖。」
 愛心媽媽將富餘的乳汁存放進儲奶袋,捐贈給母乳庫。 受訪者供圖
愛心媽媽將富餘的乳汁存放進儲奶袋,捐贈給母乳庫。 受訪者供圖媽媽們的力量
3月18日,清晨7點,天剛濛濛亮,小蘇拎著冰盒走進醫院。這是她產後第十八天,也是女兒住進新生兒重症監護室的第十八天。分娩時女兒因嗆入羊水總是不見好。小蘇每天雷打不動送的母乳,成了她唯一能替孩子做的事。
護士核對標籤時,她聽見值班台里的對話:「三十週早產兒乳糖不耐,得調兩袋捐贈奶。」小蘇低頭看冰盒里的奶。自家孩子吃不完的份量,攢著也是攢著,重症室里那些皺巴巴的嬰兒,若能用這些奶少打幾針抗生素總歸是好的。
很多捐獻母乳的母親都有相似的經歷:她們的孩子曾住進新生兒重症監護室,或得到過他人幫助。正因如此,她們更能體會其中的焦心滋味,一些生下二胎三胎的媽媽們成為捐贈者。
32歲的何曉靜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五年前頭胎生女兒時,孩子落地只哭了兩聲就沒動靜了。何曉靜清晰地記著,女兒小臉紫漲著,裹在藍布包被里,護士抱去搶救,留她盯著產床頂的白燈發怔。
孩子在新生兒科養了近倆月。那些日子,何曉靜最熟悉的是重症監護室里的病床,探視時間,她扒著重症監護室那扇窄窄的窗戶往里看,三斤四兩的小人兒臥在暖箱里,身上纏著蜘蛛網般的管子。
二胎產後第4個月,何曉靜在網上看到了西北婦女兒童醫院母乳庫告急的消息後,想都沒想就來醫院捐獻母乳。「陌生的母親,素不相識,你借我一捧雪,我還你三寸冰往來著。」她說,媽媽們就是這樣,一代又一代的,在受捐與捐贈的過程中形成了循環接力。
李霞也是愛心媽媽中的一個。撥通新生兒科的電話時,她正彎腰整理冰箱里的儲奶袋。產後五個月,女兒每次喝奶都像啄米的小雀,喝夠120毫升就扭頭吐奶嘴,冰箱雪藏室快被塞成了馬賽克牆。
在電話裡護士告訴她,上週收治的26周寶寶體重剛過400克。李霞看向旁邊熟睡的女兒,突然覺得鼻子有點酸,五個多月大的孩子,在此刻顯得格外沉實。
通話持續了2分17秒,之後李霞決定立刻前往醫院。
捐獻母乳的過程並不複雜,簡單的宣教後,李霞洗淨雙手,用濕巾清潔乳頭,在醫用電動吸奶機幫助下,乳汁漸漸連成細流,沿著瓶壁彙集到奶瓶中。
她盯著奶瓶中不斷上漲的刻度線,想起女兒每次喝奶前急吼吼的小模樣,嘴角不自覺地揚起來。大約四十分鐘後,她捐獻了490毫升母乳。
招募愛心捐乳媽媽的信息發佈幾天后,西北婦女兒童醫院新生兒科的座機徹底甦醒。
此起彼伏的鈴聲不斷衝刷護士站的寧靜。「我在哺乳期,寶寶剛滿四個月……」電話總是這樣開場,有人問得急切,像是要抓住轉瞬即逝的哺乳期窗口;有人輕聲細語,反復確認捐獻流程是否會影響自己懷中的嬰孩;還有人說著說著就哽嚥了。
 3月19日,捐乳的媽媽收到西北婦女兒童醫院頒發的愛心媽媽證書。 受訪者供圖
3月19日,捐乳的媽媽收到西北婦女兒童醫院頒發的愛心媽媽證書。 受訪者供圖「當媽後,見不得任何孩子受罪」
醫院消毒水的氣味在何曉靜的衣服上停留了許久。
從醫院回家的路上,不足三斤的早產兒蜷縮在保溫箱里的畫面反復閃現,她想發動更多媽媽為有需要的早產兒捐贈母乳。丈夫提出了一個建議:「要不把捐乳的故事發在社交平台上試試?」
手機備忘錄里的文字增刪了多次:「產後十個月內,母乳充足的母親,可以捐贈給西北婦兒醫院母乳庫。」光標在注意事項的段落停留良久,最終,何曉靜在帖子最後添上一行字,「每個孩子都應該被愛著。」
發出的文字像石子入井,直到第五天半夜才泛起第一圈漣漪。
28歲的玲玲是第一個看到帖子後聯繫何曉靜的媽媽。一開始,玲玲客氣地向何曉靜請教捐乳需要準備的體檢報告。
接著,她們開始互相分享自己孩子的日常以及對於早產兒的心疼。從那一刻開始,她們彼此都體驗到了一種特殊的聯結感,是人與人之間、母親與母親之間的強烈聯繫。
這種聯結以具象的形式生長。幾天后,她們相約一起到醫院捐乳,兩個母親並排坐在一起采奶,那是一種難以描述的複雜感覺。
玲玲說,當媽後見不得任何孩子受罪,會發自內心地心疼,這種偏愛並不限於自己的孩子,公交站台嬰兒車里的酣睡面孔、超市收銀台前揪著糖果袋的小手,都會讓她不自覺地放緩腳步。
帖子發出後,何曉靜成了信息中轉站。她的手機開始頻繁震動,後台顯示已有十幾個陌生媽媽發來私信,詢問捐乳流程。
陌生人的留言大多是暖心的。最讓她觸動的是來自一個早產兒媽媽的留言,那位母親寫道,「我的寶寶1130克,吃了五個月好心媽媽的母乳,現在他學會翻身了。」
但質疑的聲音也逐漸在評論區集結。「別人的分泌物多髒啊」「為什麼非要別人的奶喂給孩子?」「誰知道這些媽媽有沒有偷偷抽菸喝酒?」類似的評論在母乳捐獻相關的帖子下面堆疊了兩頁。
何曉靜不生氣,反而覺得更多人關注母乳捐贈是好事。她截屏保存了那些質疑的評論,連夜篩選出近五年有關母乳庫的學術論文,用紅線標註「母乳降低早產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發病率」等結論。
然後,科普長圖通過私信發出,接收者列表包含了13位曾留言「捐贈母乳不衛生」的用戶。
梁翠萍是廣州婦女兒童醫療中心臨床營養科主任、母乳庫的負責人,每日經手的乳汁進出記錄如同一本精密台賬,而她的工作就像一名倉庫管理員,把關著母乳的流進、流出。
她向新京報記者解釋,成為母乳捐贈者需要跨過一道嚴格的門檻。每位捐贈者在捐乳之前必須提供近三個月的HIV、乙肝、丙肝、鉅細胞病毒和梅毒檢測報告,並簽署無吸煙飲酒史的承諾書,以確保捐贈母乳安全。
不同醫院採取不同採集方式。部分醫療機構要求母乳捐贈者必須在院內專用吸奶室完成操作,另一些醫院允許捐贈者在家採集後24小時內冷鏈送達。
捐贈的乳汁在經過細菌學檢測、病毒檢測、巴氏消毒後,最終獨立包裝,標註好採集時間存入-20℃的儲存冰櫃中。每個標籤均印有可追溯的批次編號,如同一份份等待投遞的生命契約。
 北京華信醫院母乳庫頒發的捐贈證書。 受訪者供圖
北京華信醫院母乳庫頒發的捐贈證書。 受訪者供圖「希望未來母乳庫像血庫一樣」
很快,關注母乳庫的媽媽不僅僅局限在西安。
來自北京、河南、上海等地的媽媽們紛紛加入了這場愛心接力。她們自發組建了一個名為「幫助早產寶寶」的群。最多的時候,群裡有一百來人,媽媽們來自全國各地,年齡橫跨25歲到40歲。
關於捐乳的各類信息以碎片形式在群內流動。群公告置頂的在線文檔每日更新,羅列著全國27家醫院母乳庫的對接電話。
母親們不斷在表格填充捐贈量,北京寶媽將自己一個月內攢下的母乳全部送往了北京華信醫院,上海寶媽發來的儲奶袋照片上,標註的時間精確到分鐘……群中發送的語音消息背景音里,時常混入孩子的哭鬧聲。
流轉在陌生媽媽與早產兒之間的乳白色液體,串起了陌生人之間最樸素的善意。
與此同時,遠在廣州的梁翠萍也關注著有關母乳捐贈的最新動態。從業二十餘年,梁翠萍見證了母乳庫的發展歷程,她說,儘管關注母乳庫的媽媽們越來越多,但目前國內母乳庫的儲存量,遠遠不能滿足NICU(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的臨床需求。
「26周、28周的早產兒,放在以前幾乎沒得救,那時候家長都直接說不救了,醫生只能搖頭。但現在不同了,連2斤重的早產兒都有存活下來的機會。」梁翠萍認為,隨著醫療技術不斷提升、公益基金覆蓋了部分無力承擔的家庭,使得超早產兒存活率大幅度提升,對母乳庫的需求也成倍數增長。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婦產醫院兒科主任韓樹萍在《我國人乳庫建設面臨的問題及未來發展》中揭示了矛盾根源,當前母乳庫80%以上奶源依賴住院產婦的「餘糧」,但超早產兒母親往往自身泌乳不足。儘管近年來公益組織協助招募社會捐乳者,仍有不少母乳庫每月出現斷供的情況。
資金鏈壓力進一步勒緊母乳庫的咽喉。
梁翠萍告訴新京報記者,「每100毫升捐贈母乳的綜合成本約1500元,包括血清檢測、巴氏消毒、冷鏈運輸。」她逐項核算,所有的檢驗費用都由醫院負擔,雖然部分醫院獲得政府的專項補貼,但運營成本仍有缺口。
醫生的認知差異製造著另一重阻礙。資源充足的醫院可能更容易推廣捐贈母乳,資源有限的縣級醫院可能更依賴配方奶。同時,醫生的個人經驗和培訓背景也會影響他們的選擇,比如是否接受過相關培訓,是否瞭解最新的研究成果。
梁翠萍解釋,是否使用捐贈母乳要依靠主治醫生的診斷,有的醫生更瞭解母乳對於早產兒的好處,會積極給早產兒使用母乳庫的母乳。與之相反的,一些醫生則更加謹慎,他們認為,配方奶粉的營養配比更精準,或考慮患兒家長是否願意接受捐贈母乳的因素。
轉機出現在今年3月。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牽頭發佈的《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捐贈人乳應用與管理專家共識》,首次從循證醫學角度規範了人乳庫管理流程。
共識指出,親母乳汁不足時,應使用捐贈人乳,直至親母乳汁可以滿足早產兒喂養需求或體重達到1800克以上或校正胎齡達34周。
「以前各家自定標準,現在總算有把統一的尺子。」梁翠萍覺得,這是標誌性的里程碑,但母乳庫想要在全國範圍內提高聲量與影響力,恐怕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建設。這不僅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還要提升公眾意識和捐贈意願。
「我們希望未來母乳庫也像血庫一樣,每個城市都有一個母乳庫,統一管理捐贈母乳的收集、消毒、儲存、分發等工作,讓最急需的寶寶都能用上捐贈母乳。」梁翠萍說。
新京報記者 鹹運禎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