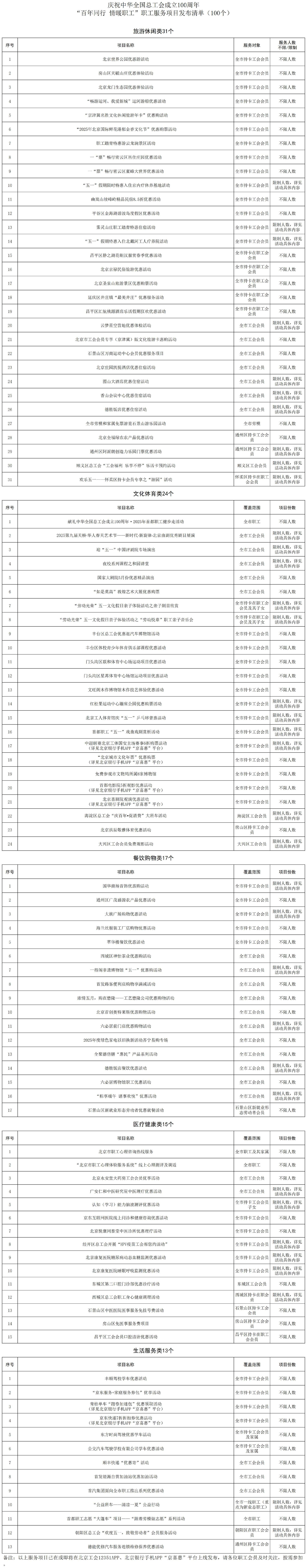對話《雁回時》導演楊龍:用「反叛精神」撕下傳統古偶的標籤|談藝錄
封面新聞記者 雷蘊含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封面新聞:《雁回時》展現了女主角莊寒雁的成長,並且有很多「女性互助」的情節,有許多網民將其稱之為一部「女本位」的劇集,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楊龍:我們在創作過程中,的確是有意識地想把主題上升到女性互助。我跟編劇老師一直在探討一個問題,我們覺得真正的女性力量體現應該是「自洽」,這也是為什麼陳拖連奴飾演的莊寒雁會被很多觀眾接受。她長得並不是很凶,但是她又有自己的堅韌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觀眾在看的時候可能就會覺得這個女孩,用她身上被別人稱之為柔弱的特徵去解決了所有問題,達到了目標。所以你剛才說這部劇是不是「女本位」,我覺得應該是的。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封面新聞:陳拖連奴之前演的大部分角色都比較偏「小白花」「白月光」的風格,但這次她飾演的莊寒雁讓大家看到她有更多的可能性。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陳拖連奴來出演這樣一個角色呢?
楊龍:在《雁回時》的創作過程中,我一直在想盡一切辦法讓所有的地方都不套路、不傳統,我想讓大家看到一個新的東西。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如果選一個看上去就「不好惹」的演員,這個故事也許就會落入俗套,可能她還沒演,觀眾就能猜出她下一步的行動。因此,當時選擇陳拖連奴來出演,一方面是她的長相氣質不那麼「狠」,另一方面是她和莊寒雁身上「堅韌」的特質很貼合。她非常認真,在表演上有一種「死磕」的精神,對於所有問題都一定要弄明白,而且會不斷反思自己。在播出過程中,她跟我聊得最多的就是「我這裏沒演好」「我很緊張」「我怕我後面有哪裡演得不行」等等。所以我覺得她身上這些特質很像莊寒雁,當然她自己也非常努力。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封面新聞:您覺得辛雲來和傅雲夕這個角色的貼合度高嗎?
楊龍:我們當時覺得傅雲夕的人設應該是非常有安全感的,這種安全感就相當於你看到一個人,不會覺得他心思很花哨、不可靠。當時見了辛雲來之後,我感覺他是一個不爭不搶、很放鬆的狀態,而且他的心態很好,不會特別玻璃心,所以我覺得他還蠻能給人安全感的,然後就選了他。
封面新聞:劇中阮惜文、宇文長安、周如音等角色也都很豐富立體,可以聊一聊這些角色和演員嗎?
楊龍:這次《雁回時》讓這些中生代演員都受到了觀眾的關注和喜愛,我非常開心。這些演員們對於角色都非常認真,因為在這部劇中,他們的角色都有很完整的故事線,發揮空間也很大。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封面新聞:莊寒雁和傅雲夕兩個人的很多行為都是「利益」和「利用」在驅動,這種人設和感情線的設計其實是不常見的,你們在創作的時候有沒有擔心過觀眾接受不了?
楊龍:我們覺得這種情感模式其實蠻成年人的。我們必須承認,生活中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一見鍾情的愛情,我們看到的大部分情況是在相親角裡邊,大家互相比較條件,對吧?古偶里的故事當然是給大家一些美好的幻夢,這是很好的,讓大家覺得生活有希望,對愛情充滿憧憬,但問題是如果大家都這麼寫的話,可能趣味性就有點低了。所以我們就想做一個新的內容,更加真實,莊寒雁和傅雲夕之間就是兩個人互相比對條件,然後覺得還挺合適,那就試試在一起,然後在這個過程中發現「我是愛你的」。其實這種感情很克製,傅雲夕和莊寒雁一直在克製他們的感情,但是越克製就越痛苦,我覺得這種掙扎和糾結比較有意思。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封面新聞:《雁回時》不算是一個很傳統的古偶劇,您自己會把它定義為一個古偶劇嗎?
楊龍:就像你說的,它確實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古偶,但是它也有愛情的部分。這個問題也要看我們怎麼看待古偶這個概念,大家現在很多時候都有給古偶打標籤的習慣,因為這似乎是一個讓創作變得更簡單的方式。但不得不說,這個類型實在太多了。現在短劇這麼流行,而且短劇中有非常多反套路的設計,其實對長劇也造成了衝擊,所以我覺得長劇也應該做一些創新。
封面新聞:所以《雁回時》在創作的時候有從短劇汲取一些靈感嗎?
楊龍:這個問題應該這樣來說,觀眾看短劇其實並不是因為它短,而是因為它戲劇衝突強烈。一部短劇2分鐘一集,一共100集,其實看下來也是3個多小時,和一口氣看5集40分鐘的長劇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在創作上應該做好的還是人物關係的設置和變化,以及懸念的製造,同時在其中進行創新,營造好氛圍感,使其能影響觀眾的情緒,才能帶給觀眾新鮮感。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
《雁回時》劇照。圖源官博封面新聞:當時拍攝用時多久?遇到壓力最大的事是什麼?
楊龍:壓力最大就是週期緊,我們只拍了106天。而且陳拖連奴的戲特別多,情緒起伏又特別大,所以她會比較累。但比較神奇的是,我們開播的那一天和去年開機是農曆的同一天,破3萬那天剛好又是陽曆的開機第二天。
封面新聞:您接下來的創作計劃是怎樣的呢?
楊龍:我接下來古裝戲可能會偏多一點,因為我覺得古裝戲的戲劇衝突會大一些,可以創新的地方也比較多。但是我一直覺得現偶也挺好,只是需要碰到比較好的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