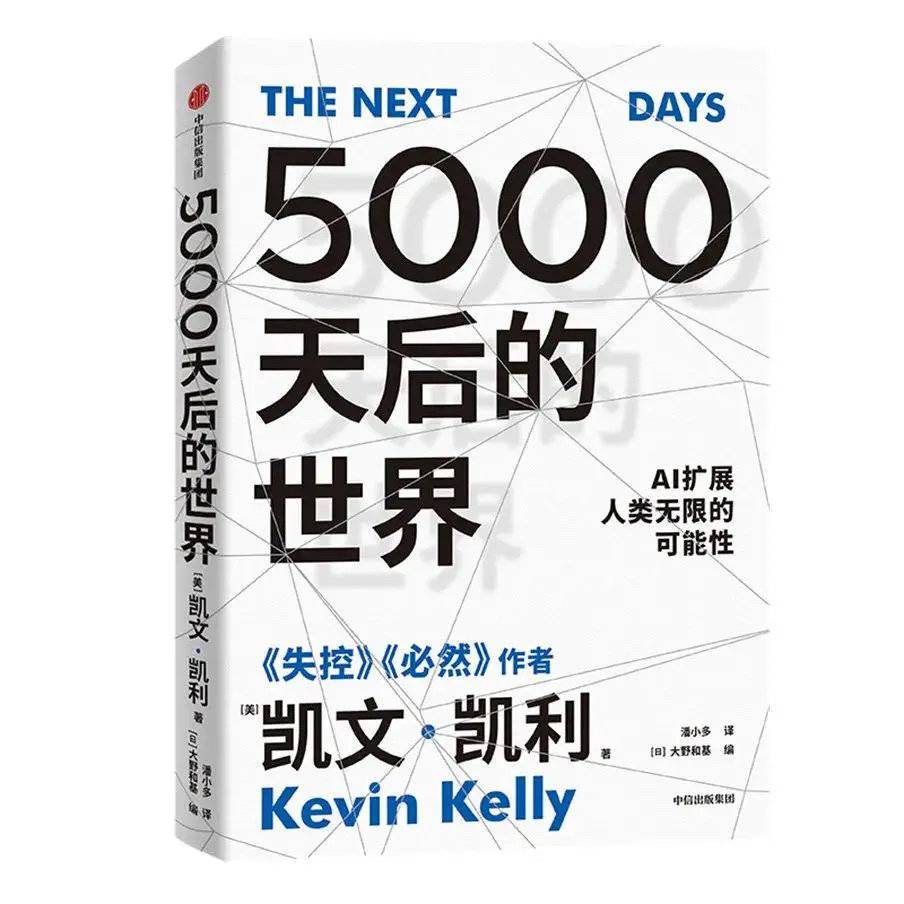引爆暑期檔的第一劑猛藥,又爽又噁心
 作者 / 西貝偏北
作者 / 西貝偏北編輯 / 朱 婷
運營 / 小餅乾
剛剛過去的週末,暑期檔被給予厚望的《抓娃娃》上演了一波假撤檔熱搜,不知道彼時多少電影人在家冒冷汗。幸而,只是虛驚一場。
一個不爭的事實:2024上半年年電影院行情不算樂觀,半年來240億大關未破,甚至有回到2015年網絡購票方興未艾的趨勢。博納影業董事長於冬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接受採訪時表示:“今年全年票房能否達到去年,就看暑期檔了。”所以,沈騰、馬麗主演的《抓娃娃》可不能撤。
焦點拉回近期被冠以暑期檔第一部小爆款的《默殺》,該片以三天破億、四天兩億的成績,淺淺“殺”出圈一下。燈塔專業版顯示,截止發稿,《默殺》累計票房為4.12億,多方預測最終票房平均值為13.5億左右。
和一路走高的票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搖擺下跌的口碑。同樣是社會議題,聚焦兒童教育問題的《年少日記》的8.4分;聚焦養老院虐老、性侵特殊兒童的《白日之下》7.9分;更早的聚焦高考升學與校園霸淩的《少年的你》8.2分,而集齊了校園霸淩、虐殺施暴者、絕地複仇等聳動的話題《默殺》僅有6.8分(還在降)。
與此同時,“現在不拍虐女就不會拍電影”話題高掛微博熱搜,不難看出觀眾對為了強調視覺刺激、而將鏡頭一次次對準被傷害女性的厭倦和反感。
一、量大管飽,然後呢?
相比於單一類型的極致探索,《默殺》主打的是一個“量大管飽”。
對於普通觀眾來說,抱著看犯罪片的期待進入影院,你會看到一個懸疑+驚悚+犯罪+邪典+砍殺+家庭+複仇的雜糅電影。但這並不是什麼誇讚,而是經典的陳思誠式元素堆砌。
故事本身不複雜:被校長女兒和她的擁躉們霸淩的女主,為了給同樣被校園霸淩致死的閨蜜複仇,和閨蜜父親達成合作,殺死了所有的校園霸淩者們,最後逃離自己恐怖的原生家庭。
沒錯,是天生讓人血脈賁張的複仇故事,柯汶利用他擅長的懸疑設置,倒轉因果,閃回+夢境+幻想亂燉,混淆真實與虛構。其中不乏有很多熟悉的影子,觀影過程堪比影迷找彩蛋。
(這是劇透線,介意者慎看~)
part1,校園暴力議題的青春片。
東南亞某國的女校,陰雨連綿,樹木蔥蘢,宗教+特權buff疊滿。你會看到《悲傷逆流成河》+《少年的你》里的校園暴力以一種更加殘暴、有儀式感的效果呈現。
女主是特殊教育班的啞女小彤(王聖迪 飾),被校長女兒安琪和三個霸淩女孩擄到廁所,把她頭髮用粘稠的澆水粘在廁所牆壁,十字架的造型猶如受難基督;而在此之前,她的好友惠君(徐嬌 飾)曾被安琪逼迫站在頂樓天台臨時補屋的透明玻璃上,在生日當天從樓上墜落到禮堂,當場死亡,頭上還戴著滲血的荊棘冠。
天台的鏡頭“早就壞了”,惠君以自殺結案;小彤的媽媽時學校的清潔工李涵(張鈞甯 飾),和校長關係匪淺,潛台詞用情色交易給小彤從普通班轉回特教班,這種痛感給了小彤和惠君父親充足的複仇動機。
part2,clut砍殺片。
你會看到東南亞恐怖片的經典橋段,三個小跟班的女高學生半夜不睡覺出來玩遊戲,相繼被面具男砍殺。剩下的安琪因為生病當晚沒去,僥倖逃過一劫。但她死得更慘,被放置的朋友手機誘騙到封閉的廢氣校車里,拿滅火器和男人搏鬥後,在一個煙粉瀰漫的校車里被殺死,中間用到了無數的jump scare技巧,一驚一乍。
part3,《消失的她》式懸疑片。
一邊,小彤消失,李涵開啟了母親尋女線。母愛四溢的李涵成了《九龍城寨》里的戰神,一路開大,懷疑學校的屋頂修理工林在福(王傳君 飾),就要爬空調外機進入他家裡,手上紮了釘子鮮血淋漓,還和沒事人一樣,儘是癲狂。
一邊,安琪死掉,警察開始了破案線。吳鎮宇把《無限超越班》的導師高光搬到了這裏,作為刑警戴,一舉一動都是厚重的表演感,奉獻了一驚一乍、盡皆過火的表演。長年來偷拍女性成癮的吳望(黃明昊 飾)既是嫌疑犯的虛晃一槍,他拍的dv又成了線索,記錄李涵曾經以母愛之名家暴過小彤,展現了母愛的陰暗面。
part4,暴走爹媽的複仇片。
惠君被霸淩時,小彤也在場,她想阻止卻被李涵拉扯走了,事後小彤撿到了霸淩者拍視頻的手機放到了小彤的櫃子裡,讓林在福看到,兩人由此開始開始打配合,一個在學校觀察提供信息,一個執行殺人計劃,事後,林在福把小彤藏在家裡的冰箱里拉走,讓她遠離一切是非。
可李涵卻不知道,她以為是林在福擄走了女兒,目的就是報復她們當時的不作為。因此你會看到低配版《涉過憤怒的海》里的父母開車,撞車後在地上互撕,林在福質問李涵有能力為什麼不幫自己的女兒,李涵只會機械詢問“我女兒”呢。
part5,原聲家庭之苦:家暴+性侵。
李涵的變態式母愛來自於小彤原生家庭之苦。在李涵嘴裡二婚、一直在廣州的老公是《別和陌生人說話》式的家暴男,她動了殺心想殺他時,正趕上9歲的女兒小彤在浴室被他性侵。
小彤快李涵一步,用剪刀手起刀落,提前殺死了家暴性侵的繼父,李涵把他種到了天台當肥料,滋養金桔,還製造了名場面——當她給別人送金桔時,都會補一句,“這是我老公種的金桔”,絕對的硬核種植。
期間還有以及《西虹市首富》里出圈的“臥龍鳳雛”和蔡明老師上春晚式的插科打諢橋段,非要在這種緊張嚴肅的時候塞一些不合時宜的喜劇。
故事的最後,林在福從天台摔下死了,李涵替女兒頂殺繼父罪坐牢了(沒有必要的設計,那個東南亞法律難道沒有青少年保護法?),小彤在《暮色迴響》中打開冰箱門,在晃蕩的卡車上走向未知的未來。
“反校園霸淩”的主題先行,複仇猶如砍瓜切菜,血飆到了銀幕外的觀眾臉上。
尺度確實很大,但這真是導演想給到觀眾的情緒共振嗎?
二、年紀輕輕就開始自我致敬?
壞消息,曾經翻拍了印度《誤殺瞞天記》為《誤殺》的柯汶利這次又在翻拍。
好消息,他翻拍的是自己2022年的同名獲獎作品《默殺》。
導演的創作生命有限,柯汶利為什麼要把原來拍過的東西再拍一遍?
功利來看,《默殺》作為導演的長片首作在電影節反響很好,證明其是一部有市場潛力的類型佳作,但演職人員多半來自台灣,缺乏內地市場,因此這次就是“內地特製版”,創作思路就是對著答案再做一遍題。
導演對作品質量的自信,也源於他初次創作時的真誠。影片靈感是柯汶利在台北攻讀碩士時看到了一則新聞,所報導的案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一個母親回家後發現女兒失蹤,於是開始挨家挨戶地尋找女兒,最終她發現了一戶可疑的人家,結果闖進對方家中後,在床底下發現了一個垃圾袋,袋子裡裝著女兒的屍體。
可悲的是,當時女孩遇害時弄出了很大的動靜,鄰居們明明都聽到了,但都覺得這是別人家的事情,沒有選擇報警,也沒把自己聽到的事情告訴女孩的母親。
這則新聞的震撼讓導演有了“默”的高概念:沉默者殺人,沉默著殺人,沉默就是殺人。
校園暴力屢次發成的根源,是階級差異導致的權力失衡。
在電影里,受害者是特教班的學生,社會邊緣群體,家長是做清潔、裝修臨時工等底層工作者;加害者是權貴和權貴附庸,這種失衡導致不同角色壓抑了基本良善和是非判斷,扮演者不同程度的“睜眼瞎”。
有的人瀆職,因懼怕校長權力的保安,幫安琪驅趕圍觀同學,讓霸淩者能更有空間“施展拳腳”;有的人裝聾作啞,以行動貫徹了宗教的虛偽。
這種系統性的惡是造成校園霸淩持續不斷的重要原因,在《少年的你》《黑暗榮耀》等講校園暴力的影視劇里屢見不鮮。但另外一部分也是導演重要強調的,即看似置身事外者的“平庸之惡”。
為此,影片專門設置了一組對照,一個是林在福,一個是霸淩者女生之一的鍾曉晴媽媽(李夢 飾),同樣是暴雨,同樣是在校門口為了尋找愛女死亡的原因發傳單,攔截家長,兩個人瘋得都很極致,表現出為人父母為了子女的爭取和愛護,但後者在前者失去孩子時只是冷漠地接著自己的女兒離開,再次證明了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同理心的缺失、人情冷漠是顯性症候,只有刀割到自己身上才覺得痛。
類型雜糅的確一種討巧和偷懶的創作技巧,但真要雜糅起來在鏡頭語言上也是需要能力的。柯汶利用了很多伏筆和暗示細節來鋪墊,的確吸引了觀眾的注意,但最終又淪為一種類型技巧的濫用。
比如對霸淩者懲罰式的施虐用的是拍恐怖片和驚悚片的技巧,濕漉的月夜,手機音樂突然響起、跳下、音效驚悚;開場的暴風雨和林在福墜海和之後林在福選擇和女兒同樣的“墜落”死法,配上bgm的父女溫情mv,形成一種強勢煽情的呼應……
諸如此類。通過氾濫的暴力轉移觀眾的注意力,用新的暴力奇觀來掩蓋之前的漏洞。似乎能看到柯汶利導演做奮勇狀的使勁,可走出影院,卻對其所要探討的“校園暴力”毫無觸動。
三、當我們討論“校園霸淩”時我們在討論什麼?
有一說一,《默殺》對校園暴力的探討,不可謂不“五毒俱全”、面面俱到。
柯導拍校園霸淩的觸目驚心,拍出了自己的特色,但這種特色是通過塑造暴力奇觀的方法。傳統拍霸淩就是毆打+撕衣服+dv錄像三件套,這次就要在施暴的造型上更獨特、在手段上更殘暴,最好能有更充分的解讀空間,試圖營造一種校園暴力的奇觀堆砌。
因為真實的校園暴力沒有那麼多“儀式感”,更是日常的無限放大。Be like:
——《少年的你》,校園暴力的動因貫徹始終,陳念被魏萊推下樓後,面如常色毫無愧意的睥睨著她是霸淩的常態,而最後這一推被陳念在樓梯上還給了魏萊;
——《黑暗榮耀》,用捲髮棒的燙傷來表現炙燙留下的傷痕一生無法忘記也無法療愈,用穿鞋進屋來表現對於弱者的輕蔑也側面印證高高在上者內裡的粗鄙,這些設計都足夠日常,痛感卻也足夠擊中人心。
校園暴力受害者背後的原生家庭,柯導演也拍了。可他的情感表達淪為一種光與暗式的二元對立,是最二極管式的人物塑造。母親這裏,正面是極致癲狂的母愛,背面是用暴力來管束曾經受到傷害的女兒;對父親來說,他是無路可走的底層,是為女複仇心切式的癲狂父親,他無法從宗教上得到救贖,在他的記憶力里和女兒的相處全是柔光濾鏡。
可這種極致類型化造成的失真感,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默殺》的浮於表面,為了市場選擇了捨棄各種向內滲透的表達。
哪怕已經到了東南亞,哪怕堅定了用暴力來做興奮劑來激發情感,《默殺》還是欠缺“暴力的餘味”。
同樣是改編新聞的《白日之下》,到最後案件的原型張建華直接逃脫了指控、逍遙法外。影片一方面重現了現實中讓人憤怒的結果;一方面直接劍指法律的不公:“我們建立了那麼多制度,但你告訴我現在這所謂的制度,最後連一個小女孩都保護不了?”
另一部探討原生家庭的《涉過憤怒的海》,觀眾最震撼的不是颱風天里的追車戲、天上下魚大場面,也不是老金為了找到女兒娜娜死亡的原因如何歇斯底裡表演“父親的憤怒”,而是而是娜娜的窒息,夢境里父親的死亡,和日語課上用“愛”造句的那句,“愛,がない(沒有)”。刺破父愛表演性虛偽和深挖年輕人對於愛的渴望心理的表達深入人心,或許每個人都會有一瞬間“娜娜”式的無助和渴望愛。這些這些觸動觀眾心弦的餘味,在《默殺》裡通通沒有。
導演柯汶利淪為暴力的信徒,拿審查當遮羞布,既不挖掘受害者心理,也不對制度性進行反思。最後用“娜拉出走”式的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但當所在之地是一片惡土之時,離開真的有用嗎?不還是從一個泥潭陷入另外一個泥潭?到這一步,花活還沒完,這一切的一切,最終成為內地特供版片尾——小彤進入少管所後,模仿《唐探》張子楓式的陰暗一笑,她不是啞巴,她會說話,哇哦,真的是好大的驚喜!
誠然,類型片是一種現實的彌合,不負責解決現實的問題,柯汶利把背景放在虛構的東南亞,用堆砌的奇觀和血漿以及無所謂的隱喻,很明顯,他和背後的資本都很想復刻《誤殺》的成功。
可這一切都更確證了當下現實題材電影的困境——對堆砌的視覺奇觀樂此不疲,對深層的系統性不公漠然置之。
這何嚐,不是另一種“默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