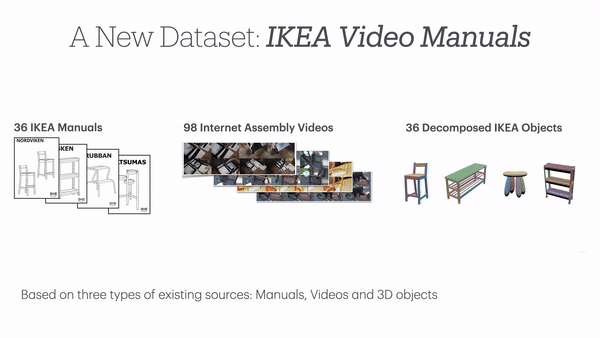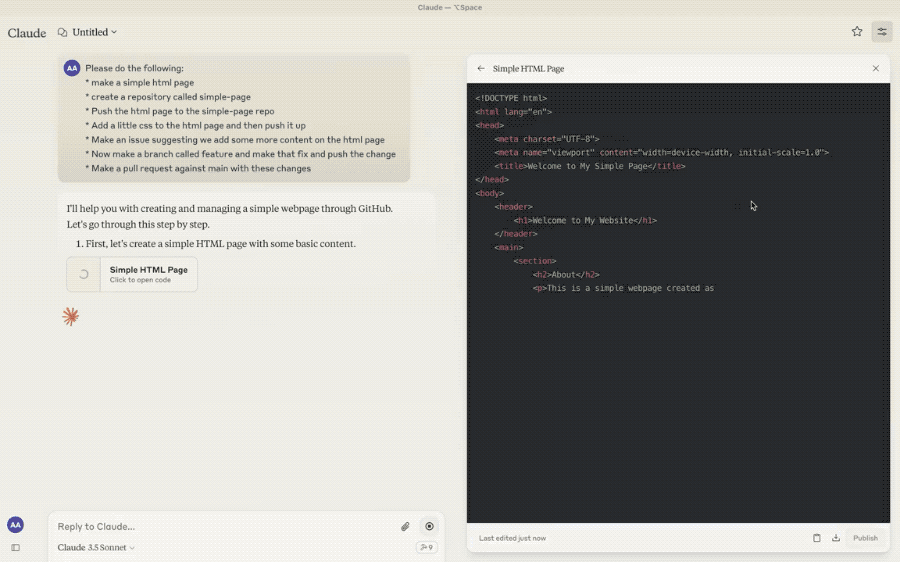除了情懷與設定,《太陽星辰》看什麼?
 作者 / 耳東陳
作者 / 耳東陳運營 / 獅子座
有人為情懷買單,有人衝懸疑入股,還有人為男頻駐足。
不管怎麼說,在紅果日活即將「幹掉」優愛騰芒的節骨眼上,能在騰訊站內躋身「流行暢銷」榜第10位,在會員增長卡瓶頸的時期拉新,還能作為華語罪案劇在Netflix同步上線。
從新港劇的浪潮,到獅子山下的迴響,《太陽星辰》值得嘮一嘮。
一、新港劇語境下的「跨時空緝兇」
頂鍋防拍:kk對《太陽星辰》的初印象,頂配是《信號》,幻視是《隧道》,左不過重來一遍港版《時空來電》。
過於熟悉的「穿越設定」:20世紀90年代,景順大廈大火引發系列兇殺案,香港重案組警察楊光耀追擊兇手麥誌鴻,追逐中進入居民樓電梯,遭遇墜梯事故,門再打開的時候,楊光耀已經來到2018年。此時,兇案仍在新發,麥誌鴻像抓不住的泥鰍,而楊光耀則不得不面對妻女下落不明,週遭環境物是人非的處境。
emmm,甚至在第一集的結尾,楊光耀得到消息趕往「下水道」,並在此發現蒙面殺手的橋段,早被網友認出高度疑似2017年的韓劇《隧道》,不僅分鏡眼熟,甚至人物關係都如出一轍:
《隧道》中的警察樸光浩來到30年後,跟親生女兒申在伊和準女婿金善載搭檔共破新舊懸案;《太陽星辰》中,楊光耀穿越到25年後,重逢因自己失蹤被領養的女兒陳凱晴,曾經受害消防員的兒子張天明也已長大從警,與陳凱晴處在「友達以上」的拉絲階段。
某種程度上,類型和設定趨於成熟的標誌即重複。就如同「最後一分鐘營救」寫進教科書一般,通常在大結局到來之前主人公都會迎來成功在即的一次失敗打擊,區別不過在於「費人」或「誅心」。
《太陽星辰》最吸引人的(此處特指kk)並非「跨時空緝兇」或「貓鼠遊戲」諸如此類的概念噱頭,縱然理解宣傳同學絞盡腦汁的拚搏奮進,可長劇到了這份上,到底是一些可持續、能延宕且夠走心的細節更能留人。
在人物關繫上,《太陽星辰》徹底摒棄了港劇熟稔使用的CP亂燉戲碼。來跟kk回憶一下,《衝上雲霄》系列,唐亦琛跟蘇怡還有何年希到底誰是官配?《刑事偵緝檔案》中「勇婕同心」分分合合幾次?《鑒證實錄》里家原和寶言之間夾個小唐菜難不難受?《壹號皇庭》和《法證先鋒》系列放到今天才是換乘戀愛的鼻祖,古早港味講的是愛情不成友情在,雖然最後不能拍拖,只要還活著,大家還能做朋友。
《太陽星辰》做減法到一對一和雙箭頭。
2018年的楊光耀頂著陳家傑的身份和長大成人的女兒搭檔探案。kk幾度擔心在認女過程中冒出「一樹梨花壓海棠」的不倫父女戀,不僅沒有一星半點苗頭;腆著一丟丟啤酒肚,扮成落魄中年警察的陳偉霆褪去油頭粉面的精緻,竟然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和「爹張力」。開始懷疑凱晴是自己女兒的階段,楊光耀小心且笨拙地試探,結果還是鬧出烏龍,被凱晴發現並當成「變態」;過程中碎嘴子式的絮叨,恰到好處卡點一個父親面對成年女兒的分寸感。
當然還有港劇慣用的「做兄弟有今生沒來世」的義氣。比如偉滔試探楊光耀,問他是否記得當年在案發現場對自己說過什麼,楊光耀不打磕巴回答「按內關穴,止吐的」;再比如面對既是上司又是師長的葉誠的背叛,先是難以置信再是痛心遺憾的情緒遞進……感情的真永遠勝於設定的巧。
《太陽星辰》張力在於,用世界通行的語言和敘事模板,講述的是當代香港乃至華語語法中對於人的情感理解和價值堅守的理解;其次是節奏的快,最後才是所謂設定。
二、赤裸的「壞蛋」和「慾望」
在《太陽星辰》及其承襲的TVB罪案劇敘事里,對「壞蛋」的摹寫是尤其值得當下內地劇與之看齊的;而對於「慾望」的勾勒,曆來坦誠的姿態更是當下內地劇不及的。這裏有個限定是當下,具體到時間線,3-5年內幾乎都是這樣。
內地編劇在寫作「壞蛋」時,總想著給壞和惡找個值得同情的理由,以此彰顯格局眼界,以致從創作者到表演者都背負了過重的道德牌坊。就像《好傢伙》的導演邵藝輝說,當初找飾演前夫的男演員困難重重,大家似乎都不願沾染存在道德汙點的角色,更遑論存在犯罪事實的罪犯。
因而內地劇中的「壞蛋」,總有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悲切,忙著推翻「人之初性本惡」,而篤定站隊「人之初性本善」,彷彿一切罪惡的源頭都是外界環境的罪過,「都是XX逼我的」。不適感類比法醫勘驗現場後越俎代庖,不論是無罪推定還是有罪審判,都顯得於理不合。
《太陽星辰》里的麥誌鴻作為從開篇就交代的「大壞蛋」,隨著景順大廈幕後黑手的逐漸現身,作為棋子的「變態殺人狂」有了更加複雜的底色。但是不影響創作者從開始就站定麥誌鴻的「壞蛋」身份,至於底層邊緣人、反社會人格乃至精神分裂的屬性設定,都不是給惡找藉口的遮羞布。
麥誌鴻童年遭遇欺淩,甚至連自己的母親都是加害者:吃了自己的寵物狗,因而劇中他殺人時連狗也不放過,卻也會善待流浪狗;精神分裂出的「阿包」是童年飽受欺淩自己的鏡像,給肆意屠戮找自我安慰的藉口。精分的兩面,讓人看到的是對於壞蛋的唏噓,注意是唏噓而不是同情。當他手染鮮血的那一刻,「再冷也不能用別人的血暖自己」《甄嬛傳》課堂開課重複讀三遍。有時候看著內地劇,著實要哀號一聲還是「存天理滅人欲」能收了氾濫聖母心的神通。
再來說《太陽星辰》的慾望,有行業洞察或者觀眾視角,把這部劇當成「大男主複仇」爽劇,倒也合理的。拋開連環案件,實際上全劇始終圍繞楊光耀的「慾望」展開,他作為全劇的主人公,動機極其明確:在20世紀90年代是抓住麥誌鴻、老婆孩子熱炕頭兩條線;來到2018年後,先是數度嚐試重返20世紀無果後放棄,開啟異時空追兇,繼續抓麥誌鴻,找女兒,查妻子之死真相,總體是角色動線推情節動線,也有被困境絆腳的情況,但整體螺旋向前。
主人公極其明確的行動線,在戲劇邏輯上是盪開bug的有效手段。觀眾的注意力都在楊光耀身上,他想要做什麼,會遇到哪些困難和阻礙,能否成功,這就夠了。到劇情過半,相比於糾結他來到2018的合理性,觀眾恐怕更揪心的是他一旦還能回去,這些失而複得的人們將如何告別,並重過一次?
除了劇作上學習「慾望」的動力,精神慾望的直白呈現或許也是當下內地劇應效之法。回憶一下,除了《風吹半夏》許半夏的慾望分明寫在臉上,實踐在行動上,且有著灰度和況味,《狂飆》里高啟強為保護弟妹不再做軟弱賣魚佬,自此踏上不歸路;近幾年還有哪些角色或人物的慾望是不加矯飾,被分明展現的?
就像給惡找個情非得已的藉口,內地劇中的慾望總透著欲拒還迎,半推半就,既不敢做,也不敢當。相比之下,《太陽星辰》中被拉下水的葉誠顯得乾脆俐落:妻子嗜賭,被作局欠下巨額賭債,也成為拉攏他的把柄。他背棄了作為警察的責任,同時也在良心的底線上給自己留一點轉圜的機會,有一種「一碼歸一碼」的灰度。
多說一句,港劇的聰明之處在於,戲核或設定,只要是創作者擅長且跨時代通吃的,都會被完好保留下來。如果互聯網有記憶,「麥誌鴻」這類壞蛋在港劇中並非首次出現,《陀槍師姐》二三部中的高智商變態鮑國平與之如出一轍,通過人格分裂高概念獵奇、嗜血殘忍的作案手法吸睛,最後是扭曲性格養成的過程延宕,從師奶一路通吃到Z世代,一代有一代的童年陰影。
內地劇不大會這麼做,講創新就得吃著飯砸著鍋,過去的事都別來沾,我們是開天闢地獨一份,凡事講究無對標,最好也後無來者。對比的意義從不在於「拉踩」,創作這些事,不外乎是向領先的學習,然後迎頭趕上,交替向前才有意趣。
三、獅子山下的迴響
還是要說到懷舊。
陳偉霆在看片會上表達了與謝君豪、馮德倫、吳岱融等港劇黃金一代同框演戲的「含金量」;《太陽星辰》表面上是兩個時空,實際以九七為界,三個時代的香港城市文化被定格為分層設色地形圖,留在螢屏之上。
如果說劇中彩蛋式影片《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用明線給時間軸打點,Beyong的《情人》則是一重繞不開的時代與文化隱喻。特殊的歷史背景使然,香港影視劇不論題材類型,自我身份的認同都是繞不開的母題,《太陽星辰》勾勒普通人在常態下對正義公理的追求和捍衛,電影《焚城》則通過構建極端的災難場域表達「守城」的決心,可以說今年的香港影視劇,對曾經的獅子山精神迴響尤甚。
作為旁觀的「他者」,恰好對香港影視劇的觀看經驗從20世紀90年代延續至今,又恰好被個中身份認同和精神認同打動著。每個人都來自過去的歲月,「我們曾經是誰」決定了「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將會成為誰」,這樣的追問始終在香港影視劇中延續,並形成內化的高度自洽,也給了新港劇值得繼續愛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