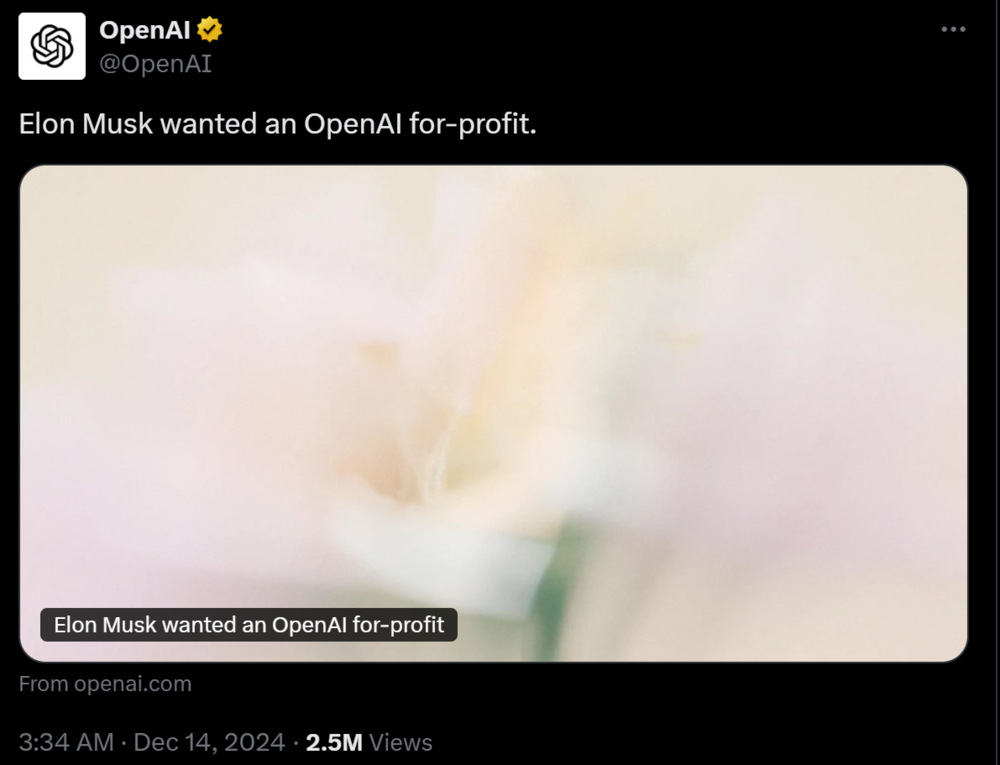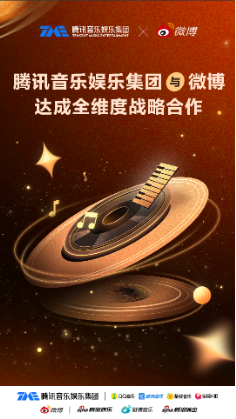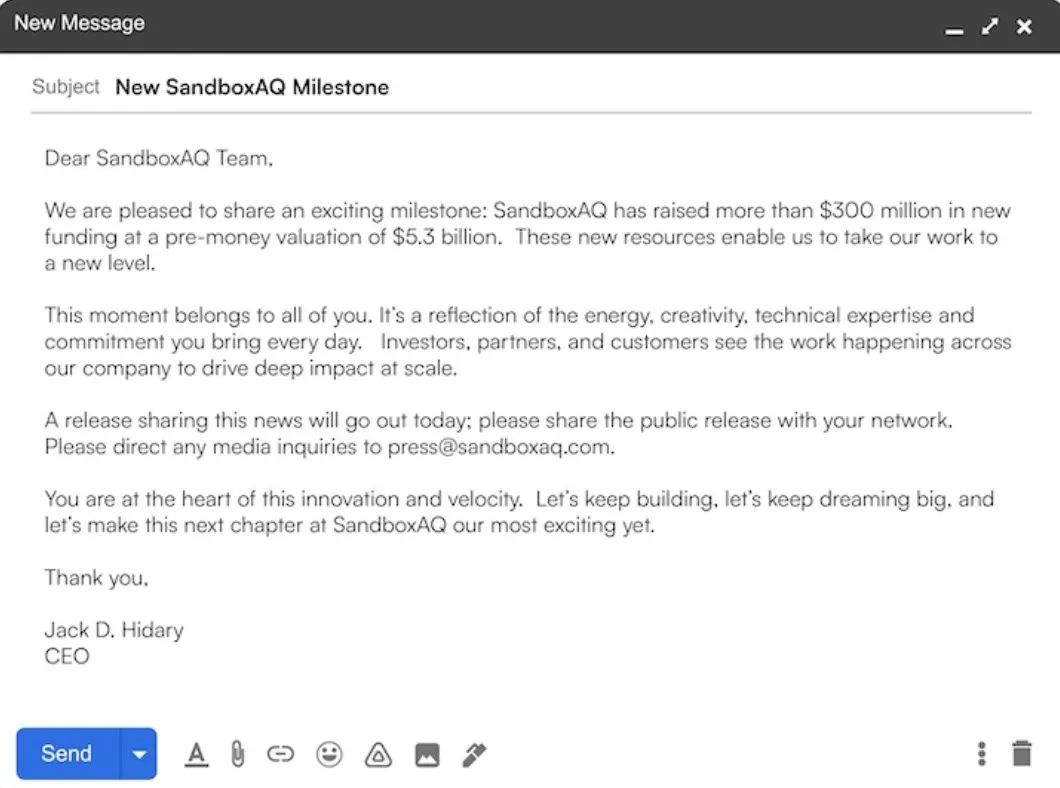拿到拆遷款,又迅速返貧的人

城鎮化率已突破65%,近10年,中西岸城市發展尤其迅猛,很多近郊居民一夜暴富,搭上時代紅利的晚班車。
缺乏掌控財富的心智與能力,這些新富的幸運兒沒能吸取東區城市拆遷暴富群體的前車之鑒,在慾望的鼓噪下,被不可靠的投資、賭博以及毒品掏空。
因房暴富之後
早晨6點,西安市區天剛透出些許濛濛的光,侯季安就出發了。他把攢了一週的紙殼和廢品裝上三輪車,準備拉到臨近的村子去賣。他不想等到7點。侯季安怕,那時候上學、上班的人們陸續起床出門,他拉著廢品在路上容易遇到熟人。他覺得有些害臊。
鄰裡間,侯季安撿破爛這件事不是秘密。但撿廢品時,他還是偷偷摸摸地專挑半夜、淩晨等人少的時候出門。隱入暗暗夜色之中,他感到一種隨時能藏起來的安全感。
最多的時候,侯季安賬上有200多萬元現金。這對世代在西安城郊的鄉村務農為生的侯家來說,是一筆天降巨款。
和村里很多人一樣,侯季安是因房致富。2011年夏天,侯季安人到中年趕上了縣城最早的擴建紅利。生養他的村莊位於西安城區郊外,當時,全村約1700畝土地被完全徵收。全部的村民戶籍也由農戶轉為了非農業戶口。而後,隨著西安市拆遷改造規劃正式啟動,村里人陸陸續續地離開世代耕作的土地,從這一輩結束了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傳統。到2012年年底,全村99%的村民撤離了這片土地,在等待搬進回遷小區之前,到外部居住過渡。
侯季安一家得到5套回遷房,200多萬元現金也是那時作為賠償款打到了他的賬上。那時,西安的房價每平方米五六千元。
因房暴富,村民們的生活快速駛向富裕。
在真正抵達富裕之前,很多村民已經提前適應起即將到來的安逸。村民孫莉莉記得,拆遷款下來之前,村里很多人雖然還沒拿到錢,脖子上已經戴好了大金鏈子。村里抽菸的人,煙的檔次也從2元一盒的猴王變成了尊貴身份象徵的中華牌香菸。還有一些年青人,頭一天還在上班,第二天就見人辭職了,去車行提平治車。這樣的年青人當時在村里不少,當然,用的是上面發的補貼款。
為了尚未落袋的拆遷款,村里的人們忙碌了起來。
劉明說,當年他的婚姻,是趕著拆遷倉促而成的。2009年,他剛高校畢業,距離法定結婚年齡還差4個月。村里傳開了要徵地拆遷的消息,應屆畢業的劉明還沒開始找工作,就忙著張羅相親結婚了。
最多的時候,他一天參加了6場相親,見了6個女生。劉明回憶,他後來和妻子結婚時兩人從認識到領證,前後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對方那時候家裡需要錢,覺得劉明人也不錯,知道他家要拆遷,也就很快答應了。
劉明對這樁婚事也很滿意。妻子看著順眼,她的家裡人不錯,第一次妻子去家裡見家長,後來的嶽父拉著他跟他保證,自己的女兒不會好吃懶做,如果女兒不務正業、亂花錢,就讓劉明跟他說,他來收拾女兒。劉明說:就覺得這家人老實。
趕在拆遷正式開始前,劉明領了結婚證,往家中的戶口本上添了一口人。2011年村里拆遷,劉明家原本的小二層住房和幾畝農業土地,換回了每人8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分配面積,和每人20多萬元的「人頭費」。此外,其它建築的賠償和安置、過渡等費用,合起來額外又多了小幾十萬。
如今,劉明37歲。他時常感慨自己在婚姻上很幸運。「村里那時候都著急結婚,現在其他當時趕著結婚的夫妻,也離得差不多了。」說這話時,劉明坐在居委會辦公室里,看著桌子上堆積的幾份離婚判決書不住搖頭,剛把哭訴的二嬸送走,樓下的大爺就又敲門進來了:「娃,村上給我的證明開好了嗎?這個弄好,她之後就再也不會回來要錢了吧?」
他的辦公室還在村莊舊址上。一抬眼,窗外已不是舊時的模樣。2009年之前,這裏全是村莊的樣子。村頭立著牌匾,寫著村名。進了村,大都是自建平房,也有若干多層小樓,家家戶戶幾乎都有小院子。每戶人家都有幾畝薄田,人們過著簡單的生活,沒多少人夢想著一夜暴富,也沒多少人聽說過妻離子散。
城市化來得太突然了,這裏太快被拆掉,又太快成為了城市社區的一部分。村民搖身一變成為了市民,外面的殼子換了,但內裡又沒換。這種急速的生活轉換,催發了新的願望,人們卻難以掌握新生活的技巧。
如今,從回遷小區的圍牆外看,這裏和城市里多見的普通大型社區沒有什麼不同。圍牆裡,高樓林立,綠地不多。白天,小區里都是老人,人們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嘮嗑。
大家真正抵達了因房致富的富裕之中,一些看不見的事物,比如觀念,還停留在舊時,久久走不出村中時光。比如,大家依然不習慣把村委會喊作「居委會」,依然不懂為什麼要收物業費和垃圾費。
在這個回遷房小區里,住慣了院子的人,對於高層筒子樓里的生活很不習慣。劉明的老父親,睡不慣劉明為他專門買的席夢思,堅持把大床拆了,在房間里按在村里時的習慣盤了一個大炕。樓里不可能燒火搭煤爐子,土炕也失去了保暖的功能,但劉明的父親倔強地說,在炕上睡踏實,否則睡不著。「總不能不讓我種地,還不讓我睡炕吧。」
孫莉莉對於小區里雜亂無章的綠化帶有些無奈。十幾年前,她家門口院子4平米的土地上,夏天種黃瓜,冬天栽蒜苗,揚上一把菜籽,用不了兩個周,就會密密麻麻冒出青翠翠的嫩芽,苦苣,菠菜,上海青,香菜。覆上薄薄的一層塑料膜,什麼時候去都有最新鮮的菜苗可以掐,吃都吃不完。
哪像現在,叫不上名字的綠葉葉裝滿了整個小區的綠化帶,「沒什麼好看的,土大也沒人收拾,還不如全拔了種菜,能吃還能看。」孫莉莉說,住進樓房多年,她依然不解小區里為何要鋪設大面積的綠化帶,它們因無人打理而雜亂無章地生長著。
 圖 | 回遷房樓棟一隅
圖 | 回遷房樓棟一隅迷茫的拆二代們
拿到賠償款後,20多歲的李磊辭去了在汽修廠的工作,沉溺在鈔票創造的夜夜笙歌之中。
他成日和附近的「拆二代」混在一起,天天泡吧、喝酒。夜店一晚「就消費好幾萬,點的都是最貴的888、皇家禮炮」,李磊說。他記憶中,縱情聲色的時光十分絢爛,大家輪流請客,輪番開銷,日子確實瀟灑。
本來,李磊計劃著,吃吃喝喝就算了。他的父母也覺得,吃能吃去多少,由他造吧。這個家在貧窮中浮沉多輩,如今終於過上了新生活,享受幾天也沒錯。
不曾預想,天天在那些地方混,李磊又不懂得低調,兜里有點錢就囂張起來,天天吹噓家裡有多少錢。一來二往,有心之人盯上了李磊。沒過多久,黃賭毒他全染上了。
因為賭博,李磊家拆遷賠付的近200萬元現金,幾乎拱手讓給了賭場。劉明回憶那之後的李磊,「整天看著人不人鬼不鬼的。」那時候李磊結婚不久,老婆也跑了。到2017年整村回遷,李磊家裡連裝修的錢都掏不出來。好在,他們靠賣了一套拆遷房,簡單裝修了賸餘3套房子,住上了人。
到如今,李磊35歲了,多年放縱喝酒的瀟灑日子讓他的肚子形成了一個略顯誇張的弧度。見面那天,興許是為了表達尊重,李磊的頭髮上明顯上了一些髮蠟,只是可能因為沒有控制住量,有的地方已經泛起了白絮。
問到最近在忙什麼,李磊翹著二郎腿,嘴巴的煙一根接著一根,「跟俺夥計弄了個項目,搞直播電商。」但往細處問,他露出明顯的侷促和慌張:「小生意,小生意,不掙錢。」劉明則說李磊:「你聽他胡吹。什麼直播,一天直播間都不超過5個人,就是混吃等死呢。」
賭與毒,是很多拆遷戶返貧的最大禍首。
「這倆東西是真花錢,真上癮,跟無底洞一樣。」劉明無奈地說。他想起自己的表弟。小時候挺乖一娃,話也不愛說,戴個眼鏡,看著文氣得不行。家裡人都說光看那白淨的長相,慈眉善目的,以後鐵定有出息。
確定拆遷後不到一年,劉明的這個表弟就被「有心人」盯上了。他被帶著沾染了「哈哈」,吸得不見人形。1米83的個子體重只剩80多斤,以前沒什麼血色的臉,現在更沒血色了。後來,他因為攜帶被抓,坐了7年牢,打官司又從家裡掏了幾十萬。劉明感慨,表弟一家的拆遷款,就被毒品這一樣掏空了:「他和媳婦結婚才3年,進去時候娃剛生,等出來,娃都要小學畢業了,至於婚,當然離了。」
村里類似李磊和劉明表弟的人並不少,劉明想了想自己彼時同村一起上過小學的同學,「滿打滿算30來個,20多個都混得不咋樣,反正我們那屆沒幾個在外面混出眉目的。」
劉明想不通,以前在村里,大家上市場買個菜為幾毛錢的零頭都能跟人在街道上大吵大鬧砍半小時價,怎麼一旦染上了賭博和毒癮,幾十上百萬就可以這麼隨便扔出去了呢?當然,劉明也清楚,有些人雖然不是自己主動入了賭局,但被盯住的「肥羊」又哪能辨別出什麼是陷阱,什麼是好意。
拆遷款下來後,村里人捨不得分開,都會集中租住在附近其他的小區或城中村里,而一堆人的集聚也引發了別人的猜測和打聽,一個地方猛一下有了很多新鮮面孔,「麻將館、地下賭場、開老虎機的,自然聞著味就都來了。」有的老闆更誇張,會直接腆著臉請村里人去自己開的賭場里玩,話術也好聽「你們辛苦了大半輩子,享受生活的時候到了。到我那娛樂娛樂,吃喝免費還有專車接送,保證你們玩個痛快。」
「一般剛開始玩,也會讓你贏幾把,感受一下快樂,但一旦上癮了,那也就是魚該上鉤了。」劉明回憶著他見過的那些尋著村民們找上來的賭場。賭場都是專門做的局,哪是村民們想贏就能贏的。村里人哪懂這些,說白了,錢來得太容易了,所以不心疼,都變成數字了。越輸越紅眼,越紅眼越輸更多。「財富和智商不匹配。」劉明感慨。
受不了挑逗和誘惑的,堅持不了多久就會下場,而一旦上了頭,便再也很難從牌桌上靠著自己的意志力下來了。
輸光了口袋里的錢也不要緊。人家知道你是拆遷戶,還有房,那就按手印讓辦抵押貸款。賭場樓下就是錢莊,想提幾萬就提幾萬,也不過就是簽個字按指頭印的事。
儘管已經輸得急紅眼了,也有老父親拄著拐棍跑到賭場哭鬧下跪,勸兒子戒賭的,但總想著贏錢補倉回本的人哪能聽得下這種勸。還有一家人,劉明回憶:「過年除夕,討債的進了家門,把家裡老太太硬生生氣死了。哎,不能多說不能多說,真是造孽。」 劉明感慨。
村里人現在評價本村年青人的用詞已經從最早時候的年輕有為,變成了「乖」一字概括,問到具體「乖」的維度,也無外乎,「人家那個娃娃不胡成精(陝西方言,比喻不務正業),不亂花錢,不出去黃賭毒,最起碼有班上。」
村里的年青人結婚後,很多根本不願住在安置區,要去更好的商品樓、有品質的好小區住。加上近幾年對於學區醫療地段的炒作,很多拆遷戶也傾向於購買商品房,這也將很多家庭的存款消耗殆盡。
過往,有些人家靠出租安置房掙錢。在當地,這樣的房子租金價格約2000元,出租3套房產生的6000元,遠遠達不到支撐每戶6到7口人日常生活開支所需。
在劉明看來,突然暴富帶來的安逸和閑適,讓村里的年青人失去了奮鬥意識。「村里多的是不思進取和坐吃山空的人」,劉明回憶。
孫莉莉有點難過,「不是我說,我們這種村子,基本沒一個有出息的娃們。」儘管孫莉莉說得有些絕對化,但認真盤算起村里得知拆遷後還能好好上學的孩子,「確實是刨不出來一個,別說考上一本大學,就是二本都簡直都是祖上冒青煙的程度了。」
孫莉莉如今的心思全操在了自己剛上初二的孫子身上,「他爸是指望不上了,就看我們家這個還能不能給咱念下書,真的是吃了沒文化的虧。」
孫莉莉羨慕的人,是小區外圍那對租了鋪子賣快餐的四川夫婦。「一天就靠賣盒飯,硬生生供給了兩個大學生,那麼小的店面,滿打滿算不到15平米,一天來來往往的都是人,娃在那種情況下不僅幫他爸媽幹活,還能不受影響學習。」
這種豔羨,會在想到自己家孩子的時候,偶爾冒出來。「哎,淨跟村里不三不四的娃們胡混,成天說要發大財,今個投資加油站,明個說要搞自媒體,但只見光找各種理由問我要錢,從來沒見往回拿過的。」 孫莉莉不明白,明明只要安分過日子,不想著天下掉餡餅的好事,原本憑藉這些拆遷款加上出租房屋的租金,「怎麼都能養活起家,但咋就逼的都出去撿破爛了呢?」
孫莉莉也不知道要怪誰,失去土地的人們,無所事事成了最大的事,湊在一起除了打麻將就是打麻將,「打麻將打得不管娃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村里的人都這樣,沒有辦法不受影響的啊。」
被投資掏空的家庭
從手握百萬現金加幾套房產,到只能通過撿破爛來補貼家用,侯季安坦言,「不過短短4年。」如今,侯季安已經成了年逾70的老人,但是再回憶十年前的日子,侯季安還是會覺得「像夢幻一樣,總覺得不是真的。」
拆遷前,侯季安是村里的「能行」人,勤勤懇懇幹活。他在南方打過工,見識過大城市,又懂得多,人也活絡,雖然沒一猛子掙上大錢,但也算是個小生意人,日子過得紅火,誰見了都得稱讚一番,遇到難事了其他人還會專門去找侯季安打聽打聽,讓侯季安幫忙出個主意。
侯季安的生意夢,栽在了融資的陷阱里。拆遷後,侯季安像換了個人。他天天喊著理財,惦唸著讓錢生錢。
他說,靠著銀行的那點子利息,永遠都過不到「上層人」的生活。劉明現在還記得那時候侯季安說:「上天給了我們發財的機會,我們就得抓住,堅決不能讓機會從我們手裡溜走,當守財奴的都是大傻子。」
他記得,拆遷搬離的公告出來沒多久,原本安靜的鄉村就迎來了從未有過的熱鬧。
最熱烈的話題,則無非是有關如何花錢,比如未來如何盤算,做什麼投資。大家七嘴八舌,討論著各種金融地產和理財的話題。人們憧憬著補償拿到手後怎麼讓錢繼續生錢。
劉明有點恍惚起來。以前嘴裡都是東家長李家短的陳芝麻爛穀子,或是小麥玉米蘋果價格漲幅情況。隨著補償款到賬,一夜間,鄰里都像是懷揣幾百萬投資款的大老闆,聊的儘是未來,理財、智能、科技、大項目。
2015年,西安聯合學院的非法集資事件引發了全國轟動,據彼時新聞報導,有約130億元牽扯其中,集資參與的人數也有10萬餘人,該事件也在2015年被西安市地方誌辦公室列為「地方大事件」。
侯季安的錢,包括村里很多人當時拿到的拆遷款的錢,都進入了聯合學院的口袋,據侯季安回憶,早年,聯合學院就已經開始在西安及周邊各地設立辦事處招募業務員,借助社會力量向民間集資,年利息10%—20%不等,用來開發學院投資的一系列實體項目,包括彼時一個大型養老院和急救中心。
現在提起,侯季安對於當時的宣傳話術都充滿嚮往,「大巴車把我們一車一車的人拉到學校去考察,走訪,有專家領導做彙報,還送我們好多的禮品,每個月,人家業務員恭恭敬敬地就把利息送到家裡來了,那麼大的陣仗,那麼多的人,怎麼能是假的呢,怎麼可能是假的呢?」
過去近10年,侯季安還是無法接受這樣的失敗和沉重現實。「把我家,把我們村的人都坑慘了。」他說。
侯季安提到被騙的不止他一個。「我們村至少搭進去了一億,全是讓騙走了,再也沒了。」為了獲得遠超銀行利息的收益,侯季安不僅投入了全部身家,還從親友處借了很多現金,加起來300多萬元。
侯季安一家分到了5套回遷房。這場投資傷筋破骨,以至於回遷之後,他不得不在房子到手之後,火速低價處理掉了其中4套,一家7口人擠在一套三居室里。
回憶起拆遷這些年的經歷,村民孫莉莉眼神中透露著深深的無奈,她舉起一隻手,開始算賬,村里的人拿到賠償款後,「3成覺得自己苦了一輩子,這下好不容易混出頭有錢花了,可得好好享受一下;3成的覺得自己得錢生錢,好好投資做個生意,圓一下老闆夢;2成覺得有錢了,得找個好項目理財投資賺個利息;2成覺得這錢還是穩穩存著吧,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可不能賠光了。」
等2017年,四散各地過渡的村民們在安置房小區重逢,孫莉莉發現「最後只有兩成的人守住了手裡的錢。」
因為借錢消磨掉的人情,更難以啟齒。多年不聯繫的親戚,都會突然冒出來說自己手頭緊,想借錢周轉。孫莉莉說:「別人覺得你的錢就是大風颳來的。」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借了不還的也多了去。問要,有的村民還會被反問「給兄弟幫點忙怎麼了」,被指責有錢就瞧不起人,賴賬。不借也會被罵沒有良心。因為錢反目成仇不來往的很多,家家都有難念的經。
這裏是既新又舊的地方,鄉村習慣和城市生活交織在一起,難捨難分。失去了土地的人就像是離家出走的孩子,回來卻再也找不見熟悉的家。
問題逐漸顯現,批量的離婚是,住慣了院子住不慣筒子是,鄰里之間的情誼在多年間的消耗而被瓦解的分崩離析也是,包括因為借錢還錢弄得不愉快而反目成仇的更是比比皆是……那筆曾經的財富真的像夢幻一樣 ,留存在了很多人心裡,又消失在了很多人心裡。
天色漸暗,侯季安又騎上三輪車,準備去小區附近撿破爛了。KTV、洗腳店、檯球廳一家接著一家閃亮起LED的招牌。這些年圍繞著安置房陸續建起的商場和小餐廳連成片地開業,夏天的燒烤攤、冬天的火鍋店整晚冒著熱氣,大有將這裏的夜空描成白晝的架勢。年青人渾渾噩噩地從麻將館出來,轉身又進了按摩房。
暗暗月色接納了侯季安。
他已經66歲,工地不要,年紀大了,沒什麼工作能應聘得上,招日結工的一查他的身份證,60多歲的老人家了,也不同意雇他。無處將勞動力兌現,拆遷款被掏空,撿破爛給了一點兒收入。
被騙的候季安,如今帶著遺憾跟全家人一起擠在僅有的一套房子裡。
感受過短暫暴富的兒子兒媳一家,不願意老實本分找個工作好好賺錢養家餬口。太辛苦的工作不想幹,要技能知識水平的又都不會,不是早上起不來,就是嫌老闆態度不好,轉來轉去還是決定回家躺平。一等到村里集體門面分紅的幾千塊下來,就拿出去再揮霍。
侯季安覺得,目前的生活,成天就是為了補貼娃娃們的家,「沒有明天」。
村里,很多年老的人們守著如今朝不保夕的生活惶惶不可終日。劉明眼見著,也只能感慨,拆遷款帶來的瀟灑日子,短暫停留後驟然消失。黃賭毒、投資掏空了一些家庭,另一些拆遷時爭當壯年的老年人,拆遷把他們的孩子養老了,而在陝西這個普通的村莊,很多老人想著補貼、照顧後代,70多歲了都忙著勞作掙錢。
如今,村里老一輩出門找保潔保安工作打工的人也已經越來越多,大家放下了面子,也失去了裡子。受各種因素影響,村里的房子空置率越來越高,村里一些原本想靠吃老本出租的錢養活自家的村民,在經過孩子娶妻生子,養兒育女,外面買商品房之後,積蓄也已經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有時候,劉明也會懷念曾經沒拆遷之前的歲月,他想不明白,為什麼很多人房子分到了,錢也拿到了,但家卻不知丟到哪裡去了?
 圖 | 回遷房樓內居民開設的超市
圖 | 回遷房樓內居民開設的超市*應講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