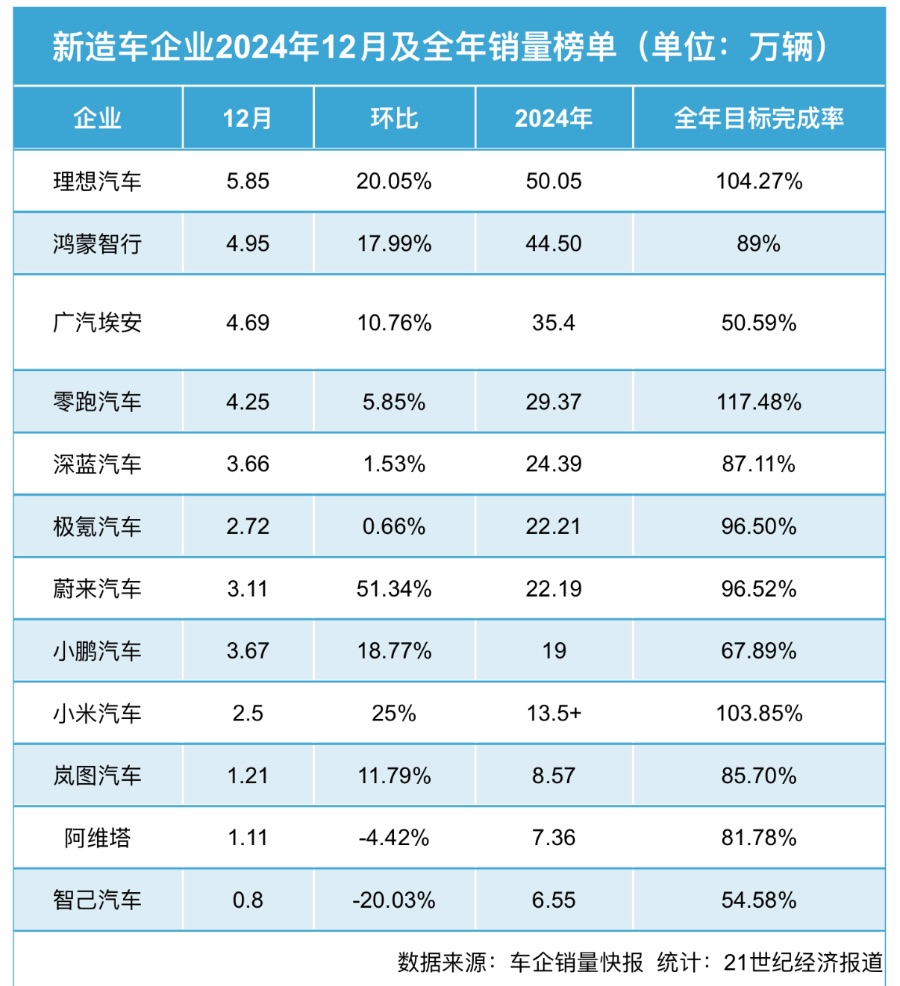《她的房間》,千萬個劉小樣
 作者 / 西貝偏北
作者 / 西貝偏北編輯 / 朱 婷
運營 / 獅子座
“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2002年,陝西鹹陽興平,一個農村婦女身著紅衣,在央視先鋒女性節目《半邊天》的記者張越的採訪下發出這句石破天驚之語,她不要“無知的滿足”,她讀書要獲得知識,雖然她只能從有限的書本和收音機上獲得這些——因為她不能出去。
她是劉小樣,一個最高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村婦女,但她蓬勃的生命力和超脫地域甚至時代的思想,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無波的湖面,瞬間激起千層浪。人們第一次在國家級媒體平台聽到一位普通農村女性的呐喊,而她的呐喊也影響了很多人,紛紛表示“我就是劉小樣”,其中包括持續關注劉小樣的記者安小慶。
可是,這個對處境有著先天敏銳的婦女,這個被“考古”放在短視頻平台點讚量必破10w+的主角,卻在逐漸湮滅在了公眾視野……劉小樣去哪兒了,她走出去了嗎?之後的生活怎麼樣?
2020年,曾在《人物》雜誌寫稿的記者安小慶多方聯繫找到了消失在公眾視野的劉小樣。她覺得這是一個“不完成自己就會後悔的選題”。安小慶於2021年完成了這篇長達 2萬餘字的靜態報導——《平原上的娜拉》。
通過安小慶的文字,我們知道後來的這些年,劉小樣在縣城、貴州、江蘇崑山乃至西安多地打工,當過商場櫃員、學校生活老師、食堂阿姨,去過圖書館、看過電影、聽過音樂會,見過大好河山……最後,在2016年因為婆婆生病需要照顧,回到了平原的老屋,至此未再“出走”。
按照今天所謂“大女主”的標準來看,沒在事業上做出成績而後撤回家劉小樣是失敗“覺醒者”,她再一次被母職、妻職捆綁不得不妥協,她的突圍和出走都中斷了……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今年,劉小樣和曾將她的事蹟傳播給千萬網友的央視主持人張越(已退休)、安小慶相聚在大理(安小慶從《人物》辭職後居住在此)。原本只是一次簡單的三個人的聚會,機緣巧合之下,優酷人文欄目決定以她們三個的故事為開始,推出女性人文紀實節目——《她的房間》,在這檔偶然產生的節目第一、二期,劉小樣的心靈荒野再次被探尋。
節目片段在短視頻上廣泛傳播,大家紛紛感慨:過了20多年,時代的浪潮終於追上了劉小樣。
一、回家的決心
劉小樣回家了。
魯迅先生曾著《娜拉走後怎樣》,揭示娜拉出走後的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影視作品里也很少拍出走後的女性如何,她們總是在覺醒的路上,囿於社會規訓、困於愛情親情漩渦。如果說樸讚鬱拍湯唯如何下定“分手的決心”,尹麗川拍李紅如何下定“出走的決心”,那麼劉小樣就用生命書寫了她為何在出走後,下定了“回家的決心”。
沒錯,回家也是需要下決心的。尤其對劉小樣這樣永遠“發著低燒、持續陣痛”的人而言,在別人眼裡溫馨和睦的家庭,於她卻是帶有某種束縛。坐落於農耕文明中心的“平原之家”太平了,平地一望無際可以看到頭,她結婚生子,操持家務,按部就班地生活,可總感覺不對勁。
“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不需要別人阻止你,你會自覺自願地去遵守這些規矩。”這是2001年她結婚十年後的一個秋天,向央視發出的“求救信”內容。
節目播出後,劉小樣的名字比她本人先“出走”,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2005年,劉小樣受《半邊天》欄目“我們的十年”晚會邀請,第一次來到北京,在張越的陪同下錄了節目、逛了書吧,敏銳如劉小樣並不開心,如大夢初醒,她更清楚自己的處境了——出走,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事。
劉小樣的先後經曆了次出走三次出走。
第一次“出走”是在2006年, 縣城招聘會說普通話的售貨員,鼓起勇氣的劉小樣在快40歲時獲得了第一份工作,2008年,劉小樣公司倒閉,她找到機會去貴陽出差了半個月,但因為感覺不對勁就回家了。回家後,劉小樣在縣城一所寄宿小學當生活老師,一年時間就幹到了生活老師里管事的一位,但在兒女考學後,擺脫了母職束縛的她想繼續“突圍”。
第二次出走時她已經43歲,風塵仆仆地去了江蘇崑山的一家工廠的食堂做員工餐,沒有朋友待遇也不好,很不快樂的她在幾番糾結之後,在2010年底又回家了,離開前還去了崑山市圖書館。
第三次出走,劉小樣已經50歲左右,她不懂自己痛苦的“用處”,於是去了西安的醫院“看病”,她在醫院後勤工作,每月能拿一些報酬補貼家用。但她的病始終沒能治好,於是在2016年她回到了家照顧生病的婆婆,2019年婆婆去世,伴隨著女兒兒子的結婚、孫輩的降生,她沒再出走過。
劉小樣說自己是莫言書里那個“晚熟”的人。表面上,劉小樣兜兜轉轉30年,還是回到了農村婦女結婚生子、含飴弄孫的既定軌道上,但kk認為正是這個出走和回家的反複中,劉小樣不僅擁有過“出走的決心”,更反複磨煉了“出走的能力”。
一方面,她發現大城市並不是她要的“詩與遠方”。
城市燈火通明,疲於奔命的庸碌生活讓她連“看清一朵花的時間”都沒有。在浙江崑山打工時,內向如劉小樣,某天為了弄清道路上一簇瑰麗紅色小花的名字,連續問了三四個路人,在無數個“不知道”的回應後,最後在保安口中得知了它們是“山茶花”。
這不對勁。活著卻不知道身邊的花叫什麼名字,劉小樣覺得“如果連這麼美好的造物都被忽視了,那我們豈不是辜負了它?”
另一方面,她很難割捨她充滿了關懷與愛的家庭。
劉小樣總覺得自己很“幸運”,嫁給了門前寫著“耕讀之家”的丈夫,對於她喜歡讀書的愛好,老公王樹林雖不理解但會支援,親戚送給劉小樣一個打好的書櫃,王樹林負責裝滿它——他會在聽說有人不要書時,扛著袋子替老婆撿書,劉小樣不喜歡收拾,他就幫她把書碼整齊。劉小樣的婆媳關係很好,婆婆跟她“能吃到一起去”,從不疾言厲色地禁錮她的想法。
劉小樣的一雙兒女成家立業在城里工作,但因為惦記她,每週末都要回家。女兒會帶媽媽聽音樂會、看宮崎駿電影,給媽媽買新衣服、新項鏈,兒子會給媽媽買當地沒有的百合花種子。
一個細節,當張越問劉小樣她的媳婦孝不孝順她時,她下意識回答“我覺得一個家,應該講愛,不講孝順。”她的回答讓無數網友感動,在她廣泛的閱讀和敏銳的感知中,捕捉到了“孝順”所承載的道德捆綁和權力施壓,只有發自心底的愛,才能滋養彼此。
kk相信,劉小樣已經不是多年前被農村的環境、社會和時代困住的她了,出走成為了她隨時可以進行的選擇。
她要遵從的從不是社會期待,她也無意當什么女性先鋒,她只遵從自己的心。因此,回家對她而言,不是一個結局,而是一種選擇,更是一個過程。
從“看山是山”到“看山還是山”,回家了的劉小樣也沒放棄詩和遠方。相反,她找到了獨屬於她的尋找之路。
二、詩和遠方,觸手可及
或許對劉小樣來說,詩與遠方需要的不只是“體驗”,而是“創造”。
《出走的決心》里有一個細節:李紅帶孩子搬到城里時專門帶了一個玻璃花瓶,她希望花瓶里時刻插滿鮮花,卻沒想到遭到丈夫“這能吃還是能喝,這要花多少錢”的苛責。在她掙錢後,她堅持買鮮花插進花瓶里,無視丈夫的冷嘲熱諷,而片尾她開著車駛向遠方,車廣播里放的也正是《夏日裡最後一朵玫瑰》,悠揚婉轉。
花就是這樣,花期短,需要侍弄,會枯萎還沒實際用處,和農村莊稼人的務實精神大相逕庭。但花美麗動人、生機勃勃,是一種強大精神像征,詩人經常以花寄情,劉小樣也是如此。
曾經的劉小樣只在家裡的前院種了幾盆歪斜的牡丹,更多的花開在她的心裡。正如婚紗照對面牆上的粉紅便利貼上抄寫的故事:“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而2019年後,劉小樣開始刻意地在院子裡種花,茉莉、玫瑰、百合、山茶……“誰也不能動我的花,誰動我的花我跟誰急。”就連縣城綠化帶的花她也不放過,春天她騎車路過看到了粉白的海棠,覺得“這麼好的花,應該種到我家。”
於是在《她的房間》里出現了神奇的盛景——同樣是農村,別人家門前的空地都種蔥和辣椒,而劉小樣卻種了一大片紫茉莉和玫瑰。
養花,就像是重新養育自己。正如伍爾夫所說的“女人要想寫作,必須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而劉小樣正在創造一座屬於自己的花園。據張越透露,節目名字《她的房間》也正是源於這句話。
讀書,也是她多年來從未放棄的愛好。
她曾說在在給《半邊天》寫的信里表達過自己的無書可讀的痛苦,“你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自己因為沒書讀,別人是看電視,而自己是“讀電視”。
20多年來,零零散散讀了太多書了,海明威、契訶夫、加繆、尼采、叔本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或被解構玩壞或被束之高閣後現代主義哲學家、文學家成了劉小樣的“精神麻藥”,她總能在書里找到靈魂共振。
她並不盲目推崇一些“經典必讀”,相反,她總是能結合生活和其他的書表達出一番自己的見解。她不讚成《月亮與六便士》中查爾斯為了追求藝術棄妻兒於不顧的行為,她有一種莊稼人的誠實,不認為追求藝術就比在家幹農活要高級,藝術比家人更重要;她喜歡《老人與海》,覺得只拉回魚骨架、被視為失敗者的老人是個“英雄”,“我們用盡全力,該做的已經都做了,結果是什麼我們不問了。”
劉小樣還有邊讀書邊做筆記摘抄的習慣,每次朗讀還會自責自己“為什麼沒寫出來這些”,於是《她的房間》成為一堂極佳的讀書交流會。劉小樣朗讀她摘抄加繆的《置身於苦難與陽光之間》,想要和他一樣“拿石頭打磨自己這塊石頭,一直讀書,一直痛苦,一直愛著從痛苦荒蕪里生出來的喜悅。”讀到契訶夫《三姐妹》里那句“至少給自己創造另一種生活環境,安排像這樣的住處,有花,有大量的陽光……”她精神矍鑠,“這就是我想要的那種(生活),他雖然是俄國人,但他說的話,咋跟我的想法那麼接近。”
她不怕痛苦,她只怕沒有機會接近陽光,因為她渴望在痛苦中開出花來。
相比於蘇敏一直在和父權與規訓鬥爭(無賴丈夫、經濟壓力),劉小樣的鬥爭更為隱蔽,借用她摘抄的加繆的話來說,她一直在和自己的“無知狹隘,偏見,陰暗,見招拆招”——母職與農村環境的規訓早已內化在她骨子裡,而她天生的敏銳思想和聽收音機、閱讀帶來的充盈在不斷提升她的饑渴感,當貧瘠的土壤無處汲取養分時,她只得逃離。
而現在,她不做乘涼人,而要做種樹人。既要身體力行,去勞作去打掃;也要保持好奇心,去創作去養育。
就像曾經的《半邊天》節目里,劉小樣穿一身紅衣在灰黃一片的天地和田壟間,猶如想和現實的碰撞,她不想被灰黃吞噬。而在《她的房間》,她穿上了白色T恤,但她卻把那抹紅種在了家裡,塗在了嘴上,或許表現方式變了,但燃起的火焰從未在她心中熄滅。
三、千萬個劉小樣
當年半邊天的開頭,張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生活在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修養、不同貧富條件下,人和人之間心裡到底有沒有一個真正共通的東西?”
劉小樣的事蹟告訴我們,有的。
曾經劉小樣在公眾視野“消失”後,對她的尋找從未消失。她似乎無處不在,她對於精神生化自覺又強烈的追求在媒體傳播下,感動、啟發了許多女性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中有河南農村多女家庭的女兒,不受重視,但在看了劉小樣那期節目後備受鼓舞,最終去看平原外面更廣大的世界,現在在歐洲做紀錄片導演,和張越在倫敦進修時偶遇抱著她哭訴自己受到的影響。彝族女孩安小慶也是在看了《半邊天》後逐漸被點亮,追逐著劉小樣的步伐,並將她當做必須要完成的選題、要去接近的人,她認識了張越,幾番周折才寫出了《平原上的娜拉》。
而這次《她的房間》第一期,也是劉小樣、張越、安小慶一起在雲南大理錄製的。她們見面時緊緊擁抱在一起,互送了花朵。
劉小樣聯結了不同地域、不同領域的女性。打通了人和人之間心底共通的東西。這種共通不僅在知識本身,更在於知識賦能後能傳遞的力量,能帶領她們打破狹隘的固守觀念,成為一場燎原的星火。
她們可以走出房間,去探索更廣闊的世界。在《她的房間》里,開海季的傍晚,漁舟唱晚,張越和劉小樣在洱海旁聊起《老人與海》,拍攝快結束時,洱海對岸出現了一道彩虹,她們大笑著迎接它,感受它。
她們也需要屬於自己的房間。去讀書、寫作、思考,自由表達觀點,捍衛痛苦也不要麻木的權力,維持始終思考的能力。“沒什麼,都是西西弗斯的石頭”。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的影視行業出現了越來越多屬於女性的“房間”,不僅僅有《她的房間》,還有《出走的決心》《好東西》《熱辣滾燙》等等,都讓人充滿著pa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