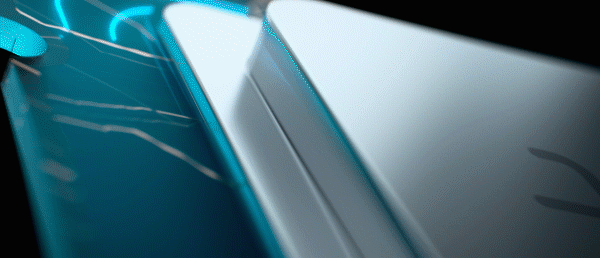安東尼·葛姆雷:AI正在取代身體,而他用磚塊重塑了存在感
安東尼·葛姆雷用雕塑重新定義了身體和環境的關係,他的作品讓觀眾重新回歸身體的感知與體驗。
在電影《黑客帝國》(1999)中,尼奧從矩陣中醒來,他驚恐地發現,自己原本以為的真實生活不過是一場幻覺,而自己的身體則被封閉在一個巨大的人工裝置中,像一塊電池,成為機器獲取能量的工具。在矩陣中,他的感知、行動甚至身份,全部由一個人工智能系統精心編織的虛擬現實操控。身體變成了一具沉睡的軀殼,而真正的他似乎只存在於一串信息代碼之中。
 (圖/《黑客帝國》)
(圖/《黑客帝國》)在今天看來,這一情節越發像對技術時代未來的隱喻。從智能手機到虛擬現實,從可穿戴設備到腦機接口,人類與科技的關係正在變得前所未有地緊密。當人類越來越依賴技術,身體的歸屬感會不會因此逐漸消失?在千禧年的預言越來越接近現實的當下,這個問題愈加顯得重要。
美國學者N.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在她的著作《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中,分析了技術如何改變我們對身體的認知。她提出,隨著計算機和虛擬現實技術的興起,人類越來越多地將身份和存在感轉移到數字空間中。身體的重要性逐漸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和意識的優先地位。
歷史學家尤瓦爾·諾亞·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的進步可能徹底改變人類對身體的依賴。未來的「身體」可能被增強、編輯甚至完全數字化。這一未來圖景或許令人興奮,但也讓人感到不安。
然而,這種視野並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葛姆雷的藝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他用雕塑重新定義了身體和環境的關係,他的作品讓觀眾重新回歸身體的感知與體驗。
在常青畫廊呈現的葛姆雷的展覽「棲息之所」中,藝術家用堆疊的磚塊構築了一片迷宮式雕塑叢林,這些雕塑或蜷縮,或舒展,或散落開來,述說著身體的不同狀態。葛姆雷用這些生動的「身體雕塑」提醒我們,無論技術多麼先進,人類的身體依然是我們最原始的「歸屬地」,也是我們與世界建立聯繫的起點。
「有了世界,我們才會被塑造」
在展覽「棲息之所」的現場,一系列由磚塊堆疊的雕塑以迷宮般的結構橫陳在展廳中,這些雕塑一起構成了展覽的核心作品《休憩之所II》。它們以靜止的姿態分佈在展廳中,有些像嬰兒一樣蜷縮著,呈現一種自我保護的姿態;有些則像在進行拉伸運動,將肢體的末端向外延伸;還有一些無規則地鋪展開來,像在草地上沐浴陽光——生活在英國的葛姆雷應該對這樣的姿態再熟悉不過,在英格蘭難得的好天氣里,草地上都會「長滿」這樣的身體。葛姆雷說:「我希望通過這些姿勢,讓觀眾感受到什麼才是讓自己感到輕鬆的狀態。」
葛姆雷將此次展覽的核心概念解釋為:「有了世界,我們才會被塑造。」在他看來,人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不僅定義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也深刻塑造了人們的存在方式和身份認知。
這是葛姆雷在中國做的第14場個展。2016年,在常青畫廊為他的個展「屯蒙」特別隔出的414平方米的區域內,從昌平區地表以下挖出的泥地鋪滿了展廳地面,從天津港運來的海水灌進了土裡,水深23釐米。土與水以50∶50的比例混合,形成了一片95立方米的「海」。「那時我在展覽主空間里注入了大約100噸海水和5000公斤泥地。通過引入外界元素的方式——可以說是把自然景觀帶進來——將這些元素帶進了人類建造的空間。對於觀眾來說,觀看就變成了一件有門檻的事,因為這樣的佈置讓人只能從外部或者遠距離觀察它。」葛姆雷說。
 「棲息之所」展覽現場。(圖/由被訪者提供)
「棲息之所」展覽現場。(圖/由被訪者提供)「棲息之所」的展覽中,構成作品的磚塊全部是在中國本土燒製的——這種紅色磚塊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建築材料——它們沒有將觀眾拒之門外,而是允許人在磚塊堆疊而成的「身體叢林」中穿行。葛姆雷認為:「這樣的佈置要求觀眾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去回應作品。‘屯蒙’選擇的方式是讓觀眾站在一個平台上,把人固定在一個位置。而這次展覽則直接把人引入有組織的空間里,這些堆疊而成的‘身體’構成了一種迷宮式結構,觀眾被邀請在中間走動,並因此成為創作的一部分。」
這樣的設計試圖讓人們通過身體的移動,喚醒感知,讓人重新審視空間與身體的關係——在一個越來越依賴虛擬交互的世界中,這種對物理空間的體驗顯得尤為珍貴。
連接土地與記憶的藝術
葛姆雷曾多次造訪中國,從單車仍佔據街道的年代,到城市建設如火如荼的階段,再到摩天大樓構成天際線的今天,葛姆雷以旁觀者的身份注視著這裏的變化。他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改變了物理空間的佈局,也影響了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從以胡同為代表的低密度佈局到大樓林立的高密度佈局,棲居在這裏的人類在物理空間的演變中逐漸失去了與土地的連接。
葛姆雷的作品始終希望與土地保持緊密的聯繫,他形容展覽中的雕塑為「靜止的身體」。他說:「這種靜止並不是死亡的象徵,而是一種放鬆的狀態,是身體在脫離工作後進入的自然休憩。我希望通過這些作品讓大家重新思考身體本身作為一個‘空間’的意義——作為我們最初的歸屬地,它如何承載我們的存在與體驗。」
葛姆雷出生於倫敦,他的創作也紮根於這座城市。儘管這裏是全球重要的藝術文化中心之一,但行走在倫敦市中心,不會時時刻刻都讓人感到距離藝術很近。不過,當你走到國王十字附近的街區時(這裏是中央聖馬田藝術與設計學院的所在地),藝術氛圍就開始濃厚起來。葛姆雷的工作室也坐落在這片區域——一個佔地約2000平方米的創作空間,大約有30人各司其職,葛姆雷就像「船長」。每天,他都會在早上8點至9點抵達工作室,通常工作到晚上6點以後,有時甚至更晚。
葛姆雷喜歡與人一起工作,無論他們是專業的藝術家,還是與藝術遙遙相望的人群。
從1980年起,他開始與世界各地的不同社區合作《土地》系列,這組作品令他獲得英國藝術界最高獎項——透納獎。《亞洲土地》是葛姆雷於 2003 年與廣州象山村村民合作完成的。
回憶起當時的創作經歷,葛姆雷說:「我們就在一所中學的籃球場上工作,空間開闊,有大約350人參與了創作。這簡直就是一次社區的慶典,可以說是一個派對。參與者來自不同的年齡段,有些大家庭結伴前來,他們是彼此的孩子、父母和祖父母。通過一起做事、結識人,是一種非常深入的體驗。這種氛圍讓我感受到中國家庭和個人之間那種特別的聯繫,我與他們一起準備食物,圍坐一桌,一起剝豌豆,每個人都沉浸其中。」
在眾多參與者中,葛姆雷對那些年長的女士印象深刻:「她們很多人都已經超過80歲,仍然加入了這個項目和自己的孫輩一起做事,她們告訴我很多關於舊日中國的故事。有一位非常有尊嚴的女士,她很能幹,年紀大了卻一直保持著非常獨立的工作能力。她經歷了很多,甚至見證過溥儀時代,與她交談時產生的那種直面歷史的感受讓我記憶猶新。」
對葛姆雷來說,身體不僅是個體意志的容器,還承載著無法被替代的記憶。在技術日益支配生活的當下,傳統的「身體」不停被消解,被數字化的意識和虛擬技術邊緣化。然而,通過與社區居民的合作,他看到身體依然是人類記憶與情感的最直接載體,是連接個體與文化、歷史的橋樑。
 「棲息之所」展覽現場。(圖/由被訪者提供)
「棲息之所」展覽現場。(圖/由被訪者提供)《亞洲土地》在廣州首次展出時,葛姆雷專門安排了大巴車把參與製作的村民接過去,他說:「我覺得很多人對自己參與的創作產生了感情,雖然加入的時候他們並不完全知道自己參與的是什麼,但當他們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一個巨大的地下停車場中展出時,那種感動是非常真實的。」許多人知道葛姆雷,是通過他創作的那些已經成為城市地標的大型公共藝術裝置,而「身體」是貫穿這些作品的標誌性符號。作為當代雕塑界的領軍人物,葛姆雷將那些廣泛陳列於美術館、畫廊中的鑄鐵人體雕塑引入公共空間,將它們安置在廢棄的煤薩克達廠(《北方天使》,1998)、摩天大樓的樓頂(《視界》,1997)、英國西北部的海岸線(《別處》,1997)……這些作品與他們的締造者一樣,審慎地思考著身體與環境的關係。
看著葛姆雷的作品,會讓人燃起創作的希望:無論選擇哪種媒介,無論此種媒介已經被使用、濫用、誤用到哪種程度,都會發現創造的天花板是如此遙遠,可供想像的空間似乎無窮無盡,因此對未來充滿樂觀的期待。
在一個越來越傾向於「後身體時代」的社會中,葛姆雷的作品讓人們意識到,身體是構建歸屬感、文化認同以及情感交流的根基。他的雕塑提醒我們,創造的邊界是開放的,而身體的意義將無法被忽略或簡化。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週刊」(ID:new-weekly),作者:Ariana,編輯:尤蕾,36氪經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