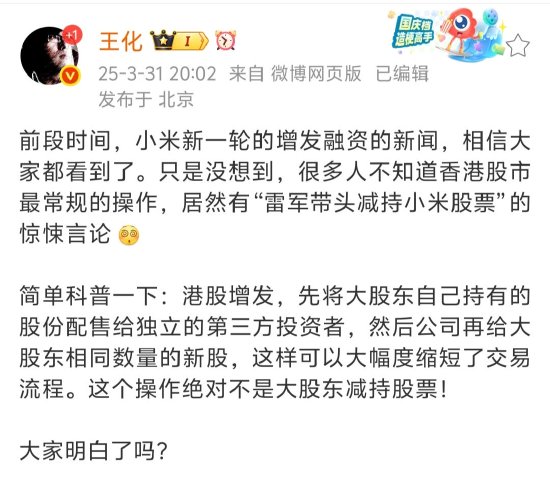趙冬苓聊《沙塵暴》:在荒漠刑偵敘事中打撈那些被現代化進程“吞沒”的人|Talk對話
 作者 / 朱 婷
作者 / 朱 婷運營 / 獅子座
編劇趙冬苓、導演譚嘉言,監製高群書,主演段奕宏、王鏘、張佳寧、張瑤、黃小蕾,在《沙塵暴》未開播前,率先吸引眼球的無疑是其“王炸”班底。怎麼看,這樣一個陣容集體創作出的東西都不會差吧。3月28日,優酷白夜劇場開年力作《沙塵暴》開播,誠不欺我。一組組大西北的空境,隨著警車、摩托車一起起飛的漫天黃沙,像極了劇中一個個暗藏秘密的角色,都在空中飄著,但似乎永遠飄不出那片荒漠。在這些充滿西北粗糲質感的畫面里,包裹著一樁塵封八年的鍋爐藏屍案。
值得一提的還有,《沙塵暴》亦是國產懸疑劇罕見地將大西北的地貌特徵作為敘事容器,打造具有雄渾粗糲質感的“荒漠”刑偵懸疑劇,成功補齊國產懸疑劇地域版圖。
而對於編劇趙冬苓而言,《沙塵暴》無疑也對其編劇生涯有著尤為重要的意義。她在與包括《文娛Talk》在內的多家媒體的對話中,毫不掩飾自己是一位懸疑題材的深度愛好者,雖說《沙塵暴》是她的首部原創懸疑精品劇,但實際上她認為自己已經為此準備了很多年。
和常規的懸疑劇不同,《沙塵暴》選擇在一開始就有意無意地透露一部分真相,甚至是兇手跡象,這樣的去推理化,是對故事和人物本身的一種自信。更為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她要寫的不是某個具體案件,而是整個群體在時代裂變中的失重狀態。在她筆下,荒漠地區也好,其他地區也罷,都不僅只是地理概念,更是現代化進程中那些被遺忘之地的隱喻。
誠如被問及創作初衷時趙冬苓的表述那樣,她想呈現的是快速現代化進程中,那些被甩在身後的邊緣地帶,在那裡發生的事和人。不僅是經濟差距,更重要的是城鄉之間、中心與邊陲之間觀念和生存狀態的撕裂感。或許,是時候停下來想一想,時代的列車呼嘯向前,那些被現代化進程‘吞沒’的人,他們跌落在哪裡?如今生活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以下是《沙塵暴》編劇趙冬苓與《文娛Talk》等媒體的對話:
一、創作緣起
最先引發大眾熱議的莫過於鍋爐里突然掉出來一具燒焦的屍體,這個充滿暴力美學的場景亦是《沙塵暴》的敘事原點,隨後,編劇趙冬苓便由此虛構了這一段發生在大西北荒漠偵探的故事。
Q:《沙塵暴》這個故事虛構在西北荒漠,在中國的懸疑里地理位置上不是那麼的常見,又以鍋爐掉下屍體這樣的強視覺衝擊開端,開篇靈感來源是?以及為什麼把背景虛構在西北呢?
趙冬苓:《沙塵暴》這個故事和我過去創作別的作品不太一樣。最早在最高檢採訪時,有檢察官提到一個案子:裡面有個鏡頭是從鍋爐里掉下來一具屍體,當時這個畫面衝擊力特別大,我就覺得這是個絕佳的故事開頭。但具體要寫什麼主題、發生在哪裡,當時完全沒概念——這和我過去從採訪積累素材再創作的流程完全不同,屬於從單一影像反推故事的特殊情況。
在反複修改過程中,故事方向逐漸清晰。我想表現中國快速現代化進程中,那些被甩在身後的邊緣地帶。不僅是經濟差距,更重要的是城鄉之間、中心與邊陲之間觀念和生存狀態的撕裂感。就像我每次回老家,總覺得那裡時鍾走得特別慢,人和事都停留在某種舊時光里。這種傳統生活形態與現代文明的碰撞,正是我想捕捉呈現的。
有了這個之後,才開始設置這個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比較合適。我想寫一個資源枯竭的小城,它不一定是要設定在西北,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第一集,鏡頭從大片原來的鐵路通過,不光是西北,內地也有很多類似資源枯竭的城市。這樣的小城不光是資源枯竭,你回到那兒會發現基本上都是熟人社會,而大城市就意味著陌生人社會,這兩者之間在生活形態上、思維方式上都會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寫這個東西!
追問一下,為什麼聽到這個案件就有了創作靈感?
趙冬苓:太驚悚了!當時我腦子裡就有那個畫面了,鍋爐轟轟響,突然扒鍋爐灰時掉下來一具屍體,隨後,激起漫天灰塵。我們出來之後立馬就討論起這個畫面,當時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寫個故事,把這個畫面用上,這樣的場景,衝擊力太大了。
作為一個懸疑劇,第二集時大家就猜出來兇手或者兇手之一,這個是您的刻意為之嗎?
趙冬苓:現在的觀眾都非常聰明,你再掩飾觀眾也會猜到誰是兇手,我更喜歡那種老鷹抓小雞的模式。《沙塵暴》一開始會讓觀眾隱約猜到兇手或者兇手之一是誰,但對他到底為什麼去作案還是得往後看,這個過程正是藝術所要著力表現的地方,我也希望這一點對觀眾有足夠的吸引力。
Q:好奇這個本子大概寫了多久,以及您在寫的時候有沒有代入演員人選?
趙冬苓:劇本從構思到創作曆時3年,中間經曆了兩三次大的推翻修改,最終一稿是一兩個月完成。至於代入演員與否?我做編劇時間太長了,深知代入是沒用的,最後永遠不知道會碰到什麼演員。但對陳江河這個角色是想過的,比方說現在的主演,段奕宏這一派比較硬漢、比較粗獷的演員,但確實不確定到底能不能找來他們。
二、一次類型敘事與社會觀察的有機融合
Q:您覺得《沙塵暴》這個故事題材,最重要的是懸疑推理還是城鎮化的縮影呢?
趙冬苓:這兩方面都有體現。這次寫《沙塵暴》,特別想打造一個嚴謹的破案敘事——通過兩個相互關聯的案件,展現抽絲剝繭的推理過程,確保每個破案環節都經得起邏輯推敲。
同時,在劇本構建過程中,自然融入了對城鄉差異的觀察。現代化進程與傳統農耕文明的碰撞,構成了故事的重要底色。這種時代背景與罪案推理並非刻意疊加,而是隨著人物命運展開逐漸浮現的。可以說類型敘事與社會觀察在這個故事里形成了有機融合。
Q:在這樣一個空間里所謂的法理和情理之間的矛盾,反而不是劇中人物最重要的動因。比如支撐留下來的那群人,他想用情感維繫周邊的人際關係;而想走的那群人,更多可能是慾望驅動,想邀請趙老師就這個點做一下分析。
趙冬苓:就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來說,維繫陌生人社會的絕對不是情感,維繫熟人社會的大部分是情感,維繫陌生人社會的可能就是彼此之間的利益,或者是規則、法律。
Q:這個劇里小鎮的女性都想走出去,但男性最後都選擇了留下來,對此,您是如何考量的?
趙冬苓:引起案子的主要人物劉大誌是一個男性,他首先走出去,而且堅決不回來。原來所有人都想走出去,包括陳江河,正是由於他想走出去才導致其師父的受傷,又因為他師父受傷,導致他在這個地方有了羈絆沒有走出去,最後選擇留下來。劇中的主要人物王良,他從來沒有見識過外面的世界,所以一直不想走出去,一直到最後他死在回家的路上。
坦白說,確實沒有考慮過性別,而是根據每個角色的人物軌跡發展去設計到底要不要走出去。
Q:為什麼要讓孫彩雲成為如此重要的角色,包括成為連接兩個時間點,兩起焚屍案件的關鍵人物。
趙冬苓:孫彩雲挺像我以前在農村碰到的,或者前些年成千上萬的農村打工妹,她們身上有特別強烈的生命力。
有一次我站在一家物流公司的院里,晚上燈火通明的大樓,大家還在分揀,伴隨著轟鳴的機器,我站在那裡熱淚盈眶。我覺得這真的是獨屬於中國的故事,而背後驅動的是所有來自非常底層的人,他們那種強烈的要發財、要改善自己生活的慾望。劇中的孫彩雲也是這樣種人,一定要衝出去,不管用什麼手段。當然孫彩雲和我剛才說的非常正面的奮鬥形象不一樣,她走了另外一條路,但這種非常原始的慾望是一致的。
Q:您認為哪一集的哪一部分讓您感覺非常驚喜,和劇本當中呈現的完全不一樣?
趙冬苓:我看的是粗剪版,台詞還沒有調音,但能看出來譚導(導演譚嘉言)對劉盈盈(張佳寧飾演)情有獨鍾,他對這個人物充滿了感情,所以他拍盈盈拍的非常好。和他交流的時候,我說導演不能愛一部分人,不愛另一部分人,作為編劇尚且可以偏愛某些人,寫這些人物的時候寫的比較細,有些很次要的人物傾注的精力可能就沒有那麼大,但導演應該平等地愛所有角色。
其實也不止是導演,相信觀眾對盈盈這個角色的接受度也會比較大,我覺得她是“大女主”,自己做事自己當,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身上有這種決絕的氣質。
Q:您自己在寫的時候,讓您覺得寫的最過癮的角色是哪個?
趙冬苓:其實就是兩個女性角色,孫彩雲和劉盈盈。
三、趙冬苓的原創懸疑精品首秀?
Q:您之前都是長劇居多,《沙塵暴》聽起來既有懸疑,也有城鎮化縮影的故事,濃縮到12集的創作體量會是一個挑戰嗎?
趙冬苓:這兩年我其實已經創作了六七部精品短劇(目前尚未播出),對短劇體量有充分實踐。我認為單一敘事本身天然適配短劇形式——若僅聚焦案件本身,十幾集已是容量極限,這點從美劇的單集案件模式也能印證。
《沙塵暴》的12集體量並非刻意設計,而是創作規律的自然呈現。相較於常規懸疑劇,我們在案件主線中嵌入了七八個主要人物的完整命運軌跡。每個角色不論戲份輕重,都被賦予了鮮活的生命曆程:從核心人物到看似邊緣的配角,都具備獨立的人物弧光。
這種創作慣性源自我始終堅持的敘事觀,即拒絕將人物工具化。即便在懸疑類型框架下,我仍要求每個與案件相關者都成為“完整的人”。當這些立體角色與小縣城城鎮化背景深度交織時,12集的體量便成為承載人性厚度與時代縮影的必然選擇——是人物命運的重量而非案件複雜度,最終決定了故事的敘事尺度。
Q:《沙塵暴》和其他作品相比,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方法?
趙冬苓:《沙塵暴》雖然長度只有12集,但我完全是用做長劇的方式做的。我現在慢慢總結,現在所提倡的短劇和長劇有什麼區別呢?第一是因果關係,鏈條要縮短。比如一個40集的長劇,第一集寫的因,最後才發展到果,可能要延續40集,或者延續好多年,這個故事才算整個發展脈絡。而一個短劇的因果關係,鏈條必須縮短。
第二個很重要的點在於短劇壓縮了人物成長的空間。如果10集以內、或者12集的劇,又要達到大家希望的一出場就炸場,全程高能不斷反轉,那種強刺激、強輸出這種,就很少可以為塑造人物留下空間。但塑造人物就需要細節,需要一定的空間,需要建構人物關係,需要占篇幅。
Q:從別的領域開始來寫懸疑劇,有哪些個人的風格是可以延續過來的?哪些方面是有突破的?
趙冬苓:儘管《沙塵暴》可以說是我第一次寫懸疑劇,但我覺得好像已經為這一天準備了多年。我一直對這個題材,包括我小時候看的書,都對這方面的故事有所偏愛。比如說過去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後來日本的推理劇/推理小說,我看了大量這方面的書,所以說對寫這個題材的作品算是早有準備,但不是有意識的準備。
另外,我在編劇里還算是邏輯思維能力比較強的。比方說我喜歡寫法律題材,喜歡寫法庭辯論,平常涉獵的也比較廣泛,這些可能都是我創作上的特點。所有這些在我有機會處理懸疑題材的時候,我會一發而不可收拾。寫懸疑對我來說,更多是在塑造人物、表現宏大背景前提下,做到邏輯上的嚴謹,不能說毫無bug,但不能出現太大的bug,因為現在的觀眾太聰明了,有一點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他就是會挑出來的。
所以,邏輯推理是我最大的挑戰,我也儘可能謹慎,希望做到最好。具體到寫《沙塵暴》最大的困難,可能是前面那一部分比較焦慮,我喜歡這個故事,鍋爐里掉下一具屍體,圍繞這個開頭怎麼推理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一段對我來說是比較痛苦的,就是你需要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最後慢慢克服了,找到了現在的表達。
我的劇本每一個字都是我自己寫的
Q:這兩年懸疑劇挺多的,在您看來《沙塵暴》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趙冬苓:我不敢說《沙塵暴》就獨一份,寫的時候也沒有這種野心。因為我本人創作的特點,導致《沙塵暴》呈現這個故事,一個是主題的追求,它涉及到非常大的主題表達,即:現代化進程當中,農業文明一下子過渡到現代文明,兩種文明的差距產生了很多故事,大背景賦予了這個故事;再一個,在破案上我就希望能夠很嚴謹地把一個案子寫得精彩,破的過程比較精彩,在這一點上我不知道做的是不是很好,但希望這個案子不僅僅是這個案子,而是所有人無論大小、無論戲份多少,人物能夠鮮活,能夠有它自己自始至終的命運。但你說是不是好呢?我覺得還是交給市場和觀眾去檢驗。
Q:現當下市場里,懸疑劇的節奏成為觀眾審判的重要維度,很容易陷入一集棄、三集罵的局面,您會擔心《沙塵暴》播出後有這種困境嗎?以及作為創作者,短視頻時代下要求很快,又要給強情節,這些點會影響到您的創作嗎?
趙冬苓:坦白說,到現在我也不大會去考慮豎屏短劇的衝擊,有人說“長劇短劇化”,對這種理論我認為是有待商榷的。所謂的短劇,它的呈現方式如果只壓縮到10集,10分鐘、20分鐘的短劇,那就談不上什麼人物塑造了,它更加追求的是一個強情節、強情緒的輸出。作為創作者,還是希望通過時間、空間、一定的情節去塑造人物。就像寫小說:有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也有講笑話、講段子,我不相信所有人都只喜歡聽段子。
所謂豎屏短劇的衝擊也是這樣,幾分鐘一個反轉,非常極致的人物設計,抓馬的橋段,一定會吸引大量的觀眾,但我不相信所有觀眾都希望打開屏幕全是“霸道總裁愛上清潔女工”,我不相信!會不會流失一部分觀眾呢?我相信也會的,其實電視劇市場最後細分的結果就是各美其美,各種題材、各種體量的電視劇去尋找自己那部分觀眾,那部分觀眾也會尋找自己喜歡的電視劇。
Q:很好奇您現在的工作狀態是怎樣的,怎麼保持這種超強的產出能力?
趙冬苓:很多人都懷疑我有槍手,但我沒有,我的劇本每一個字都是我自己寫的。我平常的生活狀態:每天不是在寫作,就是在去採訪的路上,幾乎沒有更多的生活,有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像一部寫作機器,對這個行業,對我自己從事的這份工作充滿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熱愛,而是把它看成我的生命。難以想像,如果有一天我不寫作了,我會怎麼樣,我正常的工作就是坐在這兒寫作。
另外,我的劇本很少有改動,《沙塵暴》算是改的比較多的一部。我的大部分作品基本上都是寫一稿就差不多定稿,所以我能夠保持產出量比較多。
Q:您怎麼看待《沙塵暴》在整個作品序列中的位置,它對您來說挑戰和興奮度是什麼?
趙冬苓:興奮度就是我寫了第一部懸疑劇,《沙塵暴》是我完全把劇本做成熟了,拿到平台,平台通過,再開拍。所有的作品,我自己特別喜歡的一部可能也是大家不太能記住的《沂蒙》,不大具有商業性,但我特別喜歡。其他的,我一視同仁。
寫在最後:某種程度上來說,《沙塵暴》這個劇名,既想表達罪案真相如沙塵般撲朔迷離,也暗示那些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個體,終將歸於命運應有的軌跡。趙冬苓在那個晚上看到的燈火通明的高樓,何嚐不像另一個巨型鍋爐?——有人苦苦掙紮,有人燒得熱烈,有人化為灰燼,但總該有人記錄下每粒塵埃的故事。於是,趙冬苓執筆寫下《沙塵暴》,在荒漠與現實的雙重風暴中,固執地打撈著那些即將消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