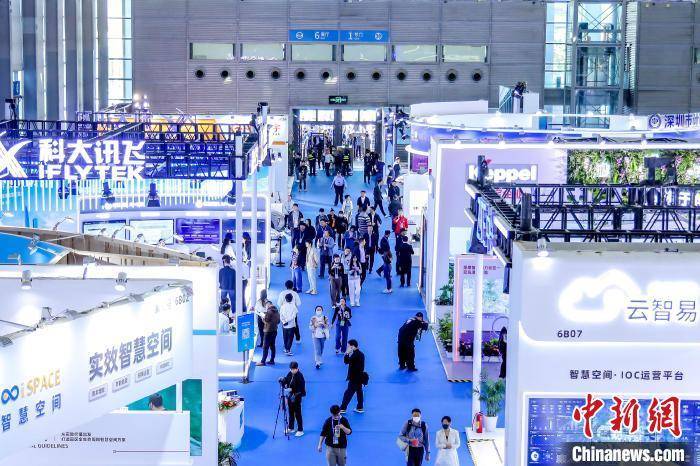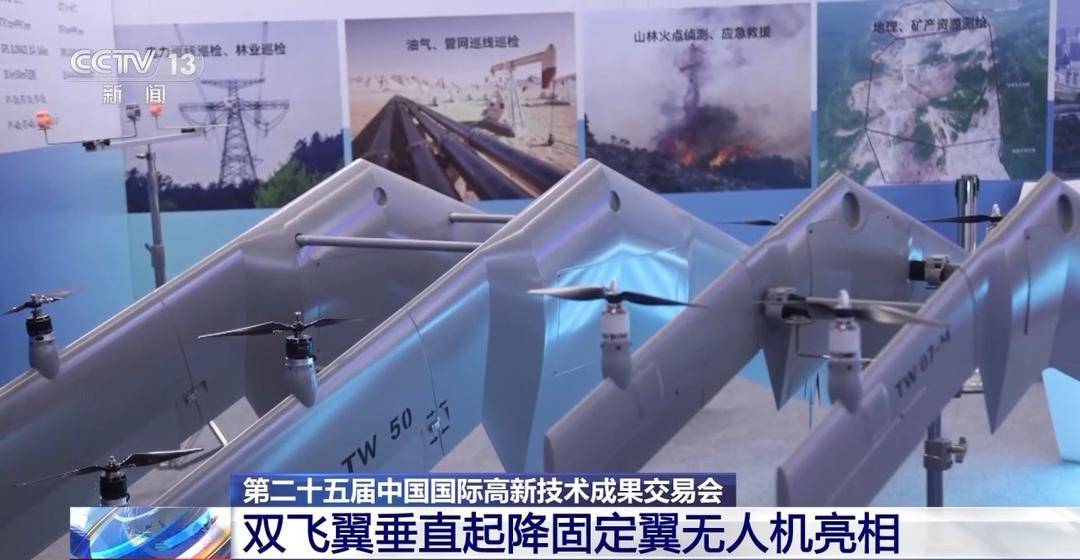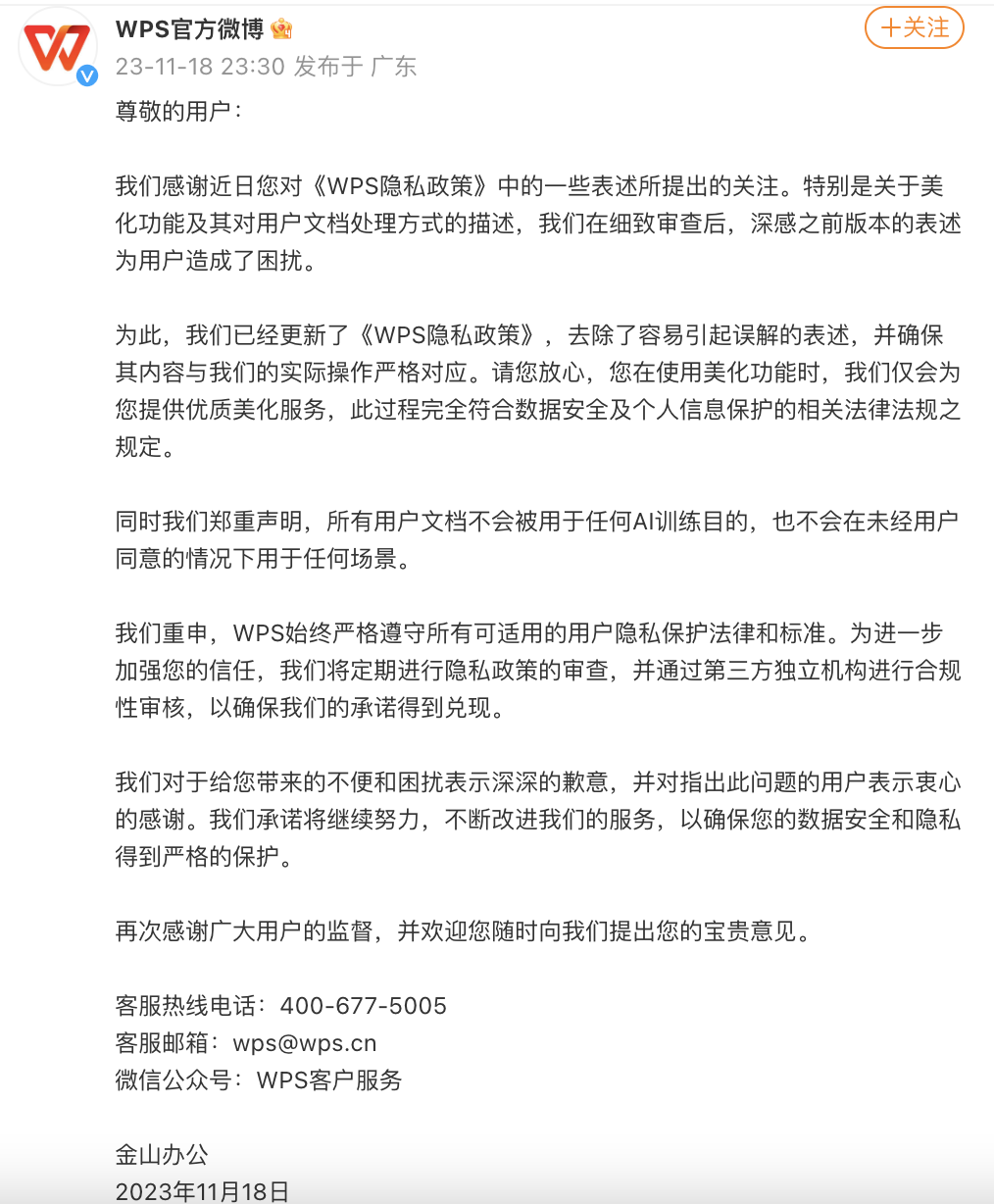錢鍾書的“圍城”意象:從婚姻到人生萬事
【編者按】
張文江先生的《錢鍾書傳》按時間順序將錢鍾書的一生劃分為早年生活和求學、意園神樓、滄浪之水、槎通碧漢、群峰之顛五個階段,將經曆與著作交織考索,做出自己的解讀,尤其從結構系統的角度分析了《管錐編》《談藝錄》《七綴集》等著作,本文是關於錢先生著名的“圍城”意象的解讀,澎湃新聞經上海文藝出版社授權發佈。
錢鍾書一生有著多方面的成就,其大類有二:作家與學者。如果作為學者的錢鍾書可以用《管錐編》《談藝錄》為代表的話,那麼作為作家的錢鍾書只能以《圍城》為代表了。《圍城》是作者一生寫成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其地位無可替代。錢鍾書在寫作《圍城》前,還有散文隨筆和短篇小說的創作,這些創作都可以看成寫作《圍城》的準備。它們包含的創作信息,至《圍城》初步成象。錢鍾書寫完《圍城》就感到不滿意,則這一形象應當有所變化,那就是第二部長篇小說《百合心》了。
錢鍾書寫完《圍城》後,還不滿四十歲,還有足夠的創作衝動和能力,以錢鍾書“不斷叩向更上一關”的精神,第二部應該勝過第一部。錢鍾書評論《百合心》時說:“對採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百合心》應當符合作者“分外地甜”的信念。不僅如此,《百合心》還未必達到高峰,錢鍾書還有創作其他長篇的可能,大致延續至1957 年與完成《宋詩選注》的時間相齊———也許錢鍾書這時才會真正轉移興趣———那才會是錢鍾書小說的真正高峰。然而,錢鍾書在完成《圍城》後,1949年在搬家的忙亂中遺失《百合心》手稿,以此為契機,錢鍾書“由省心進而收心”,就此中斷了小說創作,這極為可惜。但也因為如此,反而使本來多少具有實驗性質的《圍城》就此保存了創作方面的全部信息,在錢鍾書著作系統中屹立不變,占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錢鍾書開始寫作《圍城》,是在1944年的上海。那一年錢鍾書和楊絳同看楊絳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錢鍾書突然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很高興,催他快寫。當時錢鍾書在修訂《談藝錄》,又在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於是楊絳在多方面給予幫助:她讓錢鍾書減少授課時間,進一步節省本來已經節省的生活,並且自己兼任女傭的工作,甘心情願地做“灶下婢”。這樣,錢鍾書才得以集中精力,在1944年至1946年兩年之內,“錙銖積累”地寫成了《圍城》。《圍城》最初在鄭振鐸主編的《文藝複興》上連載,之後在1947年出版單行本,1948年、1949年重印,大受社會的歡迎。
楊絳指出:“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題材全屬虛構。”錢鍾書觀劇回來發興寫《圍城》,只是具體的觸發。而小說的種因,卻相當久遠。如果以錢鍾書1938年夏的歸國為界,對此遠因的追溯,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後兩部分的接續是長期的打底,而後一部分則漸漸成熟為小說。如果沒有對社會和人性(作者所謂“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的長期觀察,如果沒有對婚姻戀愛的體悟和觀照以及對大學生活的體驗,《圍城》的寫作就不可能順利。對社會生活的觀察極長期也極複雜,難以言說,這裏的交織和相合,來自一點一滴的積累,絕無速成之理,然而也能稍稍找到一些早年因素。
正如錢鍾書在大學時代遍讀宋以後集部,是他以後撰寫《談藝錄》的前導;錢鍾書在大學時代對大學生活的體驗以及對婚姻戀愛的觀照,也應該是後來《圍城》小說的前導。1933年,錢鍾書從清華大學畢業,他在畢業年刊上寫了一篇《後記》,其中說:“真正直接描寫中國大學生活的小說至今還沒有出現”,這裏是不是有點微微透露《圍城》的先聲呢?而如果把錢鍾書歸國後的經曆和小說對照,可以看出兩者基本相合:
1938年,錢鍾書和楊絳同船回國,船上的情形和《圍城》里寫的很像。那是小說的第一章。
錢鍾書出國以前在上海的經曆,輔之以1939年夏、秋的自昆明回滬探親,可以相關小說的第二、三、四章。
1939年秋,錢鍾書未回昆明而到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去了。他把從上海到湘西的旅途所經寫進了《圍城》。那是小說的第五章。
錢鍾書在湘西教書兩年,所遇到的一部分醜惡的人和事,構成了《圍城》的素材,真實地進入到角色中去。那是小說的第六、七、八章。
在湘西的兩年中,主要是寫作《談藝錄》的時期,也是完成《圍城》構思佈局的時期。而錢鍾書1941年回滬探親後困頓於上海淪陷區的經曆和情緒,對於完成小說第九章並且最後確定書名為《圍城》,有著重要關係。有此一筆,以貫通小說的題旨,則全盤皆活。
錢鍾書歸國後,沒有回上海,直接到西南聯大去了,這是作者經曆和小說不對應的一段。論者也指出:在《圍城》中找不到聯大人物的形象。西南聯大真的和小說完全無關嗎?聯大的一些人和事是不是也化入“國師”得到了描述呢?錢鍾書在離開聯大時一度不很愉快,也許將來會有人揭示這裏的關係吧。
錢鍾書晚年在談到《圍城》時引用康德的話:“知識必自經驗始,而不盡自經驗出”,斷然否定了關於《圍城》是“自傳”的猜測。但是,錢鍾書的生活經曆還是和小說密切相關,唯其積累豐厚,所以能在兩年時間內“錙銖積累” 地寫成,基本屬一氣嗬成。從生活經曆到小說,必須有長期的醞釀過程,其中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難以追溯複原的轉變。所以儘管《圍城》包含著許許多多和作者相關的人和事(楊絳指出過一部分,應該還有其他部分),它還是一部虛構的小說,一部復合型的虛構小說。
《圍城》有其豐富的內涵,以男女主人公的戀愛為主線展開,但它不是愛情小說,而是一部從婚姻反觀愛情的小說。從人類性愛、情愛的全過程來看,“愛情小說”實際上僅僅是“半截子”小說。愛情小說往往以婚姻的成敗為結束,無論其結局是悲劇還是喜劇,對平常的實際人生來說,總是簡單化的。而從婚姻反觀愛情,所包含的內容自然要複雜得多,在《圍城》中則不得不顯出一種困境。這種困境,如果和社會文化結合,則更為豐實。而在《圍城》中,這種困境處處出現,成為小說發展的推動力。這種困境在小說中有其中心意象,就是作者最後用書名來點題的“圍城”。“圍城”意象,後來被總結成以下一段話:
圍在城里的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在《圍城》小說中,這一意象點出在第三章。最初是借小說人物褚慎明之口帶出羅素(Bertie)稱引的英國古語:
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小說隨即又借蘇小姐之口引述法國成語“forteresse assiégée”點出了這一中心意象:
結婚如同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這就是作者借小說人物在客廳議論中點出的“圍城”意象,所述尚以婚姻為主。而在第五章,又借離開上海的主人公方鴻漸之口對這一意象作了呼應:
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
這就從婚姻擴展到人生萬事了。從婚姻到人生萬事,從人生萬事到婚姻,範圍雖有變化,仍然契合。在小說中,經過反複鋪墊已然厚實的“圍城”意象尚屬空間,但衝進衝出,永不停歇,又蘊含時間。而這一時間變化在小說中,以第九章的祖傳怪鍾來點題,這隻走時落伍的計時機和實際時間竟相差五個鍾頭,它在小說結尾中出現:
無意中包涵了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的語言,一切啼笑。
由此“圍城” 意象和怪鍾結合,完成了小說的卒章顯誌。怪鍾的時間錯亂,也是時代錯亂,反映了作者杜門寂處、蟄居於淪陷區時,觀察種種世相而憂生傷世的心境。
從“圍城”意象觀察整部小說,小說的實際情形和那句法國成語表面似乎並不一致:方鴻漸想逃避衝入蘇小姐的城(“圍城”比喻在小說中出自蘇小姐之口),卻在無意中不知不覺地衝入孫小姐的城,情景似乎反了一反。但是從擺脫一個困境始,到落入另一個困境終,在更高的層次仍然被那句比喻套住,這也說明了“圍城”意象的涵蓋意義。

《錢鍾書傳:營造巴別塔的智者》,張文江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