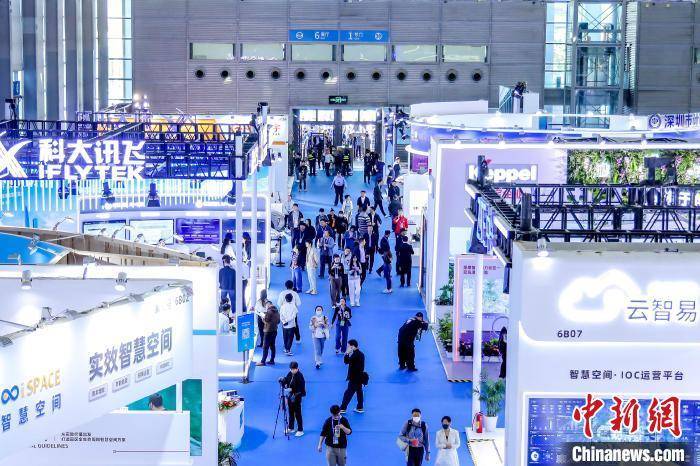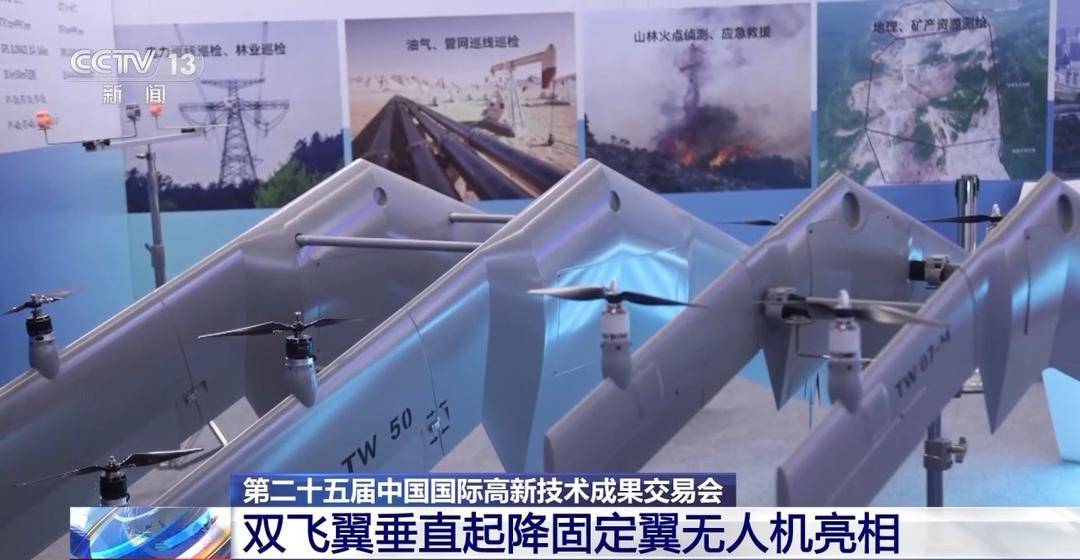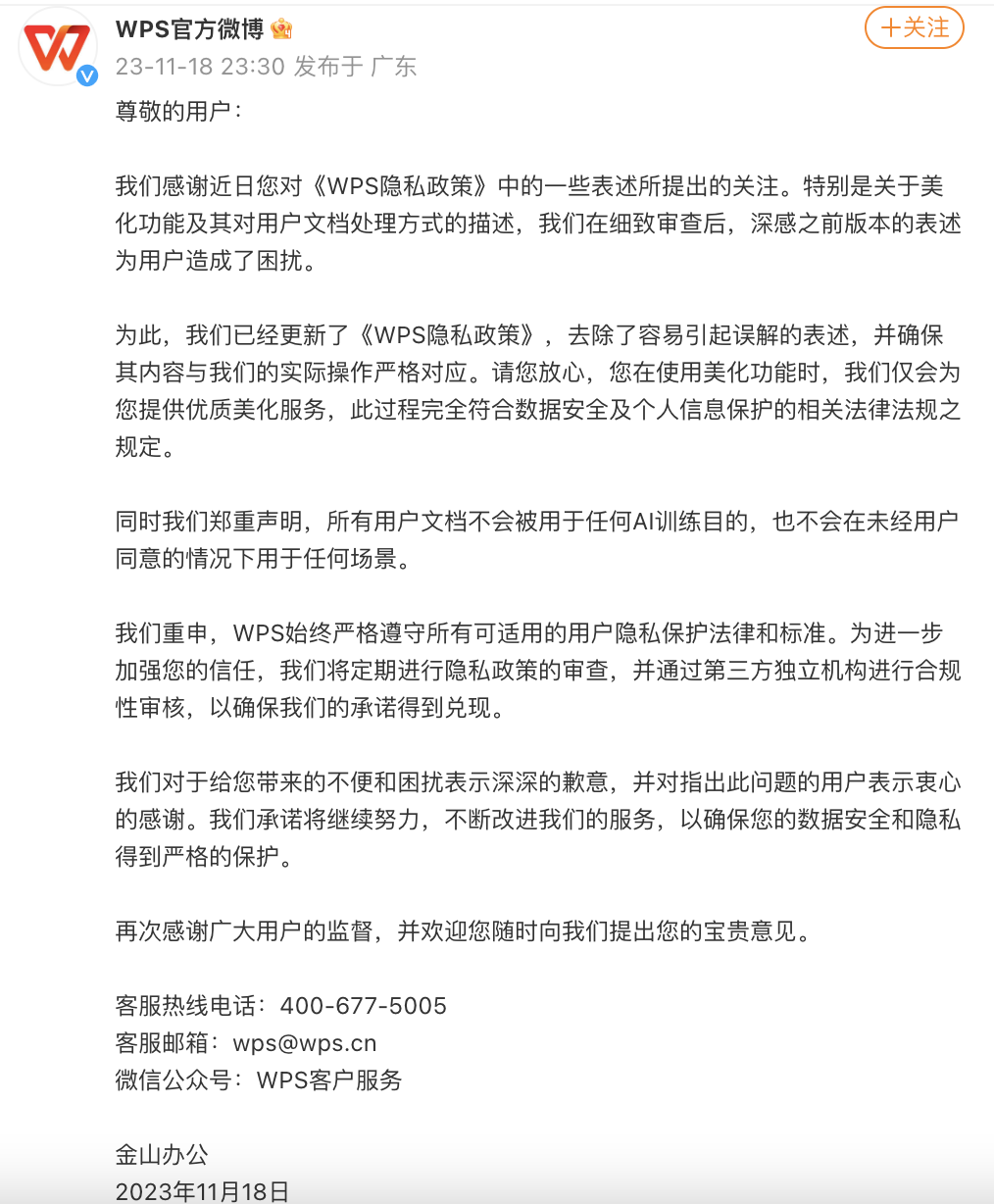線上壟斷,線下碾壓,美國科技巨頭如何加劇不公?
互聯網用戶和平台之間的關係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被強加的《用戶協議》、無法攔截的廣告彈窗、讓人哭笑不得的個性化推薦、同質化的內容、病毒式傳播的網絡用語、背景音樂……我們似乎越來越難在網上的海量內容中找到自己喜歡的。這不是錯覺,全球用戶都在面臨同樣的問題:網絡平台壟斷與內容同質化。
產品經理不再為用戶體驗服務,而是想盡辦法引導無意義的點擊、停留、互動。用戶貢獻了內容、人氣和大數據,但對平台卻毫無約束力。卸載?平台可不在意,我們卻可能失去一個樹洞和一群熟悉的網友。互聯網誕生之初是多元、自由的象徵,而現在科技巨頭都選擇迎合中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傑西·林格爾(Jessa Lingel)在《被互聯網辜負的人:互聯網的士紳化如何製造了數字不正義》一書中試圖探究,二十年間,互聯網如何從屠龍者變成惡龍。
我們每天使用的網絡就像一座線上社區,和線下社區一樣,本應擁有豐富的設施、活動,不同群體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但規劃者只想掙多數人的錢,不再理會少數群體的想法。“你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難:留下,無法參與決定社區的未來;搬走,帶不走你在社區里熟識的鄰里、你給社區貢獻的東西。”科技巨頭帶來的壟斷和擠壓不僅發生在線上,線下也未能倖免。作者指出了這些公司搬到哪裡,那一片的房價就會飆升,本地居民再也住不起只好搬走。
這是真實發生在互聯網近二十年里的事,互聯網像遭遇士紳化的老城區,變得更加便捷、光鮮但缺乏多樣性,有明確優先服務的人群,極端重視利潤而輕視社群,急著把最初搭建社區但已不再有利用價值的人群邊緣化甚至掃地出門。本書以美國為例,記錄這個過程怎樣發生,它的實質危害如何,以及網民可以如何行動。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被互聯網辜負的人》,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被互聯網辜負的人:互聯網的士紳化如何製造了數字不正義》,[美]傑西·林格爾著,馮諾 譯,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科技行業的文化已經改變
科技並非憑空出現;它來自人和公司,對科技能解決的問題以及人類如何使用科技,這一群體有特定的想法。要得到關於互聯網和互聯網政治的答案,我們得看看科技巨頭的目標和價值觀。
正如《連線》雜誌的一位記者史蒂文·約翰遜(StevenJohnson)所言,“不論你怎麼看科技巨頭,這一新財富和信息網絡的聚合體,可以說是人類曆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群體。能準確參透其政治將是件好事”。士紳化提供了一種參透科技巨頭政治的方式,幫助我們理解這一行業如何重塑大城市,其平台如何造成不平等與偏見。

電影《社交網絡》劇照。
科技行業在三個方面造成了士紳化:公司總部占領了社區,科技巨頭員工缺乏多樣性(它也造成了孤立),行業塑造的商業文化把利潤置於人之上。科技巨頭與士紳化之間最直接的關聯體現在對城市空間的爭奪上,科技業從業者是城市士紳化的衝鋒部隊,他們的目標則是公司總部所在城市或總部附近的城市。
第二個議題與誰能夠在科技行業工作有關。跟科技巨頭支持的士紳化社區一樣,科技業本身就存在嚴重的多樣性不足:在科技巨頭工作的人里,白人、男性和年輕人佔據了與人口結構不相稱的比例。缺乏多樣性乃是重要問題,因為同質化的勞動力影響了他們設計或推廣的設備和平台。
最後,我會展示互聯網在其優先事項上是如何士紳化的。互聯網始終允許人賺錢,但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科技行業的文化改變了。銀行業專家的大量湧入帶來了新的優先事項,強調加強控製,消滅競爭者。結果就產生了一個這樣的產業:推動它的是正在建立的壟斷而不是激進的創造力。
沒有哪個行業可以被籠統地概括。科技巨頭包括了幾千家公司,製造了無數產品。沒有哪一種觀點或哪一套政治能夠完全體現這一切。每個行業的內部,甚至每個公司都有表達異見的通道。
從2017年開始,主流科技公司如Google和微軟都受到內部抗議、罷工、要求保護員工和拒絕重大國防合作等行為的衝擊。我在大科技公司和媒體公司(微軟和維亞康姆)工作過,所以我直接地知道大公司中有不同意公司所有決定的員工。即便如此,仍然存在著指導行業整體的規範和趨勢。

美劇《矽谷》第一季劇照。
我說的“科技巨頭”,是指推出廣受歡迎的產品和服務的主流科技公司。我在這一章中談論科技業的時候,我真正談論的是左右了矽谷的主流價值觀。(矽谷是主要的科技產業聚集地,但世界上還有其他中心如班加羅爾、柏林和特拉維夫。我沒有空間細述矽谷意識形態散播[或並沒有散播]到全球的方式,但是其中連接他們的共同因素包括,相信技術的進展會驅動社會改善、支持資本主義、抗拒監管。)
科技巨頭的信仰體系常常被稱為網絡自由意誌主義(cyberlibertarianism),或者叫加州意識形態。這套價值體系包含什麼?科技巨頭常常相信科技是社會問題的答案。認為技術驅動社會變革的理念叫作技術決定論(techno-determinism),意指技術決定了社會結果。
技術決定論一個絕佳例子是,“每個孩子一台筆記本電腦”計劃,該計劃認為向每個拉美兒童發放電腦能夠克服貧困、種族主義和歧視方面的主要障礙。正如科技行業研究者摩根·埃姆斯(MorganAmes)在對該計劃的長年研究中發現的,單靠電腦不能“解決”拉丁美洲或任何地方的教育問題。真正需要的是給教師更高的工資、更多的培訓和更大的社會安全網。
科技巨頭價值體系的另一大關鍵特徵是優績主義(meritocracy)。理論上優績主義是好東西,因為它強調做事的能力並且(據說)忽略種族和性別等身份標籤。問題是在科技行業中,是否能得到鼓勵和獲得培訓資源,常常跟種族、階級和性別有關。在實踐中,優績主義常常無法把特定群體面臨的不利因素考慮進去。
值得銘記的網絡自由意誌主義者最後一大特徵是他們常常在社會議題上是自由派,但涉及聯邦監管時偏愛不幹預的政策。相信加州意識形態的人,常常不介意納稅(或者建立非營利組織解決社會問題),但是他們並不想讓政府監管科技業。
這些價值觀在一起,表明了一種這樣的價值體系:提倡社會變革,但用技術手段去做,且不對資本主義提出實質性挑戰。(更多關於矽谷的政治和價值觀的內容,請參閱梅根·斯潘納·安克鬆[MeganSapnarAnkerson]和弗雷德·特納[FredTurner]的作品。)
當科技巨頭成為你的鄰居
在本書中的大部分場合,我把士紳化作為一個隱喻來思考數字技術背後的政治。但士紳化和科技巨頭之間也有一些現實中的聯繫,比如當科技公司遷入然後開始營業,它所在的城市或社區會發生的事情。許多城市熱衷於把科技巨頭招徠本市,認為他們能夠刺激就業和本地商業。
2018年,亞馬遜宣佈計劃建立第二總部(第一總部在西雅圖)。此新聞引發全美國城市的騷動。各個地方政府使出渾身解數,提供減稅等激勵措施,比如承諾提升公共交通、增加綠色空間。
亞馬遜最終宣佈計劃開設兩處新總部,一處在華盛頓特區外,一處在紐約皇后區。在當地活動家和立法者的抵製之下,皇后區總部計劃破產,活動家們提出的一大要點圍繞著這個問題:為什麼地方政府要給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減稅?

美劇《矽谷》第一季劇照。
在經過多年的不盈利之後,亞馬遜現在是世界上賺錢最多的公司之一。根據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的安德魯·戴維斯(Andrew Davis)記錄,2018年亞馬遜獲得創紀錄的利潤,淨收入101億美元。
同年,亞馬遜繳納的美國聯邦所得稅是0美元。事實上,亞馬遜還收到了美國聯邦政府退還的1.29億美元稅款。儘管亞馬遜倉庫里的工人得承擔個人所得稅,亞馬遜公司自身實際上卻能憑空進賬。地方政府樂意效仿聯邦政府,為這家富得流油的公司減免稅收,與此同時卻無視對平價住房的呼籲。
城市研究者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形容亞馬遜尋求第二總部的行為是提升經濟增長的“災難性”挫折。他稱提出的激勵措施“製造了虛假競爭,來操控程序和攫取獎勵。政客即便知道這是惡政,也依然竭盡全力地參與其中,因為他們認為奪取這一錦標會讓他們煥發光彩,贏得選票”。
不用非得亞馬遜級別的利潤才能走上地方政府鋪設的紅毯。城鎮或社區認為招徠大公司入駐是有利可圖的善舉,科技公司常常利用這一點。但把公司辦公場所引來入駐並不總是好事。根據經濟學家阿米海·格萊澤(Amihai Glazer)的觀點,給大公司的稅收激勵常會適得其反,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如果公司沒有達到交易的目標,激勵措施里也沒有相應的懲罰,這意味著即便之後出現裁員或公司倒閉,他們依然能獲得減稅。其次,大公司給一座城市帶來的收入,幾乎從來不會超過這座城市花費在激勵措施上的收入。並且大多數時候(達75%!),稅收激勵並不在公司的決策中起到主要作用,也就是說即便沒有許諾條件,該公司依然會搬遷到那座城市。最後,格萊澤發現得到稅收激勵的公司比沒有得到稅收激勵的公司稍稍容易失敗。所以從統計學上來說,城市提供稅收減免吸引企業入駐,沒有人會成為贏家。
但是假設你不像皇后區那麼幸運地躲開了科技巨頭。如果科技公司真的遷入,會發生什麼呢?它們會對房地產市場施加壓力,過去多數人買得起的社區被湧入本地的員工擠滿。除了提高住房競爭,科技巨頭還降低了人們對周邊的商業需求。科技公司給員工提供免費的午餐、零食甚至啤酒,實際上是減少了去本地餐館的人流量。還有就是前面提到的稅收漏洞。
所以這些企業不僅提高了社區生活成本、降低了生活質量,同時還避開了本可投入學校和道路等公共資源的公司稅收。考慮到這些缺點,科技巨頭非但不是地方經濟來的裨益,而且還給周邊社區帶來了負擔。

美劇《矽谷》第一季劇照。
關於科技行業在士紳化過程中的作用,最激烈的鬥爭發生在加州北部。儘管20世紀四五十年代科技行業就在矽谷紮根,但過去20年士紳化問題明顯地惡化了。我成長於20世紀90年代的灣區,時值科技行業的第一次繁榮。本地企業如Google和蘋果研發的技術給加州(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普通人帶來了重大改變,但是他們對周邊城市如舊金山和奧克蘭的房價並沒有產生重大影響。當時,科技行業主要集中在矽谷,也就是灣區南部。跟之前的硬件公司一樣,軟件公司幾乎都位於聖何塞郊區,比如丘珀蒂諾和帕洛阿爾托。
然而,2008年經濟衰退之後的科技繁榮則完全不同。全美國的年輕人以創紀錄的數量湧入城市。在加州北部的大城市,科技公司鋪好了路,用簽約金和特殊福利吸引年輕人。公司提供班車,在舊金山和灣區南部之間運送通勤的員工。結果即便科技公司的總部是在城市外很遠的地方,它仍然製造了嚴重問題。在舊金山和奧克蘭,富裕居民的數量猛增,給先前主要供應給低收入或中產有色人種的房地產市場帶來了壓力。
我土生土長的灣區朋友常常互道關於房價飆升的恐怖故事。房產可能比要價高數十萬美元,而買家則帶著足夠多的現金直接買下房子。結果加州北部的大城市越來越不平等,越來越不多元。在過去的25年里,舊金山、聖何塞和奧克蘭的有色人種數量急劇下降,而富裕的白人居民則飆升。舊金山起初是士紳化的震中,後來它擴張到附近的其他城市。
在奧克蘭,失所現象更嚴重地出現在非裔黑人家庭和有孩子的家庭中。2000年至2010年之間,奧克蘭聯合學區失去了超過1萬名有色人種學生,奧克蘭市失去了3.4萬非裔居民,降幅達24%。2015年至2016年這1年之間,奧克蘭兩居室平均租金上漲了25%。科技行業不是催生這些變化的唯一行業,但它已經成為最能體現企業財富和地方社群之間的鬥爭的一面。
在疾速士紳化的社區,有很多關於來自科技業的人(主要是白人男性)出現種族主義和階層歧視行為的故事。這些事件表明特權與權利的緊張關係。2014年,一些Dropbox(在線存儲平台)員工穿著公司T恤趕走了舊金山一座足球場上的本地孩子。Dropbox員工堅稱他們通過一個手機應用“預約”了場地,卻不管孩子(主要是拉丁裔)一直都在這個場地踢球。

美劇《矽谷》第一季劇照。
跟這些大公司員工當鄰居是什麼感覺,我覺得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來自2015年的一個事件,也發生在舊金山,《芝加哥論壇報》的邁克爾·米勒(Michael Miller in the Chicago Tribune)留下了該事件的記錄。
Justin·凱勒(Justin Keller)是一名軟件開發者和創業者,他在2012年搬到了舊金山。3年後,他給舊金山市市長和警察局長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對本地的流浪人口採取措施。在信中,凱勒抱怨道:“每天我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看見人躺在人行道上,到處都是帳篷,人類糞便,以及癮君子的一張張臉。這座城市正在變成貧民窟。”
凱勒繼而承認很多人已經想到了士紳化,但是他拒絕為這座城市出現的問題承擔任何責任:“我知道人們對這座城市發生的士紳化感到沮喪,但現實是,我們生活在自由市場的社會里。富裕的有工作的人掙得了居住在這座城市的權利。他們出門闖蕩,接受了教育,努力工作,然後掙到了這一切。”
凱勒在信中也把無家可歸者說成是“賤民”(riffraff),從他的信里,我們看到了科技巨頭對優績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信仰中危險的一面。對凱勒來說,優績主義意味著努力工作就能得到回報。這種想法的另一面是,一無所有的人一定沒有努力工作。
或許凱勒這樣的人確實為自己的成功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但這不能說明,沒有高工資或者好房子的人就懶惰而且不配得到這些。對凱勒這樣的人來說,士紳化是變革的積極力量,是資本主義社會自然循環的一部分。

美劇《矽谷》第一季劇照。
站在凱勒的角度,舊金山的士紳化步伐跨得還不夠大——沒有足夠的失所,城市依然太多樣化。凱勒等人聽到士紳化會認為它是“進步”,對他們來說,士紳化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表述。但正如城市研究者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堅持認為的,“對於困頓者、被驅逐出住處的人以及被驅逐後被迫流浪的人來說,士紳化的確是一個肮髒的詞彙,而且應該始終是一個肮髒的詞彙”。
科技行業與灣區士紳化之間的關係中頗具反諷意味的是,科技巨頭正在驅趕的這些社區,恰恰是激發美國早期互聯網極端創造力的社區。媒體史學家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寫過數字科技的反主流文化根源,從嬉皮社群到火人節。但是科技巨頭對反主流文化的價值觀似乎只是做做樣子,一面驅趕著這種文化的核心社區。
正如《衛報》科技記者奧利維亞·索倫(Olivia Solon)對灣區的觀察:“這裏曾經有一種反主流文化,它的語言和感悟力有時會被科技行業採用,但它的踐行者幾乎都被科技行業用錢擠出去了。”
科技公司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其總部附近房價危機的重要原因。解決這些問題的動機與其說是利他主義,倒不如說是務實:在房價近乎難以承受的城市里招聘員工很難。在舊金山、奧克蘭或周邊郊區買房已經難上加難,即便是工資六位數的人。2019年,Google宣佈將在未來10年投資10億美元,建造2萬套公寓住房。
據何欣(Vivian Ho)在《衛報》上刊發的報導,其中7.5億美元資金將把現有的Google辦公空間改造成1.5萬套公寓住房。Google還捐了5000萬美元給致力於解決無家可歸問題的非營利組織。剩下的錢將分配給開發商作為建造5000套平價公寓住房的“激勵”。
Google能夠意識到自己在士紳化中的作用,並願意出錢解決該問題,這很好。但是Google對抗士紳化的計劃中,仍有一些重大的未知數。我們不清楚這些新房中有多少會分給Google員工,又有多少分給其他人,而平價房屋與高價房屋的比例依然沒有達到本地活動家呼籲的數字。最重要的是,我們得牢記——Google本質上是在解決一個由自己助長的問題。
其他公司走的則是舊金山初創企業Zapier(該公司主要業務是讓不同網絡應用組成自動化協作流程)的路徑。2017年,該公司開啟了一個新的“遷離”項目,為其員工搬出灣區提供1萬美元。這項計劃利用數字溝通的優勢,也打破了員工必須住在灣區的思維。2020年,為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許多科技公司要求(沒有被裁掉的)員工居家辦公。
推特等公司宣佈措施是永久性的,此舉對作為科技巨頭樞紐的矽谷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舉措對巨頭內部的低薪工作者和後勤人員並沒有太大意義,他們常常沒有這些福利(也常常被裁掉或停職)。
科技行業認為自己具備前瞻性,專注於解決問題,因此我們應該要求他們對自己正在製造或助長的問題提供創造性解決方案。但士紳化是非常宏大的議題,依靠單個公司的零散實驗和利他主義是無法解決的。我們也需要地方的住房監管和圍繞行業規範的大範圍社會壓力。
好的鄰居應該是什麼樣的?科技公司里常常有叫“社群經理”(community managers)的員工,鼓勵員工中的協作和交流是他們的工作。如果其工作描述重新定位為與當地社區協作、交流呢?社群經理不是促進同事之間的士氣和協作,而是通過培養關係和解決問題成為當地社區的橋樑。如果科技公司不再把很多錢花在奢華的節日派對和貴重物品上,而是把資源投到當地學校、基礎設施和住房計劃上呢?
科技公司也需要不再要求減稅——地方政府也應該停止提供減稅。並沒有很多數據表明,減稅對企業有好處,但有大量證據表明減稅對於提供減稅的城市是有害的。要成為更好的鄰居,應該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共同努力,企業解決住房問題要跟研發新產品一樣具有創造力,員工對社區要像對創新技術一樣投入。

美劇《矽谷》第一季劇照。
科技巨頭怎樣能成為更好的鄰居,對此最瞭解的人,或許是那些親身經曆了大型科技公司搬入帶來的變化的人。2019年,約蘭達·查韋斯(Yolanda Chavez)給Google首席執行官孫達爾·披猜(Sundar Pichai)寫了一封公開信。作為一個舉家在加州聖何塞生活的移民和活動家,查韋斯對Google將在她家附近建立新辦公園區心存擔憂。對於科技公司如何成為更好的鄰居,她也有一些可靠的實際建議:
您的新園區將依賴數千名服務人員做飯、打掃、安保、開班車。這些人比你們的其他員工更可能是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人。您會保證他們對工作有發言權,能自由地聚在一起協商更好的工作環境嗎?您會採取措施僱傭來自聖何塞的未來工程師和程序員,並且為我們社區更多的孩子提供教育和從事這些工作的培訓機會嗎?
查韋斯的公開信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們士紳化不只是人們和科技巨頭之間關係的隱喻。在某些情況下,社區紐帶、平價住房和科技行業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實實在在的,代價非常高昂,迫切需要地方上的行動。
原文作者/[美]傑西·林格爾
摘編/荷花
編輯/王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