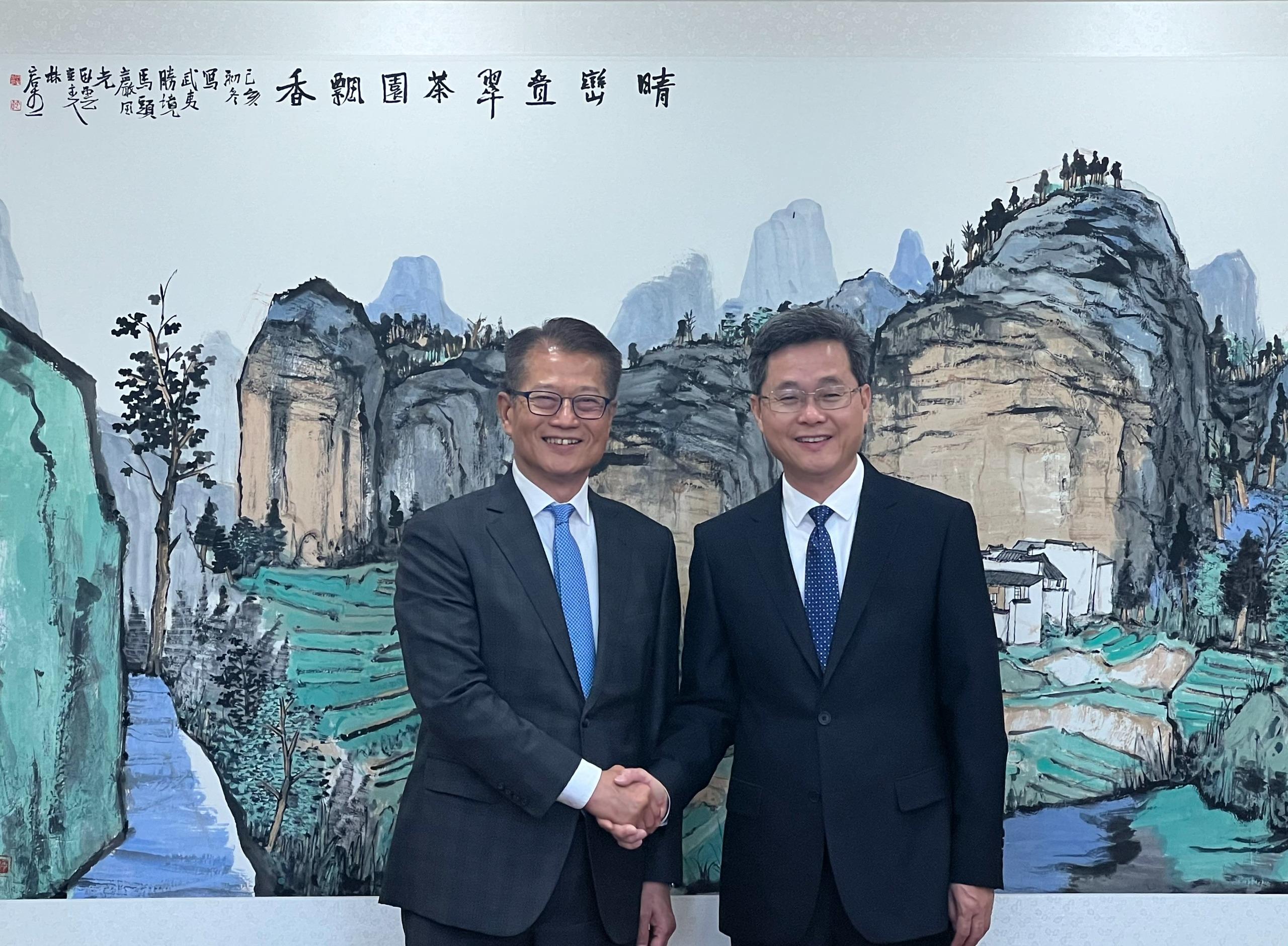故鄉里的中國|我的表哥,將鄉愁泡成熱茶
滾燙的熱水衝入杯中,熱氣升騰,卷揉成細繩狀的葉片在水中舒展。茶湯漸漸透出琥珀色,氤氳出醇厚香氣。
表哥張楠嫻熟地用食指抵著杯蓋頂,拇指中指捏著蓋碗的沿兒,將茶湯倒入公道杯中。春節里,搞衛生、拎著新茶拜訪親友,一天忙活下來,臨近傍晚,張楠才有時間坐在茶桌前泡上一壺熱茶。
我的家鄉是福建武夷山,因茶聞名。
我和我的表哥張楠一起在這長大。高中畢業後,我們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活軌跡。我嚮往大城市的生活:上海、倫敦、北京。而張楠在大學畢業後回到了武夷山,師從大紅袍製作技藝傳承人。從茶葉學徒做起,一步步經營起他的茶葉事業。如今他漸漸能獨當一面,成為兒時人們口中流傳的“做茶師傅”。
這些年,茶不僅成了我們兄妹倆的聯結,也成了我和家鄉的聯結。
 武夷山的茶山,因有“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的特質土壤,尤其適合茶葉生長。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武夷山的茶山,因有“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的特質土壤,尤其適合茶葉生長。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一
我所在的小城年輕人大抵分為兩種。靠讀書考上小城外的大學,去往其他城市發展;留在小城,做些小生意,或學著做茶賣茶。
表哥屬於後者。我的姨父開著一家紡織廠,姨媽在家中操持家務,大哥則幫著姨父一起管理廠子,表哥張楠是家中次子。考上大學後,他在大哥的建議下報考了福建省內一所大學的茶葉專業。他對此沒意見:“學了茶葉,在武夷山也多條出路。”
我的家鄉武夷山,是中國四大“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之一。但更為人熟知的,是家鄉的茶,大紅袍、正山小種、金駿眉等名茶都發源於此。曆史上武夷茶是帝王的貢茶。17世紀,武夷茶開始外銷海外,歐洲人稱之為“中國茶”。
在武夷山,喝茶就像喝水一樣尋常。武夷山人平日最愛喝“肉桂”“水仙”。“肉桂”香氣出眾,“水仙”則茶湯清雋悠長,是武夷岩茶裡頭最出名的兩個品種。“武夷岩茶”因茶樹多長在岩石邊,被稱之為“岩茶”。
起初,周圍人以為表哥會去經營父親的紡織廠,但他不適應紡織廠的工作,只做了半年就離開了。
“人年輕的時候總要學點手藝。”大學里學的茶葉製作和茶山管理,都和綠茶相關,面對家鄉的烏龍茶,張楠還是一塊白板。通過父親的人脈,他找到一位武夷山頗為出名的大紅袍製作技藝傳承人,向他拜師學藝。
提到武夷山,人們最先想到的就是大紅袍。它被稱為岩茶中的極品,製作工藝複雜,國務院、文化部公佈的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紅袍的製作工藝就名列其中。
第一年,說是學做茶,張楠卻沒碰著茶葉。師傅的茶葉珍貴且量少,不輕易讓新學徒上手,張楠便只能在一旁看,掃地、扛茶葉袋,打打下手。
直到第二年,張楠才開始上手做茶。
一開始,師傅教做茶的“公式”。每一步的工序如何,溫度多高,師傅給的公式里都有大致標準。但真正上手後,張楠才發現做茶不是工廠的流水線作業,光靠理論知識遠遠不夠。
張楠覺得艱辛,又說,“這也是人必經的過程。”
每年4月是武夷岩茶的採摘季。做茶人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休生養息,為的是4月做茶季開始後的連軸轉。
 做青間每年最忙碌的是四月,春節期間機器都閑置著。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做青間每年最忙碌的是四月,春節期間機器都閑置著。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做茶就像雕刻一件工藝品。“一泡茶好不好,從做青時便定下了。”這是張楠學茶時獲得的經驗。茶葉從山上採摘下來,是茶青狀態,要經曆萎凋、搖青、做青、炒青、揉撚、烘焙、揀剔、歸堆、複焙這幾個過程。每個過程都與茶最終的滋味息息相關。
他還告訴我,做茶的原理是“走水”,是把茶葉的水分從葉片里“趕”出去,讓香氣留下來。“搖青發酵、炒青、揉撚、炭火烘焙,都是讓水分從葉面散發出去,這樣能把茶葉的香氣從枝幹里提取出來。”
做青時,張楠抓起一把茶青湊近一聞,有濕潤青味、香氣清楚,便是好青。他說,茶青階段最重要的是“均勻”。搖青時要均勻,走水要均勻,茶葉最後的香氣才能飽滿。這意味著做青期間,機器在轉,人也不能閑著,他得不停在機器旁翻揀茶葉。“若是茶葉做工不均勻,茶湯沒有滋味感,品起來也苦澀。”
做青若是做得好,葉片呈“綠葉紅鑲邊”。一條清晰的紅線鑲在茶葉邊緣,有經驗的做茶師傅一看,便知此茶為上品。
 做青時,茶葉擺在水篩上“走水”。受訪者供圖
做青時,茶葉擺在水篩上“走水”。受訪者供圖二
張楠學茶,一開始並不被看好。他到師傅廠里學茶,大家都叫他“張二少”。做茶辛苦,很多慕名而來的人學上一兩年,掛個“大紅袍製作技藝傳承人徒弟”的招牌,便自己做茶賣茶去了。有人說,張楠這樣的“公子哥”是待不了一年的。
沒想到張楠一待就是五年。最髒的魚塘他總是主動去洗。每進一次做青房,他都要用掃把掃淨掉落在地上的碎屑。“地都掃不好,還做什麼茶?”這是師傅教他的。
焙茶是最累的階段。每焙一次茶,前後至少要12個小時。張楠要守在焙茶房外,每半個小時進去翻一次茶。焙茶房內的溫度高,有時能達到五六十攝氏度。人在裡頭只需待上一分鍾,全身便被汗浸透。為了把控茶葉的品質,每隔一段時間,張楠要從高溫的茶堆裡取一把茶葉衝泡,確定茶湯的滋味。
 做青時,表哥張楠在翻揀機器里的茶葉。受訪者供圖
做青時,表哥張楠在翻揀機器里的茶葉。受訪者供圖茶葉產量大時,幾天下來,張楠幾乎無休。
茶也成了張楠和家人為數不多的談資。張楠在家人面前不健談,大部分時間里他只做不說。在廠里學了哪些手藝,發生了什麼趣事,他不和家人聊起。只有做出一泡自認不錯的好茶,他才帶回家給家人品嚐,“我做的,你們喝喝。”
我從北京歸家的第二天,就來找表哥喝茶。他有泡新製的肉桂要我嚐嚐。
高中畢業後,我很少待在武夷山,和表哥見面的機會也少。
表哥大我兩歲,兒時我們總在一塊玩。武夷山不大,購物街只有兩三條。我的童年記憶里,整個城區只有一家老舊的電影院,沒有肯德基和麥當勞,大街小巷都是各類小吃髒攤。夏天,我倆就站在小賣部生鏽的捲簾門前,吹著綠色老式電風扇吃棒冰。
記憶里更多的場景是和茶有關的。武夷山人走門串戶,身上必定帶著幾泡茶葉。家家有一套功夫茶具,木質的茶盤雕琢各式花紋。坐到桌前,便拿出茶葉來“鬥一鬥”。
 春節期間,我來找表哥張楠喝茶,他正在泡新製的肉桂。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春節期間,我來找表哥張楠喝茶,他正在泡新製的肉桂。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列易搭(來喝茶)”,是武夷山人與人打交道的方式。
開水衝入杯中,第一波香氣先衝上杯蓋的弧頂。掀起杯蓋細嗅一嗅,好的茶葉香氣足,能聞見各類蘭花、梅花等花香,或是木質味、青苔味、粽葉味。我常聽做茶人說起,武夷山的茶葉味道多至上百種,鮮少有人能品盡。
武夷山人喝茶慣喝熱的。一口杯的滾燙茶湯,得細啜上好幾口,還得喝出聲響來,“簌——”,才能體現自己在認真品茶。武夷山的烏龍茶湯與其他茶系不同,入口後,有細微苦感,落入舌苔便很快泛起陣陣甘甜——這是做茶人常說的“回甘”。而後舌頭兩側不斷生出口水來,這是“生津”。茶葉越好,生津便越多。喝見底後,還要細聞杯底,茶湯留下了溫熱香氣,品起來又是另一番滋味。
泡茶用的水也有講究。山泉水泡起茶來最甜,入口潤滑。有人會特意驅車到山裡,接岩石壁上滴下來的泉水,蓄滿一桶,只為泡上一壺茶。
小時候,我們跟著大人們喝茶,常常裝出一副懂茶的樣子。學著大人入口時含著茶湯,刻意發出吸食的聲音,隨後讚歎,“好喝!”再大了點,學會抿抿嘴,說“這茶有回甘”。大人常常會誇,“小孩會喝茶。”
後來,我漸漸懂得茶葉的精深,自認學到的茶知識淺薄,故常常和人對坐飲茶時品而不語。
三
我問表哥,武夷山人為什麼愛喝茶,表哥的回答是“習慣”。家裡人常常說,自己如果兩三天不喝茶,就會“渾身不舒服”。
他的大師傅們做了一輩子茶,總有些精深的理解。但現在表哥的眼裡,茶是安家立業的手藝。
他去年結了婚,經營著自己的茶企,他說,“還在起步階段,不擔心那些(生意),就看茶做得好不好。”
 表哥張楠在茶廠里檢查機器的運作情況。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表哥張楠在茶廠里檢查機器的運作情況。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家人們常說,表哥還像個小孩,沒長大。表哥不這麼覺得,“成了家,身上就有了責任。”
這些年,武夷山也在發生肉眼可見的變化。馬路不斷在翻新,從泥地變成了水泥地,又從水泥地變成寬闊的柏油路。武夷山茶越來越出名,栽種茶的山頭便也越來越多,山間的茶葉廠像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
小時候,我和表哥常在家樓下的沙地玩耍,用玻璃珠在沙地上按出一個個淺淺的坑,再輪流將珠子彈入坑內。如今,過去荒蕪的地長出了高樓,路上行駛的汽車越來越多,一個個童年玩耍的沙地也被翻新,成了停車場。
我長得越來越高,小城變得越來越小。我和表哥的生活軌跡漸漸分離,我離開武夷山,身上帶著表哥做的茶。表哥留在武夷山,生活圍著茶轉。
家鄉和遠方,只能選其一。這些年,每當別人問起我家在哪,我答“福建武夷山”,對方便會接上“大紅袍”。像是對上了“接頭暗號”。
從小我只聽說武夷山茶出名。聽做茶人說起,武夷山的紅茶“正山小種”“金駿眉”遠銷海外,甚至專供英國皇室享用。長大後我才知道,英國人慣喝的伯爵茶、英式早茶,也都是武夷紅茶拚配而成。
無論走到哪,我的行李箱里總是揣著一整套茶具。開水衝出茶葉的香氣,是我每天和家鄉奇妙的聯結。
姨媽也曾讓表哥去大城市闖闖,表哥不願意。他身邊的朋友都留在了武夷山,有的做點小生意,有的在機關單位里謀個職位。有時電話響起,即便是深夜,幾個朋友也要聚在燒烤街上,喝著啤酒,聊聊最新的電競比賽。
他和我說,做茶是一門活到老學到老的手藝活,自己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想把茶做好,“在武夷山就挺好。”
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劉軍